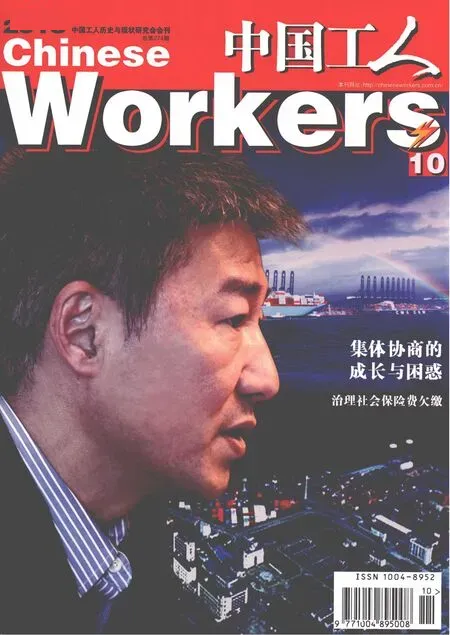五十知父母命
●何诚斌

“五十知天命”,这话我现在说起来,不是淡然,而是愕然,怎么自己一下子就50 岁了?对“天命”的想法很多,还是按住不表吧,因为头头是道对自己并非管用。我更情愿把“五十”与“知天命”分开来看,五十是五十,知天命是知天命。
我不打量自己这50 岁的光景,而逆时光看我父母50 岁时的情景,更有一种历史感,一种缅怀的意义。我的父母50 岁时,世界已有我的身影,我的足迹,我的目光,我的回忆。父母是经历过多个时代变革的人,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等,他们都经历过,同时还遇到过战争与大饥荒。他们的人生沉甸甸的,而其中生计问题占了很大分量,至于权利、自由之类的追求微弱无质,他们虽不奢谈什么“知天命”的孔子理论,但会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之类的民间俗语。
1973 年父亲50 岁。那一年我8 岁,正式入学,就读于怀宁县洪镇街道小学,而我的户口落在离小镇3 公里的东风大队。我家下放到牛棚生产队已5 个年头。父亲差不多从一个商人蜕变为一个农民。还有我的二姐、我的大哥也随父亲一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农村,内心极其抵触着“扎根”二字。后来,二姐嫁给一个农民,定居农村,这被她长期看作“不幸”,直到50 岁她的家境大大改变,她才没嫌自己命不好。1973 年我大哥作为下放知青,在生产队拉板车、打芦苇,什么活儿都干,同时也干打牌赌博的“勾当”(赌资几毛钱或者赌香烟),父母常常摸着漆黑的路到村里去抓他回家。1975 年大哥招工进厂,全家欢天喜地。
50 岁的父亲,有7 个儿女,我大姐已出嫁,二姐、大哥参加劳动能拿工分,二哥、三哥和我在读中学、小学;我还有一个几岁的弟弟。至少这四个人需要大人抚养。虽然有生产队可依靠,但由于粮食按户口和工分分配,而我家工分数与人口数出入太大,所以分配的粮食不够吃。牛棚生产队的田地多在低洼的冶塘湖,容易受水灾而颗粒无收,靠政府赈灾拨救济粮解决民生。救济粮有两类,一是直接发放粮食,一是发供应票。后者不是全部无偿,而是一种价钱相对便宜的粮食;或者花钱就能买到的粮食。记得我小时候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总是嚷:“肚子饿了、肚子饿了……”父母不爱听这种声音,回答我:“做个饭袋背在身上。”母亲看见父亲挑回家的稻谷干瘪,山芋瘦小,就很受委屈,大发脾气,骂生产队的干部欺负下放户,甚至跑到村里去讨公道,多半哭着回家。有时,当她得胜地拿回补发的粮食,全家自然特别高兴。
在农村干了5 年,50 岁的父亲尽管很老实谦和,不与人争长论短,但还是难以真正地被村子里人接受,因为整个村子就一个姓氏——陈。对于姓何的这一家人,被他们看作是利益的侵占者。何况“何家”的确处于一种“半养”的状况。父亲可能想到了自己一家人对陈氏村庄的添累,所以自从我二姐嫁给这个村子的一位农民后,他才感到我们家终于被这个村子接纳了。二姐想招工成为“国家人”,不愿意嫁给农民。父亲骂她,甚至打她。一个从不发脾气、习惯于迁让妥协、被人们笑作“老好人”的父亲,在我二姐的婚姻上流着泪、咬着牙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我记得当年是三哥带我去报名入学的,学费只要5 毛钱,可是家里却拿不出来。我的名还是报上了,新书比别的同学晚了一个多星期才领到。至于5 毛钱后来是补缴了,还是免了,我不记得了。我穿着哥哥穿旧的衣服,背着哥哥用过的书包,上学了!父亲50 岁的时候,我是一个裸童,在夏天。那时候春天入学读第一学期,到了暑假,我仍光着屁股。有一天,被班主任老师看见了,她说我已经是一个学生,要学会穿衣服。她却不知道,我家买不起布制作衣服,我只能等待哥哥长个子被淘汰的衣服。实际上,到我母亲50 岁,1977 年的时候,我的衣服还是很少——衣不蔽体是假,不够换洗是真。
我的衣服紧张,更多的时候出现在开运动会和参加学校演出活动的时候。我很遗憾,读小学时没有照过相,从现在自己的这张脸看,怎么也想象不到我小时候那么的风光,那么的讨老师喜欢,演出挑大梁,什么开场舞、对口词、快板书都是我的节目,还当过主持人。有一次以小军人的形象,演快板书,上身黄褂子,下身蓝裤子,这行头是向邻居家借的。偏偏我的作文和数学竞赛又都得了第一名,上台发言,白衬衫也是借来的。数学竞赛前,我听到了一个平时数学成绩在同届几个班名列前茅的同学讲,他妈妈已承诺,如果他考第一名,就给他做白色的确良褂子(当年最时尚的衣服)。我回家,对母亲说:“如果我考了第一,你给我做的确良褂子吗?”母亲笑了笑,然后说:“我给你做。”可是,母亲却没有兑现,直到几年后,我才穿上的确良褂子。
可见,母亲50 岁的时候,家境还是那么贫困,但比父亲50 岁时要好一些了,因为大哥已招工进厂,二哥高中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母亲自己先后在学校、邮局做厨工,一个月能拿到15 元钱。母亲的娘家在渔村山口镇,她织渔网的技术相当高,有空就织,向外出售,这也能贴补家用。可是,母亲的压力却很大,她意识到五个儿子,一个个长大成人,将来都要娶媳妇,她说,就是一个儿子只打张婚床,也得不少钱。母亲省吃俭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健康,她50 岁后的身体很差,以致下河洗衣都困难。
1977 年的暑假,我除了拾柴、捡煤、打猪菜、捕鱼、捞虾,还有一件很不愿意做却不得不做的活儿,就是拣猪毛——把一堆黑猪毛中的白猪毛拣出来,或者把一堆白猪毛中的黑猪毛拣出来。这是个很枯燥乏味的活儿,我尽可能逃避和怠工,却挨了母亲不少骂,她骂我耐不住性子,将来没出息。我后来能捧着书一读就是半天、一天,是否与拣猪发,培养了性子有关?干拣猪毛的活儿可以挣到补贴家用的钱,这是母亲天大的问题。母亲自己也放下渔网,投入到拣猪毛的活儿中。渔网三年两载烂不掉,更换率低,母亲的渔网销量有限,她不能再盲目地编织囤积。镇上许多人家都干拣猪毛的活儿,而毛刷厂的猪毛有限,这造成了排长队等候猪毛的局面。一次,我跟母亲一道排队,终于等到母亲去仓库拿猪毛时,厂长却将秤杆子往肩上一扛,说今天结束了,气得我母亲落泪。厂长无视我母亲的泪水,可他却没想到一个少年心中的怒火是多么可怕。当天晚上,我跑到厂长家旁边,拿石头往他家屋顶上连续扔去,我听到了屋子里他老婆发出的惊叫。我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想暗中报仇的力量是危险的,我把那厂长当做所有电影中的坏蛋,我恨不得像《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砍死胡汉三!
我开始同情母亲,她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偷懒,这也让我得到了母亲的夸奖。我从天真快乐的儿童,变成了性格被染一丝忧郁的少年,为父母、为家庭感到“不幸”,为社会对我家的“不公”和人们对我家的“歧视”感到不满。母亲的思想很复杂,她说:“穷没根,富没杪。”她又说:“月到十五光阴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她乐观的时候,在五个儿子身上看到希望;她悲观的时候,为我父亲的社会活动能力差和自己被疾病缠身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她不喜欢农村。三年后国家出台政策,下放户回城,我家户口从农村转出,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镇上有多户“下放户”,将回城视作“解放”,欢天喜地了很长时间。
兴奋是有理由的,因为城非户口的青年,国家会安排工作。可是,国家的政策并不完善,我父亲没有恢复供销社营业员的身份,他洗尽了两腿泥,快60 岁了,却成为一名无业者。母亲为了父亲能够恢复公职,她往县城跑了多年,递交申诉,哭求,可始终没得到解决。父母晚年,虽然几个儿子有工作并给他们赡养金,可因不能像镇上其他老人一样按月领退休金生活而失落。父母的晚年是不幸福的,儿子们一个个要结婚成家,需要家里打家具,而儿子及儿媳妇们的想法不同,要求不一,故而为“一碗水端平”很费脑筋。父母一生吃了太多的苦,遇到了太多的坎。这是命,个人的命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离不开社会的变革。何况,人往往是难以决定自己命运的。父母,一生大多时候选择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能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