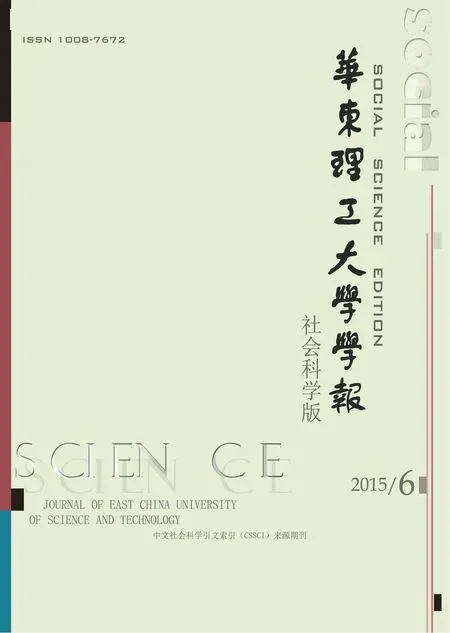民间环保集体行动产生逻辑及破局关键——基于太湖污染治理的考察
马道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民间环保集体行动产生逻辑及破局关键——基于太湖污染治理的考察
马道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根据奥尔森的观点环保集体行动产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事实上,在污染区域各种形式的民间环保集体行动时有发生,主要形式包括:有组织者的集体行动、无组织者的集体行动和环保精英们的行动。从风险社会理论分析,环境风险和环境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而环境污染属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存在分配的不公平性,弱势群体“集体被剥夺感”的蔓延有力地催化了民间环保集体行动。环保NGO的成长会使作为环境受害者的弱势群体受到常规性的力量支持和帮助,通过制度化参与的途径实现环境正义,使环境冲突处于可调控的范围内。环保NGO的成长才是民间环保集体行动破局的关键。
[关键词]环境风险环保集体行动弱势群体环保NGO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或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是指某种带有一定诉求、无明确组织、无明确计划、临时而起、利益双方或多方面对面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集群行为。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有:发生时是自发的、无正式组织的行动;是非制度化的行为,即违反常规的或不受制度和规范约束的行为;众多人共同的行动即受到相互感染、影响、鼓舞的许多人的一致行动;临时性、不能持久,行为周期较短暂。①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学海》2009年第1期。集体行动的主体是准群体,它是一种准群体的行为方式。环保集体行动就是因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与民众环境权益之间产生冲突,民众带有明确环境诉求目的、自发为主、无正式组织的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行为。民间环保集体行为中的行为主体是环境权益受损的民众。
美国学者奥尔森在1966年发表了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根据该著作的观点,集体行动的目标是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是个人力量无法缔造,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可以获得的物品”。②董国礼:《作为经济社会学议题的集体行动——从奥尔森到科尔曼》,《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并且公共物品的显著特性是:“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①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与形式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因此,当一群理性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自己却坐享其成。用奥尔森的话来说,“尽管集团的所有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的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②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根据这种推理,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即集体行动不可能产生,“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③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太湖污染地区环保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太湖污染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但是太湖水质的改善、环境的好转,其受益者是每一个生活在太湖周边的人,即一旦存在针对太湖污染集体行动,那么这种集体行动提供的公共物品就可以被所有人享受到,无论这些人参与了集体行动与否。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但是理性的算计是普遍存在的。在理性算计的影响下,集体行动产生似乎就不太可能了。但事实上,在笔者调查的太湖周边地区,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民间环保行动时有发生,这好像与奥尔森的理论分析似乎相悖,那么太湖地区民间环保集体行动产生的逻辑是什么?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正确引导民间环保集体行动,以降低社会风险的破局关键又在哪里?这些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太湖周边环保集体行动主要呈现形式
通过太湖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在太湖周边地区存在不同形式的环保集体行为。如果从性质上考虑,这些环保集体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污染企业的环境抗争行为。实际上,不仅仅在太湖周边地区,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据统计,目前环保问题排在当前全国群体性事件十大原因的第九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增长速度排在第七位,其年增长率在29.8%。④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群体事件增多,政府为企业埋单被指不公》,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10-11/17 /content_21366872.htm。在笔者调查的地区,小企业普遍存在,且以化工企业为主。化工企业造成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小企业的小本运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负担得起庞大的污染物处理费用。因此,将污水、废气等直接排入河渠、天空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地民众与污染企业结怨已久矛盾尖锐,环保集体行动时有发生,主要呈现三种表现形式。
1.有组织者的集体行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湖污染也非“一日之功”。因此,当地居民和污染企业的针锋相对已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恩怨期。居民曾经与这些污染企业进行过多次的谈判和交涉,但成效甚微。面对众多指责,污染企业表面上答应不再排放废气、废水等,但是他们转而采取在夜里偷偷直接排放,矛盾因此更加尖锐。在屡次交涉无果之后,当地的一位民营Z老板组织居民采取了果断行动。经过反复思考,Z老板和儿子决定带领附近居民去逼迫这家有污染的化工厂关闭。一位被访者这样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Z老板拿着喇叭对村民喊:‘乡亲们,他们(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企业主)让我们喝污染水,我们生产的菜都不能吃……我们要生存,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他的鼓励下,我们(村民)占领了好几个化工厂。后来镇政府派人来,他们来了好几辆警车要保护化工厂,还把Z老板抓了起来。我们非常生气,他们不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还要帮那些污染企业,我们就把警车给掀到了污水里,有几个人也掉进了沟里。为了救出Z老板,我们也抓了一个政府的干部,和他们以人换人,这样就把Z老板救了出来……后来,镇上看事情很严重吧,就把当时被我们闹过的几个小化工厂都给关闭了。”
这是一次在当地民营Z老板的带头下开展的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行动,他们试图通过比较激烈的手段来占领工厂,以迫使工厂关闭。这样的行动也引起了政府的干涉,政府的偏袒使得前来参与“解围”的人成为村民斗争的对象,警车也被掀到河里。现在看来,这些过激行为在关闭工厂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它促成了基层政府慎重考虑居民的要求,对污染企业采取了关闭措施。这样的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有赖于一个坚强的领导——Z老板。在居民的眼中,Z老板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人。他通过发展企业富裕之后,出资修建道路,让居民告别了乡村泥巴路,走上了水泥路。在这次集体行动中,他积极倡导并组织,最终化工厂被迫关闭,这些令村民们对他更加敬佩。
2.无组织者的自发集体行动
在Q村的对面,隔河相望是一家化工厂。这家化工厂每天都排放大量的黑烟和有毒气体到空气中,还将大量的黑水排放到河里。与化工厂仅一河之隔的Z村村民受尽其苦。有被调查者告诉我们,近几年,他们村先后有若干人死于食道癌,也有人得胃癌。该化工厂排放的有毒气体气味非常浓烈,村民反映人闻到这种味道会恶心、呕吐,甚至昏厥。村民要求化工厂对废气进行处理然后再排放,没有得到化工厂的响应。化工厂一再漠视村民的要求后,Q村村民开始了他们和化工厂的激烈抗争。某年的一天夜里该化工厂又向河里排放了大量的“黑水”,导致很多村民半夜被臭味熏醒,难以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村民就三五成群地去了化工厂,对化工厂进行了围堵,村民和厂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还爬到工厂的厂房房顶,去揭厂房的瓦。村民和厂方对峙了近一个上午,厂方最终答应不再进行排放,但是村民已经不再相信厂方的承诺。村民最终警告厂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将会再次来围堵。次年冬天该化工厂被政府勒令关闭。
在这场村民和化工厂的对峙中,村民用激烈的手段对化工厂采取了行动,迫使化工厂作出了让步。但是,与前面一个集体行动不同的是,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出现明显的组织者。村民大都是在亲身感受到污染之后,自发前往化工厂,或者是看到其他人去了,自己也跟着去。
“去年的时候那家化工厂,它白天不排放,到夜里偷偷排,河水臭得不得了。我们村里就去了几百人到工厂。这个根本不需要组织,一个人叫一声,大家就都会去,不需要村长组织。也不需要通知,只要大家闻到了味道,人是吃不消的,我们就会自发地去。我们去了之后,有的爬屋,有的跟他们理论……”
实际上,在该村,与这个化工厂的对峙已经不是第一次,村民都已经比较熟悉了这样的模式了:只要有一个人准备去化工厂抗议,其他人就会跟着去,并且会叫上自己的邻居,不需要有人组织。这已经成为村民们相对熟悉的自发组织路径,村民已经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自发群体。
3.地方精英们的环保行动
在太湖周边,除了村民的环保集体行动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环保精英”在行动。在调查中,笔者访谈了五位曾经写信举报过太湖污染的人。这些人大都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学历都在高中以上,并且多拥有较好的工作,或者是已经退休。这五位被访者分别是退休工人、退休教师、退休干部、农民和水电站管理员。他们主要通过写信举报等形式向相关部门反映太湖污染情况。这些环保行动的参与主体我们称之为地方“环保精英”。迫使这些人成为环保精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育他们的鱼米之乡的消逝”。
他们都是自幼生活在太湖周边的人,目睹了太湖从鱼米之乡转变为今天污染地带的过程,他们对这种转变深表担忧,同时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看到太湖水一步步变坏之后,我就很痛心。我认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我所喜欢的事情就是希望看到家乡青山绿水,看到小河沟里再出现鱼虾,看到鱼米之乡的复现。于是,我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开始我是匿名举报,向环保部门举报有污染的企业、化工厂啊等等,但是效果不明显。后来,我就改为实名举报了。实名举报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实名举报也给自己惹了麻烦……”“我举报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上面下来调查果然是这么回事,所以渐渐地开始在周围有些名气。在这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来找我反映他们的污染问题啊。”
因此,他们认为在太湖环境恶化的过程中,自己不应该袖手旁观。当河渠的水由清澈变污浊时,当他们不得不放弃饮用河水改为饮用自来水时,当他们不得不呼吸有味道的空气时,他们开始了行动——写信举报。他们曾经向镇政府、县级市政府、地级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反映过情况,有的甚至曾经给国务院有关部门写过举报信。但是,这些举报信往往石沉大海,鲜有得到重视。他们说:“只有写到地级市政府以上的举报信曾经得到过答复。”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过对政府的信任,他们深信政府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他们仍然在坚定地走着自己的环保维权路。
这些环保精英们除写信举报之外,他们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环保卫士”。他们自觉向当地居民宣传保护太湖的知识,向居民宣传自觉将垃圾放到垃圾回收处;他们每天去太湖边捡垃圾,散步在各条河渠上,随时制止往河渠里扔垃圾的行为;他们时刻关注着河水、湖水的变化,发现变化迹象即会向“河长”①为了更好地管理太湖流域,整个太湖流域的河流都实行“河长制”,每条河都有负责管理的河长,在每个河段都有标示牌,写有河长的姓名、负责范围、监督电话。反映。他们偶尔也会被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参加有关太湖问题的群众会议或民主会议。调查中,一位被访者曾经给笔者展示了去年他被邀请参加镇里举行的一次民主座谈会的材料。
二、民间环保集体行动的产生逻辑
环保集体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科塞将社会冲突分为两种类型:现实性社会冲突和非现实性社会冲突。“由于在关系中的某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可以叫做现实性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不过是获得特定结果的手段”。②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从这一角度分析,民间的环保集体行动属于现实性社会冲突。它是民众表达自己的不满,要求改变现状的一种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采取了激烈的方式。这是一种污染驱动型的环境抗争,是民众作为受害者,在遭遇环境污染的威胁下争取健康不受损害、农作物不被污染的权利,因此是民众争取生存权的抗议运动。
中国农民是最不会惹是生非的一个群体,那么在太湖地区,如此忍耐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会形成一些激烈的环保集体行动呢?我们可以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来加以分析。
“风险社会”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来的。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社会被定义为工业社会。第二阶段,社会被定义为“风险社会”。在第二阶段,“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了问题”。③[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显然,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应该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在贝克看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传统的财富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每个人却要面临未知的不可预测风险。而且“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④[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页。在风险社会中,工业化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并且这个威胁防不胜防,人们无法用常规的经验来对付,而且这些新的风险是现代制度也无法解决的,风险已成为一种“制度化”风险。吉登斯则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⑤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产生。“在某个时刻,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①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环境风险和环境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它是由环境问题而引起的社会风险和冲突。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不可逆性以及系统性,因而环境风险和环境冲突也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具有特殊性,这就导致了环境风险和环境冲突也具有不同于传统环境问题的社会风险。严燕等认为,我国环境污染及环境冲突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两方面,现实风险主要表现在健康风险、灾害风险、经济风险等,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等。②严燕、刘祖云:《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3期。
引起当地民众的环保集体行动的“风险”——环境污染,是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同时,这种风险的分配又是不公平的,它是依附于阶级模式的——“财富积累在社会上层,风险则聚积在社会底层,贫穷吸附了大量的风险,而财富则可以购买安全和规避开风险”。③朱力:《当代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显然,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不公平地承担着大部分环境污染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很现实地威胁到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健康。同时他们又没有能力来应付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灾难和损害,他们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基本设施和安全保障,而社会政治体系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力或必要的支持。环境风险无疑加强了这种弱势地位的感受,使他们产生更大的“相对剥夺感”。④赵闯、黄粹:《环境冲突与集群行为——环境群体性冲突的社会政治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相对剥夺感”就连当地的所谓的“精英们”(知识分子、一般企业主、普通地方官员等)也不例外,他们共同感受到了对他们不公正的环境剥夺,因为面对强势地方企业和“财税”地方政府的联合,他们同样无力改变现状,同样扮演着弱势群体的角色。这种“集体被剥夺感”一旦形成,由此激发的不满情绪会不断地蔓延和相互感染,并可能在集体意识上达成某种默契,将有力地催化试图改变这种“被剥夺”现状的集体行动。环境集体行动者会对后果做出二元判定,即计算利弊得失,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环境抗争产生的风险,他们也会尽力增加人数。由此,集体行动蓄势待发。⑤赵闯、黄粹:《环境冲突与集群行为——环境群体性冲突的社会政治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在太湖地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力量开始大规模地、有深度地向乡村推进,这在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经济社会面貌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其环境面貌。城市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包含了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向乡村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受“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的影响,招商引资,在当地强力推进工业发展,而这种所谓的“发展”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而污染的后果并不仅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通常还意味着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紊乱,健康乃至生命本身的伤害,以及生活希望的破灭。这种灾害所带来的实际风险可能大大超过将无数的小农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农民负担”。⑥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下的“三农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当农民的土地、水源乃至呼吸的空气都遭遇污染、生存环境遭到破坏,面临生存风险时,在地方政府“污染保护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企业的排污和侵害行为得不到公共权力的有效制止,造成受害农民逐渐对当地政府不再抱有期望,而去选择“自力型救济”——太湖地区民间环境集体行动就此产生了。尽管由于环境的公共性,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存在理性的算计,但当民众共同面对风险以及集体被剥夺感时,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集体行动的爆发也就不可阻挡了。
于建嵘曾经将农民的集体行动归结为“压迫性反应”,具体是指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①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学海》2006年第2期。在太湖污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这种外部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污染企业的污染,另一方面是来自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两者的合力严重威胁了民众的生存权,使当地民众面临超出承受范围的生存风险。而生存伦理是根植于民众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当面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看不到蓝天白云,周围的亲朋好友不断被各种疾病折磨甚至被夺取生命之风险时,当地民众捍卫生存权的集体行动就更加坚定了。
所以,在前文提到的几个案例中,民众和污染企业的抗争都已经进行了多个回合。在调查过程中,许多村民表示,他们曾经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即使在镇长作出表态之后,污染企业仍然在继续生产。”在当地农民看来,某些地方政府已经成为财税政府,他们关心的是税收的多少,而不是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企业能够给政府带来税收,正是这个利税使得地方政府对其网开一面。尽管污染企业盈利颇多,但对农民的补偿是不足的甚至是没有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污染企业都没有对农民进行补贴。少数企业虽然对农民进行了补贴,但是也少得可怜,如防腐厂——房屋遭到腐蚀的村民仅仅得到了一点水泥补贴,村里的老年人得每人300元的补贴。这是对农民的绝对剥夺,必然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无论是相对剥夺感还是绝对剥夺感都比较强。面对这样的具体情境下,无可奈何、忍无可忍,他们必然会选择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以降低自己不应该承担的风险。如果没有有效的“安全阀”机制缓冲这种不满,随着矛盾累积,对抗势能增大,大规模民间集体行动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三、NGO的成长是环保集体行动破局关键
孙立平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博弈时代。②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真正进入博弈时代。博弈要求博弈双方的对等性。就太湖地区的民间环保行动而言,民众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双方不是对等的对话主体。尽管民间的这些抗争行动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绝不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而发起的抗争行动。当地民众的这些行动都有各自具体的、特殊的诉求目标,这些目标仅涉及经济、民生利益,与政治不搭界,群众也根本没想到以体制外的行动方式来谋求体制内的权力再分配。③于建嵘、单光鼐、简华新:《群体性事件应对与社会和谐》,中国社会学网,2009-1-7,http://www.sociology.cass.net. cn/shxw/shwt/ t20090107_19965.htm。这些环境行动背后实际上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受损和巨大的社会不公。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各种形式的民间环保集体行动。目前民间环保集体行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首先,目前的民间环保集体行动没有规划性,大都是针对突发的污染或者是积累起来的污染而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说,这些行动都是在环境问题产生之后才有的,是一种事后行为。而民间环保行动要有序开展,必须有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但民众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只有等污染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被迫采取行动。其次,目前的民间环保行动分布还比较零散,仅仅是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主要是在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才出现,带有“地方特色”。而在一些环境问题尚没有严重到相当程度和仅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的地区,或政府“控制”得比较好的地区,还没有形成预防性、组织性的全民环保联合行动。
“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政府单方面的决策充满风险,政府也因此意识到,只有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才能使决策更具合法性,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协同治理才是社会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其发展壮大将会更好地对政府活动形成辅助和监督作用,推动政府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减少弱势群体的集体被剥夺感。环保NGO的成长会使作为环境受害者的弱势群体受到常规性的力量支持和帮助,通过制度化参与的途径实现环境正义,从而降低了受害者群体走向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①赵闯、黄粹:《环境冲突与集群行为——环境群体性冲突的社会政治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可见,民间环保NGO参与环境利益冲突的解决,靠的不是控制和强制,而是通过群体间的共识、主动参与,互信互利,使冲突各方充分表达意愿,从而做出在最大程度上反映环境公平正义的决策,使环境冲突处于可调控的范围内。因此环保NGO的成长是民间环保集体行动破局的关键。
晏阳初先生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预见到:“只有自动的组织才真能有力量。所以,要培养力量,还得从教育起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②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因此要实现环保NGO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政府要改变对环保NGO的管理机制,让民众可以自发组织起来。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的制度。这种体制在强化社会组织准入条件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的同时,也使其“降生门槛”过高。社会组织在跨越合法登记注册的门槛之前,必须跨越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门槛,这种审批制度为所有的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设置了法律和行政制度障碍。据有关专家的调研估计,目前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数量,大约十倍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在太湖调查中,笔者也听到了当地环保精英希望成立民间环保NGO的愿望,但是由于政府的层层管制,最终未能被批准。“我的这些行为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不可能形成什么国外的NGO啊。我也曾经申请过成立环保NGO,但是没有被允许,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地方政府还是不太喜欢总是挑刺的人。”所以,政府应改变对环保NGO不信任、不放心的态度。环保NGO的存在是为了让民众民主地、制度化地参与环境事务中来,更好地促进环境冲突的解决,而不是给政府制造麻烦。要从社会体制上让民间环保NGO能自发组织、合法存在,并创造条件让其能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环保NGO必须承担起培养“环境公民”的职责。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环保NGO通过环境讲座、环境调查活动和环境拯救活动,激发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环境教育和环保传播,环保NGO吸引了大量志愿者长期献身环境公益事业,为民间环保积蓄坚实的后备力量。吸引更多民众自觉融入“环境公共领域”,实现参与者、行动主体从精英分子向普通民众的扩展以及精英分子与普通民众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这需要环保NGO实施专业化、联合化、互动化策略。③欧阳宏生、李朗:《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总之,环保NGO在培养具有自觉批判精神、现代环境观念和自组织能力的“环境公民”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编辑:肖舟)
Folk Collective Action Logic and the Key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Based on Pollution Governance of Taihu Lake
MA Daomi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 is of public goods property,so the possi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very small according to Olson. But in fact,various sorts of folk 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 in pollution area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These mainly are: organized collective action,non -organized collective action and environment elites' action. Analyzed from risk society theory,environment risk and conflict are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a kind of“made risk”. The spreading of“collective deprivation feeling”of vulnerable groups catalyzes effectively folk 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 The growth of environment NGO can make the environment vulnerable groups supported and helped by conventional power,realiz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way,and making environment conflict in controllable range.
Key words:environment risk;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vulnerable groups;environment NGO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5)06-0106-08
[作者简介]马道明,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