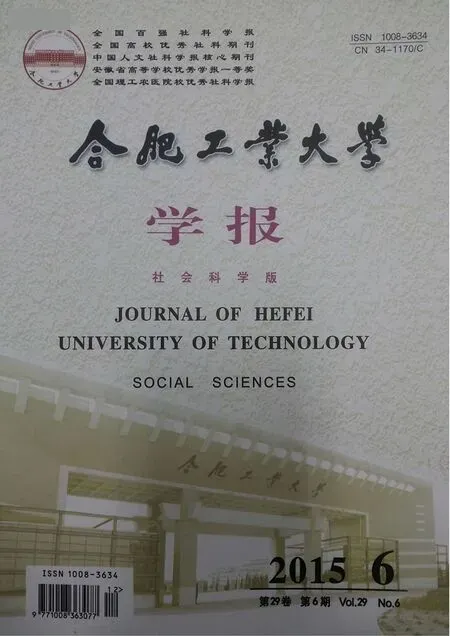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以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为例
唐 静
(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南宁 530004)
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以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为例
唐静
(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南宁530004)
摘要: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呈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等趋势,2013年首次出现的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的一次突破。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的出现,似乎使得偶尔为之的领导人形象传播转变为有组织、有规划的长期传播。文章以“学习小组”为例,对其2015上半年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学习小组”对领导人形象的象征化塑造效果积极,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信息环境下的传播需要。
关键词: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领导人形象传播;传播效果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领导人形象传播是各国政府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如何精准有效地进行领导人形象传播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与探索的问题。在塑造领导人形象时,媒体成为首选的工具,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美国总统竞选时媒体对两党候选人的形象塑造上。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领导人形象传播有了更广的领域,我国在这方面虽起步较晚,但领导人形象传播在最近几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改往日严肃正统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为主的方式,在互联网上以卡通视频来展现中国官员的选拔、领导人的工作常态等。新媒体环境下领导人形象传播有了新的载体,如微博、微信乃至专门的APP,它们开始定期有组织地进行领导人形象传播,甚至分类为专门的为某一个领导人进行的个人形象传播。
本文讨论的“学习小组”专为习近平形象传播而设,在订阅号的名称及栏目名设置上,也与“习近平”相关联,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本文选取2015上半年的内容分析,透视其与“母媒”《人民日报》在领导人形象传播方面的相互补充。通过对“学习小组”微信订阅号的领导人形象传播研究,可以探析我国新媒体形势下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具体操作,探讨这种新媒体形式下领导人形象传播的特点以及取得的传播效果。
二、微信订阅号成为领导人形象传播新阵地
1.官方媒体的非官方表现
通过检索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的历史推送消息可知,该订阅号于2014年2月27日推送了第一条消息。2015年1月23日,南方周末的《“学习小组”的尺度》一文,在探讨谁是学习小组的“操刀者”中描述,维护“学习小组”的是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五个年轻记者、编辑。
尽管在微信认证一栏已显示“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是推送者,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在评论一栏也设有“学习小组”专栏,但“学习小组”从界面设置和内容处理上都在刻意淡化官方身份,更多地向接地气的民间、草根媒体靠拢。
“学习小组”的微信功能介绍里这样写着:“这十年,我们好好学习。与习一起进步,一起担当。错过习的前60年,不再错过现在。”整个界面以“习语”、“经典”、“平天下”三个方面组成,其内容和语言风格的非官方表现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具体论述。
2.受众虽多但分群现象显著
“学习小组”与名为“侠客岛”的订阅号在五个年轻人的管理下,粉丝量突破11万,庞大的粉丝群是领导人形象能够广泛传播的第一步。受众面越广媒体传播的内容才能越大范围地与受众见面,才有可能谈及传播效果问题。领导人形象传播更是如此。让更多的受众认识、了解、认可,粉丝量的多少有着重要意义。
“学习小组”表达了对组员属性的界定:“有志于学习并读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志于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华人华侨。”其揭示了受众定位主要为体制内的中高层官员,最起码也是知识分子,这些均属于社会精英群体。
微信推送中关于组员来稿也体现了粉丝群的分众现象。2015年3月4日,“学习小组”刊登了题为《官方多次提“铁帽子王”的背后深意》的一篇组员来稿,作者供职于某中央机关单位。整个3月中关于组员来稿均刊登来自有一定知识背景或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稿件。
三、“学习小组”的传播特点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内容为王”重新成为媒体竞争的主要手段。其含义是指媒体做足传播内容,不断挖掘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官方性质的媒体在内容上能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以下截取2015年3月两会期间“学习小组”的推送内容为样本,并进行传播上的特点分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领导人的高密度推送
“学习小组”在介绍其内容时有一段直白的表述,“习近平说的写的;说和写习近平的;习近平读的看的;与习近平有关的。”通过对比分析3月份的内容,不难发现所有的报道和文章都围绕习近平展开,从领导人的政治、生活、往事回忆等各方面开展传播活动。在推送频率上,“学习小组”基本做到每天推送,3月份中,一共推送23次,共51篇文章。
2.整合媒体资源强化与时事的粘连度
由于3月正值全国两会召开,特殊时期更是领导人形象传播的关键时期,观察这一时期的“学习小组”,其利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的有关习近平两会的新闻稿件,如《人大开幕,习近平强调了什么》、《两会第二天,七常委都在干嘛》等。党和政府的内刊资源优势,使得其有效地实现优质媒介资源的整合:3月7日的《道光帝的那碗面片儿汤》、3月17日《从正定到中央,习近平一直强调这事》转自《学习时报》,3月13日《习治国理政的5种思维方式》转自《求是》。
“学习小组”并不满足于转载传统媒体的内容,在时效性上往往抓取新闻的第二落点。两会期间,传统媒体满足受众对于新闻的基本需求,“学习小组”则结合两会题材强化领导人形象传播。如3 月3日,《习近平的两会时间:今年履职新期待》一文,以回顾2014年习近平两会时间安排来分析今年领导人两会时间。此外,由于正值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习近平在上海团审议后与一位代表提到路遥,3月7日“学习小组”随即推出1993年习近平所作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些与时事高强度粘合性的推送,最大限度地将新闻事件的大环境与领导人相结合,对领导人形象宣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3月18日刊发《李光耀如何评价习近平》,这则消息正是在之前李光耀去世的假新闻曝出后推出的,在李光耀病逝后,“学习小组”发文回顾了习近平与李光耀的四次会面。“学习小组”善于重发文章,但这些重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文章堆砌,而是与新闻事件相结合。在《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后,即推出《习近平从足球领悟政道》,这篇文章于2014年5月28日已经刊登过,重复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宣传的效果。
3.寓形象传播于解读和评论
“学习小组”在对文章的转载方面并没有直接摘抄传统媒体的稿件,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以解读和评论传统媒体的新闻为主。正是这种改编奠定了推送内容的亲民性。
3月12日,《习近平如何评价2014年军队反腐》梳理了习近平出席解放军代表团会议的内容,对习近平的一些话语做了标注与解答:“习近平用‘大力推进’一词,没错,徐才厚等人的落马不大力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综观3月里的所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篇文章开头都加有编者按,直截了当地告诉受众推送这一篇文章的用意,有时也是对文章的中心主旨的提炼和概括。3月5日解读李克强政府报告时,“学习小组”从政府报告里提炼总理5次提及习近平,传播习近平在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航程上的领路人角色。对“绿色化”的解读是在3月24日政治局会议首提“绿色化”之后,“学习小组”详细地讲解了何为“绿色化”及政府提出这一概念的深意,触类旁通地回顾了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期间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理念。
四、微信订阅号的形象传播效果分析
技术革新对于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继微博之后,微信成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交信息平台,传统媒体也纷纷开设其微信平台的订阅号,推送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内容。
“学习小组”的微信订阅号集聚了即时、海量、互动等一系列特点,相比传统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来说,在传播习近平的形象上取得了特定的效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
领导人形象传播是各国政治传播的重要方面,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指主流新闻媒体充当政治传播的把关人角色,是他们在设置政治议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政治议程的设置已经不止存在于传统媒体手中,而是出现了多元轴心。 “学习小组”的出现正是适应了新环境下产生的新型受众群体,这里的新型受众群体的“新”主要体现在他们选择使用媒介形态上的变化。相比母媒《人民日报》,“学习小组”能够弥补不断流失的受众群。
正如前面所述,“学习小组”围绕时事议程设置,通过对上半年推送内容统计可知,推送内容与当日新闻相关的约180篇。围绕领导人的活动,通过整合传统媒介议题,将传播者认为可能引起受众兴趣的议题组合式重复传播。如6月29日关于亚投行的“基本大法”,“学习小组”配发了近两年习近平关于亚投行的讲话;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学习小组”更具有宣传性质,特别是利用“重复传播”这一宣传特有的传播方式,在领导人形象传播过程中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陷。
“学习小组”采用罗列领导人讲话的方式直接表达观点还体现在刊发评论和编者按上。如,习近平在十八大前后做出关于党员干部修养的重要论述,3月26日,“学习小组”以习近平为当官的指明道路为题,刊发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徐伟新的学习总书记讲话感悟。这些并不是单纯的新闻信息,而是包含了传播者的观点和态度。
在出现当日新闻中鲜有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报道时,“学习小组”充分发挥了宣传价值中的“时宜性”,选择适当的时机传播领导人形象。3月5日全国学雷锋日,《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第四版中刊登有关学雷锋日的报道,但并没有涉及习近平参与相关活动的新闻。当天“学习小组”推出《习近平说,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回顾了2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传递的学习雷锋不过时,以及习近平怎样谈雷锋、怎么学雷锋,该篇文章摘录了自1989年以来习近平的讲话与文章,是习近平谈学习雷锋问题的一大汇总。
通过议程设置来吸引受众的兴趣是形成公众舆论的第一步,受众兴趣的转移还需通过凝结受众群来实现。“学习小组”的受众群,对其他受众来说是“参考群体”,这一群体给受众心理造成的权威感比媒体本身更容易吸引受众靠拢。
2.个人形象的象征化塑造
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多次提及“象征” 的重要性, 他提出“没有任何一位成功的领袖会忙得顾不上培育那些能把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的象征”[1]。他所提及的“象征”是用某种事件来代表统治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态度,继而达到团结民众的作用,他以城市地铁适当收费问题被用来象征“人民”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在李普曼眼中,“象征”蕴含了不可忽视的感情,这种感情对凝结舆论起了重要作用。“象征”在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中展现了关键位置,“学习小组”与母媒《人民日报》严肃格调有所不同,领导人形象不再走高冷的政治风,而是以亲民的“家长范”出现,着重在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上做文章。
“亲民化”在“学习小组”的文章标题上便能体现出来。3月4日的《习掌门的“巡视剑法”》,3月27日的《习近平教你如何处理领导的批办件》,对习近平“掌门人”的称呼比传统媒体常用的“主席”更能吸引受众。处理领导的批办件,“学习小组”用“习近平教你”这一表达,无形中拉近了领导人与各级党证机关工作人员的距离。在文章的内容上,“学习小组”也用足亲民的手法。以3月16日和3月17日习近平分别会见哈佛校长福斯特、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例,“学习小组”以“两会一结束,习近平抓紧见了哪3个人”为题,首先编者按中用领导人的会晤到底开出了什么“花儿”吸引受众的阅读兴趣;在报道习近平谈到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时,给出了一段俏皮的话“请留意‘正能量’三个字,没错,中美之间也还有负能量”,那些唯恐南海不乱的人就是负能量。
此外,通过选择领导人日常生活场景、老照片来塑造领导人形象。3月21日《重情重义的习近平》里,回顾了各个时期的习近平生活、工作经历,并配以其在地方主政期间的照片,为领导人脱下神秘外衣,重塑其生活里的人格魅力。除了“亲民化”象征,“学习小组”还以“反腐”作为重要象征,塑造领导人“反腐斗士”的形象。通过微信订阅号设置的《习语》栏目中,专门设置子栏目“谈反腐倡廉”,截取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下发表的反腐演说,以直白的话风展现习近平反腐的决心。如“自己不干净、怎么管别人”、“我看天塌不下来”等话语,体现了反腐路上的“习大大放狠话”。
刻板印象是民众对大众传播已形成的固定成见。“学习小组”所塑造的习近平“亲民化”、“反腐斗士”的个人形象,有助于打破受众对于我国领导人形象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树立了新的象征性形象。
五、影响领导人形象传播的不足方面
“学习小组”成为专门为习近平量身定制的形象传播微信订阅号有其创新之处,但成立至今在具体操作中仍有不足,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传播形式较单调
新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拥有传统媒体几乎所有的传播形式,例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性在“学习小组”上未能体现。 “学习小组”在新闻的推送上几乎全为文字稿,很少有视频或音频。即使在管理员层面,也很难发送一些来自管理员的“声音”。因此,在新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上都没能脱离传统媒体的局限。
2.单轴权威仍在继续
新媒体造成的新环境在媒介化的政治传播中使得以传统媒体所代表的单轴传播体系被认为将面临瓦解。“媒体数量的扩张和普通新闻周期的变化为非主流的政治参与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影响政治议程的构建和设置”[2]。但新信息环境并未给我国的政治传播带来多元话语中心,领导人形象传播也仍以官方媒体单轴形式出现,“学习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已经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但其核心受众仍为精英群体,这一点从学习小组摘选受众来稿可以看出,被选录的稿件作者均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底层传播受阻可能缘于仍然存在信息社会的数字鸿沟现象,还有许多人不能利用网络媒体。
此外,造成单轴话语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普通受众没有机会进行话语表达。“学习小组”虽然设置微社区,但这一板块已经关闭。受众无法自主开设话题并形成多元舆论场,以推动主流媒体就这些话题进行新的形象传播。单向传播可能导致受众群体的流失,以传播者为核心的传播缺乏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六、结束语
总之,“学习小组”作为新媒体将领导人形象传播作为固定化的常态运作,表明国家重视新媒体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应用。它有效地适应了新型受众的阅读习惯,通过议程设置发挥传播作用。
“学习小组”对习近平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更加系统和统一的特点,有效形成了领导人“亲民”和“反腐”两个核心的形象,但未能摆脱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缺乏与受众的互动性。受众在形象传播的建构中仍处于被动角色,官方媒体牢牢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但作为微信订阅号,“学习小组”的出现就是一种突破,至于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领导人形象传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李普曼. 公众舆论[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郎劲松,侯月娟,唐冉. 新媒体语境下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塑造——解析十八大后领导人的媒介符号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5):36-40.
(责任编辑蒋涛涌)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 Case Study of A WeChat Subscription
Account Called “Learning Group”
TANG Jing
(College of News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has demonstrated a diversity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The cartoon images of Chinese national leaders that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3 mark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in the new media context.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WeChat subscription account called “Learning Group”,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that used to be scattered seems to have become a long-term,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endeav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Group” of the first half of 2015 reveals that this subscription accoun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ymbolized cre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images, which, to some extent, has met the communicative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information context.
Key words:WeChat subscription account; “Learning Group”;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communication effect
作者简介:唐静(1989-),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5-08-13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5)06-00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