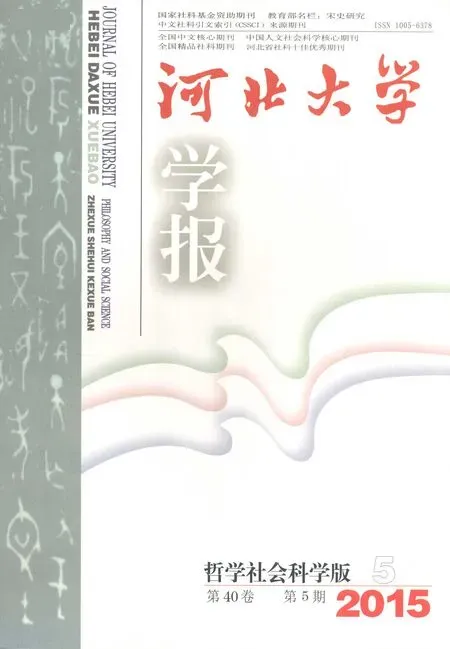论宋代女性经济犯罪问题
夏 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宋史研究◎教育部名栏◎
论宋代女性经济犯罪问题
夏 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义利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活跃态势,特别是社会下层女性广泛的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加之处于特殊的社会动荡时期,所以一些女性在面对钱财诱惑、悬殊的贫富差距时,难以把持自己的欲望,往往心生邪念,利用自身性别优势和职业之便实施犯罪。宋代女性犯罪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凸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盗窃、欺诈、略卖、行贿等行为。其犯罪形式和动机,既有时人经济犯罪的共性,也显现了女性低社会伤害性、易结伙性等特有的特征。
宋代;女性;经济;犯罪
在唐宋变革之后,宋代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呈现出新的特点,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和要求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宋代社会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运作,也为人们心中的钱财观注入了新认识[1]。女性犯罪行为的多样化以及参与犯罪活动的增多与她们社会作用的扩大直接相关。相比较而言,宋代女性犯罪类型中的经济犯罪问题更加凸显,主要表现为盗窃、欺诈、略卖、行贿受贿等形式。因其犯罪行为的动机大都与经济、财产等因素有关,将其划分为经济犯罪,与现代法律意义来划分犯罪类型相较不同①学界对于经济犯罪问题的研究,早在1999年张晋蒲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第五卷(宋)第三章民事法律和第四章经济法律中就有过详细的论述,其论述内容主要从物权、债权以及工商、土地立法等宏观法律方面着眼。其他学者对宋代经济犯罪的着眼点多倾向于社会中官吏、商人等层面,如韩瑞军《宋代官员经济犯罪及防治研究》(2008年河北大学的博士论文)、《略论宋代官吏经济犯罪的防范机制》(2007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1991年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王丽丽《宋代商人经济犯罪研究》(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等。王文渊的《唐宋女性犯罪问题探研》(2012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对唐宋时期女性的社会性犯罪及其原因、刑罚、社会对女性犯罪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宋代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学界对其涉及的经济犯罪问题的研究却相对空白,所以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很有进一步细致研究的必要。。
一、宋代女性与窃劫财物相关的犯罪行为
宋刑统规定:“潜行隐面而取,盗而未得者,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以次而加至赃满五匹,不更论尺,即徒一年。每五匹加一等,四十匹流三千里,五十匹加役流。”而相比较“窃”而言,对“劫”的惩处更加严重。“强盗以威若力而取其财,……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2]卷一九,300-303。宋律对窃劫行为的惩处力度之大,也侧面反映出宋代此类经济犯罪之盛。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时人对金钱的价值观念受社会风气影响而发生变化,拜金奢靡之风逐渐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3]卷二《书怀示友十首》,9,就是这种心态的最佳写照。甚至连出家人都认为“钱如蜜,一滴也甜”[4]卷八《钱如蜜》,62。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女性也在所难免的产生了对钱财的追求。外加宋代贫富差异影响,一些贫穷人户中的女性更是不惜为此铤而走险。
窃劫行为因犯罪性质不同分为窃和劫两种,“窃”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如徐二的后妻阿冯不愿交出夫家财物的管理权,在丈夫死后违背其已立遗嘱,受人唆使而盗卖夫家财产,终受到法律“堪杖一百,年老免断,监钱”的惩罚[5]卷九,304。宋代女性对于家庭经济或者是丈夫财产的可控性是很强的。这或许跟传统中国男性习惯“男主外,女主内”,把钱财交予家中的女性掌管的习惯有关。基于此,女性熟知家庭经济状况,是家庭中财务大权的实际掌控者,在有犯罪意念的时候,侵夺、盗窃夫财①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特殊性,所有未经丈夫同意的使用、支配、买卖都被算作为窃取夫财,被宋律定义为“盗”。在此则是因为法律定义“盗卖”中的“盗”,而将其行为归类为女性盗窃类的经济犯罪行为,这种所谓的偷盗,大多实际上属于处理夫财不当。就更加容易得手。
在家庭事务中,除了妻子会因处理夫家财产不当而被判为盗窃外,妾婢的偷盗行为更是多见。妾婢偷盗行为的频发,与宋代的社会经济原因密切相关。从市场方面来看,妾的价格约在数百贯到千贯之间[6]194—195,雇佣婢女的价格也需数贯之多[7]卷三,118—119,在京师和经济发达区还要更高一些。从当时的生活水平来看,雇佣一个婢女的价格大致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基本生活费用[8]379。再者,妾婢对于主家来说多是服务性的,她们的存在是主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奢侈性消费”。所以雇买得起妾婢的家庭,大多是经济水平比较富裕的家庭。这些沦为妾婢的女性,多半出身贫寒,当她们进入主家以后,生活环境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悬殊对比有时会刺激她们偷窃的犯罪意念。
光宗初年,尚书黄子由的夫人胡氏死后,一名婢女趁机窃物而逃,被捕之后供述说被缴的赃物是主母生前与棋手郑日新私通时作为收买送给她的。判官临安知府赵从善与胡氏素有嫌隙,加之婢女所言本就无法取证辨别真伪。于是赵从善“逮郑日新系狱黥之”[9]卷十,183,因个人恩怨而间接认可了婢女的言辞。该婢女在盗窃行为被发现后,为了脱罪而诬告主母胡氏,本该罪加一等,但赵从善却借此趁机报复,败坏其名声而雪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荣王赵元俨的侍婢盗卖家中金器,恐事发而纵火[10]卷八四,1928。纵火理应是重罪,可见该侍婢一定是窃取了大量财物并将其变卖,才铤而走险企图以这种手段掩盖犯罪事实。由于妾婢的特殊身份,有近距离接触、保管主家财物的可能,这种条件也给了有犯罪动机的妾婢擅自处理或者侵吞主业的机会。
还有一类犯罪行为被称之为“劫盗”,一般对受害者的人身和财产均造成了严重伤害。由于女性是提供饮食的主要来源,其性别特性又容易使人降低警惕,所以通常以接近被害人饮食用酒药迷惑之的方式,使被害人暂时失去意识或行为能力后,再由同伙共同实施犯罪。如鄂州旅舍的鱼氏夫妻,对来投宿的送寿礼的官吏打起了谋财的主意。鱼妻偶尔以卖药为业,便接近客人饮食将毒药投于酒中,杀人图财[11]卷二,22—23。再如襄阳九江山区一个小旅店,店主夫妇意欲图谋客人携带的财物,企图杀人夺财[12]支丁卷四,999。《水浒传》中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也是为劫财物而药杀旅客[13]364。这类女性犯罪者皆是借职业之便,经常得以与客人接触,在心生歹念之后限于自身体力较差等先天生理因素而与丈夫合谋共犯,得手几率较高。
再有孝宗淳熙年间,一严州客商带着丝绢到浦城永丰境内的一家村民开的旅店里投宿,店妇在与之通奸后发现其所带财物甚多,于是图谋杀人越货。当邻居听到客人呼救赶来救援时,店妇将之拒之门外并用客商的丝进行贿赂。最终,店夫妇在客商儿子的查访下,罪行败露,“并伏诛”“官毁凶室为墟”[12]乙志卷三,204。在整个案件中,店妇始终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并一直处于积极作为状态。其行为除了杀人谋财的动机之外,还有对赶来施救者进行的抵制和贿赂。可以说,该女性的犯罪行为是具有极其强烈的、明显的犯罪故意的。
有些女性还会利用家庭条件或者社会关系,涉及集团性的劫掠活动。刘氏仗着儿子为官,纵容并协同孙子一起恣行不法。蓄养爪牙,私设牢狱,为祸乡里。因为地处三县交界之处,仗着黑恶势力,掠抢乡民和过往客商钱财。私设盐库、税场,抢夺国家税收,对国家经济造成影响[5]卷十二,471—473。刘氏的集团式的犯罪行为,劫掠乡民、客商财产,给国家收入也造成了极坏影响,其犯罪动机之明确、性质之严重也可谓极尽。此类性质的女性参与的团伙性犯罪还有无赖王林夫妇,二人集结十多名同伙,劫掠官银[12]补志卷五,1594—1595。可见女性犯罪者借同伙之力实行集团式的抢劫,通常有详细周密的计划,涉案金额一般也属大宗,因计划周密、同伙众多,得手几率比较大。
由此观之,这类参与经济犯罪的多为职业女性。
她们作案的直接动机在于求财,地点比较固定,物色的对象大多是以从外地而来的官员、商人或士人。由于其自身生理特点,又容易依靠同伙共犯、周密的计划和接近被害人饮食用药、酒将其迷晕甚至毒死的等方式来提高得手几率。可见此类犯罪中的女性,手法缜密,犯罪主动性强。
二、宋代女性参与诈骗行为相关的经济犯罪
与欺诈行为相关的经济犯罪行为,主要是指通过使用谎言、欺骗或者其他方式以外在表象博得被害人信任,从而借以非法侵占他人所有权,获得被害人财物的犯罪。此类犯罪行为可分为“诈骗”和“诈伪”两种,其区别在于:在诈骗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通过欺瞒、捏造等方式来获得受害人的信任,从而达到侵犯受害人财产的目的。诈伪则是通过假冒他人名义来达到犯罪目的,其犯罪客体是受害人的身份权。
女性涉及诈骗犯罪,多是利用人性的贪婪或者是男性好色的弱点,设局诓骗受害人钱财。有一名假扮宫女的中年女性,与某恶少假扮兄妹,以寻求配偶的名义,找术士杨二算命。杨二每次都收取高额费用,本以为是占了便宜,没料到却被全家下药,眼睁睁的看着这对骗徒将家中财物洗劫一空[11]卷二,30—31。更有妇人为谋财想出了非常手段。南宋时,兴元县有一对夫妇得一弃儿,在抚养过程中发现孩子长的美丽可爱。该夫妇便决定将此儿扮成女子,教之以歌舞,将其深藏屋内,节其饮食,饰其肤发,“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不使人见,人以为奇货”,有欲求之为妻者,均被拒绝。“于是女僧及贵游好事者踵门,一睹面,辄避去,犹得钱数千,谓之看钱”。后来有一通判花七十万钱买得此儿,宴请宾客,让其歌舞伴酒。夜半客散,才发现其实为男儿之身,再要找寻其父母,早已逃的无踪影了[14]463—464。这种完全出于恶意的诈骗行为的出现,可见宋代个别女性为了贪图不义之财可谓挖空心思。
女性利用美色设下“美人局”意图诈骗的也不在少数。徽宗宣和年间,平康诸妓与恶少数辈伪装成官员及其姬妾,诈骗沈将仕财物,并彻夜逃走[12]补志卷八,1621—1623。临安某妇假扮美妾,充当骗徒眼线,盗取郑主簿随身财物[12]补志卷八,1620—1621。都城娼女,与奸狡之徒假扮宗室夫妇,色诱宣教郎吴约与之私通,随后即实施勒索,在得手后窜逃[12]补志卷八,1616—1617。赵大夫妻,姿态即佳,与恶子假冒官员夫妇,诱李将仕与之通,借此向其索财[12]补志卷八,1618—1619。黄家客店美妇,与恶子假冒官员夫妇,诱一官人通,遭捉奸后,官人恐惧逃窜,妇人与恶子将其财物席卷后离去[12]补志卷八,1619—1620。
由上述这些案例不难发现,宋代女性在此类诈骗活动中,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作为状态,并在案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受害者多为官员(尤其是外地官员)、士人和商人,他们独在异乡,不稳定的生活容易引发其内心的孤寂和漂泊感,在犯妇的美色诱惑下往往难以自持。这些女性借其职业之故,通常能将冒充的角色扮演的惟妙惟肖,加上与市井恶徒一唱一和,很容易使被害人深信不疑。她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受害人情感空虚、风流好色、好面子、事发后怕张扬、害怕因此而影响仕途等弱点,成功作案并从中渔利。外加其作案手段蒙蔽性强,识破这些伎俩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等被害人发现受骗,犯罪人早已卷款逃逸了。
在宋代女性的诈骗犯罪中,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就是“诈伪”。一般为身份诈伪,是较为特殊的诈伪犯罪。两宋动荡的社会环境,让此类女性犯罪者有机可乘,靖康之难后表现的尤为明显。高宗年间发生的两起假冒皇亲的诈伪案即是此类。开封民妇易氏在靖康之难中被乱兵所掠,与其一同被掠的宫内人向其说了不少禁内秘事,归宋之后便自称是荣德帝姬。宗室成忠郎赵世伦将她送到荆南,请在宫中任过职的朝请郎苟敦夫的女儿其暗中观察、辨其真伪。经过一番试探,被认为确系荣德帝姬。高宗皇帝听闻此讯派人前往验明正身,结果确认易氏为假冒,易氏的诈伪行为以失败告终[15]卷六一,1555。
另有乾明寺尼李善静为金人所掠,与其一同被掠的宫人张喜儿见其言貌很像徽宗之女柔福帝姬,并告知她很多宫中秘事。她在南还之后又为强盗所掠,成为一个小强盗的妻子。后来在官府剿匪的时候被抓,她为了活命便伪称自己是柔福帝姬。当地官员将其送至京城,高宗派去验证真伪的人认为属实,遂被召入宫中并封为公主。直至绍兴和谈后,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被金人送还,才得知真正的柔福帝姬早已死在了金国[15]卷一四六,2871。在假冒公主的十余年间,李善静从中渔利可谓不少。虽然其原始的犯罪动机并不在于谋财而是保命,但在谎骗成功之后,李接受了来自于皇室经济上的赏赐和俸禄等大量钱财,所以其犯罪性质也可以定义为经济诈伪一类。
以上两个案件中,犯诈伪罪的两位女性都是因为“靖康之难”的缘故为金人所掠,在被带往金国的途中与同被掳的宫人在一起得知了一些宫廷秘事。在其有幸南还之后,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均假冒公主身份企图欺骗朝廷。此二人的诈伪犯罪所侵犯的是被她们假冒身份者的身份权以及这种身份权所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类型的诈伪犯罪只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具有社会普遍性。
三、宋代女性参与略卖人口的犯罪行为
略卖意指“经略而卖之”,即使用周密计策掠夺人口,并将其贩卖。宋律明确规定:“诸略人、卖略、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又规定“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卖者,以和诱论,藏隐者减一等,坐之”“略卖周亲以下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无服之卑幼亦同,即和卖者,各减一等”。不仅对实施略卖行为的犯罪人进行惩处,即使是“私从奴婢买子孙及乞取者准盗论,乞卖者与同罪”[2]卷二〇,313—315。由此可以看出,宋律以受害人的身份和犯罪者的略卖手段作为判罪轻重的标准,如果双方有血缘关系,判刑更重,且不仅只对略卖者进行惩处,买主同样要受到惩罚。
虽然在法律上的惩处力度如此严苛,但宋代略卖人口的现象仍然十分猖獗,对象多以女性和儿童为主。女侩利用其职业的特殊性及其性别优势,是略卖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之一。还有一部分女侩不直接参与“略”,只是在买卖的环节中充当“介绍人”“中间人”的角色,主要是在奴婢、妾室和儿童的买卖双方中间牵线和帮助订立契约。她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不在乎这些被卖人口的来源是否合法,只管牵线搭桥,因此略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往往与女侩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女侩的外表光鲜亮丽,言谈机诈,基于职业影响稔熟物价信息,雇佣双方往往在交易中受其摆布。有些女侩为了谋取利益,与官员勾结,诱拐及略卖人口,从中获利。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西京有八位女侩,听从外戚王继勋的指示,与三名男性合伙,“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出弃于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16]卷四六三《王继勋传》,13542。这些女侩,为了丰厚的佣金,在明知道受雇之人可能会在雇主家丧命的情况下,仍然与人结伙,略良为贱。牙婆程氏也是与官员黄有竟、官牙人潘某合谋贩售婢使[5]卷九,357。由于宋代官府通过向牙侩收交易税作为制约牙人从人口买卖中渔利的机制,所以联合官员合伙营生,官、牙双方皆会因此得到更多牟利。对于官员来说,女侩也会因其性别优势,成为他们首选的合作对象。
还有一些女性,虽不是女侩,但也涉及了略卖人口的犯罪。开封民陈文政与妻子阿宗诱拐虎翼兵士妻,使其受雇用而得钱[17]天圣元年十月开封府言。梁自然诱拐卓清夫的女使碧云,藏匿于家中,其妻阿陈将其贩卖[5]卷十二,451。这两起案例皆为夫妻伙同略卖女性。前者为军妻,后者为婢女,受害人的身份不同,所以对二犯妇的处罚也不同。
宋代社会对女性的大量需求,形成潜在的买卖市场。合法与非法买卖并存的社会市场环境中,涉及略卖犯罪行为的女性的犯罪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买卖程序;另外一种是利用女性以获取他人信任的性别特性,以非法的手段略卖人口。涉及第一种犯罪形式的大多为女侩,而后一种模式中的犯罪主体则相对较广,即使是普通家庭妇女也有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参与违法谋利的犯罪。
四、宋代女性参与行贿、受贿等犯罪行为
宋代女性经济犯罪中的行贿受贿行为被称之为“坐赃”。按宋律:“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赃论……”“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减主司罪三等”[2]卷十一,174—175。在行贿受贿的犯罪中,行贿者要罚、受贿者要罚、相关的官员要罚,即使是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亲属受贿许了事也要被罚。
涉及受贿的女性大都是朝廷官员或权势之家的女眷,她们往往会利用其丈夫、儿子或家族中其他男性亲属的权势,受人请托,获得财物。真宗咸平五年,举子任懿通过两位僧人与任职贡院的王钦若之妻李氏搭上线,并向其表达了希望能够获得帮助而中举的愿望,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予相应的报酬。李氏“密召家仆祁睿,书懿名与左臂,并口传许赂之数,入省告钦若”。王钦若在得知消息后,遣仆人告诉李氏“令取所许物”[10]卷五一,1119。最终,任懿如常所愿登第,并被朝廷派往临津任县尉,王氏夫妇的受贿行为也既成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王氏夫妇一样侥幸,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度支员外郎、知河中府勾克俭之妻“性悍戾,与豪家往还,因缘纳贿,克俭不能禁”,终于案发后,“降克俭知宁州”[10]卷八六,1968。勾妻不听丈夫劝告,与地方势力联手索贿,虽然并非克俭本意,但仍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这样类似的受贿案还有很多,如哲宗绍圣四年,三泉县君王氏与其夫朝请大夫盛南仲在任贪赃事发,王氏被判“追封邑,罚金”[10]卷四八五,11529。高宗绍兴三年,右朝奉大夫晁公为之妻任氏受贿[15]卷六五,1615。相隔二十多年间,同为右朝奉大夫的陈良翰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阿附秦桧,其妻更是公然受贿,她甚至“内通关节,时人谓之女提刑”[15]卷一八五,3627。还有孝宗淳熙初年,县吏高某妻以丈夫职务之便,私纳税金[12]支景卷五,915—916。这些案例大体可以反映出这些涉及受贿的女性,大都依赖丈夫的官职而进行权钱交易。她们的犯罪动机简单明确——钱财,只不过有些是与丈夫共谋索贿,有些是违背丈夫意愿自行索贿。但这就反映出:在整个受贿犯罪的过程中,无论男性掌权者是否参与其犯罪行为,受罚最重的还是男性,而对女性惩处力度不大。可见朝廷对于此类案件态度认为,对她们受贿表象下的权力依附者的降职或者免官,是从“源头”上剥夺非法获利的根源。
除了受贿,还有的女性涉及行贿。当女性涉及犯罪或争讼时,在认为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所以容易用钱财贿赂官吏,希望藉此规避刑责。太宗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氏犯奸,诬告丈夫的前妻之子王元吉下毒,并贿赂审案官员将其治罪[17]雍熙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咸平县张赟的妻子卢氏,与养子争讼,贿赂官员希望惩治养子之罪[17]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七日。刘、卢二人的行贿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打赢官司,在家庭财产纠纷中受益。另有恶人唐梓,行骗乡里,为恶一方。他靠敲诈、行骗等手段积累了一万一百一十八贯钱,并将其交由小妾赵秀掌管。后为人所告,蔡久轩审案判决唐梓“决脊杖二十,刺配广南远恶州军,仍籍没家财,用锁土牢不放”,其小妾赵秀动用赃款上下活动,行贿官员,希望能够帮唐梓减轻刑罚[5]卷十四,525—526。此案中的女性行贿意图则更加明显。
由上得知,女性涉及行贿、受贿有关的经济犯罪,直接动机一般都是与钱财有关。女性受贿者多出自官宦或权势之家,借家中男性成员的权力替他人解决问题,从中获得经济上的回馈;女性行贿者或者是希望在争讼中获得更多利益,或者是因犯罪而买通关节从轻量刑。无论行贿还是受贿,都与宋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人们的经济观念分不开,这一种类型的经济犯罪是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
五、宋代女性经济犯罪的社会背景及时代特征
从大环境来看,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宋人重财观念亦盛。对钱财的追逐,是导致经济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且宋代雇佣制度渐趋成型,雇佣与宋人生活息息相关,上至达官之家,下至平民百姓,雇佣者和受雇者都被纳入社会经济大潮之中。无论是雇用、购买妾婢,还是寻求雇主,都需要牙侩的介绍。于是阅历复杂、舌灿莲花的女牙侩在宋人的生活中活跃起来。陈普曾有诗言“插花做牙侩,城市成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18]《吉田女并序》。这些女牙侩本就是从事着买贱卖高的投机生意,所以她们也特别容易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利用其职业和身份之便,出入闺阁,趁机犯罪。盗窃、受贿牵线引诱良家妻女、略卖人口等经济犯罪行为在女侩身份的掩护下格外容易得手。另一方面,宋代的人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量相当大,底层百姓人家的穷苦女性成为富人家雇佣侍婢的主要供应来源之一。如前文所言,宋代雇买妾婢的价格不菲,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无法承受这种“奢侈性消费”的。当贫穷的妾婢进入富庶的雇主家中,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极易引起人们心中的不平衡之感。对金钱的格外向往,加之妾婢对主人生活习惯、贵重物品存放位置等的熟稔,这些妾婢往往会因一时贪念,触犯盗窃罪。穷苦的妾婢在考虑自身的弱势性之后,又容易形成联合其他共犯作案,对主家经济威胁更大。
还有一些女性,利用其性别优势和职业便利,可能为他人提供住宿或者接近他人酒食,在酒食中做手脚,使受害人暂时的失去意识或者反抗能力,实施犯罪。这种女性的犯罪行为多出现在乡村酒肆、旅店,地理位置偏僻且受害人相对处于弱势。这些女性一般家境清贫,靠小生意维持生计,容易与丈夫同谋,构成盗窃、劫掠等犯罪。在此类犯罪中,女性还经常利用美色引诱被害人,使其放松警惕并观察其财物状况。还有类似同样利用美色犯罪的行为即是诈骗,在京城等大都市屡见不鲜。洪迈曾提到过这种“美人局”多半发生在城镇,尤其是都城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士大夫旅游都城,为女色所惑,率堕奸恶计中”[12]补志卷八,1616。娼优与游手多在城市活动,又同属于社会底层,容易串通一气联手作案。这种女性经济犯罪行为的出现,也属于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负面衍生物。宋代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受社会义利观念影响,为谋财而选择铤而走险、不择手段。
种种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宋代女性经济犯罪特征均为:首先,女性犯罪往往带有低暴力性或非暴力性,一般具有家庭型特征。即女性经济犯罪常常与家庭相联系,或者是发生在家庭之内的盗窃行为,或者是为家庭中男性成员联手共犯,亦或者是依赖家庭成员而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是很大,属于小规模犯罪活动。虽然也存在大规模的团伙性犯罪,但属于特例,而且同样是因依靠家人、子孙势力而犯案。其次,女性犯罪行为的阶层性也相对明显,社会上层的女性涉及的经济犯罪多为因势力优势而受贿,下层女性的犯罪动机则多是受钱财刺激,希望借不义之财来改善生活状况。再次,官方基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对其犯罪事实的惩处也是有严有宽,比如盗窃、略卖人口等惩处力度就相当大,对于类似官宦人家女性受贿等问题的处理就显得相对宽松。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钱财观念带来极大冲击,女性对于钱财观念的变化也属正常[19]。而且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女性社会活动的身影也显得格外活跃,因难以抵制诱惑而引发经济犯罪,实属在所难免。
[1]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窦仪,等.宋刑统[M].吴翊如,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陈与义.简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释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张四维,等辑.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伊沛霞(PATRICIA EBREY).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8]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9]周密.齐东野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鬼董;夜航船[M].栾保群,点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2]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8]陈普.石堂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郭东旭.论宋代婢仆的社会地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15-20.
【责任编辑 侯翠环】
On Women Economic Crime in the Song Dynasty
XIA T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s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has also changed. In the Song dynasty women show active postur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lower social class women broadly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 a particular social turmoil, some women, in the face of money tempt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ires, and often have evil heart to commit crim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one's own gender advantages and professions. The female crime in the Song Dynas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y for theft, fraud, slight sale, bribery, etc. The crime form and motivation, sometimes have the commonness of economic crime, also appear the characters of the women’s low social harm, and easily banding together.
the Song Dynasty; women; economy; crime
2015-02-26
省级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立项项目《宋代女性经济生活研究——以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为中心》(sj2015014)
夏涛(1987-),女,河北秦皇岛市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女性犯罪问题。
D929
A
1005-6378(2015)05-0044-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