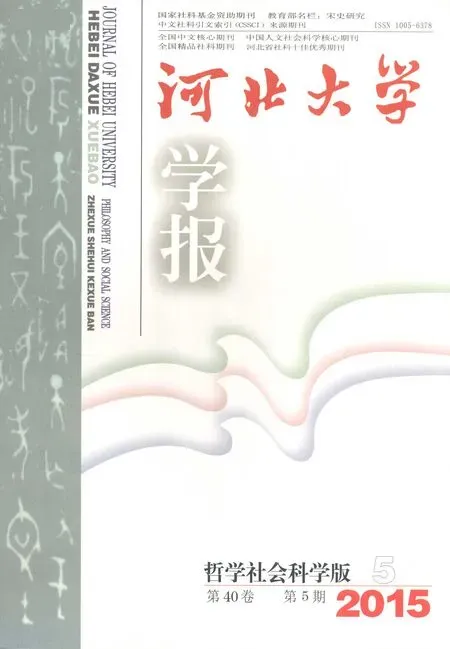非利他性视角下慈善捐赠的立法激励
李喜燕
(重庆文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法学研究
非利他性视角下慈善捐赠的立法激励
李喜燕
(重庆文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在慈善捐赠中,捐赠主体往往具有追求精神利益或潜在物质利益等非利他性动机,并能获得相应的非利他效果。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的存在有其相应的合理性,但当前立法对慈善捐赠中存在的非利他性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不足。我国应正面肯定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同时明确非利他性的边界,在捐赠冠名、税收优惠等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激励和规范慈善捐赠,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慈善捐赠 ;利他性 ;非利他性 ;立法激励
2014年11月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世界135个国家中捐赠指数排名倒数第八[1],这说明我国慈善捐赠意愿总体不足。究其原因,近年来接连不断的慈善丑闻无疑是影响我国慈善捐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强调慈善捐赠主体的无私付出,忽略甚至否认慈善捐赠中客观存在的非利他性,也是影响慈善捐赠积极性,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表明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激励慈善捐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正视慈善捐赠中客观存在的非利他性及其合理性,分析探讨我国有关慈善捐赠非利他性的立法问题,能够为激励慈善捐赠,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及其合理性
(一)慈善捐赠中非利他①此处采用“非利他”而不是“自利”的说法,原因有二:一是笔者认为非利他的范围比自利要广,非利他不仅包括利己,也包括既不纯粹利他又不纯粹利己,比如为了追求特定的个人偏好或者社会认同的慈善捐赠行为体现为既不是纯粹利他,又不具有典型的利己性的行为。二是因为常识认为慈善捐赠行为是具有利他性的行为,采用非利他性的说法是为了突出和强调其与利他性的对应。性的基本界定
一般而言,利他或非利他通过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从行为动机的角度考察,纯利他主义者进行慈善捐赠决策时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完全不考虑自身利益,但是慈善捐赠主体在捐赠时往往不仅仅是基于纯粹利他动机,还可能基于非纯粹利他动机。非纯粹利他的动机应该分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与对于精神利益的追求两类。物质利益的追求主要体现为捐赠价格的降低与间接经济利益的取得,而精神利益的追求体现为对荣誉地位、特定个人偏好和社会认同的追求等方面。当然,现实情况下,有些捐赠中的非利他性也可能同时体现为对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追求。其次,从行为效果来看,慈善捐赠通常能够取得利他效果,但相当多的情况下也能产生非利他的效果。非利他效果包括捐赠人作为慈善个体能够感知到的价值、在社区中地位的提升、社会和商业方面资源的开拓、通过捐赠一个有价值的事业而获得的良好感觉等非显性的效果[2]。因此,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指慈善捐赠人在非纯粹利他动机驱使下进行慈善捐赠而取得的非利他效果,是非纯粹利他动机与非利他效果的结合。
(二)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的合理性
首先,非利他性的存在不影响慈善财产发挥其慈善功能。比如不能因为捐赠人的名字刻在建设大楼上而改变其属于教育、艺术或者其他公益事业的功能,但若不允许冠名捐赠或者去除捐赠冠名,则可能导致捐赠的减少或某项捐赠的终结;而慈善捐赠人追求税收减免、礼品或者其他的交易机会等物质利益的存在也不会影响慈善财产本身的公益功能。其次,由于在集体行动中,存在“搭便车”行为,公共利益就难以成为利己主义者进行捐赠的动机。然而,如果捐赠人能够获得排他性的非利他私人收益,则能够激发捐赠者进行捐赠。费格森等人认为在经历了多种付出以后,捐献人表现得更加的关注其他人的福利,这就促进人们毫无条件的帮助其他人,并且帮助本身能够进一步强化这种行为[3]。再次,税收优惠不仅节约了国家的征纳税成本,也减少了政府对公益事业的行政成本支出,提高了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用。同时,对慈善捐赠主体进行褒扬和激励的方式,也具有导向和辐射功能,亦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用。而所得税税收优惠后,使税后的净收入额度降低幅度减小,其结果是企业或个人税后净收入与捐赠总额之和大于不捐赠时的税收净收入总额,也增加了捐赠主体的私人效用。而冠名捐赠等形式在利他的同时,也提升了捐赠人的知名度和形象,实现了作为“经济人”自利的目的,最终表现为行为人利他且利己的效用最大化。最后,从法理上讲,权利义务是法律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人们进行慈善捐赠,就类似于主动自愿地履行了这个义务,而履行了义务的主体必然希望享有相应的权利,而税收优惠等非利他性的存在实际上是为履行了捐赠义务的主体提供了享受权利的机会。捐赠者有权享受这些权利,而不捐者则无权享受这些权利,给社会主体多了一个选择的砝码,既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也能达到激励慈善捐赠的效果。
二、非利他性视角下慈善捐赠立法激励的不足
(一)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的现有立法检视
当前慈善立法重点关注的是实现慈善目的,而对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则更多体现为防范与限制,现有的支持性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公益事业捐赠法》第8条体现为对于慈善捐赠人荣誉地位追求的肯定与支持。《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4条规定了捐赠冠名。1997年国家教委也具有冠名行政许可权,2004年被国务院取消了该权。此外,冠名的有关规定还体现在部分效力层次低的地方性规范文件。比如,2012年,九江市慈善总会就已经出台《冠名爱心小基金设立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允许设立以个人(家庭)或单位名字冠名的爱心小基金,比如九江市慈善总会——×××基金。其次,我国税收立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慈善捐赠人降低“捐赠价格”的利益追求。个人慈善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以内与企业法人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此外,《公益事业捐赠法》第5条、第12条表明在满足公益目的前提下,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捐赠财产,且捐赠人享有对于捐赠用途的决定权,表明立法允许满足捐赠人对于捐赠用途的特定偏好。根据《合同法》第190条、192条、194条规定,立法肯定了一定条件下合同的撤销权,但这个规定是否适用于慈善捐赠合同也存在争议。
(二)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的有关立法不足
其一,有关冠名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期限不明确。《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4条冠名权的适用范围相对狭窄,是否包括对已经存在的建筑物进行修理维护的冠名权、其他类型的捐赠冠名权还值得商榷。冠名是否永久,能够享受冠名所需捐赠的数额或规模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某个主体姓名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名称也未见到全国适用的规定。即使现存在冠名规定也缺乏操作性、程序性、具体化的规定,更缺乏一定情况下取消冠名的相关规定。清华真维斯楼事件颇受非议的原因便是缺乏民主程序和信息公开程序的典型案例。此外,关于冠名以外的其他荣誉地位的立法规定不充分。《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开表彰对象覆盖面窄,且不能满足捐赠主体其他类型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未见到关于捐赠者享有获得名誉职位、捐赠证书、纳入捐赠名册等内容的立法规定。当然,现有立法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于捐赠意愿的尊重,但是这些条文仍然缺乏一些可操作性。
其二,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税收优惠资格受限,且税收优惠比例不一致。目前税前优惠待遇仅仅适用于向具有慈善捐赠税收优惠资格的受赠人捐赠,向不属于立法规定的公益慈善组织捐赠、向属于法定的符合税收减免资格但尚未获得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公益慈善组织捐赠、针对个人的捐赠无法享受这种税前扣除待遇,不仅影响了慈善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限制了慈善捐赠人的捐赠对象。同时,在能够享受捐赠税前扣除的受赠组织中,向政府主控的公益机构捐赠可以享受全额扣除①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等 5 家单位的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第 204 号)、《关于向宋庆龄基金会等 6 家单位捐赠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第 172 号)等规定。这些文件规定向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政府主控的公益机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前全额扣除。;而向其他经过批准享有税前优惠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和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组织捐赠,只能享受税收优惠比例扣除。因此,扩大慈善捐赠税收优惠认定范围,构建公平的税前优惠扣除环境,是促进慈善捐赠亟待解决的问题[4]。其次,所得税优惠比例偏低且不能向后结转。我国对于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扣除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而我国不允许捐赠额向以后年度结转的做法也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影响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再次,其他税收优惠种类不全。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方面规定以捐赠方式转移货物的,均视同销售,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在资源税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税法关于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仅见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相关立法中,税法优惠规定不完整甚至存在漏洞。比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就缺乏相应的规定,财产税法中房产税和车船税等也无相关税收优惠规定。最后,实物捐赠如何估价的规定也存在一定问题②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第9条。,而且慈善捐赠退税手续繁琐、复杂,增加了捐赠人办理退税手续的成本,操作性差,严重影响了公众慈善捐赠退税的积极性。此外,现有立法对利用慈善捐赠而获得非正当性利益的情况缺少专门立法规制。比如通过向高校捐赠而获得该校的点招名额或者通过慈善捐赠而获得市场交易机会,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不正当的竞争,获得物质利益。
三、非利他性视角下慈善捐赠激励立法的完善
制度架构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利他水平和道德风尚。立法应该认可、肯定慈善捐赠人非纯粹利他动机,满足慈善捐赠主体合理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需求,方能充分激发慈善捐赠人慈善捐赠动力,方能有效做大公益慈善的“蛋糕”。同时,针对理性选择的“经济人”趋利本性和可能引发的不正当竞争,需从制度上规范与限制慈善捐赠人不合理的非利他利益追求。一是捐赠财产必须是慈善捐赠主体合法拥有并具有处置权的财产,且非利他追求的目的必须是合法的,不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对受赠人或受益人附加不合理的条件。二是当慈善捐赠主体非利他性追求和慈善目的发生冲突时需要遵循公益优先原则。三是慈善捐赠中所获得荣誉称号、荣誉职位、冠名或者税收优惠等非利他性利益必须是慈善捐赠的伴随性结果,而不是属于条件性要求。四是慈善捐赠主体所追求的非利他利益不排斥其他慈善捐赠主体类似的非利他利益的追求。这就要求立法需要明确非利他性的追求必须符合合法性、附属性、伴随性及非排他性的要求,不能偏离整个活动的慈善性质,不能利用慈善捐赠名义而在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当慈善目的与非利他性目的之间发生冲突时,以优先满足公益利他性为准则。
(一)关于慈善捐赠主体精神利益追求的立法激励建议
其一,就慈善冠名而言,慈善冠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慈善事业还正在发展阶段,对冠名捐赠更应宽容激励,而非严格约束,方能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的欣欣向荣。当然,在肯定冠名权的同时,应该明确冠名权的赋予必须设定明确的适用条件和严格的冠名程序,以避免如清华“真维斯”楼事件似的轩然大波。同时,建议允许慈善捐赠冠名适用有限的时间段[5],并应该视情况不同给予不同期限,把公益目的视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条款而永久存在,而把冠名条款作为次要条款因情况而改变。针对冠名基金而言,比如因高校不再派遣参军学生,用于资助参军学生的基金目的不能实现时,基金名称不受影响,而是可以改变基金目的;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某个冠名基金因不再拥有可以分配的基金,则视为自动终止,并办理相应的退出手续。针对建筑物冠名而言,如果捐赠人不能提供建筑物的维护费用,则可以设定一个允许冠名的最长期限,比如50年。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的公益募集中就明确提出冠名的期限为5年。若因建筑物本身成为危房而需要重新修建,原有的冠名建筑物已经无法继续存续,而捐赠人不能提供修建费用时,可通过一种雕像或者壁挂等形式的替代性冠名的形式满足捐赠人冠名要求。针对公益项目性质的冠名而言,持续存续并开展工作的可以参照冠名基金的做法,一次性开展工作的则可以参照建筑物冠名的情况处理。冠名捐赠的替代性处理也需要避免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比如“公益募集机会主义者通过宣称不可能实施、不可实现等借口以逃避捐赠人意愿来构想拙劣的公益慈善经营方式”[6]。那么当受赠人与捐赠人或其代理人、继承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所涉捐赠金额又达到一定数量时需要通过法院审判程序来判定是否应继续冠名。而当冠名者声誉出现污点时也需要分两种情况:若捐赠财产是非法所得则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若捐赠财产是正当取得的财产,则不应因冠名者的声誉而发生改变。此外,冠名的市场部分如何进行测算本身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即使在美国这样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暂时还一直没有实施,而我国当前慈善业发展不足,暂时也不应规定在计算捐赠额时扣减冠名捐赠的市场价值部分。当然,实践中可能存在通过冠名捐赠而扩大捐赠主体的知名度或者美誉度,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最终达到满足其物质利益追求的效果。这种情况是冠名捐赠所带来的伴随性的效果,其冠名本身与其根据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开展的市场经营行为直接相关,不应该由此而否定其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
其二,对于冠名捐赠以外的其他精神利益的追求的立法建议。除冠名外,荣誉地位的追求一般表现为名誉职位、荣誉证书、捐赠证书、捐赠名录等。名誉职位往往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捐赠人才能够享有的一种荣誉,而荣誉证书、捐赠证书或纳入捐赠名录则对捐赠的数额或者规模没有太多的要求,立法应该明确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创设各类慈善捐赠荣誉,或者对于相应种类和级别的公益人士在职务升迁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其次,对于慈善捐赠中特定偏好的追求而言,在满足合法性、附属性、伴随性和非排他性要求的基础上,禁止慈善捐赠人借口个人偏好追求而干涉慈善捐赠项目运行本身的专业化或违背慈善组织的宗旨或使命。对于慈善捐赠目的本身的偏好而言,只要其是属于慈善事业的范畴,本身无可厚非;对于慈善捐赠人借口个人偏好追求而干涉慈善捐赠项目运行本身的专业化应该明确禁止,避免不具有某方面专业的慈善捐赠人干涉专业化操作行为;而对于指定捐赠资金的支出限制有利于实现受赠组织的事业目的的产品可以支持,而对于不是受赠组织完成其事业目的所需要甚至与其本身宗旨背道而驰的限制则应该明确禁止。当然,在鼓励慈善捐赠的同时,也应该对片面根据社会身份的高低而进行相应捐赠的习俗予以纠正,鼓励平民慈善和自发慈善。另外,立法需要严格禁止顶着慈善捐赠的目的从事非法交易行为,比如利用公益之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或者获得个人晋升、子女升学或者其他不正当机会。对此类情况需要从立法上明令禁止,并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关于慈善捐赠主体物质利益追求的立法激励建议
对于慈善捐赠主体物质利益追求的满足方式主要有:通过税收优惠降低捐赠价格,通过给予捐赠主体一定价值的捐赠纪念品给予物质激励,或者通过捐赠获得良好的口碑,从而增加捐赠主体市场交易机会而获得物质利益。因此,立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激励:其一,就税收优惠立法而言来说,将受赠人税收优惠资格的行政许可制转变为核准制,降低受赠人税收优惠资格准入条件,对于向具有税收抵扣资格的受赠主体捐赠,适用同样的税前优惠扣除比例;强化过程监控与事后监督;建立免税资格组织退出机制,对不再符合相应条件的组织取消其免税资格;将个人慈善捐赠扣除比例由30%提高到 50%,同时,把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由12%提高为30%;建立税收结转制度,对于超过规定税收优惠比例的慈善捐赠额允许结转至下一年度,结转年度最长不宜超过 5年;增加有关慈善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资源税立法,修订城市维护建设税等行为税法,增加现行房产税、车船税中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开征遗产税,从反向激励纳税人进行慈善捐赠;对财物捐赠等其他捐赠形式设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作价办法,若出现估价情况不同,则以较小的为准。并且捐赠者要享受税收优惠,应当在捐赠财物时出具市场价格证明,由税务机关审定,否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对股权捐赠、公益信托等其他慈善捐赠方式的税收优惠予以立法认可并设定可操作的税收优惠规范。其二,关于其他物质利益追求的立法。公益组织对于慈善捐赠人一些礼品的回赠也意味着捐赠价格的降低。这种做法尽管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不过需要限制礼品金额,避免小额捐赠获得大额回馈的情况。而针对慈善捐赠人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追求交易机会的增加问题,可以分两种情况对待。第一种情况是因捐赠提高个人信誉从而在符合市场自有公平竞争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交易机会。这种情况应该视为是慈善捐赠的伴随行为,本身不违背市场公平自由的交易原则,无需立法专门予以规制;第二种情况是慈善捐赠人以慈善捐赠为手段,获得与公益组织或相关主体的市场交易机会。这种情况下如果该类商业机会本身是其独立的市场交易行为,并非是以慈善捐赠为条件而获取,且不违背市场交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则从立法上需允许此类慈善捐赠行为。如果慈善捐赠与获得交易机会是通过合同或类似合同的形式,并且以直接的商业交易为条件,则可以视为是商业赞助或者商业广告,不应享受慈善捐赠税收优惠。
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是促进慈善捐赠的有效手段和重要动力。我国应该正面的认可慈善捐赠中客观存在的非利他性的正当性,并予以立法支持,同时,还应该对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予以立法规制,保证慈善捐赠人的非利他性存在于在一定的范围与限度内。本文对慈善捐赠主体非利他性追求的立法建议,仅仅是抛砖引玉,理论和实务界还需要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法制上对其予以支持与限制,以达到激励和规范慈善捐赠,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1]CHARITIES AID FOUNDATION.“世界捐助指数”中国为何排名不佳” [EB/OL].[2015-03-30].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3030.html.
[2]LISE VESTERLUND.Why do People Give?[M]// WALTER W POWELL, RICHARD STEINBERG.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572-73.
[3]EAMONN ERGUSON. Exploring the Pattern of Blood Donor Beliefs in First-Time, Novice, and Experienced Donors: Differentiating Reluctant Altruism, Pure Altruism, Impure Altruism, and Warm Glow[J],TRANSFUSION, 2012(52):343, 353.
[4]卢代富.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规定研究——从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谈起[J].现代经济探讨,2009(3):17-19,23.
[5]LINDSAY WARREN BOWEN, JR. Givings and the Next Copyright Deferment[J] FORDHAM L. REV. 2008(77): 809, 815-819.
[6]PLUMMER MEM’l .Loan Trust Fund[J], N.W. 2d. 2003(661):307, 312-313.
【责任编辑 王雅坤】
Legislation Stimulation of Charitable Don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on-altruism
LI Xi-yan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zhou, Chongqing 402160, China)
In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the person who donates with the non-altruism often has the motivation of spiritual interests or potential material interests,thus get the results of the correspodent non-altruism.The exsitence of the nature of non-altruism has its correspoding rationality, but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doesn’t approve and sustain the non-altruism. We should not only confirm directly the non-altru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define the boundary of non-altruism,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on the aspects of denomination of donation, and tax preferance in order to encourage and regulate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the nature of altruism; the nature of non-altruism; legislation motivation
2015-04-25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2013PYFX20);民政部慈善事业创新和发展理论研究部级重点课题(2014MZFLR177);重庆文理学院重大培育项目(201310)
李喜燕(1974-),女,河北尚义人,法学博士,重庆文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社会法学。
D923
A
1005-6378(2015)05-0103-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16
——兼论与证券公开发行行为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