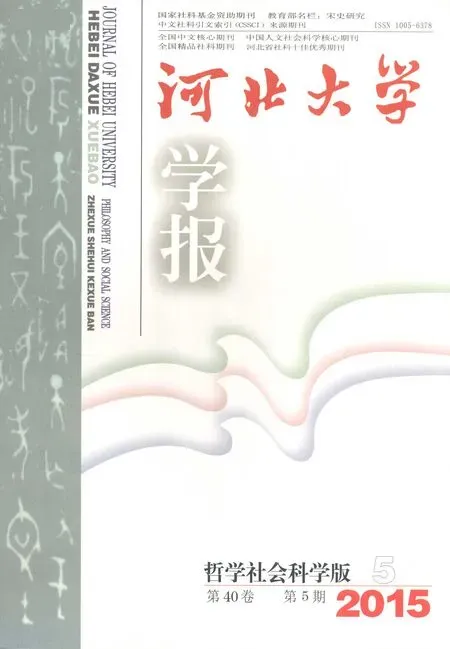略论中国社会想象的基本特征
谭诚训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略论中国社会想象的基本特征
谭诚训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通过与西方社会想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社会想象具有时间想象、人伦想象、两极想象等基本特征。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解决任何社会发展问题,除了源于世界的先进思想,还要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固有的社会想象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视角与参考框架。
社会想象;时间想象;人伦想象;两极想象;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想象是社会主体超越现实存在的集体性构想,它包括神话想象、宗教想象、历史性想象、思想性想象和共同体想象等多种想象形态。社会想象决定社会意志与社会行动,社会想象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生长源泉,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在传统社会中,由伦理、宗教与民族等因素产生的社会想象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一直处于自在状态。在现代国家,社会想象控制社会与影响历史的自为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进行社会设计与社会规划的社会想象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具有科学与理性特征的社会想象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性与建设性作用愈来愈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中国社会固有社会想象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视角与参考框架。
一、中国社会想象的基本特征
(一)时间想象
在空间想象与时间想象两个想象维度之间,中国人更倾向于时间想象。时间想象是想象主体超越此时存在的构想,空间想象则是想象主体超越此地存在的构想。西方人的社会想象更多的是空间想象,最神圣的存在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他们把这个最高存在想象为上帝。中国人的社会想象更多的是时间想象,中国人在对时间万古长存的无限想象中产生了时间的神圣性,时间想象既是追根溯源的想象,又是绵延不绝的想象,最神圣的存在是时间最为久远的存在。时间想象是向着前后两个方向延展的,向前延展的时间想象就是祖先,是列祖列宗;向后延展的时间想象为子孙,是千秋万代。中国人的社会评价就属于时间想象,要么名垂千古,要么遗臭万年。西方人的社会评价则更多地属于空间想象,不是升入天堂就是堕入地狱。中西方对时间想象与空间想象这种选择性差异,应该是由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决定的,那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中,人类的想象思维只能允许在一个维度上建立无限性想象,而这种无限性想象往往被视为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状态。这种对无限性的向往是人类超越必然王国、追求自由王国的理想维度,另一个维度则是人类置身必然王国可以而且必须把握的现实维度,这是一个有限性维度。正是在必然王国有限的现实维度之外还存在体现自由意志的理想维度,还存在对自由王国的无限向往,才使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完全受必然规律支配的其他动物。中国人对时间进行千秋万代的无限想象,时间想象因此获得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与理想设置,空间想象作为我们可以把握的现实部分就相应地被压缩为有限的空间整体。不管是天人合一观念、大一统观念还是整体主义与系统性思维,都是一种空间想象有限化与整体化的结果。对时间想象那种“愚公移山”式的超凡的信念使中国人在空间想象方面相对显得薄弱与简单,不尊重空间的实体性,对空间的规模、结构与细节都不是特别在意。西方文化是在空间维度上建立无限想象的,上帝作为一种绝对存在就是空间想象无限化的产物。在空间维度上既然建立起无限想象,那么在时间维度上建立的想象就相应地作为有限的整体受到轻视与忽略。西方人把时间想象为有始有终的有限的、整体化存在,他们关于时间的想象就自然产生“创世论”和“末世论”,有限的时间整体不过是无限空间的一个段落而已。在方法论意义上,西方人更多通过空间想象而中国人更多通过时间想象的方式认识与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从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到20世纪末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俄罗斯人都是通过突变式的空间想象进行革命与改革的设计与实践,而中国的革命与改革事业则都是在渐进式的时间想象中完成的。
(二)人伦想象
从想象对象比较,中国的社会想象更多地属于面向族群存在的人伦想象,“伦理本位最能表示中国社会的特征。”[1]西方的社会想象则更多地属于面向个体存在的人性想象。在西方人看来,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共同体,需要上帝这样绝对超越并统制一切个体之上的最高存在。所以在古代那种社会功能比较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就是通过上帝这样的绝对观念与意志来实现对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和对人性多样性的规范。中国在社会管理中就不需要那种高于一切的上帝来产生全社会的服从与规制,而是把家庭的管理模式放大到所有社会层级,也就是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小家到国家再到天下的放大过程。这种由小到大的演化是一种人伦想象不断扩展的过程,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就是在这种想象与演化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家国相分的文明方式相对立,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路径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2]以家庭为起点与核心的人伦想象也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产生巨大凝聚力的想象源泉与精神能量。如果说西方的人性想象的最高形式是基督教式的泛爱想象,那么中国人伦想象的最高形式则是大同社会的泛亲想象。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一种“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大家庭社会想象。在中国,大家庭想象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父子结构,其次才是兄弟结构。在中国的仁义体系中,父子想象崇尚仁,兄弟想象崇尚义,我们是以仁为主,以义为次。而处理兄弟关系的正义原则却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最高追求。
在中国,不管是古代的君臣关系还是现代的国民关系都被想象为父子关系。作为父权社会,古代世界的社会想象普遍存在一种父子想象,而父子想象又可以分为西方宗教式的天父想象与中国伦理式的人父想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共同体想象更多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父子结构,古希腊的社会共同体想象则更多的是缺少父道、崇尚霸道的实力主义的兄弟结构。西方进入基督教统治之后,其社会共同体想象就是由古希腊的兄弟想象与基督教的父子想象构成的,俗权社会是兄弟想象,神权社会是父子想象。西方缺少世俗社会的人父想象,正如中国缺少宗教社会的天父想象一样。当西方结束神权统治、天父想象失去神圣地位之后,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具有平等与民主特质的兄弟想象就取代天父想象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想象。而中国则是在几千年父子想象的历史与文化中不断巩固人世间的父道统治,这种父道在国家层面来说就是王道。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看起来似乎是由父子结构与兄弟结构交替构成的,但在文化上中国的父子结构一直是全社会的主流想象。兄弟结构社会在中国人眼里是四分五裂的霸道世界,而父子结构社会则是统一和谐的王道世界。争雄称霸的兄弟结构社会对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是分裂与战争,这种对兄弟结构社会的历史认同可能就是中国人拒绝西方式民主的心理根源。中国社会人文型父子想象也可能将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成为中国民主道路的文化规定。
(三)两极想象
两极想象与单极想象是中国与西方想象模式存在的差异。中国人关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想象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体两极的想象模式。在这种想象模式中,任何事物都被认为是由阴与阳这样两极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满整体。钱穆说:“中国人所讲的‘道’,正是在此一阴一阳中之全体活动。”[3]这种关于世界的两极想象源于中国古老的《易经》。《易经》对万事万物进行了阴阳两极的基本分析,这构成后来中国人对一切问题最基本的想象方式与思维方式。西方人对事物的想象则相反,在他们的想象中,任何物体都应该是由一种单极因素或者说绝对因素构成的。中国人把一切事物都想象为阴阳两极的一体存在,从人体到宇宙、从无限小到无限大概莫能外。对自体、他体乃至全体的这种一元化想象,构成中国人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统观念,也使中国人在人格上处于自体内部阴阳俱备的完整状态,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处于神与人、超我与本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状态。西方人的一体想象不是两极想象而是单极想象,一体要么是善极,要么是恶极,一体总是为单极想象。中国人可以把天与人这样的两极因素视为天人合一的一体关系,西方人眼中神与人的关系则是绝对不同的两体关系。对人类自体的单极想象是恶,对上帝作为他体的单极想象是善,善与恶这样的两极因素分别是由上帝与人两体担负的。康德对上帝与人类的两体认识就是这样的:“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4]两体化的二元思维必然导致斗争观念与征服意志,善与恶的对立、斗争及其胜负结局因此就成为西方一切想象的不懈主题,一定要有一个孰是孰非、孰胜孰败的结局也就成为西方单极想象无法摆脱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模式,这与热衷于大团圆想象的中国文化完全相反。但是我们同时还应看到,单极想象容易产生终极想象与本质想象,西方的科学是在对自然本质的终极想象中产生的,宗教则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想象中产生的。费尔巴哈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5]所以,西方的单极想象会更多地导致本质想象,而中国的两极想象则会更多地产生关系想象。我们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想象中产生了儒家思想,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想象中产生了道家思想。
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想象思考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解决任何社会发展问题除了源于世界的先进思想,还要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社会想象基本特征的时间想象、人伦想象与两极想象已经构成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一)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至今仍颇具影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产生过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可为什么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如果从社会想象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大都被归笼到中国传统的社会想象体系中,它们的社会功能也基本上是在这种社会想象体系的规制下发生作用。现代社会想象特征基本上也是西方那种空间想象、人性想象与单极想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并由西方主导的原因。而中国传统社会想象特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总体上是一种背离关系。科学发现是在单极想象与本质想象的不懈探究中产生的,中国那种过多的两极想象与关系想象就可能造成对科学探究的羁绊与限制。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技术的发展明显优于科学的发现。技术发展的精神动力往往来自某种功利性关系想象,科学发现则需要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本质想象。我们应该在制度上与文化上鼓励科技工作者加强为科学而献身的纯科学的本质想象。这样我们才能在对世界本质的探究中产生更多在基础领域推动世界进步的科学发现。
(二)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中属于时间想象范畴的始端崇拜现象。我们古代教育更多地面向时间的始端,缺少空间意义的教育,这使中国教育一直成为盘绕文化始端的衍生品。在目前应试考试的教育体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教育那种对知识始端的崇拜、承袭与衍生的传统,我们的教育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知识始端衍生品的附属地位。这种面向已知领域而不是面向未知领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传统自然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我们的教育不仅要面向已知领域,也要更多地面向未知领域,不仅要有时间想象,还要有更多的空间想象,这样才能培养出既功底厚实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
(三)老幼优先的福利制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亡》)是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的完美理想,作为人生时间序列的前后两端,老人与幼儿一直处于我们民族时间想象的优先地位。根据中华民族这种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考虑实行社会福利的老幼优先制度。福利制度属于社会的二次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贡献大小进行空间性的差异化分配,并在对社会贡献的激励机制中不断扩大社会的中间阶层规模。而在二次分配领域则可以根据年龄的差异实行老幼优先的福利制度,也就是以时间序列为坐标,形成老人与幼儿享受较高社会福利,而青壮年实行相对较低社会福利的年龄差异化福利结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完全均等化的无差别福利制度,既会形成社会过重的福利负担,又会不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与保持,甚至可能会使社会丧失生机与活力。这样,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橄榄型结构,在二次分配领域形成哑铃型结构,两种分配结构就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互补型社会分配格局。
(四)大家庭想象与协商民主
“以天下为一家”的大家庭体系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要普遍地趋同家庭关系,或者说都必须纳入到所有社会成员共认的大家庭体系中。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寻求变革的历史道路。冯友兰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就是“大同”社会的概括。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礼运》的这一段话很受推崇。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农民起义的革命家洪秀全引它,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引它。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引它。孙中山在各处的题词,常写“天下为公”四个字[6]。中国的社会共同体想象一直是一种大家庭想象,社会管理也根据家庭的结构与价值来进行,“以孝治天下”就是把家庭的孝道放大为国家的王道。我们民族的一切社会想象或多或少都与这种大家庭想象有关。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而且把协商民主正式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在统一而非对立的前提下进行利益协商而不是利益对决就属于一种大家庭想象。
(五)一体想象与全球命运共同体
关于全球一体化问题,赵汀阳有一个说法:“天下体系”体现出只有“地方观念”的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政治世界观,中国政治哲学首先是试图创造一个政治世界观,也就是“天下体系”理论[7]。中国人善于进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一体想象。在中国人一体两极的社会想象中,注重自体内部的两极关系与两极平衡一直是我们认识与处理任何问题的固有方式。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新的全球化概念,这意味着中国人把全球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大自体观念正在形成。在这样一种观念中,我们应该强化我们善于处理体内关系的优势与传统,把他体关系变为自体关系、把外部关系变为内部关系,由小自体格局变为大自体格局,变国家自体为世界自体。只有在这样一种自体化与内部化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我们才会以我们古老的一体两极的想象方式与思维方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西方垄断资本在无限扩张的单极想象、人性想象与空间想象中,推动着全世界实现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但是西方目前却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他们渴望占有全世界的资本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他们缺少兼容性的文化却无法承受全球一体化的局面。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从荷兰殖民主义到美国霸权主义,一直是在世界性的兄弟结构中,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竞争与征服,以天下无敌的实力获得雄霸天下的地位。西方这种两体想象与外部关系意识只能使他们以实力称雄世界,而不可能达至把世界视为自体的文化容量。可以说,“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体现出我们文化传统中特有的天下一体的世界政治观念,中国古老的“以天下为一家”的天下体系在当今世界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全球大家庭体系。应该说具有天下胸怀与一体想象传统的中华民族,更具备引领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容量与文化资格。
[1]翟学位.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8.
[2]陶思炎.东方文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205.
[3]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2-143.
[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1.
[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0.
[6]谢遐龄.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96.
[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12.
【责任编辑 侯翠环】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Imagination
TAN Cheng-x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social imagination, we find that, the China social imagination has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ime imagination, human relations imagination, and two poles imagin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ells us that to solve any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is not only from the advanced ideas of the world, but also from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a.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are an important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reference fram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ocial imagination; time imagination; human relations imagination; two poles imagin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
2015-03-20
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规划研究项目《媒介形态社会想象与社会倾向互动模式研究》(11BXWJ01) 作者简介:谭诚训(1965-),男,山东烟台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想象、媒介文化。
B018
A
1005-6378(2015)05-0129-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