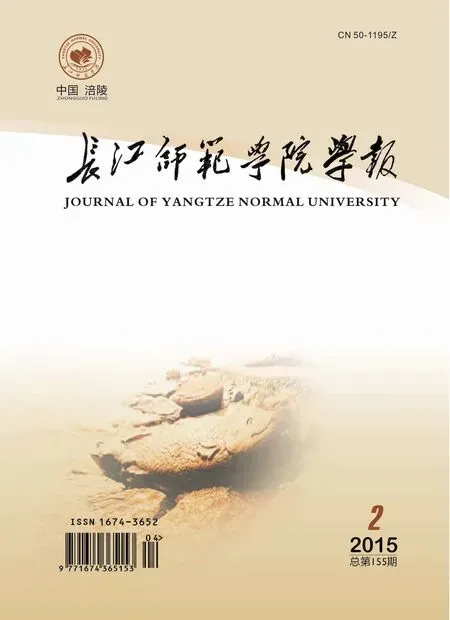文学如何“虚无”历史?
文学如何“虚无”历史?
魏巍,马玥玥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笔谈,就当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文学评论》在2014年第2期再次发起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的笔谈,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于当前的某些文学创作现象进行剖析,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无异于一个伪命题,文学虽然与历史相关,但无论如何,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而历史也不是文学。
[关键词]文学;历史;文学“虚无”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2-0090-04
[收稿日期]2014-12-15
[作者简介]魏巍,男(苗族),重庆酉阳人。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视野下的沈从文、老舍比较研究”(13YJC751061)。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笔谈,就当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文学评论》在2014年第2期再次发起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的笔谈,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并不是因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日报》“开栏的话”与学术界之间话语的错位问题。
在“开栏的话”中,主持人这样写道:“文艺创作虽然活跃,当代文学主体理论建设却严重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认识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滋生蔓延,对于文学创作和受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1]显然,开设栏目所要讨论的初衷是文学批评界的问题,可是,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却都把矛头对准了文学创作,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价值的错位。
张江认为,“文学与历史是分不开的。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这不仅适用于历史题材创作,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2]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重申,在《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中,他强调说,“任何进入载体和介质的文学作品,也都在书写历史,文学与历史互文互证。”[3]如果说论者所针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穿越剧、宫廷剧、抗日神剧等文化现象,这种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并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观点推而广之兼及文学创作,则明显超出了文章所能把握的理论范围。在张江所言中,文学与历史具有某种同构作用,我们不否认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这两者间的关系并没有到共存亡的程度。我们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会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学创作都与历史相重合。除非能够证明白流苏这样的女人与范柳原这样的男人结婚,必须要以一座城池的陷落作为代价(张爱玲:《倾城之恋》)。那么,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界线?在这样的追问下似乎就没有论者所强调的那么严重了。
事实上,文学不会“介入”历史——如果说“介入”是指干预的话——历史终究已经成为过去,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无论文学如何“介入”,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真相。论者并非不清楚这一层,他们所担心的,是文学通过“改造”历史进而“介入”现实。“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4]。矛盾的是,论者旋即又改变了这样的主张,认为“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5]。不
管论者强调多少次文学“虚无”历史,这种理论的“紧张”都多少让人莫名其妙。
文学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达,或明或隐地阐述了作者的立场。正如王尧所言,“毫无疑问,文学在处理‘历史’和‘事件’时从来都有其意识形态性。”[6]这样的文学理论相信早已为人熟知,伊格尔顿早就说过,“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7]这一清楚明了的文学理论常识,不仅是外国人的认识,也是中国文学的教材接受的常识,张江怎么能够说文学在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上与现实没有一点关系呢?
接下来的表述,就更让人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飘摇无根的浮萍。”[8]张江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如果对历史进行肆意篡改的话,真实就会被永远遮蔽。但是,这样的推断是建立在文学与历史同构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把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当作历史书籍来对待,我们才能建构起文学与民族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把文学等同于历史显然是理论上的谬误。文学可以虚构历史,但是历史本身却要求真实。文学的虚构是对想象的再现,而历史则是对事实的再现。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天然具有虚构的特权。虚构远不是一种立足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创作方法,它还意味着对现实规约的回避,同时也意味着对规约力量的某种反抗。文学可以作为为宣传机构服务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它也可以反过来具有某种颠覆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虚构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途径。
文学只是弱者的武器,是弱者最后的表达,而强者自有历史为他们树碑立传。正如鲁迅所言,“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8]。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以虚构的笔法,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想法。于是文学可以“纪实”,可以用还原历史的笔法来重写过去。但是,就算如此,文学也没有完全历史化的义务,至少没有承载与历史同构的任务。历史故事的内容要求真实可信,要求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非想象性的建构。历史的这种本质要求划分了它与文学之间的差别。同时,进入历史,将人物与事件历史化就意味着他们本身的超越时代性,或推动或阻碍了时代的发展。从这方面来说,小人物是根本没有进入历史的权利的。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话题,我们常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但是,翻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谁能够在里面找出他的主体地位?如果他们真的创造了历史,那么,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缺席又意味着什么?
历史不会关心云普叔(叶紫:《丰收》)一家是否有饭吃的问题,也不会关心许三观为何卖血(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当然,更不会关心强拆与房价等问题,这些问题除能够被新闻短暂性关注之外,最适合让他们进入“历史”的或许也只有文学。因此,从某方面来说,正是文学弥补了历史的这一缺憾,被历史忽略、遗忘的那些“历史的主体”只有在文学中才得以重现。
但是,历史上的农民是否都像云普叔一样吃不上饭?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是湖南人的沈从文在写到家乡的乡民的时候,至少在他的小说中,是从来不担心他们没有饭吃的,湘西人民在“边城”中活得有滋有味,那种重义轻利、纯洁朴实、乐善好施的民情民风,至今仍让诸多游客对“湘西”流连忘返。那么,在叶紫与沈从文之间,谁的书写才真正符合历史呢?如果按照论者们的“历史”逻辑,这种两极化书写至少表明有一个作家是会受到“历史”审判的。同样的现象几乎出现在所有作家身上。当我们的研究者反复强调老舍没有直接书写满族生活,是因为限于其时的政治环境,害怕被拉出去重打五十大板的时候,老舍却在《正红旗》中书写着满族之于汉族和回族人的心理优势。那么,这中间究竟是研究者对历史的过度阐释?还是因为老舍对于历史的“虚无”?
参与“虚无历史”话题的研究者都认为,文学负担着历史的功能。至少,它有辅助我们了解,认识历史的功能。“脱离‘文学’去谈历史,也只是枯燥无味,甚至会被所谓的历史来愚弄。”[9]问题是,文学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准确的去把握历史,文学可以具有辅助读者了解,认识历史的功能,但绝
不仅仅只具有这一功能:文学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仆从,它所要解答的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当前读者的审美与精神需要问题。
事实上,在读完有关“虚无”历史的文章之后,我们也很难理解,文学是如何“虚无”历史的?陈众议把“虚无”论概括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艺术’表征,简而言之,一谓‘戏说’,二谓‘割裂’,三谓‘颠覆’。”[10]这三点只能算作是文学创作的一般方法,它也并非为某一派别所独有。而张江等论者的论点则更让人如坠五里云雾,“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什么是历史真实,它与艺术真实是什么关系,也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真实;还有人认为,文学需要虚构,于是就可以无所顾忌,率性而为,用细节代替历史。这都是错误的。”党圣元则补充说,“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是指合规律性的本质真实,而不单单指事件真实或者细节真实。这是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事件虽然确有发生,但是,它代表不了历史的本质,有时候甚至与历史主流相悖逆。”简而言之,他们所要求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最终要追求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11]这里重要的已经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而是要“合规律性的本质真实”。在这种以一种本质取代另一种本质的论述中,论者们巧妙的以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虚构”理论取代了文学上的“虚构”理论。这种“合规律性的本质真实”论把历史理解为某种线性发展的阶段,把历史理解为某种必然,一切事情在发生之前似乎就已经由上天注定,换句话说,命当如此。这种观念显然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发展的玄机,只要顺应这种潮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按照既定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样,文学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也只能书写这种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忽略这期间发生的支流。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每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何况,主流也是众多的支流汇合而成的。对支流的漠视,多少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原貌的认识。
历史可以只顾及主流,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已经发生之后的故事总结,但是,文学是否应该也如此?则又另当别论。文学在书写历史事件的时候,它面对的不仅是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必须面向将来。历史当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诚然不假,但是这种“不假”也只是说历史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就“事实”而言的,至于历史的细节以及对历史的价值判断,这本身就是任人打扮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化的统一认识。同时,还应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写谁的历史?其二是谁在写历史?有没有被拔高了的历史?有没有被埋没了的历史?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用福柯的话来说,“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反过来,他从谁那里接受如果不是真理的保证,至少也是对真理的推测呢?这些个体享有——只有他们——经法律确定或被自发接受的讲同样话语的合乎规定的传统权利,他们的地位如何?”[12]没有人追问历史,却总有人追问文学。在责备“虚无”历史的文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疏忽忘记另外一种追问: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历史事件是怎样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中去的?它们为何引起了作者的注意?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这不是质疑历史,而是质疑那种认为历史都是实有其事,或者就算历史上没有的事件,只要“符合历史规律”,也可以创造出来的观念。因为正是这种观念,滋生了这样的想法:文学也应该如历史一样,以纪实的手法去实录其事,而历史也可以不拘小节,就算细节失真,也不影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谬误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把这条标准衡量文学,那么,一切童话故事,一切武侠小说都没有了存在的根基。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那些穿越时空、往返古今的表现方式,就跟童话故事中那些骑着扫把的巫婆一样显得荒谬绝伦。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宽容童话的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包容当前的某些文学创作倾向呢?实在来说,这只不过是文学的一种创作方法罢了。
有论者认为,以人性论来重塑历史人物,造成了对历史的颠覆。这样的论点似乎又让我想起了沈从文,以及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关于“人性论“的论争,沈从文的小说不正是对湘西优美人性的发掘吗?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文学固然有阶级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既然我们书写的是活生生的人,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着某些普遍的“人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因此,不管是卖国贼还是人民英雄,或
多或少都有着在历史教科书上不为人知的一面,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是否突出了人性,而在于我们是否尊重了历史的结局。至于其是非功过,本来就是留待后人评说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对于“人性人情”的书写呢?又何必去担心“如果用‘文学’的笔法,以人性人情味主纲去书写历史的话,那将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规律和本质的探寻,是对本质真的历史的歪曲乃至颠覆。”[13]
历史是事实判断,而文学是价值判断。两者具有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印证了论者们的担心,但是,这种担心首先需要建立在读者们都是苏珊·格巴所谓的“空白之页”的理论之上的。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读者,也不是如论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可以任人涂抹的“空白之页”。
长期以来,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在国家贫弱的时候,它是救民于水火的工具,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于人心、人格等一切,都指望着小说去救命;在战争期间,它是匕首投枪,是文艺上的军队;在经济社会大潮之下,它是挽救道德衰亡的救生衣;而今天,它又成了拯救历史知识的稻草。只要评论家们愿意,或许有一天,文学还会变成抵抗雾霾的防毒面具,甚至变成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谁知道呢?前些年,我们刚刚讨论完文学的生死问题,认为文学已经死了的人大有人在,似乎它已经穷途末路到了不值一文的地步,可转眼之间,文学又被赋予了如此神圣的“历史”义务。它似乎什么都是,就像万金油,但实在的说,它又什么都不是,就像一块狗皮膏药,贴完一天两天就会被撕下来随意扔掉。
在我看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讨论都是一个伪命题,犹如隔靴搔痒。文学代替不了历史,而历史也代替不了文学,文学仅仅只是文学,而历史也仅仅只是历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没有必要一看到涉及历史的文学就拿去与历史相比照,这不是阅读文学的做法,更不是文学批评的做法。文学批评要做的是,在这种差异性中去洞察作者的创作心理,以及它带给读者怎样的审美感受?至于那些想要了解历史的读者,还是请他们自己去读《史记》吧!
参考文献:
[1][2][10][11]张江,等.文学不能“虚无”历史[N].人民日报,2014-01-17(24).
[3][4][5]张江.文学不能“虚无”历史[J].文学评论,2014(2).
[6]王尧.当代文学的“历史”沉浮[J].文学评论,2014(2).
[7]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8]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6.
[9][13]商金林.文学的边界和本质[J].文学评论,2014(2).
[12]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54.
[14]魏巍,马玥玥.少数民族视野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沈从文与老舍为中心[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
[责任编辑:黄志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