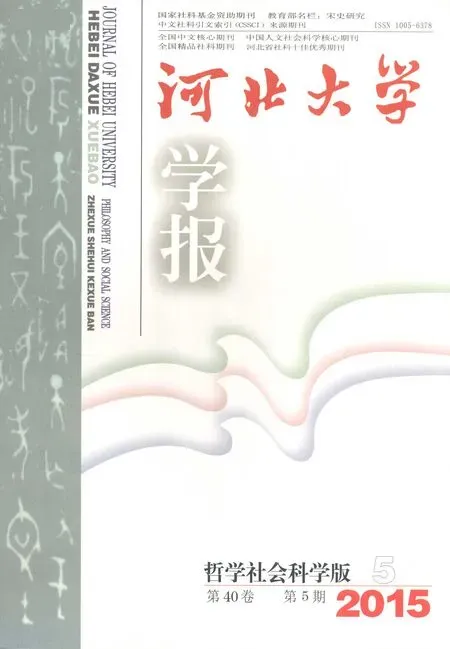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词中语言偏离的认知过程分析
许月华
(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中国古典诗词中语言偏离的认知过程分析
许月华
(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在诗歌这种话语方式中,诗人常常借助于语言偏离来实现表情达意的语用效果。从诗歌语言的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古诗中偏离手段的运用,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诗人选择偏离的心理过程。分析表明偏离的使用可以凸显诗歌的中心内容,形象并贴切地映射诗人的内心情感。
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偏离;情感;认知
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发话人为了某种交际意图,有意识地背离普遍的语法规则或语用准则的语言使用现象,被称为语言的偏离。诗歌即是一种偏离。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作者主观志趣和个性风格的文学体裁,诗歌对语言偏离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孙丙堂系统分析了英语抒情诗中各种偏离手段的运用,并指出偏离手段可以凸显诗歌的中心内容,映射诗人的内心情感[1]。于建华认为偏离是诗人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并系统分析了英诗语言的偏离手段及其审美效果[2]。对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为对偏离的效果和手段的分析,罕有学者从认知的角度系统研究诗歌语言偏离的动因,将古诗中的偏离和诗人选择偏离的认知过程结合分析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借鉴白红爱的研究成果[3],分析读者理解偏离的认知过程,进而得出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选择偏离的意图和认知过程,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语言偏离的认知理据和诗人的内心情感。
一、语言偏离的运用
诗人为了将内心的情感和思想得以凸显和丰富,会创造性地使用人们熟知的语言单位,进而打破读者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对于常规范型的期待。这种创造性的语言被称为语言的偏离。
文学作品的结构模式主要包括语音语调层,意义建构层,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和思想情感层五个层级。语音语调与意义建构属于语言层面,语言的常规(norm)与变异(deviation)的对立与统一产生语言的张力。同时,语言是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和思想情感层的物质载体,这三层也属于偏离研究的范围。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往往将两种或几种类型的偏离交汇融合在一起,达到传情达意的语用效果。
(一)语音语调层的偏离
音乐性是诗歌文体的首要特征,同时也是诗歌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较常见的“语音偏离”是“转韵”手法的运用。如谢灵运的田居诗《田南树园激流植楥》,全诗押“东”韵,而“江”“窗”二字属“江”韵,本不协调。在这里,“江”变音读成“工”,“窗”变音读作“充”与“东”韵相协调。诗里描写了优美的田园环境,景物描写很精致,层次感极强,有些动词用得恰到好处,见出了作者的情致,加上诗人对“转韵”手法的运用,更突显了作者的闲适心情。
(二)意义建构层的偏离
意义建构层的偏离首先是词汇偏离(lexical deviation),即偏离或者违背词汇常规的用法,如改变词汇的词类。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形容词用作动词,作吹绿的意思,形象的表现了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突显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句法偏离(syntactic deviation)指在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方面偏离或违背语言常规,如“倒置”(inversion)就属于句法偏离的一种。诗人不按正常的顺序排列句子成分,既是为了突出某一层意思,也有适合韵律节奏的考虑。
(三)修辞格层的偏离
诗歌情感能得以生动地体现,主要借助隐喻来实现。隐喻是诗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也是很重要的偏离手段。将隐喻用得出神入化的代表作是李清照的《醉花阴》。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其中“人比黄花瘦”堪称绝句。以黄花来比喻人因相思而憔悴,衬托出“莫道不消魂”的深意。以花木之“瘦”比喻人之瘦,表达了作者的忧郁和悲伤的思念之情。一个“瘦”字,在整篇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愁”字推向了最高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
(四)意象意境层的偏离
意象意境层是修辞格层所指向的目标,也是文学作品结构中最关键的层次,是文学作品之为文学的本质所在[4]。周密的《献仙音·吊雪香亭梅》中的抽象意象“飘寒”和“吹冻”中的形容词“寒”和“冻”被名物化,并用作动词的宾语。不说天飘寒雪,而说是雪“飘寒”;不说冻气入云,而说云在“吹冻”。这即突出“寒”与“冻”,又显得较为活泼。这样的偏离与张力,很好地表现出作者对南宋亡国的哀伤、悲愤之情。
(五)思想情感层的偏离
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上阕描述了诗人少年时涉世未深,乐观自信,却故作老成,勉强说些“忧愁”之类的话,下阕描述了诗人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渐深,充满报国热情。他力主抗战,收复失地,却不得赏识,屡遭排斥,满腹愁苦却无处倾诉,只得故作闲适洒脱地说秋天天气变凉爽了。少年时看似忧愁实则欢愉与而今的貌似闲适实则愁苦,诗人将这种矛盾对立的心情统一起来,表现了他饱经忧患,对国事那种日非自叹无能为力,那种深沉而又矛盾的思想情感,让人为之动容。
二、语言偏离的认知分析
偏离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使用手段,其目的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产生突出的效果,被突出的部分被称为“前景”(foregrounding),与“背景”(backgrounding)相对。读者在欣赏一首诗时,最注意其不同寻常的部分,正常的语言如同“背景”,偏离的语言正如被置于前景的“突出”部分,吸引读者去揣摩其内涵,进而体会其蕴藏的思想与情感。人类的情感和认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认知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情感脱离。诗人进行诗歌创作表情达意的认知基础可以通过接受心理学和图式理论等相关理论得以论证。
韦里克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SWOT方法,调查并列举企业内外部各方面的因素,形成矩阵,从而分析企业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该方法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规划、竞争环境分析等,电力设计企业参与PPP项目需要考虑众多内外部因素,适合采用SWOT方法进行全面系统分析[6]。通过分析我国电力设计企业特点和现状,搜集PPP项目政策、法规,研究PPP项目案例,总结电力设计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经验,得出了电力设计企业参与PPP项目的SWOT模型,如表3所示。
(一)语言偏离的认知基础
在姚斯的接受理论中,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5]。任何一部处于独立状态的文学作品,都是借助于作者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才获得关联和统一。“期待视野”包括两个层面,既指作家层面的预期期待,又包含读者层面的审美期待。要让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接受,诗人就必定要考虑读者的期待因素。所以诗歌的偏离是相对于读者或读者群对常规范型的期待而产生的,是诗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创造行为,而不是绝对的。当读者判断出语言单位偏离了它的常规范型时,人们对其产生的期待就会被打破。
语言中各个语言单位是相互关联的,小的单位是更高一层单位的组成部分。一旦在大脑中固化,这些语言单位就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图式的形式储存在大脑。图式作为某一事物具体构成的框架,是一种主动的信息加工装置,具有预期的作用,为人们理解某种事物提供积极的准备状态。人们对某事物的发展过程、环节和语言材料将要涉及的内容产生一个预期。在诗歌赏析的过程中,这种预期和期待跟阅读几乎是同步的。由于文学语言单线性的特点,作家创作时无法将整体创作意象和盘托出,而只能继时性地线性展开,整体意象被分解。一首诗作为整体成为一个图式储存在诗人的大脑里,读者在欣赏诗歌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地把单个意象整合成新的整体意象,在理解了整首诗的基础上才能读懂诗人的内心情感。本文以诗歌这种文体为例,来证明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是经过认知分析后才将个人心理情感以偏离常规的范式外在化。
(二)偏离——打破人们的期待
Cook将语篇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使已有图式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语篇(schema reinforcing);二是保持已有图式的现状的语篇(schema preserving);三是破坏并重组已有图式的语篇(schema refreshing)[6]。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第三类。语言偏离主要涉及有关世界的图式和有关语言的图式的重组,Cook将语类结构的图式从语言结构的图式中分离出来。语言的偏离只有在语言结构的图式被破坏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一定的语用效果。
三、语言偏离的认知过程
在语篇信息论中,交际概率与信息度成反比:一个言语生发物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可预示性愈小,其信息度便愈高;反之亦然。言语生发物的可预示性取决于交际预期。交际预期可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三种预期是基于语篇类型的预期。语篇类型能够反映语篇世界、知识构型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典型特征,因此对言语发生物具有一定的预期作用[7]。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型具有很高的信息度,读者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需要复杂的认知分析,才能够领会诗人所饱含的深情。
阅读诗歌时,读者首先要判断出语言中的偏离,也就是在整合新信息时首先要判断该语言是否符合根据原有的图式作出的期待。Graesser的SP+T(the Schema Pointer plus tag model)模式有助于人们做出对语言做出判断[8]。该模式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不同的事物和现象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以不同的内容图式表现出来的。每一种图式都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被称为典型特征(Pointer),它与图式的原型结构相一致,能将该事物或现象指向它所属的图式;第二部分被称为附加特征(tag),这部分与图式不相符或无关联。当新信息进入记忆系统表现为对原有图式既有联系又小有区别或对图式的偏离时,读者就可以断定它属于语言偏离。
(二)激活偏离使用的语言单位
语言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可以发生偏离。而语言层面上的任何一个单位一旦在人脑中固化,成为一个图式,即使它的某一部分发生了偏离,其余的组成部分仍可以激活整个常规范式。Harris运用McClelland和Runelhart的互动激活模式,以习语为例来解释偏离常规的词汇激活人脑中完整图式的过程,并将这一激活过程称之为“先锋激活”(priming)[9]。研究显示“先锋词”(prime)作为先出现的词,总能激活紧随其后的与之语义相关的词语。
使先锋激活得以实现的机制包括扩散激活和语义整合,两者通常同时起作用。扩散激活指语言单位是一个互为联系的网络,那些在语言结构上经常同时出现并在语义上相关的语言单位之间具有最强的联系。一个先锋词的出现会顺着这种关系网络扩散开来,从而激活与之相连的目的词[3]。语义整合指的是一个目的词往往很容易被同属于一个语言概念的图式网中的先锋词所激活。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自动地将语言单位的意义与它所出现的上下语境相整合[3]。两种激活机制总是同时在起作用,下面以修辞格层的偏离——隐喻来分析两者是如何共同起作用使读者脑中整个认知单位得以激活的。
以李清照的《醉花阴》为例,全词以“薄雾”“浓云”等意象开头,作为先锋词“薄云”“浓雾”会激活读者大脑中与这一感情基调及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前文呈现的所有意象意境在语义上相互关联,也为最后的“瘦”字奠定了悲凉凄苦的基调。读者要理解词人是用“比瘦”来隐喻自己的忧郁和思念之情,就需要从整个特定的诗境去理解,因为一首诗是一定诗情诗境的整体,每一句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片段。人们总是自动地将语言单位的意义与它所出现的上下语境相整合,这时候语义整合就起到了作用。通过两种机制的相互作用,读者就不难理解词人是通过描述重阳节把酒赏菊,烘托出一种凄凉寂苦的氛围,表达思念丈夫的孤寂心情。
(三)偏离所产生的语义映射
通过认知单位的激活机制可知,一旦语言结构作为整体在大脑中以图式的形式储存下来,它的某一部分发生偏离时,其余的结构仍能激活整个常规范式。此时常规范型成为背景,偏离的部分成为前景,前景被背景突显出来。语义映射将被突显的意义追加到背景意义上,丰富了偏离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映射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创造、传递和理解意义的认知能力,能够在不同的认知领域之间产生。正是这种认知能力使人们可以理解偏离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也使得人类的语言具有了创造性。Fauconnier列举了三种映射[10]。
投射映射是将一认知域的某一部分结构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上[3],隐喻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会使用大量的隐喻。有些映射由于长期使用而固化,这时的投射映射在一定程度上就自动化了。有时投射映射是对语言的创造性的使用,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的,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是暂时的。这种映射使得语言表达式之间建立了新奇的联系。如“人比黄花瘦”这句便属于投射映射。人和黄花属于不同的基本范畴,其间虽有差异,但是作为生命体,存在很多相似性,基于这些相似性产生出这一新奇的隐喻表达式。
两个相关联的认知域(通常这种关联是临时建立的),可能由某一语用功能相互映射为两种事物范畴,被称为语用功能映射[3]。转喻和提喻是语用功能映射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李白《关山月》中的“高楼”运用了转喻。这里的高楼并非真正的高楼,全句并没有出现人物,但读者却读出了主人公是一位住在高楼里的戍客的妻子。这是因为与地点高楼有关联的首先是里面的居住者,这里用地点指代人。边关的明月将戍客的思念带给家乡的亲人,戍边将士这样的日日苦颜思归,高楼中思妇们的叹息日日不息。此处转喻充分衬托出边关将士思归之苦。
当人们用已有的图式来描述语境中的某一新的状况时,图式映射便产生了。图式映射是指用抽象的图式、框架或模型来理解话语,是认知图式的自上而下的投射。图式映射有利于诗词意境的实现,是诗人经常采用的写作手法。以《近试上张水部》为例,诗人曾得到张籍的赏识,而张籍又乐于荐拔后辈,因而诗人在临近考前作这首诗献给他,借以征求意见。在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两次图式映射和一次投射映射。本诗的主题是“询问”,这一图式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CM)由三个“空档”组成,包括询问人,询问内容和被询问人。两次图式映射之间的转换是通过投射映射,即隐喻来完成的(见表1)。

表1 两次图式映射与三个“空档”对应的内容
诗歌中所传达的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情感状态,不可能用普通的、常规的语言表达出来。由于人类具有记忆、范畴化、推理等高级的认知能力,诗人总是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创造性地使用。对语言的偏离使用是在对读者期待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期间诗人经历了复杂的认知过程。首先,诗人利用语义映射将某一认知域的图式进行创造性的运用,突出自身情感;其次,在把握读者期待的基础上,判断出读者对某些认知单位具有激活机制;再次,将选定的意象意境以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诗人将特定的情感状态以偏离的语言表达出来,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1]孙丙堂, 李正栓. 英语抒情诗中“偏离”手段研究[J]. 外语教学, 2009 (2): 70-75.
[2]于建华. 语言偏离的诱惑[J]. 外语研究, 2006 (2): 76-79.
[3]白红爱. 语言创造力: 对语言偏离的认知解析[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95-99.
[4]朱立之.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03.
[5]BAMET SYLVAN. A Short Guide to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M]. Baston: Little Brown, 1975:15.
[6]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9.
[7]陈忠华.知识与语篇理解:话语分析认知科学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33-136.
[8]GRAESSER A C, G H BROWER. Inferences and Text Comprehension [M].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0:28.
[9]HARRZS C L. Psycholinguistics Studies of Entrenchment[M]//KOENIG J. Discourse and Cognition:Bridging the Gap. Stanford: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1998:55-70.
[10]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9-11.
【责任编辑 王雅坤】
An 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Language Devia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XU Yue-hua
(Wenjing College,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In the poetic discourse, language d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veal the poet’s innermost thought and emotion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various deviations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and analyze the mental process of the deviation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interpretation indicates that deviation can foreground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poem and mirror the poet’s mind picturesquely and appropriately.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language deviation; emotions; cognition
2015-06-25
许月华(1984-),女,山东莱西人,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诗词翻译、跨文化交际学。
H109.2
A
1005-6378(2015)05-0092-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