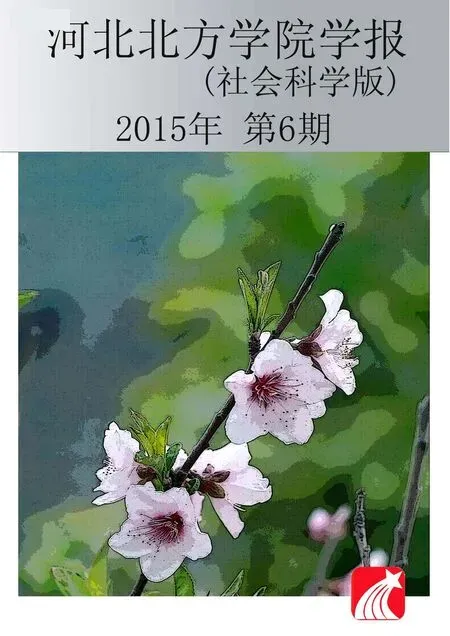网络诗歌发生概述
张 翠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中文与社会系,江苏 邳州 221300)
网络诗歌发生概述
张翠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中文与社会系,江苏 邳州 221300)
摘要:中国网络诗歌的创生可谓20世纪末中国新诗发展路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它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新生事物总是在曲折中蜿蜒前进,网络诗歌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其自身也遭遇诸多困难,暴露出一些弊病。命名问题使其处于不被主流话语认同的尴尬,狂欢化创作方式将其推向制造电子垃圾的窘境,而学院与草根莫衷一是的批评则令其理论薄弱且根基不稳。因而,认同网络诗歌存在价值、引导诗歌创作趋于理性及提升诗歌批评理论水准是网络诗歌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网络诗歌;命名;创作;批评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3.05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3
网络诗歌自产生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20年里,它遭遇了以往任何一种诗歌类型都不曾有过的争议。无论命名与创作,还是评论与批评,网络诗歌都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其先锋性值得探究。
一、命名尴尬
网络诗歌命名尴尬的背后是其急遽膨胀且希求主流话语予以认同的焦虑。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诗歌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一时间边缘化与消亡论充斥整个当代中国诗坛。互联网的普及与依托网络而发展壮大的网络诗歌无疑是中国诗坛的一场及时雨,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根力挽狂澜的救命稻草。因而,寻求正名和渴望认同成为网络写手们的群体性期待。
随着相关研究理论的不断成熟,网络诗歌的概念厘定亦日益明朗化、清晰化及具体化。网络诗人艾若认为:“‘网络诗歌’指首发于各大网络诗歌论坛、诗歌电子网刊上的诗歌作品。”[1]7张立群认为:“网络诗歌的概念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在网络上创作并通过网络发表的、可以获得广泛迅速阅读与交流的网络原创性诗歌作品。”[2]王本朝认为:“网络诗歌,准确地说就是以网络为载体写作、发表和传播的诗歌。”[3]上述3种概念在意义上大同小异,虽没有界定存误之虞,但仍有笼统之嫌。迄今为止,对网络诗歌定义相对规整的当属学者吴思敬在《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一文中所阐述的:“广义的网络诗歌是从传播媒介角度来说的,一切通过网络传播的诗作都叫网络诗歌,它既包括文本诗歌的网络化,即把已写好的诗作张贴在电子布告栏上,也包括直接临屏进行的诗歌书写。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着眼于制作方式,指的是利用电脑的多媒体技术所创作的数字式文本。这种文本使用了网络语言,可以整合文字、图像、声音,兼具声、光、色之美,也被称为超文本诗歌。”[4]当然,此界定也只是相对完整,如利用写诗软件创作的诗歌没有被归纳在内,而此种创作现象又真实存在,不应被忽视。总地来讲,网络诗歌在目前学术界大致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指传统诗歌文本的网络化;第二类是运用网络创作并发表的诗歌;第三类是超文本、多媒体及工具创作诗歌等。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诗歌,以下探讨的内容也限于此。
“新名词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同时也不免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商品。”[5]4网络诗歌作为中国新诗史上一股突飞猛进的潮流,其身份的辩证自然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附加网络媒介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等特点,有学者对网络诗歌命名提出质疑也在意料之中。如著名网络诗人兼评论家桑克即持此论调:“我一向不赞成网络文学这样的提法,也不赞成网络诗歌的提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它和诗歌是平行的概念,那是违背常识的、根本不能成立的事情。不能因为到了互联网上,诗歌就成了另外的东西,标准也跟着变了。诗歌的标准还是诗歌的标准,变化的只是诗歌的形态。如果它是从属于诗歌概念的概念,那么它也是不准确的,因为网络本身是什么呢?它赋予了诗歌以什么样的新标志和新特征呢?如果把它命名为‘网络体诗歌’似乎准确了一些,它至少点出了所谓的网络诗歌只是一种形态的变化,或者说形态上的巨大变化。”[6]桑克的质疑一语道破了网络诗歌命名的根本问题,相对桑克所谓的“网络体诗歌”,“网络诗歌”提法显然笼统与模糊,但同时也是约定俗成和公众默认的。
网络诗歌的命名尴尬是现实存在的,尤其在20世纪末网络诗歌的起步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拒斥有关这种尴尬或焦虑的讨论。“概念的产生既是人的认识伴随现实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结果,而且由于理论体系具有自律性并且在不断地运动,因此概念的历史没有终结,只有过程。任何一个概念的能指都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蕴含固定真理成分的所指。”[7]7由是观之,想对网络诗歌的确切内涵与有效外延作出精准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众说纷纭的网络诗歌命名未必只是纠结于“网络诗歌是什么”的问题,论者们更大程度上是希冀网络诗歌得以聚焦和获取认同,从而使其跻身文学史的序列,并最终完成延续中国百年新诗传统的使命。
二、狂欢化创作图景
自网络诗歌产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网络场域成为全民公用厨房,而网络诗歌写作则成为网络现场一册油腻的菜谱。各人依照自己口味添加各味佐料,有些写手更是毫不吝惜地大放猛料,网络诗歌大餐成为网民们的饕餮盛宴。白话、生活叙事及可有可无的标点,外加数次回车键的随意弹拨,一首作品即可新鲜出炉。匿名行走网络,大家争相模仿写作所谓的诗歌,多数人不追求在诗品上一较高低,却倾向于在粗俗上下工夫,很多时候令仍眷顾古典诗美的写手们颇为落寞。自然,这里讨论的是网络诗歌的总体概况,但也不能完全忽略网络赋予诗歌的强大活力。互联网的应运而生是时代发展的一大标志,是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是福泽现代人的一场及时春雨。因网络的产生,才使得更多人知道和接触诗歌。因而,民间潜在写手们也得以搭乘网络快车而发挥其潜在的诗歌天赋。但辩证来看,网络无疑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予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磨损着一些东西,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网络打碎了20世纪末种种有关诗歌消亡的论说而将诗歌推向大盛,但创作水准偏低的网络写手们披着隐身衣匿名行走于网络,他们只贪图自我发泄和享乐而置诗性与诗意于不顾,网络诗歌的“去诗化”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短板。可以说,“狂欢”是网络诗歌创作现场的高频关键词,也是个具有普适性的网络热词。由此,网络诗歌演变成一种“狂欢化诗学”,一种极富时代、媒介、心理和文化特色的诗学。总之,一定意义上来讲,网络促使诗歌走下神龛、走进大众及走向全民,是当代诗歌不断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当代诗歌修成正果的福佑权杖;另一种意义上来讲,网络的便捷及零门槛又是网络诗歌和弦律动时一道去除不掉的干扰声线。
诗歌创作有自身的规律。因此,创作者们遵循一定的秩序、法则和规约是必要的。网络诗歌场不是垃圾池,任何不负责任的倾倒都是折损人文精神的不良行为。纵观网络诗歌10多年的发展历程,创作者们滥用网络的交互性、匿名性及快捷性等优势的行为一直存在,网络一度成为诗歌历劫的重灾区。如下半身写作、低诗歌写作、垃圾诗写作、口水诗写作、梨花体、羊羔体、咆哮体和乌青体等网络写作范式的流行;又如某些以“先锋”自居的诗人,以诗歌论坛和网站为根据地拉帮结派叫嚣骂人,言辞之无耻下流。可以说,诗的最起码的“底线”已完全失守。对此,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欧阳友权教授这样总结:“由于作者身份虚拟和主体性缺位,写作的责任和良知、作家的使命感和作品的意义链也就无根无依或无足轻重,文学的价值依凭和审美承担成了被遗忘的理念、被抛弃的信念或不合时宜的观念。”[8]诗歌是文学的一个文体分支,网络诗歌也是网络文学的一个文体分支,作此援引完全不存在移花接木的牵强感。
网络是个大竞技场,诗歌写手是渺小而卑微的个体,诗歌帖子成为“电子烟尘”是常事。为了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写手们最拿手的就是震撼性的出场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而现实结果是写手自我满足了,诗性却惨遭虐杀,传统诗人们所坚守的诗意在这里变得面目全非。以垃圾诗派领军人物徐乡愁的《屎的奉献》为例:
屎是米的尸体
尿是水的尸体
屁是屎和尿的气体
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出
屎90公斤
尿2500泡
屁半个立方
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
庄稼一支花
全靠粪当家
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
我奉献屎
徐乡愁创立网络垃圾诗派,其本身具备一定的现实批判色彩,这在他的垃圾诗作品和垃圾诗派宣言中都有所体现,但其把诗歌写在“屎”和“垃圾”上的作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诗歌是语言审美艺术,而这首《屎的奉献》单从字面就让人不忍卒读,着实伤了中国诗歌的精魂,并且令对网络诗歌不甚了解的人们倍感不屑,难怪会有那么多传统诗人、评论家及网民至今仍对网络诗歌嗤之以鼻。徐乡愁的其他代表诗作如《拉屎是一种享受》《我的垃圾人生》《我不得好死》和《人是造粪的机器》等,可谓是满纸荒唐言,与传统诗歌精神大相径庭。诗性表达机制的病变源于个体心理机制的病变。说到底,网络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写作者们过度透支了网络的自由、民主和开放性能;网络诗歌火热的实质是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背后则是诗歌审美走低乃至走偏的危机。企图一改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低沉境况的本意是好的,同年代韩东、伊沙、于坚及桑克等诗人都抱有此种想法。但是,“结果,网络诗写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写作变得不负责任和随心所欲,艺术性创造演变为物质性创造,发表速度和炒作样式也似乎更为重要,每天必‘贴’和一日数‘贴’的所谓‘网络诗人’比比皆是,诗歌‘生产’空前繁荣。当然,受到最直接伤害的只能是诗歌本身”[9]。怀揣诗歌梦的诗人与评论者们无意指责网络时代的诗人与诗歌,但诗人的本身问题不可小觑。诚如青年评论家何同彬所说:“事实上,中国诗歌的问题仍然是主体问题,而不是诗歌本质和展示媒介的问题,简单地说,如今诗与美唾手可得,神灵、道、德俯拾即是,关键是主体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10]网络赋予写手们充分的自由,话语权的回归值得草根写作者、潜在写作者和民间写作者们欢呼雀跃,但滥用自由致使诗歌创作矫枉过正就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了。只见网络不见诗,到处是“诗”却没好诗,“诗在网上”更深层次可以理解为“诗在囧途”。当然,网络诗歌尚处于成长阶段,理应得到呵护,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网络上大量的优秀诗作是时代的希望,如《诗选刊》杂志一贯坚持的选诗标准就是一柄标杆,其对网络诗歌的眷顾与严格把关使人们对网络诗歌刮目相看。
三、众声喧哗的批评
网络诗歌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的步履行进太快,伴随而来的各种矛盾、危机与困境也暴露无遗,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网络场域繁杂混乱,网络诗歌作品也形态各异和千奇百怪,批评现场自然热闹非凡。网络诗歌是中国新诗的当下形态,它承载了中国诗歌复兴的重任,在呼吁网络诗歌创作观照传统与理性的同时,对其批评也要作出高要求,“批评是诗歌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语境的再次展开”[11]54。批评风向的正确性决定了网络诗歌继承大统的可能性。时至今日,网络诗歌的产生尚不足20年,放眼其发展历程,与喧嚣的创作现象相比,对网络诗歌批评的声音相对弱了一些,理论与创作之间出现脱节与断层,不好深究到底是创作前进得太快还是理论跟随得太慢。网络诗歌批评大致分为两种形态,即网络现场批评和学院批评,划分未必合理和清晰,但勉强可以概括一二。
首先,是草根化且相对低层次化的网络现场批评。和网络诗歌创作表现出的诸多矛盾一样,网络批评现场混乱的秩序和嘈杂的声音着实有伤中国诗论的尊严。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现在的不少网络诗歌批评与炒作联系在一起,除奉送一些廉价的桂冠与言不由衷的赞美辞外,看不到批评家的责任与真诚,并且缺乏传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和专业化,而是更多地体现了当下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表现为口无遮拦的随机行为,措辞尖锐,各执一端,既不乏庸俗的吹捧,又充斥着刻薄的恶骂与攻击,相形之下,基于学理的、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太少,使网络的反馈功能大打折扣。”[12]吹捧、谩骂及灌水是诗歌网站与论坛上最常见的批评状态:吹捧者不拘作品好坏,一律鼓掌叫好,老好人的嘴脸无棱无角;谩骂者唯恐天下不乱,寻衅滋事是他们的最爱;灌水者则麻木不仁,只求占座和抢沙发,只想让网络知道他来过。然而,网络批评现场也有理性的声音,其水平也不可谓不高,但这样的声音太少了。网络现场批评的游戏化与责任意识的淡化是网络媒体开放的结果,网民的匿名活动不用担负道德荆条,要么不说,要么乱说,丢别人板砖或被别人丢板砖以及吐槽别人或被别人吐槽都是乐事,群体参与的假面舞会图的就是一次性消费的感官享受。今日来看,网络诗歌发轫时人们所畅想的高效的在线交流与强势的现时交互性似乎并未实现。写作者们为追求点击率而不择手段地趋向诗歌审美的粗俗与污秽;读者为混个脸熟而肆意灌水,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从而使交流变得苍白无力。真正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和诗歌批评应该“不能停留在感受印象阶段,还必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直观上升到理论分析,从具体的文学现象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规律”[13]307。其次,是精英化且相对高层次化的学院批评。“学院批评又称‘学院派批评’或‘学院式批评’,按照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划分,学院批评可视作以大学教授为批评主体的‘职业的批评’。”[14]258学院派批评群体有知识背景或经过正规训练,他们的视野和操守与网络批评群体有很大的不同,网络批评群体擅长随机的、感悟式的及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他们的声音代表个人;而学院派批评群体则擅长长篇大论的理性分析,声音背后是一个个批评家的学术声明与学术良知。因而,他们要时刻保持学者和智者的风范,话语自然要求理性、规矩且有深度。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网络批评现场虽然众声喧哗,浮躁喧闹,但网络批评主体身处现场,观看的是最前沿的诗歌动态。尽管学院派批评以准、稳及深著称,但在狠和快方面恐怕有所欠缺。如今,网络诗歌作品年产量几乎敌得过过去一个朝代的诗歌总量,与网络诗歌有染的网民数量更是不可计量,“面对这样的庞大的文学群体和海量的作品总数,传统的批评家仅阅读的精力与涉猎的能力就难以企及,而如果没有系统与细致的阅读,没有大致与相互的比较,也就谈不上有力与有效的批评”[15],评论家白烨在谈到网络文学批评时作如是说。无独有偶,欧阳友权在《当传统批评家遭遇网络》一文中也谈到:“说传统批评家有面临网络‘失语’的窘境,大抵源于两种情形:一是自踞心态,二是语境隔膜;前者出于某种自矜式批评立场,后者则肇始于数字传媒语境的知识贫困和文化壁垒。”[16]新世纪以来,学院派批评家对网络诗歌理论研究的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杨晓民、杜国清、吴思敬、吕进、蒋登科、张清华、张德明、王珂、王本朝、张立群及杨雨等,其中杨晓民的《网络时代的诗歌》一文被称作是从“理论上揭开了中国大陆网络诗歌甚至是网络文学的序幕”[17]。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张德明的《网络诗歌研究》和2008年出版的杨雨的《网络诗歌论》,此两部著述是目前可见的专门评论网络诗歌的学术读本。
对于网络诗歌而言,网络现场批评和学院批评都各自有其优势与缺陷。如前所述,网络现场批评是自发和偏重“看”的批评行为,学院批评则是职业的与强化“认识”的批评艺术。“认识是针对过去而言,而看是现实的行动!因此,当自发批评面对历史的时候它会感到困惑,当职业批评用于现实作品的时候,它也会感到迷惘。”[18]88-89网络诗歌是现实存在并持续发展且日益趋向成熟的,不管是网络还是学院的批评,都应跟上步伐,尽可能弥合创作与理论之间的断层。网络淡化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综合观察不难发现,网络批评与学院批评也呈现交互融合的态势。年轻女学者苏晓芳便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网络批评狂欢化的语言风格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整体语言风格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专业研究者的批评语言,尽管在形式上不可能完全照搬网络批评的语言方式,但随着网络文学与传统写作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学院批评、传统媒体批评和新型的网络批评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不那么分明了。”[19]159这种融合对于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的网络诗歌批评理论而言无疑会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学院批评放低姿态,网络批评提升素质,两种批评互动交流和取长补短,网络诗歌批评理论羽翼丰满是迟早之事。
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进而寻求新的突破与好的改变。如上所述,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大都不否认网络诗歌的存在,亦不否认其优势与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创作与批评群体也不愿意无视网络诗歌这一诗歌新形式自身存在的弊端,发现问题并探索解决之道才符合唯物辩证法所认定的发展原理的要求,也只有这种敢于面对和纠正错误的发展才是网络诗歌创造、批评及审美走上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说网络诗歌是一座可供挖掘的富矿,那么审美问题就是其中最具挖掘价值的一眼矿井。以理性态度审视网络时代诗歌的真实发展状况,并以相关研究理论归纳概括其审美之维,网络诗歌就离成熟状态更近一步了。网络诗歌是诗歌的最新和当下形态,尽管其已走过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但相对中国古典诗歌几千年的磨砺,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发展过程中,网络诗歌因网络媒介自身的便捷性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遭遇了种种非议与歧视,但网络诗歌是不容抹杀的,大家应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它,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它。正如朱光潜在谈到诗歌趣味培养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须有原创性,都必须时时刻刻地开发新境界,如果让你的趣味囿在一个狭小圈套里,它无机会可创造开发,自然会僵死,会腐化。”[20]353
总而言之,网络诗歌的发展与研究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宽容接受、理性甄别及多样化批评是读者与评论者应持的态度,而尊重传统、合理创新及多元化创作则是网络诗人们应有的姿态。大浪淘沙,多年后趋于定型的网络诗歌也必定会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一脉。
参考文献:
[1]马铃薯兄弟.中国网络诗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2002.
[2]张立群.网络诗歌的大众文化特征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4,(1):75.
[3]王本朝.网络诗歌的文学史意义[J].江汉论坛,2004,(5):106.
[4]吴思敬.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J].河南社会科学,2004,(1):61.
[5][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桑克.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J].诗探索,2001,(1-2):14.
[7]于洋,汤爱丽,李俊.文学网景:网络文学的自由境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的三道坎[J].南方文坛,2009,(3):42.
[9]李佩仑.沉醉与历险:“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1):66.
[10]何同彬.空间生产与网络诗歌的瓶颈[J].当代作家评论,2010,(2):180.
[11]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肖晓英.诗歌精神的自由飞翔——网络诗歌窥探[J].茂名学院学报,2006,(2):18.
[13]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白烨.有限性与可能性——传统批评与网络文学[J].南方文坛,2010,(4):20.
[16]欧阳友权.当传统批评家遭遇网络[J].南方文坛,2010,(4):21.
[17]郎毛,吴元成.杨晓民论[J].诗探索,2001,(3-4):249.
[18][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9]苏晓芳.网络与新世纪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张盛男)
Overview of the Occurrence of Network Poetry
ZHANG C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Society,Yunhe Teachers College,Pizhou,Jiangsu 221300,China)
Abstract:The creation of China’s network poetry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brightest landsca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 new poetry in the 20th cenury and it brings fresh blood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But new things are always zigzagging in progress.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it has also met with lots of difficulties and shown many drawbacks.Naming problem makes it not be acknowledged by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The way of its carnival creation pushes it into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producing elecronic rubbish.The various criticisms from academy and grass-roots make its creation theory weak and unsteady.Therefore,if the netork poetry can have a long term development,it is the only road to idenify with its existence value,guide its creation to be more reasonable and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network poery criticism.
Key words:network poetry;naming;literary creation;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I 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04-05
作者简介:张翠(1986-),女,江苏邳州人,运河高等师范学校中文与社会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收稿日期:2015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