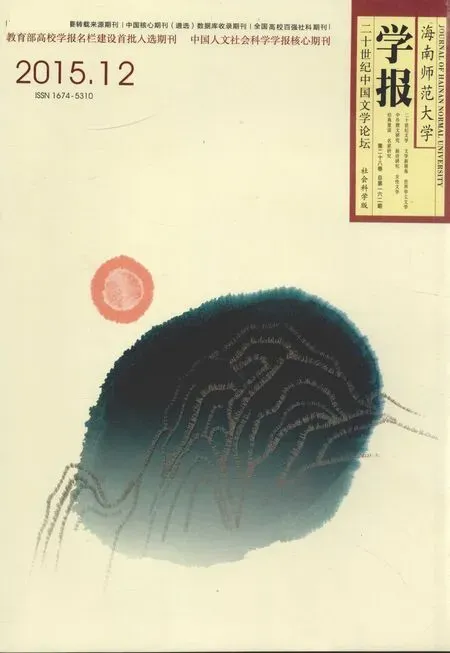当代诗歌细读的可能性
——评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
吴 昊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当代诗歌细读的可能性
——评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
吴 昊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细读”一词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和实践,中国诗歌批评家接受“细读”法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自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诗歌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急速变化的语境中,“细读”法对诗歌阅读而言是否继续有效,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洪子诚先生所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一书中所涉及的关于中国1990年代诗人作品的课堂讨论,有效地证明了当代诗歌细读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多样的细读方法。同时,参与细读的讨论者也意识到细读法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遭到“过度阐释”的质疑,因此他们提出将感悟式批评与诗歌细读相结合,使“细读”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诗歌批评方法。《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一书自出版后便受到诗歌爱好者的好评,使读者感受到诗歌“细读”的魅力所在。
当代诗歌;细读; 《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
“细读”(Close Reading)一词,由英国批评家I·A·瑞恰慈提出,并在燕卜逊、沃伦、布鲁克斯等新批评派评论家的实践中得到阐释。“细读”法强调文本内部的自足性,语言和结构在文本细读法中的地位则非常重要。在英美新批评派的具体实践中,“隐喻”“复义”“张力”“悖论”“反讽”等批评范畴得到了有效的梳理和阐释。
中国诗歌批评家接受“细读”法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所办《现代》杂志为新批评派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初步贡献。在个人成就方面,朱自清、卞之琳、废名、李健吾、袁可嘉、唐湜等诗评家都是“细读”法在中国诗歌研究领域的积极接受者和大力推广者,其中朱自清应是“细读”法在中国最早的接受者和理论阐释者之一。在朱自清的“解诗”实践中,他强调对诗的本体进行微观解析,并重视诗歌语言的功能,认为诗并没有那么神秘,是可以“解”的,应在理解的基础上对诗歌文本展开批评。同时,朱自清解诗时本着“参与的作风”[1]345,以期能够更好地体会创作者的心态,避免主观臆断。废名是把新诗文本解说引入大学课堂的先驱者,[2]而袁可嘉、唐湜这两位“九叶派”诗人的诗论可以视为英美新批评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内化。袁可嘉从“包含的诗”的要求出发,倡导现代诗歌的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综合传统;唐湜则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走钢丝”,以返观深潜的方式把握新诗现代化的精魂。[1]368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更多包含英美新批评派“细读”范例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如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3](赵毅衡本人也著有《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一书),布鲁克斯、沃伦合著《小说鉴赏》[4],布鲁克斯著《精致的瓮》[5]等,这些译著的出现使得“细读”法更为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
据洪子诚先生介绍,将“细读”法与诗歌教学相结合的实践,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曾先后在北大中文系开展过,孙玉石先生的讲授和课堂讨论的成果已结集成书出版,分别为《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洪子诚先生认为,这些在大学课堂上进行的解诗工作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6]5
关于诗歌“懂”与“不懂”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评论界和普通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此问题自新诗诞生后便一直存在,直到今天讨论仍在继续,而“如何解诗”,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推移,诗人的创作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更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诗人辈出,作品数量蔚为可观,其中不乏佳作。读者在阅读这些优秀诗作的过程中,如何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来更新调整自己的诗歌观念及读诗方法,则又回归到“如何解诗”这个问题上。洪子诚先生于2001年在北大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部分研究生组织了“近年诗歌选读”课程,并将课堂讨论内容结束为《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此书呈现出的诗歌“细读”观念可以视为“如何解诗”的答案之一。在洪子诚先生看来,“细读”活动的基本点是借助具体文本的解析,试图探索现代诗有异于传统诗歌的艺术构成,也试图重建诗歌文本和读者联系的新的途径。[6]6
从书中可以看到,参加课堂讨论的许多成员(如周瓒、姜涛、胡续冬、冷霜、钱文亮等)在当时就有诗歌创作的经历,并且这些成员后多从事学术研究和承担高校教学工作,可以说对新诗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因此,他们的解读较之普通读者,也更具有范例的功能。书中所解读的诗人主要为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与“新诗潮”有密切关系的诗人,如张枣、王家新、臧棣、欧阳江河、翟永明、韩东、于坚等,这些诗人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能代表90年代诗歌创作状况的几个侧面,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解读,能够了解90年代诗歌的大体面貌。而在篇目的选择方面,《在北大课堂读诗》更多注意“能够经受解读‘挑战’的、复杂和更多‘技术’含量”[6]9的诗。这种选择标准并不是要否定“单纯”的好作品,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课堂讨论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更多的文本阐释和成员交流空间,另一方面也与解读所使用的“细读”方法有关,体现了课堂讨论的参与者在解诗的过程中倡导诗歌“细读”的努力。
在“细读”方法的具体应用中,解读者们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模式或套路,而是根据所选诗人、诗作的具体情况以及个人的理解来选择切入一首诗的角度。这说明“细读”的过程需要灵活变通,不能拘泥于成规。举例来说,臧棣在解读张枣的《边缘》一诗时,更多地强调对一首诗思维过程的理解,突出对“联想轴”的关注,[7]21认为“边缘”的意味在于“诗人把他自己对边缘情境的体验和洞察,巧妙地融入这首诗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联中”[7]5。从这种解读角度可以看出,臧棣的“细读”实际上是把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对《边缘》的理解相结合,因为臧棣在写作一首诗时,会有意“让诗的形态最终呈现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生成的诗意的过程”,所以他的诗的诗意“往往不是由一行或两行来完成的,而是由一节甚至整首诗来完成的”。[8]臧棣这种“过程式”的诗学观念影响了他切入张枣诗作的角度,也体现出臧棣与张枣写作方式的“互文性”。赵璕在解读王家新的《伦敦随笔》时,则主要关注诗作文本中的“互文性”,注意到王家新诗歌中个人经验与文化资源的黏合特性,[7]47把王家新诗歌中的具体元素与其他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类似于将文本细读与“以诗解诗”的结合。又如,钱文亮解读柏桦的《琼斯敦》,借助了诗人的自传性材料,包括他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以及别的诗人和批评家提供的情况,同时也联系柏桦其他作品的意象词语的使用。[7]237这是把文本细读与传统“知人论世”结合起来的方法。由以上所举书中例子可见,对诗歌文本进行细读时,把诗人诗作的具体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应避免那种抹杀诗人写作风格独特性的模式化解读。从作者的角度进行思考,深入文本内部,关注具体语境,这是对前文所提及的朱自清“参与的作风”这一学术品格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细读”法在运用中的一大特色。
对不同的诗人之作采用不同解读角度的同时,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也应存在多种可能性,有时可能会是“误读”,新诗历史上李健吾与卞之琳针对《圆宝盒》一诗进行的讨论便是一个例子。可以说,“误读”在细读的过程中是允许存在的,读者与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完全重合。对一个诗歌文本进行多方位的解读不仅能够提供多层次的诗意,也显示了细读读者发散多样的诗学思维路径,正如臧棣所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潜在的作者。”[7]3针对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一诗,不同读者的切入角度就存在差异。对周瓒而言,她作为一位女性诗歌评论者可能与翟永明存在更多的契合度,她主要从“写作”这个层面来阐释《潜水艇的悲伤》,“潜水艇”暗指诗人的创作活动,并认为这是一首“以诗论诗”的作品。[7]84同样作为女性评论者,曹疏影的理解与周瓒有相似之处,而钱文亮、王璞等人则有不同的视角。钱文亮从语词方面入手,认为“借入词语”的使用揭示了翟永明诗歌的结构核心;[7]94而王璞认为“潜水艇”象征诗人的一种“远离人世的,将自我隐藏在深处的,秘密幽居于水底的内心状态”[7]96,这就与周瓒、曹疏影的理解有较大差别。不同“细读”角度的存在,说明“诗无达诂”的现象在当代诗歌细读的过程中仍然突出,并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局面。它们之间不是彼此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类似于一种“互映”。多种解读视角的并存显示了当代诗歌诗意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以及当代诗人思维和经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意图在诗歌中找到“定论”的做法也许是不必要的,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重要的可能不是要给出某种答案,或达到某种‘共识’,而是呈现富于启发意味的多种可能性。”[6]8在当代诗歌所呈现的复杂语境中,孙玉石先生总结的解诗“公共原则”仍然适用,但诞生了更多可以扩展和游移的空间。对许多解诗者而言,对具体诗人文本“细读”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诗学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说,深度意义上的“细读”是从具体文本出发,并试图看到文本背后具有普遍性的诗学问题,从而就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能的出口与潜在的陷阱。这样,“细读”就突破了以往人们把Close Reading视为“封闭式”阅读的偏见,而走向更为广阔的诗学批评领域。
姜涛在对欧阳江河的作品《时装店》进行分析时,便提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种期待,一种是对革命性的期待,一种是对诗的感受的普遍性期待。……欧阳江河的诗歌,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只是一种革命性,而不构成诗歌本身的拓展,以及可以延续的传统,这个问题值得讨论。”[7]72姜涛是在阅读一首诗的基础上,看到文本深层所隐含的问题,而不是仅对欧阳江河诗歌的修辞艺术持赞美式认同态度。“细读”若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分析,其价值可能不如对文本进行深度“透视”所得到的要大。立足于文本,并开阔思路,对文本所折射的问题做深入思考与探究,在“细读”中所占位置值得重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有些思路可能会是需要避免的误区。周瓒在分析吕德安《解冻》时谈到:“我们分析一个诗人的作品,容易与别的诗人进行比较。比较是必要的,但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路。……我们还要警惕那种概括式的谈论,它很容易抹杀掉诗人的特殊性。”[7]109由此可见,虽然“诗无达诂”是“细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剑走偏锋”的方法会使“细读”丧失其有效性,诗歌的意义也容易被扭曲,这就要求读者在实践中注意方法的积累和辨别。
在如今网络化的时代语境中,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会使诗歌阅读的速度加快,这是因为信息大量涌入而又转瞬即逝,使人应接不暇;再者,生活节奏的加速也影响了读者阅读所花费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下,普通读者面对一首诗的时候往往满足于对诗歌做表面的“赏析式”解读,“囫囵吞枣”“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般接受诗歌,只愿意寻找文本与自身相契合的部分而忽视其他,诗歌似乎成了一种文化消费品。长远来说,这种表面性赏析模式不利于读者深入体会诗歌的“妙处”,并且也有使媚俗诗歌泛滥成灾的危险。诗歌阅读需要“慢”下来,读者在“慢速”阅读中,能够获取更多的人生经验,丰富自己的心灵领域。因此,“细读”法有必要在当前的语境下得到提倡和推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细读”法为解读诗歌提供了较大的思维空间,但仍然容易遭到质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恐怕是针对“细读”中出现的“过度阐释”现象而提出的。“过度阐释”似乎是对“细读”的一种“扩充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能更愿意“把诗歌的指引能力落实到每一个字词,从而通过对一首诗的细读到达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去,把它与文化研究或者与思想史、学术史联系在一起”[7]377。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动机无可厚非,但逐字逐词落实后的解读很可能会使解诗落入机械化操作的圈套,把诗歌“完全去魅”的后果是诗意的稀释,诗歌也就就此成了一个“笨谜”。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北大课堂读诗》中所选篇目多为需要精心“细读”和推敲的诗歌,因此,此书自初版本诞生之时,便遭到一些关于“过度阐释”的批评。有批评者甚至尖刻地指出:“《在北大课堂读诗》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聚在一起共同粉碎诗人肢解诗歌的阴谋。……‘过度阐释’是一种外溢,也是一种话语暴力。一旦批评溢出诗歌魔瓶,诗魂就会四处飘零。”[9]这种声音的出现,表明有些读者对诗歌“细读”法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如前文所说,“细读”法诚然是对表面性“赏析式”解读的纠偏,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诗歌文本整体性的美感的确容易遭到破坏,但由此全盘否认“细读”法的有效性,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在北大课堂读诗》中参与课堂讨论的人员已经意识到“过度阐释”的危险,并提出了补救方案。胡续冬指出,赏析式的批评方式不能完全被抛弃掉,[7]378在细读中它也有借鉴的价值,对诗歌的主观感受力仍然重要。洪子诚先生在《初版序》中也强调了“感悟”能力的价值。[6]9可以说,“阐释性”强度的日趋增大是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趋势,但诗歌中“晦暗不明”的领域也有其魅力。对于诗歌中“不可说”的部分,“保持沉默”也许更能使诗歌保持它的艺术价值。因而,把“细读”法与中国古代的印象点评法相结合,也许能够更为有效地解读诗歌,同时保持文本本身的“神秘性”。正如唐晓渡在《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的《后记》中所指出的:“将西方‘新批评’的所谓‘细读’和中国传统的感兴式意象点评加以综合运用,同时注意互文性的把握,以便一方面通过逐行逐句语象的拆解、分析,尽可能充分地揭示一首诗的内涵和形式意味;另一方面,又将由此势所难免造成的对其整体语境魅力的伤害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10]
深入一层来说,《在北大课堂读诗》所倡导的“细读”法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在于对诗歌解读方法的纠偏,正如前文所提示过的那样,“细读”在指向诗歌文本本身的同时恐怕还要着眼于更广阔的诗学空间。一个有心的读者会在“细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从而带着问题去接触更为广阔的知识和经验层面,其收获也许比文本本身的价值大得多。正如钱文亮所说“一个理想的解读者应该是对诗歌有着比较高的专业敏感、专业训练,甚至对语言学、心理学都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另外就是对诗歌历史、当下的诗歌序列相当了解。”[7]381对普通读者来说,恐怕很难在短时期内成为这种“理想读者”,而“细读”将成为他们提高诗歌解读能力和自身诗性修养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方法上向更具有专业水准的“理想读者”靠拢,“理想读者”在细读的过程中有时也要借鉴普通读者的观点。“细读”的作用不是扩大“理想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而是促使两者在对诗歌解读的过程中能够平等对话。
就化解“理想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界限而言,《在北大课堂读诗》无疑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本。事实上,自《在北大课堂读诗》出版以来(尤其是修订版推出之后),就有许多普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对解读者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从解读者的解诗过程中逐渐习得了“细读”这一理解诗歌的有效方法,进而对现代诗有了新的认识,与洪子诚先生一起“重新做一个读者”[6]7。有读者自陈:“看书之前,我颇有顾虑,一是因为我确不知道何为好诗,怕因自己知识和底蕴的浅薄而糟蹋了书中美好的文字烙印;二是害怕如果彻底通透了诗的含义,是否那层朦胧的梦幻就消失不见了,那岂不是又辜负了作者的一番苦心?”[11]“一直以来,自己是不敢说懂诗歌的,无论是古诗,还是白话诗。古诗即便不懂,还可从音、韵、形式上得点娱人耳目的感受。白话诗歌就往往无从谈起了,打破任何现有观念和形式,所以对待现代诗歌,个人早就打定主意:重新作一读者。从这个角度说就与这本书的编者洪子诚先生不谋而合了。”[12]而读完《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之后,读者则领悟到:“只有读懂一首诗,才能感觉到它的好坏,或者说自己是否喜欢。”[12]“15节课,一本书,从文字能见出课堂的热烈,每节课的记录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诗歌的意思,是引导读者探寻诗歌的意义。读过书对于把握中国90年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方向,以及对诗歌解读的理念方法,都大有裨益。”[12]这些读者的反映说明,在对当代诗歌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的出版能够使普通读者通过阅读来逐渐接受“细读”的观念和方法;伴随着阅读的进行,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隔阂也有缩小的趋势,两者之间可以在对诗歌文本的解读中建立对话关系。
综合看来,《在北大课堂读诗》在诗歌“细读”的具体观念、方法的更新与传播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在主讲与讨论相结合的课堂教学中,参与者向读者详细展示了“细读”一首诗的过程。而《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的出版,可以视为对诗歌“细读”法的进一步“去魅”,证明了在网络化、商品化时代,对当代诗歌的“细读”仍然具有广阔的可能性。“细读”一首诗,读者享受到的并不是波涛汹涌般的语言快感,而是如同涓涓细流一样的精神陶冶。在细嚼慢咽中,读者的读诗品味会渐渐得到升华。
[1]许霆.中国现代诗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1.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美〕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M].主万,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5]〔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M].郭乙瑶,王楠,姜小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洪子诚.初版序[M]∥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王光明.可能的拓展:诗与世界关系的重建——臧棣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M]∥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80~181.
[9]丁国强.在北大课堂读诗[N].青岛日报,2003-10-10.
[10]唐晓渡.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251~252.
[11]米筱禾.读诗,读一种经历[EB/OL].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233306/.
[12]克舟.出堂入世谈读诗[EB/OL].http://book.douban.com/review/7378447/.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 Hong Zicheng'sPoemReadinginClassroomsofPekingUniversity(RevisedEd.)
WU Hao
(School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s the term "close reading" is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Criticism in Britain and US, its history of acceptance by Chinese poetic critics can date back to the 1930s. Since the 1990s,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e has witnessed tremendous changes in its context, so it is worth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he "close reading" method is still applicable to poetry reading in such a fast-changing context.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s on poems by poets of the 1990s in China mentioned in Hong Zicheng'sPoemReadinginClassroomsofPekingUniversity(revisededition) not only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perusing contemporary poems but also provide varied ways for close reading. Meanwhile, aware of the probable skepticism about the "over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se reading method in its concrete applica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ussion have proposed integrating perceptive reading with close reading so as to render the latter into a comprehensive method for poetic criticism. The bookPoemReadinginClassroomsofPekingUniversity(revisededition) has since its publication been favorably
by fans of poetry—a distinct demonstration of the charm of the "close reading" method.
contemporary poems; close reading;PoemReadinginClassroomsofPekingUniversity(revisededition)
2015-10-01
吴昊(1990—),女,山东泰安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I207.2
A
1674-5310(2015)-12-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