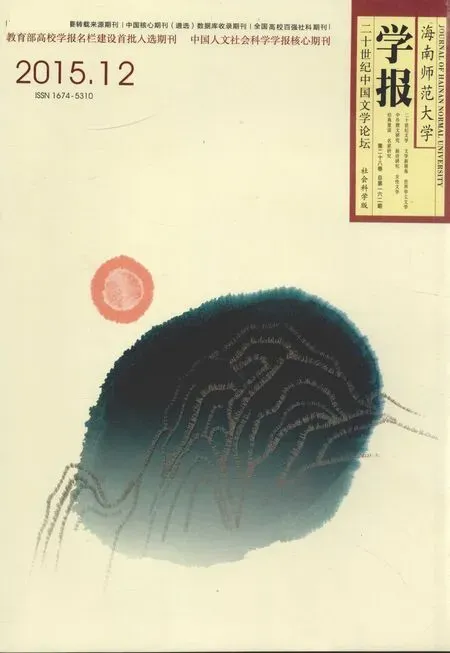重新建构文学精神资源的理性思考——《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序
丁 帆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作为断代的门类文学史研究,无疑,潘亚此书的出版对“十七年”历史剧的宏观把握与微观重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对“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作家作品的格局之中,其方法也主要采用政治/艺术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而潘亚的这部专著却从有限的创作中抓住其要害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发掘出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为文学史的重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评估,乃是20 世纪历史剧创作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环链。潘亚选择话语形态理论为视角,将“十七年”历史剧概括为四种特征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
“十七年历史剧是在一种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下生成的,它负载着强烈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使命,因而,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它是在现代话剧特别是历史剧创作传统以及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借鉴并努力民族化的基础上,在革命文学、左翼戏剧、延安文艺及前苏联戏剧的直接启示下生成的。”“既认同与归附于权威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又有一定偏离的独特的话语形态体系。”这种对于创作背景的分析大体是准确而客观公允的,“十七年”历史剧从源头来说是带有“左翼”色彩的。但就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它又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和个性风格。时代与政治,共性与个性,就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一样紧紧附着在“十七年”文学之中,其历史剧当然是更为凸显的艺术门类。
“它作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现代剧作家们在建国初,面向现实题材进行创作话语转型失败后,形成的政治无意识升华的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在泛政治化的创作语境下,史剧家们选择历史剧的形式进行话语言说,充分体现出对十七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或反抗,亦即以其符号形式的建构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出现代剧作家们强烈的现实关怀,即试图通过重新编写历史故事把历史经验复活起来,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我以为潘亚的这一论点从某种程度上是击中了“十七年”历史剧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要害,为揭开“十七年”历史剧的精神面纱给出了准确的答案!这个答案虽然是常识性的解释,但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用“左”眼去看戏剧,很难看见它们的本质特征。如今,我们顺着他指引的理论视点看过去,便可透过历史的雾霭,一眼望穿它的真实内涵。“它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史剧家们选择令今人会产生共鸣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和冲突,在历史的视野中,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规则,对其重新进行调动和安排,从而再评价他们的得与失、荣与辱,以达到‘教育’人民的作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构成。”对于“十七年”文学所构成的精神影响,我是向来没有低估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却是这个物化时代的人难以廓清的哲学命题。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夹杂着可卡因成分的,是需要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做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的艰难命题。
“这25 部历史剧深深地凝聚着十七年中,特别是1958—1962 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所赖以生成的信息基因,流露出特定年代权威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机,构成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镜像。它既折射出权威话语及时代流行的政治理念和工农兵文学创作模式的规训、制约与影响,又真实地体现出特定年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态与价值向度,昭示着史剧家们内心世界潜隐着的种种矛盾的心理与欲望。”无疑,潘亚对此“镜像”式文本的理解是深刻的,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统摄的,但是,关键是看他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围绕着作者设定的四个板块,我以为其论文的主体构架是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纵览其结论,虽然我尚有不完全同意的观点,但是,其基本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我最为欣赏的是全书对第二板块的分析,其结论有着深邃思考:
“在文体形态上,我认为十七年历史剧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呈现方式,即‘尊古写剧’、完全虚构、‘失事求似’,但由于历史‘现实观’的强烈制约,亦即对‘古为今用’的特别重视,使得它尤为强调‘失事求似’。而构成历史剧的历史性、当代性、主体性三种文本形成了共渗互动的关系。由于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使得十七年的历史悲剧普遍不悲,与表现现实题材的工农兵文学相一致,历史喜剧很少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多以大团圆的结局呈示喜剧性,因而在情节开展方式上是忌悲忌喜,正剧统一;在结构模式上,十七年历史剧创作大多采用情节推进式冲突结构,这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化的阶级冲突、斗争意识在历史剧创作中的折射。由于政治理念的侵蚀使得许多史剧在结构上出现了‘非整一性’问题,并将历史个体意志间丰富多元的矛盾冲突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单一结构,普遍采用与颂歌叙事相一致的历史‘苦难’叙事模式;在人物形态上,十七年历史剧创作形成了以扁平型为主的人物形象谱系,立体型人物屈指可数,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好/坏、善/恶的阵线分明,且均具有各自的代码与功能。男性史剧家们通过‘拟代女性写作’方式刻划女性人物形象,以历史女性形象演绎政治理念,回归爱情本体的女性话语是少之又少,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在语言系统中,由于对语言风格的探索与追求不会触及权威话语的禁忌,使得十七年的许多史剧在实现双重超越的基础上,普遍采用‘历史/现代’形态的语言媒介系统,形成了亦古亦今、化古为今的独特语言风格,以曹禺、老舍为代表一些史剧家还在语言的探索中回归了自我。但在总体上仍是以宣传说教型语言为主,普遍采用政治性的语汇。”这无疑是在给“十七年”历史剧“点穴”,通过微观分析所得出的宏观结论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必然,是从历史现场抽绎出来后,经过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过滤与思考后的结晶。
而对第三板块的分析,我却尚有不完全一致的意见。作者说:“我认为十七年历史剧在承载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许多史剧还潜隐着史剧家们对历史与生活的独特思考,即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包括借历史‘干预生活’,对人与自我的关注与呼唤和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反思;有些史剧家甚至在用生命感受历史,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就是我’,田汉‘长与英雄共魂魄’,师陀在《西门豹》中表现出的孤独而痛苦的灵魂,等等。”如果说在“十七年”文学中尚有个别作家还保有残存的现代“启蒙”自觉意识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作家是没有、也不会有“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的主体意识的,启蒙意识更多的是被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和淹没了,而凸显出来的是却是普遍的“奴性意识”。尤其是作者以郭沫若为例,就显得更不合适了。
总之,此书的出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历史剧的一次重新价值定位和理论爬梳,其文学史意义是大于纯学术意义的,因为,它在学理层面的建构是改变以往不切实际的历史性选择:“我选择‘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为题,是为了考察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所遗存的对新时期历史剧乃至话剧的影响,并从中阅读出有益于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精神资源。它并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适应21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发展的需要,并立足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建设而作出的理性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术动机——那种对重新建构文学精神资源的理性思考——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根基所在。
温潘亚是一个勤勉的学者,他不但勤于思考,而且出手也快。从他的学术成果来看,不仅数量颇多,而且质量也高。三年的博士后经历,使他在学术上更加成熟了,其学术收获颇丰,值得欣慰。但我总以为潘亚如果能坚持在学术的板凳上再坐上个十年八载,一定会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可惜他的行政事务缠身,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和制约了他的学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愿他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坐在学术的板凳上保持自己的学术追求。
是为序。
2014 年12 月30 日于紫金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