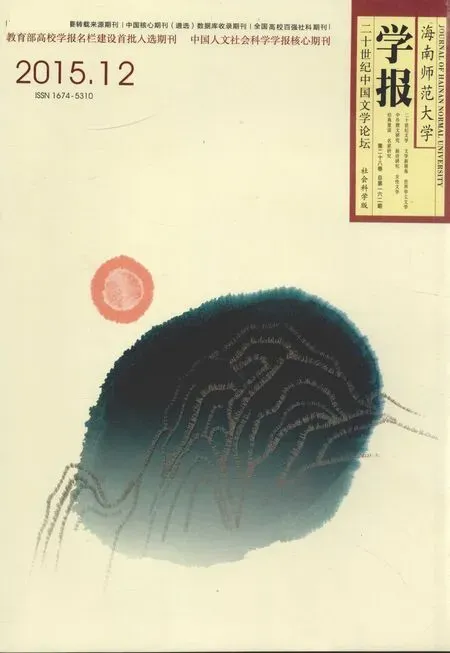商业秘密立法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崔汪卫
(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200092)
全国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制定《商业秘密法》议案,但是该立法一案仍未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①2006 年全国人大代表孔维梁、2008 年和2014 年全国人大代表李长杰、2011 年全国人大代表左延安、2012 年全国人大代表、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等等,在两会期间提交建议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或《商业秘密法》的议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基础、立法价值和构成要件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首先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基础和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说明商业秘密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加以分析,希望对未来立法有所裨益。
一、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基础
商业秘密给持有者带来无限的商机,使其始终保持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直接关系到持有者的财产利益实现,激发其创新热情,法律应当对此予以充分保护。然而,商业秘密保护一直以来存在一些争议,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基础直接影响到立法者采取何种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同时,也反映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水平。截止目前为止,对商业秘密法理基础的各种论述仍然没有一种学说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有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法理基础存在诸多争议,是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至今尚未颁布的真正原因。[1]笔者想在总结并批判继承现有各种学说的基础上,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依据进行探讨。
(一)商业秘密保护法理基础的现有学说
第一,契约义务说。亦称“保密合同说”,它最早源于英国横平法上的信托关系,例如,1851 年的Morison v.Moat 案,该案原告发明了一种药物,并告诉了其合伙人(该案被告),双方约定不得将该药配方向第三方透露,但被告在合伙结束后违反约定擅自将该配方告诉自己的儿子而进行利用。原告起诉至法院后,法院根据信托关系进行判决,认定被告违反了合同义务,禁止被告儿子利用该配方。②Morison v.Moat,68 Eng.Rep.492,9 Hare 241(1851)。美国也出现了利用契约关系说来保护商业秘密的案例,如Board of Trade v.Christie Grain&Stock Co.案中,Holmes 法官不主张从财产权角度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他认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是基于保密关系,建立了信任关系的人不能破坏信任合同以获取并使用他人商业秘密。①Board of Trade v.Christie Grain&Stock Co.,198 U.S.100,102(1905)。商业秘密的保护经历了从明示合同(express contract)到默示合同(contract implied in law)的过程,正如Robert G.Bone 所言:“商业秘密中的合同关系既包括默示合同,也包括法定默示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保密义务应被视为合同的默认条款(default rule)。……默认条款是商业秘密合同中的补漏条款。”[2]契约关系说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主要通过认定违约的方式来追究泄露者的法律责任,但是运用契约关系说来保护商业秘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在没有签订契约的情形下将无法对抗侵权行为人。例如,美国Peabody v. Norfolk 一案中第三人Cook 就以与原告Peabody 没有保密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最终Gray 法官以财产权理论驳回他的抗辩理由。②Peabody v.Norfolk,98 Mass.452,456(1868)。
第二,侵权行为理论。正是因为上述保密合同理论的局限性,有些立法者提出利用侵权行为理论来保护商业秘密以弥补合同法理论的不足,在连默示合同都没有的情况下,根据横平原则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进行制裁,保护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美国早在1939 年《侵权行为法重述》第757 条就提出商业秘密保护的侵权法理论并确立了其地位,利用这种理论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既涵盖了明示和默示合同的情形,也包括了无任何合同的情形;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的对象既针对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也针对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第三人。[3]然而,侵权法理论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只注重是否产生了侵权结果,对商业秘密的属性、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及采取的手段等都不加以考虑,这必将忽视了侵权行为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
第三,竞争法理论。为了弥补侵权行为理论的不足,一些学者主张从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引入不正当竞争理论,他们认为商业秘密是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重要法宝。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竞争法理论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用竞争法理论解释和规制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1990)、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等均以竞争法形式对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行为进行法律规制。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代表,在已有《侵权行为法重述》、《统一商业秘密法》的基础上,再次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中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作出了立法规定。各国倾向于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他们不将商业秘密视为一种财产,也看到了利用合同法理论保护商业秘密的缺陷,反不正当竞争理论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诉求;二是采取反不正当竞争理论保护商业秘密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第四,财产权理论。将商业秘密视为无形财产,对其进行法律保护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财产权理论最初出现于美国1868 年Peabody v. Norfolk一案,该案原告Peabody 持有一种用黄麻生产麻布的机器和工艺的商业秘密,被告Norfolk(雇员)被原告雇佣,他们之间签订了保密协议。然而,被告辞职后与他人合伙开办同类工厂使用原告相同的机器和工艺。原告Peabody 向横平法院申请禁令要求阻止侵权行为,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审理该案的法官Gray 认为:“如果某人运用自己的技术和努力从事某种经营活动,那么他在经营活动中所付出的技术和努力应当被视为法律上的财产。”③Peabody v.Norfolk,98 Mass.452,457-458(1868)。以此为先河,美国和诸多大陆法系国家均承认或者隐晦地承认商业秘密是特殊财产的思想。国际组织颁布的公约、各国缔结的多边或者双边条约大多将商业秘密视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一同被看作一种无形财产。1991 年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多边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 协议”)中将“未披露的信息”列为其保护的范围,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知识产权示范法之一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重点对“秘密信息的不正当竞争”作出具体规定。我国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的权利,且其更侧重财产权属性。④例如,我国学者彭万林、吴汉东、费安玲等都提出这一主张。参见: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532 页;吴汉东:《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价值及经营方略》,《中国知识产权报》2014 年1 月29 日第8 版;费安玲、Liu Hui:《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3 年第1 期,第165-178 页。商业秘密的财产属性已经逐渐为我国法律所接受,例如,我国《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 条第6 款规定就间接地承认商业秘密的财产属性。①《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 条第6 款:“本规定所称的权利人,是指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众所周知,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客体是财产,本款肯定商业秘密持有人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这是肯定其为财产的重要表现。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得通过财产权理论来对其加以保护,对此下文将进行进一步剖析。
(二)商业秘密法理基础现有学说剖析
契约义务说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依据,相对于其他学说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仅凭有无保密合同即可认定是否实施侵权行为,有效地避免了持有者对商业秘密的认定、是否采取保密措施等事实举证困难或者无法举证,但是无法囊括第三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侵权行为理论能够解决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它主要从持有人是否存在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来认定侵权事实,但是却忽视了商业秘密的属性,任何一种权利受到侵害都可利用侵权行为理论进行维权。财产权理论将商业秘密视为一种无形财产,我国法律对此较为认同,但利用财产权理论来保护商业秘密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都具有对世效力,具有排他性。然而,商业秘密尽管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从性质上而言,具有财产权的属性,但笔者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它不具备一般财产所具有的排他性特质,任何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同样内容的商业秘密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商业秘密持有者不可以排除该人取得并使用。反不正当竞争理论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他人不正当手段取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以竞争法理论保护商业秘密具有特别的优势:第一,该理论不从商业秘密性质入手,而着眼于分析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意图正当性和采取手段合法性。诚如某位学者所言:“尽管最终法官可以采取侵权理论、合同理论、财产权理论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问题的实质还是商业竞争者间是否采取了公平、诚实的竞争手段。”[4]只要竞争对手采取了正当途径,如通过自己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精力获取的商业秘密就受到法律的保护,如竞争对手故意获取他人商业秘密并实施了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之行为,即构成对他人商业秘密的侵犯,法律对此应当予以禁止和制裁。第二,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商业秘密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而且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损社会创业、创新环境。竞争法属于社会立法,理应对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因而,一旦出现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利用此法既可以对商业秘密持有人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主张赔偿,也可以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侵权行为者给予行政处罚和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达到阻却商业秘密侵权之目的。第三,利用竞争法理论保护商业秘密具有全面性。利用竞争法理论保护商业秘密,既突破了契约关系说的运用缺陷和财产权理论的思维困扰,也可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侵权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手段”定义较为灵活,执法者可依据不断变换的情势做出相应的调整,防范和打击各种新生的、立法尚未涉足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5]
二、商业秘密保护的价值分析
(一)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
古罗马时期法律就有关于“商业事务的秘密”之规定:市场主体恶意引诱或迫使其竞争对手所有的奴隶泄露其有关商业事务的秘密,其竞争对手(即奴隶的所有人)有权向司法机关提起“奴隶诱惑之诉”(actio servi corrupti),请求侵权人给予双倍的损害赔偿。[6]自此以后商业秘密保护即被赋予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的标签。为数不少的各国既存的各种学说和判例认为,基于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之目的,给予商业秘密持有者以法律上的保护,对作为明示或者默示协议的一方科以不能披露或者使用商业秘密持有人所拥有商业秘密的义务,非经过持有者同意,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法律均予以明令禁止。19 世纪以来,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成为商业秘密保护的目标,诚如美国学者Melvin F. Jager 所言,商业秘密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投资方向,谁也不愿意从事风险投资。使用或者泄露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盛行,必将导致没有任何市场主体愿意浪费时间和金钱从事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尽管这样,生产和经营活动不会停止,但是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有创新的技术、有新意的产品不会诞生,社会发展将会停滞不前。①美国学者Melvin F.Jager 指出:“让我们设想片刻,如果一个商业社会从没有听说过‘诚实信用义务’,会导致任何人的行为,对他人均不负善意义务。这一社会将没有知识产权法,虽然生产和经营不会停滞,但发生严重问题。盗窃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遍地盛行,恐惧和怀疑渗透于每一项交易中,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均有可能被交易的雇员个人出卖。如果仅靠雇佣一个跳槽者就可以得到最新的商业信息,什么人还会浪费时间和金钱开发新产品和工艺?如果任何雇员均可向出大价钱的人,出卖企业的知识,使开发投资全部付诸东流,哪个企业还会投资?”参见:Melvin F.Jager,Trade Secrets Law Handbook,Clark Boardman Company,Ltd.1983.pp.1。“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必要性,恰恰是商业界的生命和精神。”②National Tube Co.3 Ohio C.C.R. (n.s),at 462。为增强自己所持观点的说服力,Melvin F.Jager 还引用了古希腊商事交易规则来说明保护商业秘密是维护社会商业道德的必然要求。因而,基于商业秘密道德和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对于“不正当手段”攫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予以禁止,充分保障了商业秘密持有人占有市场竞争优势,保护了商业秘密权人的智力成果。
(二)促进和鼓励市场主体开展研发活动
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秩序、自由和效率,[7]商业秘密保护也不例外。“正义”和“秩序”即是上文所提及的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自由”和“效率”意指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能够促进和鼓励市场主体开展研发活动。“自由”是指权利人得以自己的意志行使基于商业秘密产生的权益与进行科技开发创造活动的行为自由;“效率”体现在促进智力成果开发以及科学技术创新上。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大多属于研究开发的智力成果,研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保护商业秘密的最终归宿是促进研发和鼓励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社会经济。例如,Wexler v. Greenberg 一案中,美国宾州最高法院指出,商业秘密保护对于补偿研究开发的开销、通过鼓励创造性开发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③399 Pa.569,578-579,160 A.2d 430,435(1960)。美国经济学家Joseph E.Stiglitz 曾指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市场竞争的形式大多数是努力研发新产品,以及用新工艺或者新方法生产老产品……研发者谋求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常以支付高昂的研发费用为代价,通过开发出更加经济、更有效率的生产工艺和方法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性能更稳定、质量更可靠的产品,即便提高销售价格也不会降低市场份额和丧失原有顾客,从而在市场上取得主动性和竞争优势,同时,它们可以一并获得先前研发付出努力的回报。④467 U.S.539,546(1985)。因此,作为专利制度的重要补充,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为商业秘密持有人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鼓励他们通过努力劳动、积极创造成果,使其拥有某种超过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
(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
自然权利学说认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劳动果实有权主张”,作为商业秘密持有者,他们理所当然享有商业秘密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司法实践,也体现了对商业秘密保护的自然权利观点。例如,Ruckelshaus v.Monsanto Co.案,法院主张“把商业秘密作为财产与财产权的劳动理论相一致”[8]。由于商业秘密能够为持有者带来独特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倘若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其竞争对手势必采取不正当手段盗用商业秘密谋取非法利益。商业秘密持有者为研发新思想或者新方法而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并独立承担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而侵权人没有付出任何努力而使用他人商业秘密,这是一种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严重侵犯。[9]我国《宪法》第13 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商业秘密具有无形财产的属性,是商业秘密持有人付出时间和金钱等开发出来的合法私有财产,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不容他人侵犯。
三、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然而不是任何与经营和技术相关的信息均属于商业秘密。认定这些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需要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来考量。由于各国文化传统、政治状况、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它们在认定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上也存在着细微不同,而并非有些学者所言的各国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存在重大差别。①尽管学界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认识只是存在着大同小异,而并非某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两大法系在商业秘密的界定上存在重大差别”。参见:陈骏、彭林:《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若干问题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 年第4 期,第73-78 页。这主要是因为《TRIPS 协议》已经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对各国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②TRIPS 协议第39 条第2 款:“只要有关信息符合下列三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其属于秘密,就是说,该信息作为整体或作为其中内容的确切组合,并非通常从事有关该信息工作之领域的人们所普遍了解或容易获得的;因其属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合法控制该信息之人,为保密已经根据有关情况采取了合理措施”。那些主张各国立法和司法中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认定存在重大差别的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将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一,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立法和司法应有之义。“权利不得滥用”、“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是各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础。因而,在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立法中,没有必要单独将社会公共利益条款列为其构成要件。[10]
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在我国学界也存在不同声音:有些学者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知识信息,是人们智力活动的成果,它未获得传统意义上知识产权的直接保护,具有非物质性、可传授性和可转让性的特性,要想成为商业秘密应当具备秘密性、经济性和一定的新颖性等要件;[11]有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秘密性、经济性和独特性;[12]也有学者认为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主要有秘密性、保密性、实用性、经济性;[13]还有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秘密性、独特性、实用性、经济性。[14]上述观点除掉商业秘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的共性以及仅内涵相同而表述有异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是新颖性是否有独立于秘密性而存在的必要;二是实用性是否能成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一)秘密性
要想获得商业秘密保护,有关信息必须具有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秘密性的观点得到了发达国家大量案例的支撑。例如,美国1979 年的Carson Products Co. v. Califano③594 F.2d 453。案中法院以产品成分在有关学术论文中,甚至在专利文献中已经用于相同产品,而拒绝原告申请食品成分保密的请求,其判决书中指出:“不用侵权手段即可以得到的信息不能是商业秘密的对象。”至于秘密性要求是绝对秘密性还是相对秘密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认为,秘密性是相对的,而非具有绝对的秘密性,即它不要求任何人都不知晓该商业秘密信息,而是有限度地公开于一定范围之人知悉。④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Unfair Competition,Section 39,Comment g。1868 年Peabody v. Norfolk 案和Pressed Stell Car Co. v. Standard Stell Car Co.案都指出,商业秘密的某些程度的公开是不可避免的。⑤Peabody v.Norfolk,98 Mass.452(1868);Pressed Stell Car Co.v.Standard Stell Car Co.,210 Pa.464,60 A.4(1904)。在我国,秘密性是指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普遍知晓”,具有“相对秘密性”,它为一定范围内必须知道的人所掌握。对于“一定范围内必须知道的人”具体是哪些人,一般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个案的不同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认定。例如,在下列情况下,商业秘密就不会丧失其秘密性:1.负责企业生产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运用商业秘密的雇员或者员工;2.按照双方签订的协作协议、技术合同等商业秘密持有人将商业秘密披露给合同或者协议另一方或者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或者人员;3.法庭庭审披露的、成果鉴定会展出的商业秘密;4.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对某一商业秘密同时合法持有;5.某一区域范围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在其他区域内可能又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上述五种情形并不影响信息秘密性的存在。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定,即客观秘密性和主观秘密性。客观秘密性是指客观上某一信息不为同一领域相关人员所普遍知晓,主要从该信息被公开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和该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两个方面加以判断;主观秘密性是指主观上信息持有者是否对该信息具有保密的主观意愿,这种主观意愿通常以信息持有者是否采取了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来加以辨别。
有些学者将新颖性作为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一,本文对此并不苟同。商业秘密的新颖性是指商业秘密非该信息行业领域公开信息和公知信息,这些既存信息通过正当手段是无法获知的。纵观各国法律,它们对秘密性和新颖性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所指涵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譬如,美国《经济间谍法》、《统一商业秘密法》和《经济间谍法》均将“秘密性”解释为:不为公众所知,通过合法手段无法获知。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将其规定为:不为普通公众所知晓。从美、日两国立法来看,美国法关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明确囊括了秘密性和新颖性;日本法明确昭示商业秘密的秘密性,然而“不为普通公众所知晓”亦暗示其新颖性的本质属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颖性是秘密性的前提,没有新颖性就没有秘密性可言,秘密性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新颖性,即在该信息所属领域内不同于既存的信息。综上所述,新颖性是秘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秘密性的最低限度,可以不作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来看待。
(二)实用性
实用性,又称价值性,意指商业秘密能够给持有者带来某种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TRIPS 协议》将“实用性”解释为“因其属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即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才有成为商业秘密的可能;具有精神价值、社会价值等都不构成商业秘密。判断一条信息是否具有实用性,主要通过能否给持有人带来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作为衡量尺度。商业秘密既包括积极信息,还包括消极信息。所谓积极信息是指持有信息者投入人力、财力经过实质性开发获取的,能给自己经营活动带来利益的信息。消极信息是指开发的信息对开发者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该信息若被竞争对手获取,可以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可以节省他们因开发出这些没有经济价值的信息而花费的大量时间、金钱,缩短研发时间,使他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极信息也是商业秘密。除了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以外,对于正在开发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性,也应当获得商业秘密法的保护。商业秘密的实用性,可以通过相关证据证明。例如,商业秘密持有者在开发相关信息过程中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为保持相关信息处于秘密状态而付出的一定努力,以及他人愿意支付费用而使用相关的信息、商业秘密持有人使用相关信息所得明显的利益,等等。
(三)保密性
保密性,即持有者应当对商业秘密相关信息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此处所采取的保密措施是根据具体情形而采取的“合理或适度的保密措施”,并非过分或者极端的保密措施。例如,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的“评论”中指出:“维护信息秘密性的措施,与确定相关信息是否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相关。维护秘密性的措施可以多种多样,包括防止未经授权而获得信息的物理保安措施,针对有限披露的程序,以及向接受者强制者强调信息的秘密性质的措施,诸如不得披露协议、标记和限制性说明。这类措施可以看作是有关信息具有价值性和秘密性的证据。”正如一句名彦所言,“一扇未上锁的门不等于一张请柬(An unlocked door is not an invitation)”。只要设有“门”虽未“上锁”,即视同持有人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过路者“禁止入内”。这在美国Eu Pont de Nemours&Co.v.Christoper 案中法院认为,杜邦公司在施工场地设置了围墙即被认定为采取了保密措施,而不能强求该公司在施工场地加盖顶棚以防止竞争对手从空中偷窥才认定采取了保密措施。①431 F 2d 1012,1066 U.S.P.Q.(BNA)421(5th Cir 1970),cert.denied 400 U.S.1024(1971),reh.denied 401.U.S.967(1971)。
法律要求对商业秘密采取合理保密措施,“合理”有两种含义:从“质”层面而言,法律要求保密措施是具有实际效果,能发挥应有作用并达到保密目的;从“量”层面而言,法律要求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仅以让接触商业秘密的雇员知晓该信息是商业秘密或者防止普通人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即可认定为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从当前立法趋势来看,“合理注意义务”成为各国认定是否采取合理保密措施的重要依据,即在合理注意的前提下,采取保密措施足以使普通人意识到商业秘密的存在,基于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考量,不特定义务人应尊重持有人的保密意志,对存在商业秘密的信息予以主动回避。不特定义务人的行为即便在通常情况下是合法的,也会被视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不正当行为。例如,雇员不能借雇主一时疏忽忘记采取合理保密措施之名(例如,忘记在保密文件或者物体等标注秘密字样、没有将其锁入柜子等)而侵占商业秘密。正基于此,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第39 条评论G 认为:倘若信息具有的秘密性和经济性为公众所周知,这时就没有必要要求权利人提供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
综上所述,未来的商业秘密立法在认定商业秘密构成要件时,宜采用“三要件说”,即秘密性、实用性和保密性。同时,根据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依据,商业秘密具有财产权属性,但是保护宜借助竞争法理论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未来的商业秘密立法中应当借鉴和移植一些竞争法相关理论,以规制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带来纷繁复杂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保护商业秘密持有者的合法权益。
[1]付慧姝,陈奇伟.论商业秘密权的性质[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78.
[2]Robert G.Bone.New Look at Trade Secret Law:Doctrine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J].California Law Review,1998(3):301.
[3]杨正鸣,倪铁.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商业秘密保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4]Ramon A.Klitzke,Trade Secrets:Important Quasi-Property Rights[J].The Business Lawyer,1986(2):557.
[5]张耕.商业秘密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66,537-540,7.
[6]〔日〕土井辉生.知的所有权——现代实务法律讲座[M].东京:青林书院株式会社,1977:179.
[7]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56.
[8]〔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M].黄险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02.
[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57.
[10]种明钊.竞争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58-262.
[11]张今.知识产权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
[12]衣庆云.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属性[J].知识产权,2002(1):40.
[13]张向群.浅谈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J].当代法学,2003(1):129.
[14]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