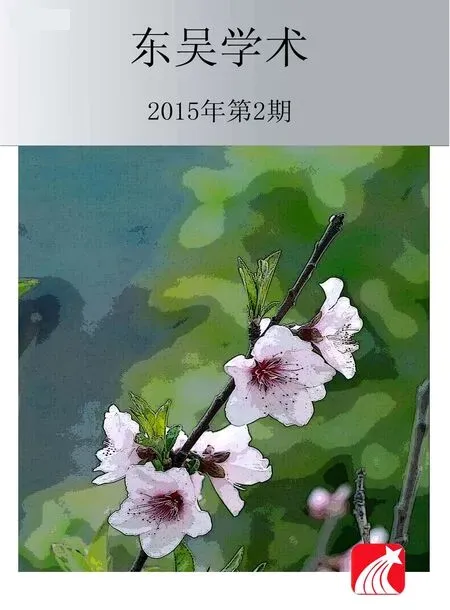背负苍茫歌未央
——评李森的诗
王 新
诗学
背负苍茫歌未央
——评李森的诗
王 新
李森近年创作的诗歌,看似清澈单纯,实质蕴涵着丰富而纯粹的诗艺与诗境探索。本文建基于文本细读,与李森个人诗学理念相印证,在中西诗学的宏阔背景中,全面阐析李森诗歌的隐喻生成与解构机制,深入剖析其诗歌合经验、意象、叙事、哲性为一体,开显“元诗”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究明李森作为一位现代意识与古典情怀两厢砥砺、精英理想与乡土气质互相纠结的诗人,最终如何以诗情和画意,敞亮物性,并通达苍茫气象的复杂诗学肌理。
李森;隐喻;元诗;叙事;物性;苍茫
李森的诗有一种静水流深的清澈。
清澈源于其诗性隐喻对素朴事物本真状态的照亮,源于古典诗学对诗性隐喻的精致提炼,源于爱智者返本归真的清明理性。清澈之下,则是苍茫的深流,流动着诗艺的丰饶织体:隐喻的生成与消解,智性追问的草蛇灰线,虚拟叙事的摇曳生姿及古典诗艺对意象与韵律的苦心锤炼,随时在诗境中波光潋滟,顾盼生情;海德格尔所期望的、多少诗人所仰望的天-地-神-人各各际遇、和谐共生的苍茫境界,①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李森通过高黎贡山下的一只梨或一块马蹄铁,就自然达成了。当然,对于所有创造性的事业来说,复杂并不难,单纯才难。李森让缤纷的诗艺、苍茫的内涵全副归于清澈,这需要君临一切、截断众流的气概,更需要璞玉浑金的天资。
这是莫扎特的音乐、拉斐尔的画中才有的气象。
看看他的《梨树和梨》吧:
听说,在天边外。秋深,晨开,夜风在山谷结出卵石。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梯子,伸进梨树,高于梨叶。
弗罗斯特不在,只有鞍在。我不在,只有箩筐在。
梨问另一个梨——所有的梨,都在问梨。
为什么,梨核都是酸的,古往今来的酸。
有一个梨说,这不是梨的决定。是梨树。
梨树突然颤抖。一棵树说,也许是春天的白花。
另一棵树说,也许是风绿,雨湿,光荫。
还有一棵树说,难道是那把长梯。那些木凳。
日过中午,不闻梨喧。日落山梁,不见梨黄。
这首诗是清澈的,因为它只说了梨树和梨,意象疏朗、节奏鲜明;这首诗是复杂的,开头,天边外、深秋、夜风、卵石,是深秋的事物和事实,但一冠以“听说”,则全部虚化,转为隐喻;诗中“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梯子”是一重隐喻,“我”可以是隐喻,也可以是事实叙述,“梨问另一个梨”,推向“所有的梨,都在问梨”,则为哲性追问。当然,所有这些意象和叙事似乎指向一个总体隐喻的生成,然而,“日过中午,不闻梨喧。日落山梁,不见梨黄”这一客观实事的呈现,以其“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自足与冷静,轻轻解构了前面的所有隐喻。尤可贵者,在各种隐喻漂移中,事物的诗性仍然得以持存,这首诗仍然很美,“弗罗斯特不在,只有鞍在,我不在,只有箩筐在”,“另一棵树说,也许是风绿,雨湿,光荫”,“日过中午,不闻梨喧。日落山梁,不见梨黄”,意象与节奏,全然是纯正的中国古典诗语,鲜活,浏亮,略带朴拙,来自唐诗宋词,更来自古老的《诗经》。这首诗未必是李森最好的诗,但可以清楚看到,李森在当代诗坛确实形成了李森式的诗艺与诗境。
隐喻:暗香浮动月黄昏
诗歌起于隐喻,现代诗歌起于隐喻的自觉建构与消解。诗歌史上,从含蓄雅致的中国古典诗词,到石破天惊的艾略特、庞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隐喻传统。隐喻的好处在于它沟通了事物(或观念),也超越了事物,弊端在于远离了事物,也遮蔽了事物,以至于一个美人经常需要从一堆美人的隐喻中抽身,一个梨也经常需要为一个梨的隐喻正名。李森之诗对隐喻的运用,充满了自觉与警觉,他经常说:面对世界的时候,语言只能追问而不能抵达。因此在他的诗中,隐喻总是在不断生成,又在不断消解,观念、隐喻、事物总在不断流转与切换,某些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诗人的机智,事实上,这种生成、流转、消解的自由与自然,更多来自于语言本身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这是一个出色诗人的标志。“寒冷的初春,与发馊的传说无关的蝴蝶还没长出来/它们嫩叶的翅膀,夹在时间的门缝里”(《寒冷的初春》)这段话至少建立了三个与蝴蝶相关的隐喻,“发馊的传说”、“嫩叶”、“时间的门缝”,然后,诗人马上说:“为了挣脱隐喻,蝴蝶拼命拉长翅膀”,通过“拉长翅膀”这一鲜活的“事实”,解构前面三个习见尘封的隐喻,呈现出蝴蝶隐喻的生成与消解过程,极富现代意识。
李森解构隐喻,消除文明层积的各种陈垢,往往是通过回到栩栩如生的生活世界,回到朴素的事物,回到语词舌头的柔软来实现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诗学理想:艺术就是使事物重新苏醒的技艺。①李森:《荒诞而迷人的游戏》,第207、6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啊,我满怀赤诚到来,奔向草莓。一直奔走。/我要来领回飞蛾。我要来安慰一把吉他,一个发音的圆孔”(《废园》)。最后一句,“一个发音的圆孔”,可以说瞬间解构了前面关于爱情的诸多隐喻,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隐秘指向的隐喻,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建构,还是解构,都意味着新的隐喻生成——尽管有时候是不自觉的,这是语言的决定”。②李森:《荒诞而迷人的游戏》,第207、6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由于隐喻与事物的多样圆活跳接、转换,李森诗中隐喻绷满了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多维张力。“随着太阳下山,小河漂满了鱼鳞/随着晚风到达,大鱼领着小鱼,进入天堂,坠满了树上的叶”(《童年的鱼》),“我(注:李树)会长成冰棱之花的一圈圈眼影。练习哑语,从叶中出来”(《壁炉》),“它在时间的虚静里开显,我在镜外徘徊。我被喧嚣捆绑,它从容不迫。/我天天抚摸啊,我们之间那块透明的玻璃。看谢了粉红的冰霜”(《紫薇》)。“冰棱之花的一圈圈眼影”、 “看谢了粉红的冰霜”这些诗句至少都有三重以上的隐喻层叠,却明净空灵,如同长夏覆盖着清凉树影的溪流,变化多姿,令人难以捉摸,却又整体清亮。
思幻:草色遥看近却无
李森是当代诗人当中少有的、对哲性智慧充满了虔诚热爱的人,两千年前困扰柏拉图的问题如今还在困扰他,思想-语言-世界互相照面、互相牵扯的复杂联系,如今还真诚地盘旋在他脑际。作为哲学家赵仲牧的学生,①李森:《信使》,施惟达、段炳昌主编:《薪火相传待后人——赵仲牧先生纪念文集》,第123—141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他至今还在云南大学的讲台上,一年一度,坚持一字一句地给学生教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老子》等哲学经典,他把诗人的气质留给了课堂,把哲性的智慧带进了诗歌。看看从《摘桃女》至《桃可知》的入思路径吧:
摘桃女
桃树可知
桃花开了
桃树可知
桃花结桃
桃树可知
桃子红了
桃树可知
谁来摘桃
桃可知
桃树可知
桃花开了
桃花可知
桃花结桃
桃子可知
桃子红了
摘桃可知
谁在摘桃
从前一首到后一首,都行进在《诗经》刀切水洗的意象与韵律中,然而追问却在步步逼进,从一般设问拟事“桃树可知,谁来摘桃”,到追问本身“桃花可知,桃花结桃”、“桃子可知,桃子红了”,充满了元反思的意趣,从而返璞归真,化身朴拙,这和笛卡尔“只有我在怀疑着,无须怀疑”异曲同工,李森的诗学旨趣可见一斑。当然,这也是西方一流诗人如博尔赫斯、史蒂文斯的旨趣,目的都是为了成就开显诗歌本身的“元诗”。
在《屋宇》、《春日》、《橘在野》系列组诗中,我们注意到诗人“我”的随时在场,“我”是事物的见证者,也是意义的引领者,是诘问者,也是坚守者。“我”在每首诗中的出现,丰富了诗境内部交错的筋络和肌理,更重要的是,方便了诗歌戏剧性叙事节奏的展开,使诗境杂花生树,摇曳多姿。在抒情诗中,虚拟戏剧性叙事,李森诗歌作出了自觉的探索。我们知道,西方诗歌史上,最为显赫的诗学传统有二:一是庞德、艾略特的隐喻派传统,一是弗罗斯特、威廉斯的经验派传统;前者总指向主题神话,后者必回归生活世界。在此而外,李森还发现了第三类诗人——布莱希特,他把戏剧性、叙事性融入诗歌,吸取民间歌谣一唱三叹的语调,创造了戏剧化叙述体诗歌。②哈罗德·布鲁姆等:《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我们在《屋宇》组诗中,可以看到李森向布莱希特的致敬与超越,这组诗非常成功地进行了文体试验,探索戏剧体诗歌的形式韵律、叙事节奏与意境营构,以《敲门》为例:
曾记得在高黎贡山下,有一间木头房子。
房外有一堵石头挤着石头的墙壁。叶挤着叶。
有一块门板立着,没有门臼。没有锁链,只是立着。
曾记得有一个孩子尝试着去敲门。
他对里面的人说,请开门吧,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里面没有回音。
他天天去敲门,门始终未开,只有花开。
他只好对着门缝说,我要对你说的那句话是:
“你是我的爱,我要告诉你我的恨。”
这是他童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次敲门。
当然,李森诗歌中的智性追问与戏剧叙述,总是诗性的,虚拟的,在诗境中结成透明丝网,若有若无,流动不居,“他是谁?是飘过南高原的年华——生出风和雨,抚摸井眼的空无”(《年华》),虚拟设问中,“年华”一度具象化“飘过”,由虚入实,二度具象化,“生出风和雨”、“抚摸井眼”,然而“井眼的空无”,骤然抟实入虚,遁入智性的空无。虚虚实实,无中生有,李森诗中布满着这样的虚拟之网,生长出许多玄意的蔓草与花枝,眼神迷离,意态飘忽,别具风致。
物性: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这个工具理性与消费理性宰制一切的时代里,在这个数千年文明覆盖的星球上,事物要呈现其本真的样貌,要与诗性与神性照面,需要一双明澈的眼睛、一颗温柔的心来引领与照亮。
李森是温柔的,他有一颗朴素农人的心。这颗心与土地、谷物、农具互相亲近,相依为命。他经常在课堂上讲,农人的心是真正体贴世界的心灵,在真正劳动者面前高谈诗歌,尤其谈论美学,是可耻的。不难理解,李森在诗中时时回首故乡,一往而情深:“流浪者呀,云雾种的青草在山坡上寻找顶针/母亲又围好了篱笆,等你牵着马去打滚”(《告别冬天》),“太想念我梦中的哥哥/那是一条在黑云下犁地的黄牛”(《最后一天》),“中午时分/我模仿一只犁/在地上/弓着背”(《映山红》),重返土地与故乡,是李森亲近事物的重要途径,故乡高黎贡山上的日月、山下的花红果黄,让他与世界肌肤相亲,轻松地抟住云的风流、玉的温润、土的生糙。其次,以哲性智慧及诗学反思的锋刃,剃除横亘在诗歌之上的诸多文化或诗学陈旧隐喻,也是其照亮事物的重要前提。
李森以其复归本真的诗性智慧,引领与敞亮了物性。他的诗学理念认为,“陌生的事物彼此映照又各得其所,陌生的事物或观念放置在一起,这事实上是存在的样态,但在文化心理中,人们忘记了陌生的事物就在一起且永远在一起的自然状态”。①李森:《荒诞而迷人的游戏》,第18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他的诗歌复原了这样的自然状态,如《马蹄铁》:
高黎贡山下寨子里的一块马蹄铁
鼠年的最后一点锈迹吞噬了它
但是,那半个椭圆还在夕阳下对抗着
山顶石坎上留下的那一串乐谱还在疯响
它代替一匹马的声音生锈,纪念一个消失的形骸
只有它还能听见那匹马在异乡嘶鸣
那个声音,那个形象,成了这半个生锈的椭圆
马蹄铁锈迹残败的物性,是那匹不在场的马在岁月中的飞扬。两者并置,对话,消磨,为我们开显了一个崭新的物事世界。李森诗中经常出现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的并置、呼应、映衬,比如金沙江的莲花与玉龙雪的犁铧、壁炉与李树、“我”与紫薇。在他点石成金的诗艺引领下,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物生成了诗的信念,产生了新的秩序,或者说回归到了物物陌生的自然。
伟大的艺术从不模仿世界,相反,世界模仿艺术。李森的诗歌让我们重新看世界的一把线条,几瓢波纹,看具象物质的色彩与声音,看它们如何唤醒并改造我们的感官。“曾在岩羊心中生出酸涩,又鼓出喉结/最终,馈赠给我一箩筐翠绿的小锁”(《橄榄》),“这里,今日的一局棋,下在池塘。水面的黑白子,跳着破碎”(《银杏道》),“让我看见,它在磨海上的齿痕”(《朝阳》),“鱼群是刀锋,水光是磨石,来回磨砺,永不停歇”(《屋宇》),这些令人耳目清新口鼻爽亮的隐喻与描述,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锐敏才具,这是如同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把月、珠、泪、日、玉自然挽合在一起的才具,只有这种才具才会长出温柔的触角,缓缓抚摸事物的细腻,婉转与迷人之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李森还是一个视觉通透、嗅觉灵敏的艺术批评家。多年来,他浪迹在造型艺术的江湖,与艺术家为友,与美为友,与创造为友,“江山笑,烟雨遥”,潮涨潮消间,他熟稔了造型艺术的点线面、体量形、光色影,也不动声色地俯瞰了当今中外“滔滔世上潮”的诸多艺术浪头。所以不难理解,李森在体物叙事间,宛如画家,随心所欲地涂抹和揉搓物事的形状、色彩与质地,欣赏一下《山歌》中的形色,“万千蝌蚪跳出牛铃,草花红了佛音,围着泥塘/春水苍苍,佛音粼粼,绿词在牛铃中蹦跳不停”,春水为佛音赋形,蝌蚪为牛铃赋形,牛铃为绿词赋形;而草花为佛音敷色,春水又为绿词和牛铃敷色,寥寥数语,一帧清脆的水彩。“童年,胯下的竹马在水磨旁飞奔,大雁指点我的江山骑着长弓” (《童年》),大雁与长弓,其形,拈自水墨山水画中的远山一痕;“多少年来,我在高黎贡山之麓,滚动一枚太阳/眼看着它渐渐苍白,沉入浪下,盖上千里雪” (《云雀》),其色,几乎自然让人想起台湾画家刘国松宇宙洪荒的抽象绘画;“人去屋空。潮湿的钝,在瓜分一筐凿子”,其质地,虚与实、湿与涩,俨然塞尚静物笔触。可见,诗人李森确实是在其诗中,自然分有了画家的生花彩笔。①李森:《我心中的画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气象:独立苍茫自咏诗
事物或者说世界,被诗性智慧引领、敞亮以后,不光呈现出宋词小令马远山水般的精致妩媚,而且还际近、化入了苍茫的大气象:一切气韵生动的事物都鲜活在苍茫的背景之下。②王新:《诗画乐的融通——多维视阈下的艺术研究》,第70—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李森之诗,时时在纯净明澈的精致背后,隐现出苍茫的景深:“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檐下需要打开,墙需要洞明。/四野需要天下,我需要仰望命运”(《窗户》),“啊,我高大的主人,黎明四脚匍匐,追逐夕阳,朝你涌来,西天的火焰”(《书房》),“千年追随着妹妹的光坠啊,挂满饮者心房/千年喷着鼻息的坐骑啊,从林中奔出/千年锁着铁的鹰隼,让我放飞天下”(《一千年后》),“日落西方/橘在野/日落橘/苍茫在橘”(《橘在野》)这些句子由象及境,由有入无,际化苍茫,臻于大境。有大境界者,方有大气象。朗声诵读李森《霍去病墓前的石马》吧:“祁连山,祁连山,祁连山/所有苍蝇都服从他们的翅膀/所有明亮的翅膀都服从它们的苍蝇/只有英雄的石马服从它的风化//大漠,大漠,大漠/我的空白向四面八方铺开/他的马蹄声,他的音符堆积如山”。
英雄的石马,在空间中悲剧性地对抗与剥蚀,英雄的马蹄声,响亮而轻快地穿透时间,从质感到动感,从形象到声音,从空间到时间,意象单纯,气韵铿锵,音声朗朗,往来纺织着音、形、色、生与死:英雄的悲和伟,都业已际化苍茫,显发出磅礴的气象,这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以来古今罕见的佳什。
如果说,从大人物、大景观生发大气象,较为常见,较为容易,那么,从小事物,而且是精致而美的小事物,生发出苍茫的气象,则更需手腕,尤赖胸次,看看《莲花锁》:“红润为我守着莲叶,圆锁为我守着莲花/蝴蝶为我守着脂粉,蜻蜓为我守着翅膀/工蜂为我守着刺,我守着风月,等万物轮回/可惜啊,那朵莲的到达是偶然,它的遗忘是永远/可惜啊,那朵花的无辜是盛开,它的远去是莲子”。
莲叶、圆锁、蝴蝶、翅膀、刺,全诗渐次绽放出精致而葱茏的生命意象,最后两句,一声喟叹,朗然窥破生命的无奈与无常,霎时推出苍茫的景深,小小莲花由此获得了苍茫气象,于此可见,李森精神腾越的高度。
纵览人类文明史与艺术史,有一点需要言明,所有思想与艺术创造的大气象者,都必然各个际遇了神性,柏拉图、尼采如此,海德格尔如此,王维、伦勃朗如此,甚至牛顿与爱因斯坦亦如此。一切物事,只有在神性的背景中,才会真正显发苍茫的气象和生命的机缘。可以补充的是,李森迷恋佛陀,也迷恋斯宾诺莎, 一六六〇年镜现在斯宾诺莎镜片中的上帝,③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洪汉鼎、孙祖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今天同样映照着中国南高原上的诗人李森。自然,迥立在苍茫背景中的李森,有分外的悲怀:“一只布谷鸟,夹在身前身后,两个美梦之间,悲如铁”(《秧苗》),“缪斯妹妹,草叶青青挂满雨水,英雄的心空空如也” (《青草》)……
至此,李森诗歌的现代意识已无须再提。值得指出的是,他多年在汉语古典诗艺中,含英咀华,涵养出来了经营意象与敲锤韵律的一流感知能力:“光阴,在一棵海棠上/炼成一点粉红,两点粉红”(《春日迟迟》),此般意象精绝过人,是贾岛推敲、也是杜甫吟安出来的意象;“有过一出戏,有过一个人。有过一种声音,一些文字。一种饥饿”(《茨维塔耶娃》),此种韵律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是《国风》流淌的韵律,平仄起落的高古乐感,起于李森舒张的脉管深处。
当然,写诗是李森的才情,教育才是李森的抱负。“寄傲琴书,以待天时”,是横亘在李森胸中的闷雷。在这个大雅不作、弦歌荒率的时代,他怀着执求大学本真精神的古道热肠,以其幽默的刀锋,“因为我的声音锁在你们在嘴里。/我的刀锋和激情都藏在你们脚下”(《猫头鹰》),无情地解剖与批判思想武功独霸的专制主义之鸟及一切学术大锅饭体制。①李森:《教育的危机》,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显然,李森是孤独的,也是隐忍的,一如他笔下那枚业已穿过苏联寒冷坚冰的“紫葡萄”:
一枚紫葡萄穿过苏联寒冷的坚冰
为了隐含那一点酸涩的汁液
不能停下来,不能破裂
看见这枚葡萄的人,拥有这枚葡萄
直到冰刀的那一点光被它收敛
王新,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