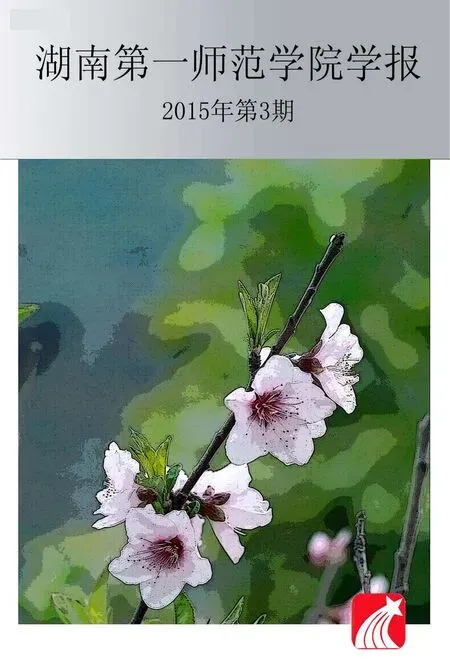语文类师范生技能训练的哲学思考
侯志成
(长沙师范学院 师范预科部,湖南 长沙 410100)
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教师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职,语言是基本的传授工具,至于语文教学更是内容与方法一体,这些都决定了语文类师范生的教学技能训练,或者说师范生的语文教学技能训练都是特别需要重视的。关于这一方面的经验文章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满足于经验的积累,而不能进一步使之发酵、升华,就势必难以有质的飞跃,要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反思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从哲学的角度看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执两用中”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礼记·中庸》载孔子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1]所谓两端,即“过”与“不及”,都是对“中”的背离。这里好像只是一个分寸的把握问题。事实上,三分法(准确而全面的说法是“一体二分三合”)不仅是量的尺度,也是结构上的模式。如天地人三才,日月星三光。老子《道德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辩证法的对立与统一合起来正好是三,民间更常说“事不过三”。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运用到语文教育中来。什么是语文教育的“两”与“中”?笔者认为,对于教师来说,“两”就是学生和通过语文呈现的世界,“中”就是语文教师。这里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教师中心论已经声名扫地了,但是“教师中心”就没有合理的意义和必要的地位吗?以教师为权威、为道或真理的化身、为教学的完全主宰,这种“教师中心”自然是不合时宜了。但是,天地万物自然而然是各自中心而又互相中介的,以中心来否定中介固然是不对的,反之,以中介来否定中心也是偏颇的。在教育上,学生为本、教师中心(中介)与教育内容(是对世界的反映,表现为广义的和狭义的教材,狭义的教材是桥梁和示范,广义的是拓展和归宿)之作为终极正好也是一个完整的三位一体。因此,一味地否定教师中心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作为一个教育者,尤其不应该跟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孔夫子能够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是与他倡导的中庸哲学分不开的。在全面把握两极的基础上,教师的自我才会有中允的定位。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际上不止己与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就说出了敌、我、友三方的分别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种更全面的观点。在一个尚不能在其中游刃有余的世界里,学生就好像是遭遇到了不怀好意的敌人,教师就是帮助他打破这种困境的朋友。站在教师的角度,明确自己的定位,帮助他的学生朋友走近并走入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使命,认清我你他,我们才好通力合作,共度难关。
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会在学生与语文之间架设一条沟通的桥梁,起到中介的作用,而一个蹩脚的语文教师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不是中介而是“中界”,也就是在二者之间起到划界和阻断的负面效果。众所周知,语文是人存在的方式和工具。人一生下来就无可选择地遭遇他的母语,这不是一般的兴趣学说可以解释的,语文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好的语文教师如同可以借力的好风,送人轻举逍遥于精神的乐土,坏的语文教师则泯灭一个人对语文已生的浓浓挚爱,逐渐变得心灵干涸。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命运实在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二、技能训练的意义
语文教师怎样影响一个学生的命运?最终的答案是技能。
教师总是通过技能来执行任务,学生也总是通过教师的技能来感知和领会。当一个学生感觉不到教师在运用技能,有可能是教师技法高超而“润物细无声”,也有可能是学生已经到了不必教的地步,因为“教是为了不教”,一个学生能够直接与意义相周旋了,就不问形式了,语文教育的使命至此也就完成了。另一方面,当一个教师感觉不到技能,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根本不知教为何物,一是他已进入化境,无招胜有招,出手即是招。二者之间是一个过渡,靠近低端的是入门阶段,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靠近高端的是正处于自我修行但还没有炉火纯青的阶段,大多数教师都会毕生停留在这个阶段,只有极少数肯用功又有一定悟性的人才可望达到最高境界。
世界从人格和人际的角度可以归于我、你、他的关系,从具体构成来看则是物、身、心的组合。粗略地说,物就是外部世界,心就是内在世界,身则是直接的世界。哲学界从传统的“形而上”、“形而下”这对范畴之外又引出“形而中”。其实,形就是形,它是直接存在的,一般泛指一切的物质。“形而上”是它的相对概念,指看不见的道或规律,为了对称,就用“形而下”来指形本身,已经是累赘了。后来,“形而下”用得滥了,尤其是身体哲学的兴起,人们觉得有必要区分物和身,就有了“形而中”。这也是语言中的回归现象,最直接、最简单的东西最后反而用最复杂、最迂回的形式来表现,这也体现了认识的螺旋式上升吧。认识已经大成了,现在回归简单,就用“心”指代形而上,“身”指代形而中,“物”指代形而下。
在语文教育中,教师所凭借的教材之类是物,没有教师的运用则不起任何作用,或者说只是等同于学生自学所用之物;教师的文化修养、专业内涵、理论储备等等都是属于心的范畴,隐而不彰,它们最终必须通过教师的身体活动来表达,而身体活动,在这里就是一个人的技能。很明显,这个技能比一般所说的师范生技能要广义些,可以说是教育哲学层面的。当前技能训练的收效不明显有很多原因,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人们易于就技能而训练技能,境界必然不高。这是因为,技能固然由身来执行和表现,但离开了心的悟性和灵气,就只能剩下邯郸学步了。归根结底,物身心三者是对世界构成的一种划分,既然有三,就缺一不可。在三者之中,身是技能的承担者,物是技能的对象、工具和场所,心则是技能的灵魂和主宰。齐白石能够从一个乡下木匠成就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就是他的心量和心境远远高于普通的美术工作者,那些只求混口饭吃的匠人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就算是匠人,也有高下之别,其中心性之别仍然是最为关键的。没有基本的技能而侈谈造诣必然是眼高手低,满足于技能的获得不思创造必然是故步自封,一个新手最首要的当然是技能,但绝不是不假思索的技能。思索,当然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前人的认识就是后人进步的阶梯,可以比较、取舍,不可以无视,这就是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了。但是理论是辅助技能的,不应该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三、技能训练在课程中的位置及其内部组合
《庄子·养生主》有个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里面有一句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3]权威的解释把“进”说成是“超过”,自然有道理,但不全面。一般把“大道”与“小术”相区别,似乎“道”一定比“术”高明。其实道与术须臾不可分离,道必形之于术,术必循道而有其用,这里的道、术与上面的身、心是相对应的。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有的人好虚,本不是问题,但不能落实,就必然成为纸上谈兵。有的人务实,一般来说是优点,但是拒绝理论,他的进境也就很有限了。所以说由技进于道固然值得钦佩,反之,由道进于技也完全应该提倡,总之是要由个人实际出发,进到比较全面的境界,才是殊途同归。师范教育要培养知识和技能兼备的全面人才,但是在理论熏陶与技能训练的结合上常常不易处理。
就一般情况而言,年龄较小的偏于技能,年龄较大的偏于理论,比如初中进来五年制的学生更热衷于怎么教,高中进来三年制的学生就比较能够接受从理论讲起。从事情发展的初级阶段来说,先关注怎么操作是自然的,然后才问为什么,而从职前教育与正式从业的关系来说,先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修养,技能定向才不会失之于盲目。一个人的类型或许有所偏属和侧重,但其个人的发展也可能呈现阶段的交替。这些问题在个别教学的时代好解决,在班级制教学的模式中怎样处理呢?水火不容吗?有必要进行辩论,赢者就是真理吗?有可能和平共处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吗?这些问题目前都有待解决,值得探索。笔者以为这涉及组织的方式问题。在管理学上有一种说法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人际组织问题。前提是要有管,不管,就散了,个人是无从谈文明的。但怎样管、管多少是大有学问的。组织涉及主体、对象、任务、时间、场所等等内容的分配,传统儒家讲“大一统”,道家则讲“无为而治”,看似矛盾,其实互补,中国的历史正反两方面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一统”在于社会机体的有机协调,但过强的组织就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上级干涉下级甚至越俎代庖,最终必然是万能的上级与无能的下级难以同心协力,上面腐败,下面无奈。“无为而治”在于社会成员的自在发展,但过于自由散漫必然造成由于各人先天后天种种机缘的差别所导致的强弱分化乃至弱肉强食。看似静态的“大一统”是以动态的“统一”来维持的,而貌似动态的“治”却是通过似乎静态的“无为”来达到的。可见大一统与无为而治虽然取径不同,而所归一致。要避免上述相同的不利结局,只有事先结合两种方法,才可望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怎样结合?具体的细节肯定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讲清的,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在动静关系上做文章。
周敦颐《太极图说》指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4]有动有静是无疑的,但是如果只有动静,它们在何处互为其根?必有第三者才能圆满,这个第三者就是混沌,混沌包罗万象,是动静转换的场所,是各种可能的大本营。合而言之,静是大体的结构,是秩序和平衡,就是学科本身的自在结构;动是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突变和冲动,就是学生基于最近发展区而跳起来摘果子的行为;混沌(或简称“松”)则是二者转换的中介,是施教者给予宽松的教学计划以及教学过程与氛围。静动松应该有着自由的组合与转换,尽量少一些教师的预设,而多让学生走自己的路,合起来就成为“无为自化”。当代的混沌学、自组织等理论是对中国古老哲学的科学回应,也是我们技能训练和习得的有益借鉴。做梦和自发练功去病是两种自组织现象,分别是心与身的自组织,又如自由市场乱中有序是社会层面的力证。一棵树的枝叶分布记录着无序中的有序,一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也是自组织形成的。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干预太多,不是自组织,而是“他组织”,这样就不是促进了技能的习得,而是干扰、延缓了这一过程。终极而言,世界是一体的、自在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上,总可能找到自组织的存在。自组织有其自身的物身心结构,即外部环境、存在形式和功能性质。自组织有其自身的我你他关系,即主体、对象、中介的分际与结合。自组织有其自身动静松的运行方式,即基础、机遇与激动的相生与制约。自组织与他组织是相互转化的,理想的技能训练模式就是要找到各相关因素的自组织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互相外在地起着消极影响。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具体的情形,一般地说。信息的足够开放、评价的适度宽松、行动的必要自由都是自组织的要件。信息的开放如学生对未来职业的知悉、对全部课程计划的实际了解,特别是课程计划本身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评价方面,或许应当成为教师对学生进行训练的主要任务和手段,不应该搞一锤定音,宜着眼其过程性、综合性、引导性。根本的还是学生主动权,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学生的入口关要尽可能把好。尽管兴趣可以培养,但终究不如入校之前就已经自己志愿从教的,特别是已经另有志愿的人更难强迫,学生为本首先就要从这个根本做起,教学双方互相情愿才好同心。至于无可无不可的学生常常是多数,就可以从人的潜能和全面发展来激发、引导,当然好好发挥兴趣型学生的带头作用是重要的。
关于技能训练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是老生常谈,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对技能训练的根本性反思,这里也进入到本文最后要强调的师资。所谓根本反思,就是要反思到根本。思属于心,反思之反(返)就是要返回到身这个根本。身体哲学的要义是回归身体,但不是只要身体,而是贯彻以身为本,使各种相关因素全面有机协调。中国的传统“以身作则”首先就贯彻在教育之中。在语文教学技能训练师资上,以往常常是小学一线优秀教师上调或兼职担任,这是符合“现身说法”的要求的,但往往失之于理论厚度不够,主要在于一直以来的教育理念和导向问题,这种影响是全局性的却又是教师个人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是技能型的教师往往对理论重视不够,那么与之同类的学生就能够得天独厚了,而其他类型的学生则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新时期新课标背景下,我们对教学法师资本身也应该有“技”与“道”互观的全面视野,如前文所述,才能更好地训练我们的语教师资。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29.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5.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中华书局,2009:106.
[4]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元公周先生濂溪集[M].长沙:岳麓 书社,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