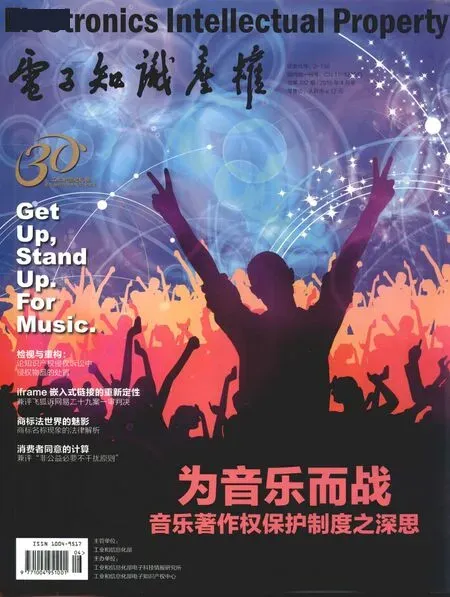音乐著作权制度的体系化历史与本土化进程
文 / 熊琦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一、引言
纵观著作权制度发展史,音乐著作权制度始终是矛盾和争议最大的领域,著作权立法变革与制度创新也总是首先在涉及音乐作品的部分出现。从1908 年涉及录音制品制作法定许可的White-Smith Music Pub. Co. v. Apollo Co.案,到2005 年涉及间接责任和交互式网络传播的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都具有载入史册的意义,都发生在音乐著作权领域,也都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为各国著作权法变革确立了影响深远和值得效仿的范式。之所以音乐著作权问题一直是著作权制度变革的始作俑者,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音乐作品受新传播媒介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音乐作品传播和利用方式的特点,因而与文字作品和电影作品相比,音乐作品更容易受到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从获取方式上看,音乐的使用者欣赏音乐的方式是听觉上的获取,这种获取方式更容易接受其他传播模式;从客体类型上看,音乐与其他类型作品相比,所占空间较小,所以在适用新技术使其与旧载体分离和新载体结合上成本更低因此,从录音技术、广播技术到网络技术,大部分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社会效果,都是首先出现在音乐领域,这主要是由于音乐的表现方式始终与传播技术的目标契合,而且音乐的使用总能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伴随传播技术的革命,音乐的传播模式也历经自动钢琴(player pianos)、自动点唱机、有线电视、卫星广播与网络流媒体等多个时代,并对著作权制度的变革趋势造成重要影响。
第二,音乐著作权的产业形态更为多元。音乐著作权一直是著作权法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从客体上看,音乐著作权中的“音乐”,既包括音乐作品(musical work),也包括基于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sound recording),甚至还有其他类型作品中包含的音乐元素;从主体上看,音乐著作权的主体涵盖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出版者,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商业用户、最终用户,以及集体管理组织等。在历史进程中,音乐著作权客体与主体的复杂性,同样衍生出了庞杂的音乐产业,其中既有涉及音乐作品音乐出版公司,也有涉及录音制品制作和发行的音乐唱片公司,到网络时代更有涉及数字音乐传播的各类互联网企业加入其中。在发展进程中,不同产业类型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存在竞争。特别是在立法问题上,各方都力图为自己争取更广泛的权利范畴,并阻止其他产业主体分享新兴市场的收益,最终导致立法进程陷入困境。
第三,音乐著作权的权利类型更为复杂。音乐著作权体系由音乐作品著作权与录音制品著作权组成,由于两者的客体形态和利用方式不同,因而著作权法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权利与许可类型。就音乐作品著作权而言,其权利范畴涵盖了法定著作财产权的所有方面,但由于利用音乐作品的目的旨在为制作录音制品和公开表演提供基础,为了保证音乐作品得以被更多主体所接触和利用,著作权法设置了制作和播放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允许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在支付法定版税的前提下在法定范围内利用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适用,也意味着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将排他性的权利弱化为非排他性的报酬请求权,使音乐作品著作权呈现出与其他作品类型不同的特殊性。就录音制品著作权而言,由于其属于邻接权,因此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的权利范畴小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但由于录音制品利用频率和范围不断增加,录音制品制作权人也在积极寻求立法上的变革,希望能够扩大其权利范畴。
音乐著作权权利类型的不断增加,音乐产业形态的日趋丰富,加之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音乐著作权成为著作权法中涉及利益分配最为复杂的领域。在因网络技术普及而遭遇大规模盗版的前提下,如何通过调整音乐著作权制度来拯救音乐产业,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法律难题。1.根据国际唱片产业协会的统计,数字音乐的收益实现了39%的增长率,不但在总收益中的比例增长,而且总收入也稳步增加。在美国等主要音乐市场中,数字音乐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总收益的一半以上,其中网络流媒体音乐收益的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1.3%。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全球音乐市场的总收益仍然在下降。相关数据来源参见国际唱片协会2014年的官方报告,IFPI: Digital Music Report 2014: Lighting Up New Markets, IFPI (201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音乐”为2015 年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正是因为音乐产业形态和音乐著作权制度都处于颠覆性的转型期,唯有音乐著作权制度契合音乐产业形态的变化,才能真正保护和激励产业的发展。2.与之前笼统围绕“知识产权”和“创新”设计主题不同,2014 和2015 年知识产权日主题来自著作权领域的电影和音乐。这种更为具体的选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互联网给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持续性冲击,以及数字时代著作权制度变革的停滞,已经引起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忧思。2015 年度主题中的“get up”和“stand up”虽然直接引自一首歌名,但此处显然蕴育着期待音乐著作权规则能够重新得到认可,以及网络时代的音乐产业能够从低谷中复兴的愿望。从我国本土音乐产业和市场看,由于历史上制度完善和执行上的问题,使得我国音乐产业在网络时代表现出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国只能在发达国家音乐著作权变革尚未完成而无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解决本土产业形态的特殊化带来的新问题。然而要想成功构建本土化的音乐著作权制度,肯定无法完全抛弃现有产业和制度基础另起炉灶,只能在全面梳理和深刻总结音乐著作权体系形成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避免全盘重构导致的过高制度成本,进而为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创新提供可行的立法经验和取舍方法。
二、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形成的历史解读
从制度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诸多著作权制度创新都首先产生于音乐著作权领域。从权利类型看,表演权和广播权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对音乐作品传播方式的回应;从许可模式看,法定许可和集中许可都是首先适用于音乐著作权领域。音乐著作权之所以成为著作权制度变革的“试验田”,原因在于音乐作品的利用范围和方式最易受到传播技术的影响,并导致既有权利体系无法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市场需求。
1.作品收益与使用的协调:音乐著作权的独立
音乐著作财产权独立于一般著作财产权体系,始于录音技术带来的音乐作品利用方式扩张和新产业主体的加入。独属于音乐产业的著作财产权类型诞生,乃是两种需求所促成:一是新技术带来的作品利用方式需要以财产权的方式加以确认,二是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收益需要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以财产权的方式合理实现收益的界定与分配,能够激励对音乐产业主体创作与传播行为的投资,并发挥音乐作品的最大效用。然而,由于相关主体在音乐产业发展过程中会因利益分配而不断博弈,引起关于权利的设定范围和配置模式也同时成为关键的争议对象。
当自动钢琴成为记录音乐的新载体后,音乐作品开始不再局限于以纸质媒体作为唯一传播渠道,也导致作为传统音乐著作权人的出版者与掌握新传播渠道的自动钢琴生产者之间就“录制音乐”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争议。在White-Smith v. Apollo 案3. 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 v. Apollo Co., 209 U.S. 1 (1908), p. 18.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自动钢琴对音乐作品的记录不属于复制权的范畴, 导致出版者无法分享自动钢琴利用音乐作品获得的收益。但随后出版者在影响修法上取得了成功,自动钢琴记录音乐作品被视为“机械复制”。同时为了平衡新旧产业主体的利益,立法者专门弱化了涉及机械复制的著作财产权。一旦音乐作品著作权人首次许可他人机械复制,则其他自动钢琴生产者可以在支付法定版税的前提下无须权利人同意而实施机械复制。4. Act of Mar. 4, 1909, Ch. 320, § 1 (e), 35 Stat. 1075.立法者认为如此安排一方面可以促进音乐作品的充分传播,另一方面则能够防止少数自动钢琴生产者获得市场垄断。5. See Al Kohn & Bob Kohn, Kohn on Music Licensing (4th ed.), Wolters Kluwer (2010), p. 733.1909 年建立在“机械复制”上的著作财产权及其限制制度,可视为音乐著作权特殊性彰显的标志,并贯穿模拟复制和数字传播时代沿用至今。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音乐著作财产权的特殊性,来源于音乐作品在利用频率和范围上的特点。无论在何种传播技术条件下,音乐作品的利用频率和范围都大于一般作品,使用者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如果坚持移植排他性的财产权制度,频繁的音乐著作权交易,将导致权利人和使用者皆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法定许可的适用,可以免除事前协商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音乐作品的传播效率。第二,音乐著作财产权的特殊性,体现在法定许可对音乐著作权的限制方式上。法定许可的本质,旨在限制音乐著作权人复制和发行两项权利的排他性,他人利用音乐作品的合法性,并非源自权利人的许可,而是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音乐著作财产权的排他性,仅在他人违反法定许可的法定要件时才得以彰显,而在其他情况下,权利人只对使用者享有“报酬请求权”。6.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其实同时对应美国法中的“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e)和“法定许可”(Statutory License)两个概念。从立法文本来看,美国著作权法115 条的标题采用的是强制许可,而111、112、114、118、119 和122 条却选择了法定许可的表述。其中111 条第一次在1976 年著作权法中出现时标题为强制许可,1999 年在没有改变条款内容的情况下将标题改为法定许可。从上述条文的内容来看,都是允许相关领域的使用者在提交使用通知和支付法定版税的前提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在法定范围内使用作品,同时当事人有权通过自由协商代替法定许可条款。可以说,美国著作权法语境下的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立法者1909 年第一次在115 条采用强制许可的表述后,之后的立法文本基本改用了法定许可。在美国版权局关于法定许可修改的立法文件中,强制许可与法定许可的表述也并没有严格区分。为了避免混淆并与我国著作权法保持一致,本文一律采用法定许可这一概念。
另一项保护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公开表演权”(Public Performance Right),虽然在设立上并未引起质疑,但权利范畴的界定则因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分歧而出现争议。在1909 年美国的著作权法中,公开表演权的成立要件,须以“以营利为目的公开表演非戏剧性音乐作品”为前提。在后来的相关案件判决中,法院也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不断对营利性做了相应的界定,也引起了音乐著作权人的不满。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分别在餐厅酒吧节目表演和广播节目表演等领域对相关主体提起诉讼,并使得法院认定上述情形下的公开表演行为具有营利性,7. See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s Highway: From Gutenberg to the Celestial Jukebox (Revised Ed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6-58.最后迫使立法者在1976 年的著作权法中对公开表演采取了更为宽泛的解释和更为严格的例外。8. See Copyright Law Revision Part 6: Supplementary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on the General Revision of the U.S. Copyright Law: 1965 Revision Bill 81, House Comm. on The Judiciary, 89th Cong., 1st Sess., Comm. Print,(1965), p. 14.
音乐著作权权利类型的不断增加,音乐产业形态的日趋丰富,加之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音乐著作权成为著作权法中涉及利益分配最为复杂的领域。
2.音乐作品与录音制品的分离:音乐著作权体系的复杂化
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音乐作品的载体类型也不断更新,从自动钢琴到数字唱片,公众接触音乐的方式一直与各类录音制品密不可分。然而,录音制品虽然长期伴随音乐作品存在,但其保护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无论在英美法系抑或大陆法系,录音制品上的权利保护都经过了录音制品制作者的长期斗争。由于产业分工的日趋细化,录音制品的制作水平和技术要求也日益提高,录音制品不再是对音乐的简单记录,而是制作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因此对录音制品著作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从现有立法来看,虽然无论是权利范畴还是权利属性,对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力度远小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但录音制品的著作财产权构造却最为复杂。
国际上将录音制品制作者权益纳入著作权保护,要追溯到1961 年的《罗马公约》,公约赋予了录音制品制作者复制权与二次使用报酬请求权,后者规定,如果以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及其复制品被直接用于广播或任何向公众传播,使用者应当向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支付一笔总数合理的报酬。1996 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WPPT),则针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录音制品著作权的范畴进行了调整,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的著作财产权除了已获得肯定的复制权、发行权和出租权外,还针对网络传播增加了“公众获取权”(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使得录音制品制作者得以控制网络传播录音制品的行为,另外二次使用报酬请求权也以“向公众广播与传播报酬请求权”(Right to Remuneration for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的方式得到了继承。不过,WPPT为了照顾各国立法传统的差异,采取的是一种“伞形解决方案”,即允许各国根据公众获取权的范畴自行设计权利类型。由于争议较大,各国的著作权法也都对录音制品著作权设定了复杂的限制机制。美国关于录音制品著作权保护的实现,仍然是相关产业主体推动的结果。虽然1971 年“录音制品修正案”(Sound Recording Amendment) 首 次将录音制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但在权利范畴的设定上对录音制品制作者却施加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复制权的范畴要小于其他作品的同类权利,新录音制品在制作过程中对原有录音制品编曲的模仿不视为剽窃;另一方面是录音制品制作者不像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一般享有控制广播、现场表演和现场播放在内的公开表演权。9.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将录音制品视为作品,而非大陆法系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客体,但从保护范畴上看,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区别。但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相似的是,录音制品上的著作权同样被集中于少数主体之手。由于录音制品的制作与发行的成本较高,因此其制作和发行皆须借助唱片公司的力量,唱片公司凭自身的经济优势,一般借助职务作品条款和转让合同成为录音制品著作权的所有者。10. See M. William Krasilovsky et al., This Business of Music: The Def initive Guide to the Business and Legal Issues of the Music Industry, Watson-Guptill Publications (10th ed. 2007), p.27.同时,唱片公司也组成了类似美国音乐出版者协会的“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IAA),主要负责涉及录音制品著作权的立法游说与保护等问题。11. See W. Jonathan Cardi, Über-Middleman: Reshaping the Broken Landscape of Music Copyright, 92 Iowa L. Rev.835 (2007), p. 849.RIAA 极力争取的是涉及广播和现场表演的“公开表演权”,但遭到广播组织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共同反对。广播组织认为,自己已向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支付版税,不应为使用音乐录音制品而重复付费;代表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则害怕录音制品制作者分享其来自公开表演权的收益。12. See Paul Goldstein, Commentary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 78 Va. L. Rev. 413 (1992),p. 414.因此即使录音制品制作者从公开表演中获取二次使用付酬权在其他国家得到广泛承认,美国仍然拒绝承认录音制品上的公开表演权。可以认为,随着投资者在录音制品制作上投入的成本日趋增加,对录音制品著作权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然而,作为音乐产业的先行者,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与广播组织却分别出于对收益与成本的考量,阻止录音制品制作者获得收取版税的合法性。录音制品著作权的加入,也意味着音乐著作权的权利配置更为分散,且权利体系更为复杂。
无论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还是录音制品制作者,都积极推进网络环境下的音乐著作权保护。但在网络传播音乐的设权范畴和分配上,各方之间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
3.数字化传播的普及:音乐著作权体系的形成
当互联网在20 世纪90 年代逐渐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后,网络传播音乐的合法性和设权问题也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阶层化”,使得形成于前网络时代的音乐产业主体地位发生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音乐获取渠道多元化,使用者接触音乐不再依赖传统的唱片发行;另一方面表现为音乐传播方式的转变,不但网络服务提供者成为了新的音乐产业主体,而且传统产业主体难以从网络音乐传播中获取收益。有鉴于此,无论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还是录音制品制作者,都积极推进网络环境下的音乐著作权保护。同时,在网络传播音乐的设权范畴和分配上,各方之间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进而在本已复杂化的音乐著作权体系上增加了新的问题。
美国首次涉及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的立法,是1995 年的“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案”(DPRSRA),其旨在增加一项保护“以数字音频传输方式公开表演音乐作品”的权利,将网络环境下的数字音乐传输纳入著作财产权范畴。DPRSRA 的通过,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与录音制品制作者共同推动的结果,对于录音制品制作者来说,其因制作和发行录音制品而向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支付的版税一直存在,而录音制品发行量却因网络音乐传播的兴起而大幅下降;对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来说,其也希望网络音乐传播能够成为新的收益来源。因此,DPRSRA 同时扩展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与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一方面将数字音乐下载视为复制和发行,并纳入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机械复制”报酬请求权范畴;另一方面承认了录音制品上的公开表演权,把数字音频传输的公开表演权赋予录音制品制作者。然而,在如何界定数字音频传输(digital audio transmission)的范围,以及如何设定其权利体系等问题上,各方仍然分歧不断。DPRSRA 在音乐作品著作权上的突破,表现在对音乐作品复制权和发行权的扩大解释,DPRSRA 在美国著作权法第115节中增加了“数字录音发行”(digital phonorecord delivery)这一概念,即“以数字传输形式实现录音制品的可识别复制”,13. See Digital Performance Right in Sound Recordings Act of 1995, Pub. L. No. 104-39, 109 Stat 336, § 4.使以数字音频形式传输数字音乐的行为,被视为包含了对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发行。在原著作权法中,录音制品的制作与发行属于对音乐作品的机械复制而被纳入法定许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对录音制品中包含的音乐作品发行只享有报酬请求权。这种以机械复制涵盖网络复制与发行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法定许可渠道即可包含录音制品制作者在网络环境下发行录音制品,无须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缔结新的许可协议,在扩张权利范畴的同时避免了增加新的交易程序;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或其他主体如需获得通过网络传播录音制品的权利,只需与录音制品制作者达成合意,避免了同时向两类著作权人申请许可。14. See 17 U.S.C. § 115(c)(3)(B).
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难题相同,录音制品制作者同样面临新传播技术对唱片发行收益的影响,数字录音制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大量替代了以唱片发行为代表的音乐商业模式,使得唱片产业的收益迅速萎缩。同时,由于录音制品制作者长期缺乏对公开表演行为的有效控制,因此更需要创制新的著作权类型以保障其经济利益。在此背景下,DPRSRA 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对网络环境下录音制品著作权的制度创新。然而,与模拟复制时代著作权人与广播组织的矛盾相似,因网络传播技术加入音乐产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录音制品制作者之间,同样从各自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利益出发,就新设权利的范畴和限制问题在立法上展开博弈,最终形成了如今纷繁复杂的录音制品著作权体系。针对录音制品的数字化和网络传播问题,DPRSRA 专门为录音制品制作者新增了以数字音频传输录音制品的公开表演权,一方面旨在使录音制品制作者得以从数字音乐的网络传输中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证广播组织非网络环境下利用音乐的行为不受影响。上述对权利范畴的取舍,主要体现在对“数字音频传输”行为的界定上。首先,数字音频传输录音制品的公开表演权意味着与模拟传输(analog transmission)无涉,说明录音制品制作者仍然无法控制他人非网络环境下的广播行为。其次,即使是网络环境下的数字音频传输,也并非全部纳入公开表演权范畴。考虑到法案起草时各方的商业模式,数字音频传输仅被界定为“预付费传输”(subscription transmission),即向按预先支付费用或其他对价的特定用户进行传输。15. 17 U.S.C. §114 (j)(14).当时符合“预付费传输”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音乐在线点播”和“付费收听音乐”等交互式使用,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付费用户的需求通过网络播放音乐,16. See Lydia Pallas Loren, Untangling the Web of Music Copyrights, 53 Case Western Reserve L. Rev. 673 (2003), p. 688.而诸如免费的网络广播(free webcasts)及其转播,则被视为数字音频传输的例外。17. 17 U.S.C. §114 (d)(1).
之所以当时对以数字录音制品公开表演权施以诸多限制,乃是唱片产业、广播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唱片产业认为数字音频传输对传统的唱片发行和传播产生了替代性效果,因此应赋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完整的公开表演权,以弥补其因网络传播造成的损失;18. See Bruce A. Leh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1995), p. 225.相反,广播组织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则认为,由于网络音乐广播与传统广播的本质相同,既然模拟传输时代的音乐广播无须向录音制品制作者付费,那么网络音乐广播亦不应由录音制作者控制。19. See Al Kohn & Bob Kohn, Kohn on Music Licensing (4th ed.), Wolters Kluwer (2010), p. 1471.考虑到各方的商业模式差别,立法者将“非预付费传输”(non-subscription transmission)排除在了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的著作权之外,广播组织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各种广播行为只要没有向用户收取费用,即可在无须录音制品制作者许可的前提下进行音乐广播。最终,在DPRSRA 框架下,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公开表演权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对于网络环境下独有交互式传输,著作权法赋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排他性的公开表演权;20. 17 U.S.C. §114 (j)(7), (d)(3).第二,对于少数符合法定条件的非交互式网络传输,例如超出特定范围的网络音乐试听,著作权法还借鉴了法定许可制度,赋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非排他性的报酬请求权,旨在弥补因网络音乐广播的听众再利用录音制品造成的损失;21. 17 U.S.C. §114 (d)(2)(C)(i)-(ii).第三,非预付费的音乐传输,则被完全排除在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公开表演权之外,延续了录音制品制作者在模拟传输时代不享有公开表演权的传统。22. 17 U.S.C. §114 (d)(1)(A)-(B).
三、音乐著作权制度的本土化困境与应对
音乐著作权日趋复杂的法律构造,激化了传播成本日益低廉与许可成本日益增加之间的矛盾。进入网络时代后,音乐与载体彻底分离,数字化传播达到了无时间差、无地域性的境界。传播方式的发达,几乎摧毁了全球的音乐产业,使音乐著作权人丧失了大量收益;而权利人对既有权利体系的坚持和对音乐著作权客体许可效率的追求,又致使许可带来的相关交易成本,抵消甚至超过了新技术所降低的传播成本,导致新技术在传播效率上的优势无法实现。正如美国版权局的一份修法报告所言,既有音乐著作权制度的运作效率远低于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是消费者选择盗版音乐的重要原因。23. See U. S. Copyright Off ice, Section 115 Reform Act (SIRA) of 2006,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May 16, 2006).最先遭遇许可效率问题的发达国家,由于既定利益分配规则已根深蒂固,各方分歧导致许可机制改革陷入停滞。著作权人以许可效率为重,即以最低成本追求许可收益的最大化,旨在维护数字环境下的版税收益;使用者则以传播效率优先,即以最低成本追求传播范围的最大化,要求降低获取作品的成本。
我国音乐产业起步较晚,音乐著作权制度并非伴随产业发展而逐步完善。然而,在网络侵权与许可版税分配等方面的纠纷,我国与其他国家却是同步遭遇。在2012 年版权局发布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第一稿中,第46 条和第48 条对现行《著作权法》(2010)第40 条“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加以细化,对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使用时间、申请备案和版税支付等问题做了规定,使之更具操作性。但由于音乐著作权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国家版权局修订草案第二稿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法设计,即完全放弃了现行《著作权法》和修正草案第一稿中关于“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规定,这意味着根据后来修订草案第二稿、第三稿和已报送国务院的送审稿,录音制作者制作录音制品的行为需要事前得到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基于同样的原因,修订草案第一稿第60 条关于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规定,也在随后的数稿中几经修改,最终在送审稿第63条中把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范围限定在“就自助点播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已经发表的音乐或者视听作品”,其它表演、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皆排除在延伸性集体管理之外,已无法实现版权局所意图达到的目的。这种在立法选择上的重大反复和持续争议,主要是因如下原因导致:
第一,从制度设计上看,我国著作权法源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公约的回应,音乐著作权制度并非契合产业发展阶段生成,导致相关立法空有条文而缺乏具体实施的产业基础和相关制度保障。音乐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否定和批评早已存在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本质上乃是对法定许可长期无法落实的不满。我国1990 年第一部《著作权法》出台时,国内音乐产业才刚开始市场化进程,既无具有市场地位的产业主体,集体管理组织等著作权服务和中介机构也皆未建立,所以《著作权法》暂未考虑引入保障音乐著作权实现的程序性规则。随后修法虽然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增加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等规定,但由于国家对出版行业的行政管制,导致关于付酬方式和标准的具体安排难以通过市场协商形成,而只能等待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第二,从理论基础上看,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长期限于单纯的立法规则引进,却忽略了理论解释的吸收,当与发达国家同步面临网络技术冲击而无法获得他国经过实践检验的制度范本时,这种制度移植上的缺陷使得立法者既难以根据制度生成的规律梳理出制度失灵的原因,也无法在缺乏成熟立法可供继受时做出制度转型的独立判断。24.参见熊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载《法学》2013 年第12 期。例如在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立法问题上,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起草者国家版权局在前后两份“立法说明”中,就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在修订草案第一稿的简要说明中,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但究竟何谓法定许可的价值取向却并未明言。25.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2012 年3 月)而在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说明中,版权局又完全抛弃之前基于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国情的立场,仅“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社会各界意见”就彻底取消了录音法定许可。26.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说明》(2014 年6 月)短时间内出现如此颠覆性的变化,说明我国立法者缺少对法定许可立法价值的稳定认识,因此在遭遇质疑后就只能被动根据不同“民意”发出声音的大小而摇摆。
第三,从产业形态上看,我国业已形成了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音乐著作权产业形态,作为提供传播渠道的下游产业,在经济和市场地位上完全压倒了作为音乐内容提供者的上游产业。换言之,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与录音制品制作者在许可条件等方面,需要“服从”控制网络传播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借助行政政策获取垄断渠道的广播电视传媒。在此情形下,无论承认与否,我国网络用户使用数字音乐已经养成了以“免费”为常态的使用习惯。这既是由于在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全球数字音乐盗版最泛滥的时期,我国未能有效抑制数字音乐的非法传播;也是因为当时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进而导致合法授权的制度设计缺乏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反观发达国家,虽然同样遭遇网络盗版,但音乐产业主体坚持通过司法诉讼和立法游说,对包括最终用户在内的数字音乐使用者施加压力,进而得以建立适应网络音乐市场的商业模式和付费机制。27.比较美国和我国涉及音乐著作权的诉讼特点可以发现。随着我国音乐产业的逐步成熟,产业主体迫切需要网络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代替日趋消亡的实体唱片发行。无论是国家著作权管理机关还是音乐著作权人,近年来都积极呼吁推行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甚至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28. 2013 年时即有音乐产业界人士明确表示,数字音乐全面付费将于当年7 月开始,但至今都未能实现。针对这一错误论断的思考参见熊琦:”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未来模式选择“,载《知识产权》2013 年第7 期。然而,在网络用户免费习惯早已形成的情况下,如何构建符合网络环境的付费制度,各方却无令人信服的方案。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立法者声称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和“延伸性集体管理”,最强烈的反对却来自作为保护对象的音乐著作权人。音乐著作权人内部虽一致主张数字音乐付费,但在如何收费和向谁收费等问题上却缺乏基本共识。29.参见周皓:“网络音乐免费午餐注定终结”,载《音乐周报》2013 年4 月10 日第14 版。
针对上述难题,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既需要建构,也面临重构。言其建构,乃是因为音乐著作权制度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已无法正常运作,必须设计出适应传播效率的新机制;言其重构,乃是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在设立之初,既未合理吸收他国已有经验,也未正确预期本国发展趋势,所以需要从无到有的规划。而在诸多改革方案中,不同权利主体利益交错,不同权利类型彼此冲突,如何兼顾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又不损害经济诱因,不但需要了解不同音乐著作权许可类型的特殊法律构造及其由来,更要比较不同路径之间的制度成本与收益,最终选择符合我国现阶段立法实际的解决办法。
了解不同音乐著作权许可类型的特殊法律构造及其由来,比较不同路径之间的制度成本与收益,才能最终选择符合我国现阶段立法实际的解决办法。
1.制度本土化调整之一:从政府驱动到产业驱动的立法模式转型
根据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转型规律可以发现,产业主体驱动制度转型必然有其独有特征。而对于我国而言,政府驱动立法毫无疑问被视为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在面临国际社会压力,且本土音乐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的情况下,产业主体并无根据自身商业模式提出合理制度设计的可能,由政府主导音乐著作权立法,一方面能够提前为本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搭建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国际化和普适性的音乐著作权规则,为我国将来的制度发展提供丰富的比较研究基础。然而,在如今的产业环境下,继续坚持政府驱动立法转型将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本土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开始呈现出特殊化和复杂化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产业介入后,我国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其特点在于下游控制传播渠道的产业主体比上游提供作品内容的产业主体明显强势,作为内容提供者的著作权人不得不听命于作为传播者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此情势下,立法者所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市场环境,因而明显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难以在立法上充分反映市场的需求。其次,在政府驱动立法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还主导了音乐著作权中介和服务机构的设立,在他国由产业主体生成的组织在我国变成了半官方机构,因此近期在版税收益分配上出现了与民争利的现象。产业主体有理由质疑,立法者可能借助本次著作权法修改进一步强化政府介入的程度。鉴于上述问题,我国音乐著作权立法应逐步从政府驱动转为产业驱动,以帮助立法者构建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制度。30.参见熊琦:“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规律的梳解与借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 年第3 期。
在政府主导立法的体制下引入产业驱动机制,首先需要区分音乐著作权制度中的公共立法和私立规则,并使政府主导的权利分配机制逐步退出产业主体能够自治的领域。
在政府主导立法的体制下引入产业驱动机制,首先需要区分音乐著作权制度中的公共立法和私立规则,并使政府主导的权利分配机制逐步退出产业主体能够自治的领域,防止与民争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在美国音乐著作权转型历史中,哪些目标可由产业主体自行完成,仅需要借助立法对特定行为加以限制,而哪些需要立法直接完成权利配置,已有明确科学的分工。针对我国修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以下几个方面可供我们借鉴。
第一,取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行政准入,允许产业主体自行创制音乐著作权中介机构。美国历史上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皆为私人创制以实现集中许可的结果。由于创制者本身即为音乐产业主体,所以集体管理组织在如何提高作品传播效率,以及如何降低许可机制交易成本等问题上,具有与权利人相同的经济诱因,也是美国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够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始终保证许可效率的原因所在。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远未发挥出来,主要原因即在于集体管理组织并非真正从实现作品效用的角度构建集中许可。音乐产业主体对本次修法中反对“延伸性集体管理”,本质上还是对我国集体管理组织行政垄断地位的不满。31.争议各方观点参见徐词:“我就要来保护你: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陷入争议漩涡”,载《南方周末》2012 年04 月19 日D22 版。这种官方性和垄断性造成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缺乏提高许可效率的经济诱因,因此既不会根据市场情势为使用者提供最优许可方案,也不会积极提高自身的运作效率。例如,根据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的《全国卡拉OK 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2010),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费支出高达每年所收版税的50%;2006 年至今,音著协和音集协在卡拉OK 版税收取标准和方式上皆缺乏与使用者的合理沟通,因此只能由官方机构强制推行。
第二,避免在法律文件中直接规定许可版税的定价标准,而改由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协商机制实现,司法裁判程序仅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介入。虽然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在修法中因遭遇质疑而被取消,但其它对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广播组织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以及商业机构公开表演录音制品等领域,应尽快建立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者的版税协商机制,以取代直接通过立法或政府指导定价。根据美国音乐著作权转型历史,法定许可制度中由第三方设定版税标准的效率问题一直是饱受各方诟病的缺陷。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法定版税标准难以随市场变化而及时调整,结果反而成为了限制市场交易的最高限价,使权利人无法根据版税的浮动来调整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成本。在进入网络时代后,这种定价机制上的弊端进一步凸显,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加不愿就不同范围和频率的利用行为支付相同标准的版税,导致相关争议一直持续。也正因为上述原因,美国法定许可制度在实践中是由集体管理组织以集中许可的方式实现,无论是早期的“哈利福克斯代理处”(HFA),还是为数字传输设立的SoundExchange,都是由产业主体参与运作,以缓解法定许可定价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事实上,上述在美国已经证明的立法缺陷,在我国也已出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则从2000 年“试行”至今,其规定的版税标准从未进行调整;2008 年《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中,法定许可版税的计算标准也已固定。即使在集体管理制度中,我国集体管理组织条例也要求定价须根据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标准。因此,取消上述立法对定价的具体安排,引入集体管理组织解决版税标准,有助于我国逐步形成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音乐著作权交易机制,避免美国已经遭遇的定价效率缺失问题。
2.制度本土化调整之二:产业现实基础上的权利内容与许可模式设计
我国著作权法的权利类型和许可机制设计与美国法大不相同,但权利配置的目标和功能并无二致,所以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转型背后的规律和成败经验,仍然能够为我国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思路。从具体制度完善的层面出发,我国主要面临两个问题:首先,音乐著作权类型如何针对音乐产业商业模式的变化进行调整。与美国极为精细的音乐著作权类型划分不同,我国音乐著作权类型存在保护不周延的情形,因而应做到在全面涵盖网络传输类型的基础上,避免美国因权利界定过于细琐而出现对传播效率的阻碍。其次,音乐著作权许可如何避免音乐使用方式变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由于我国著作权中介和服务组织的缺位,音乐著作权的许可效率极为低下。特别是对于网络最终用户的数字音乐传输行为,著作权法的约束几乎形同虚设。这显然与美国在21 世纪头十年依靠大规模诉讼建立的市场秩序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在此基础上构建许可机制,必须在考虑到本土使用者习惯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已有经验。
第一,在权利内容上,我国音乐著作权类型设计需以全面涵盖网络传输类型为目标。从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转型历史看,权利内容的调整始终是最艰难的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利内容设计直接关联产业主体的核心利益,任何变化都会引起特定主体的质疑和反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音乐著作权制度的运作完全基于权利内容设计,权利类型或范畴的任何调整,都会改变与制度运作相关的配套机制。所以在权利内容的设计上,我国不可能抛弃既有体系而直接引入他国规则,而只能基于本国产业基础进行调整。同时,美国音乐著作权类型设计的失败,说明过分细化的权利设计虽然能够满足产业主体保有和扩张收益的需求,实践中却会给制度运作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反而会阻碍设权目的的有效实现。特别是在如今我国著作权中介和服务机构极为落后的阶段,如果片面为迎合或激励音乐产业主体而增加更多权利,可能会出现与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那样陷入低效率运作的状态。从现有权利体系出发,音乐著作权首先要通过修法涵盖网络广播,但在具体立法设计上,则不应过分考虑是否为交互式的传播方式,但更应该区分永久下载和流媒体传输的权利属性。由于我国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立法结果,因此在应对传播技术上采取了不同标准,广播权的设计是以“有线/无线”为区分标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计则是以“交互式/非交互式”为区分标准。上述差异导致非交互式的“网络广播”被现有权利体系忽略,而网络广播又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借助流媒体技术利用数字音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互联网、广播网和通讯网的产业主体出现趋同化,有线和无线传播能够自由转化,音乐产业主体能够同时在互联网、广播网和通讯网上使用音乐。所以建议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为公开传播权,使其规制各种技术条件下的公开传播行为,如此还能避免因人为切割网络传输行为而导致的搜寻成本增加。另外,对于单纯的永久性下载行为,应将其明确界定为复制,而非同时纳入复制权和公开传播权的范围,避免增加使用者协商成本和版税负担,也有助于将最终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设权类型分开。
第二,在权利许可上,我国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选择应回避美国已呈现的立法缺陷,根据本土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进行构建。美国法上庞杂的许可体系,普遍被认为是阻碍音乐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多种涉及网络传输的权利类型分别由不同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既增加了使用者的搜寻和协商成本,也阻碍了网络传播效率优势的实现。美国版权局代表曾在一次音乐著作权许可修法听证会上指出,音乐著作权许可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能够通过一次许可获得全部权利,以便及时高效地向公众提供作品。32. Music Licensing Reform: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109th Cong. (2005). (statement of Marybeth Peters, Register of Copyrights, U.S. Copyright Off ice).这一路径无疑是正确的,但因产业主体之间分歧过大,虽然美国版权局自2004 年至今已数次提出各类音乐著作权许可改革方案,但都被特定产业主体支持的游说集团否决。由于我国尚不存在因产业主体过于强大而影响立法的情况,反而可以根据新兴商业模式做出更大程度的修缮。
从我国音乐著作权产业现状来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修改现行许可制度。首先,放弃已被证明存在明显缺陷的法定许可,音乐著作权人的所有权利都可由一个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构建一站式集中许可。具体做法可以是取消现行法律要求集体管理组织“不得与其他集体管理组织业务范围重合”的规定,允许现存集体管理组织(音著协和音集协)直接通过扩大许可权限范围,转型为一站式集体管理组织。特别是在我国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品邻接权大部分都由录音制品制作者(唱片公司)掌握的情况下,不存在美国因历史原因导致的出版者与录音制品制作者之争,因而大大减少了来自产业主体的阻挠。数个一站式集体管理组织并存,不但能够促进彼此为获得更大范围的权利来源而向权利人提供更好的许可条件,而且可以使得创作者获得再次挑选许可对象的机会,进而淘汰失去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主体,减少因多余主体带来的交易环节。其次,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最终用户的法律关系上,应允许网络服务提供者独立创制其适用的许可模式。由于我国音乐产业发展水平的原因,导致其无法在网络普及初期通过大规模诉讼和立法游说强行建立付费的许可机制。所以在现阶段网络用户付费习惯无法建立的情况下,短期内要求我国互联网产业主体向用户直接收取版税并不现实,而实践中权利人允许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不受技术措施限制的免费下载,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其商业模式更多依赖迟延收益,即依靠交叉补贴或第三方支付间接获取的收益。有鉴于此,现阶段严格的许可机制应建立在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而允许网络服务提供者独立创制其适用于最终用户的许可模式。同时,为避免退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最终用户之间法律关系的干预而缺乏与定价相关的评估信息,音乐著作权人在许可协议中可要求直接参与对网络音乐下载量和点播量的统计,法律也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提供真实统计信息的法定义务。
数个一站式集体管理组织并存,不但能够促进彼此为获得更大范围的权利来源而向权利人提供更好的许可条件,而且可以使得创作者获得再次挑选许可对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