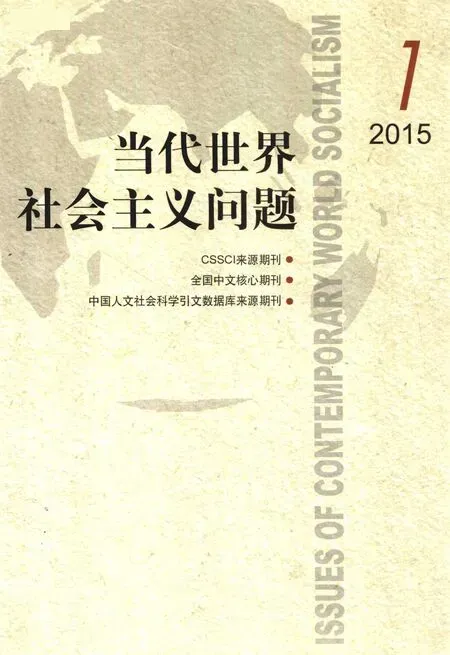爱尔巴桑记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访谈录
孔寒冰 张 卓
冷战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跟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而波动。在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东欧各国不仅最早与中国建交,而且最早与中国交换留学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当中苏关系处于“离异”时期,绝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程度上站在苏联一边。但是,有一个国家例外,它就是阿尔巴尼亚。1960年,当苏共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围攻中国的时候,阿劳动党挺身而出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阿尔巴尼亚在中苏日渐恶化的争论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而与苏联的关系日渐恶化。苏联停止了对阿尔巴尼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了全部专家和驻守在阿港口的舰队,甚至一度中断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阿关系却日益密切并快速升温,并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达到高峰。其中,经贸方面,中国为阿提供大批贷款、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到1970年代初,由于不满中国与美国接触、建交和开始与苏联缓和,阿尔巴尼亚开始批评中国,两国关系随之降温。中国逐渐减少最终于1978年7月停止了对阿援助。中国对阿的援助是全方位的,仅援建成套项目就一百四十多个,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就是其中最大的项目之一。中方不仅提供大量资金、物资,而且从全国各地选派了许多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本文实录的是原上海第五钢铁厂的侯树庭厂长、曹松庆、费民孚两位高级工程师和翻译孙忆新的口述。侯树庭厂长1969—1973年间在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担任中方第二负责人,曹松庆1974—1978年间是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工程技术管理专家,费民孚在1975—1977年间担任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自动化仪表专家,孙忆新1975—1977年是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的翻译。
侯树庭:爱尔巴桑钢铁联合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援建工程
今天回忆四十年以前的事情,可能数字不会很准确,但是基本情况不会错。那会儿是六十年代,中国已经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当年参加苏联领导的经互会,后来由于政治原因,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退出。退出以后,它在经济发展上希望有个国家能帮助它。当时,中阿两国政治倾向非常一致,是很友好的国家。我记得毛主席有一句语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语录当时全国人人皆知,还被谱写成歌曲,广泛传唱。阿尔巴尼亚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中国在同苏联争论中也需要它的支持。当时,中国了解经互会曾有一个规划,给阿尔巴尼亚建一个钢铁厂,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建立了一个试验工厂,进行着一些半工业性质的试验。由于退出了经互会,所有这些工作都终止了。所以,阿尔巴尼亚希望中国帮助它继续建一个钢铁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接受了阿尔巴尼亚的请求,同意帮助建设。
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真正的纯铁矿石,只有红土矿。红土矿含有四种元素,即铁、镍、镉、钴。这种矿的颜色像红土,因此被叫作红土矿。红土矿在钢铁业利用起来有一定难度,但阿尔巴尼亚方面要求很高,希望中国尽量想办法将这四种元素都利用起来。其实,当时中国接受这个工作也是很困难的,钢产量在大跃进期间曾经达到两三千万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钢产量大大下降。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援建阿尔巴尼亚搞这样一个项目,中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很多的工厂来做这个实验。当时上海条件比较好,“四人帮”把全国扰乱了,但要稳住上海。稳住上海扰乱全国是“四人帮”的战略,因为他们要夺权嘛。所以,上海当时的社会局面还比较平稳,工厂都能正常生产。所以,中央就选中上海,由上海冶金局承担这个任务。上钢五厂是冶金局下属的一个有两万多人的大企业,而且是一个特殊钢企业,既有转炉炼钢又有电炉炼钢,既有普通钢又有合金钢。这种情况下,上钢五厂就成了爱尔巴桑钢铁厂的承建单位,我与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就此结缘。
当时,中方的基本出发点是让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尽量用它的原料生产出适合它的产品,既可以让更多人就业,又可以发展阿尔巴尼亚经济。钢铁行业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钢铁行业,其他领域的发展肯定会有困难的,阿尔巴尼亚不可能有很多外汇去进口。所以,中方考虑的基本点就是尽量用阿尔巴尼亚的原料生产出满足阿尔巴尼亚需要的产品。因此,自力更生的口号在当时是说得最响、最受关注的。由于阿尔巴尼亚的矿石很特殊,中方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很多方案。开始时,我们是沿用经互会的火法冶金,也就是用电炉将矿石炼成液铁,把铁渣炼成钢再轧成材,这是炼钢的工艺。但是,经互会只做了一个短时间的半工业型的实验,没做完就停了。中方开始时也用这个方法,专门在浙江的建德县建了一个试验工厂,叫衡山铁合金厂,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用这种工艺有很多困难,生产钢材成本很高。所以,中方又寻找其他的方法,即先炼出镍铁和铁渣子,然后用铁渣子再去炼钢。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湿法冶金,就是把镍铁矿石经过沸腾炉焙烧之后,用氨气把里头的镍铁萃取出来,再把铁渣子运到钢厂去炼铁炼钢和轧材。所以,上海冶炼厂就搞了一套湿法冶金的设备,很成功,将金属钴、金属镍都提取出来了。钴和镍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铁渣经过烧结以后,再用高炉炼成铁。但在铁渣中,铬成分约占5%。于是,再把铬渣提取出来,送到铁合金厂去炼铬铁。剩下的就是铁了,把它送进转炉进电炉去炼钢,轧成钢材。这条路走通花了接近十年时间,中方照着这个成功经验所取的科学数据,给阿尔巴尼亚设计了两个厂,一个叫镍铬冶金厂,一个叫钢铁厂,总的名称叫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
既然叫做冶金联合企业,那就是说生产出的产品既有黑色的又有有色的,应该说有相当规模,年处理红土矿石100万吨,生产镍大概5000吨、钴200吨,还可以生产25万吨钢材。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满的结果,当时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综合利用红土矿。我估计,世界上红土矿的储量在200亿吨以上。用这种方法提炼镍和钴,这些金属可以炼成制造飞机、制造先进设备所不可少的不锈钢。所以,中方给阿尔巴尼亚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划,规模也够大的。钢产量虽然不高,但厂里什么都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全是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啊,用自己的红土矿生产出来的。
炼铁要有高炉,炼铁之前还要有焦化厂、烧结厂。铁水出来了在氧气转炉里面就炼成钢了,直接倒进电炉里就炼成合金钢了,合金钢浇成钢锭或者连续固定的圆柱胚运到轧钢厂轧成各种钢材。中方都将这些厂子建起来了。后来,考虑到阿尔巴尼亚有石油,石油出口的话需要装桶,中方又给它建了一个热轧板厂,将钢锭冷轧成很光很亮的钢板,再用这种钢板制成各种石油桶。阿尔巴尼亚要采石油,往地下钻孔时需要无缝钢管。中方给它建了无缝钢管厂。为了满足阿尔巴尼亚输送石油、天然气,中方给它建了一个螺旋钢管厂。为了给老百姓家通自来水管,中方建了一个直缝钢管厂。阿尔巴尼亚要搞建筑需要各种型材,中方又给它建了一个中型钢厂,跟原来的一些小型厂都配套上了。这还不够,为了维修设备,我们又搞了一个机修厂。这些厂都会产生大量蒸汽,白白跑掉太浪费了,我们又给它搞了一个热电厂,蒸汽出来以后先发电。总之,中方对爱尔巴桑这个冶金联合企业考虑得太周到了,全世界找不到这样一个工厂。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的一份心意,当时叫兄弟情谊。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当时说,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建成是阿尔巴尼亚的第二次解放。
在援建的过程中,中方不怕麻烦,更不怕辛苦,把这个企业从设计到设备制造到建成整个一套东西都搞起来了,钢厂已经建成,镍钴厂准备马上进行冷调试和热调试。但是,在这时中阿两国发生了分歧,中国专家只好回国了。所以,我们也感到很遗憾。
在中国援建之前,阿尔巴尼亚基本上没有钢铁行业,因为它没有铁矿石。红土矿既不能炼铁也不能炼钢。所以,阿尔巴尼亚就进口一些小钢胚,轧成一些铁丝啊、小角钢等民用小型材,用在暖棚、盖房子上。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当时的情况。
我是1955年进入钢铁厂的,是炼合金钢的,工作了两三年左右就赶上大跃进。那时候,全国各个钢厂都是有指标的,上海还少几十万,怎么办呢?于是,上海就决定快速建上钢五厂,我就被抽出来筹建上钢五厂。这个钢厂从动土到出第一吨钢只用了四十天,创造了奇迹,在世界上简直没有第二家。
为什么选择我去援助阿尔巴尼亚呢?我在亚细亚钢厂、上钢工厂都搞过筹建工作,又搞过生产工作、技术工作,还有过一段到英国学习的经历。所以,组织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可以说是有文化、又有生产经验,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就把我选中了。我那会儿也很规矩,坚决听从组织安排,组织让去干哪个就去干哪个。所以,我就被调到上海冶金局援外组,从事援建阿尔巴尼亚的筹建工作。
当时,中方派去援建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非常多,最高峰时有550人,其中200多人搞生产,200多人搞建设,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首次。所以,选派出国人员担子是很重、工作量是很大,标准还是很严格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政治要过硬,也就是说思想要好、出身要好、表现要好,如果有一条不好就不能去的。当时,中国正是强调革命的时候,这个也是必须的。第二个条件是技术要过硬。那时候的专家岗位上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必须都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你到那儿是专家、是师傅,不能说遇到困难以后向徒弟要办法,问徒弟这个事儿怎么办。这样是很丢人的,也是不可能的。徒弟如果比你还高明,那你就用不着来了。所以,技术上必须要过硬。第三个条件是身体要健康。在阿尔巴尼亚不同在中国,生活条件跟中国的也不一样。如果在那儿生了病,阿尔巴尼亚的治疗条件是比较差的。如果在那儿老生病的话,整个援建团队就会被你拖垮了,你自己也垮了。所以,这几个条件是必须的,出国人员的审查都是很严格的。被挑选中了的,大部分人是很高兴的。如果这几个条件都符合了,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感到非常光荣。
不仅挑选严格,被挑上的人在出国之前,相关部门还要进行培训,包括技术上,还有外事上的培训。到阿尔巴尼亚去的人,要了解阿尔巴尼亚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甚至也要学点简单的阿尔巴尼亚语。但是,当时懂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不多,那就请人来教,甚至不会念就把它写成中文,用中文拼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生产中遇到紧急情况,钢铁厂都是水火不留情。遇到问题就要立即处理,如果要请示再找翻译,那什么都晚了。所以,做一点语言上的培训都是必须的。这些工作我们都做了。
我们到了以后啊,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了,适应新环境总得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来的、是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来的。这两个大前提有了以后,任何困难都不是事儿了。阿尔巴尼亚方面做得也不错,专门给中国建了一个专家大院,建了好几层大楼。楼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地。为了饭菜能够符合中国同志的口味,阿方选派了几个厨师,中方也带来了大概八个厨师,同阿尔巴尼亚厨师一起工作。这样,我们每天吃的,既有中餐又有阿尔巴尼亚餐,既有面包又有米饭馒头。这样就跟在中国差不多,生活很快就习惯了。
从1969年到1973年,我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了近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中,我感觉到,阿尔巴尼亚人也像中国人一样,想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情况。所以,工人们干活都是很努力的,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甚至有些人是放羊的鞭子刚刚放下来就当了轧钢工人或炼钢工人,这是非常不容易。他们很好学也非常顽强,在这点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也很热情,不像有的国家那样刻薄。阿尔巴尼亚也很朴实,我们和他们的相处也是非常好的。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可以说从来没红过脸。双方高层管理者几乎每天都有例会,有什么问题什么矛盾都会拿到会上来解决。所以,即使有什么矛盾问题也都很快化解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1974年,爱尔巴桑的高炉建好了、转炉炼钢厂建好了、电炉炼钢厂建好了而且都出钢了,可以说第一期工程基本上结束了。不过,这里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时候用的原料都是中国的铁矿、中国的煤。阿尔巴尼亚的红土矿还没有用,因为镍钴厂还没有建好。尽快地用阿尔巴尼亚的原料生产阿尔巴尼亚的产品,这对中国援建者来说是一个急迫的任务。我正好利用休探亲假的机会回国,就赶紧想办法。当时,上海冶炼厂建了一个样板厂,就是镍钴合金厂,炼出的镍炼出的钴是金属的,铁渣子送到兄弟钢厂高炉冶炼出铁水出来,再把铁水放到氧气转炉炼成钢锭,然后把钢锭轧成材。轧成钢材还不算,要拿去做使用试验。这种钢材因为原料特殊,成分和国际上也有点不一样,跟中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们在钢种上做了很多研究,调整了成分。如果总是含有一点残余的镍和铬,这种钢就会太硬。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碳含量适当降低。我们用计算公式做了好多试验工作,最后根据试验结果,连洋钉、铁丝、螺旋焊管、直缝焊管、钢板都生产出来了。然后,我们将这些产品交用户去用,比如,我们就把那个直径500毫米的大螺旋焊管送到广东新会县武陵水电站,那里正好在建水电站缺钢材。建筑方把这个钢材拿去一用,效果非常好,他们很满意。后来,这种钢材又用在制造汽车上。生产出来的汽车在浙江一家运输公司去做实验。汽车从杭州一直开到镇江,在山上盘来盘去,跑了好多公里,最后把用这种钢材制造的齿轮拿下来称重量,看磨损了多少,结果也都很令人满意。我们拿类似阿尔巴尼亚红土矿的原料炼成的建筑钢材,用在建设浙江的艮山码头的旅客大厅,做这个大厅的钢结构,也是非常成功。这样一来,我们心里就很有底了,当然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也不晓得跑了多少地方。很多钢铁企业都参与了这些试验,像承德钢铁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上钢一厂、上海铁合金厂、上钢五厂、上钢三厂、上钢二厂等都参加了。这些科研成果取得以后,我们就放心了,我就准备带着这些成果回到阿尔巴尼亚,准备用阿尔巴尼亚的红土原料进行生产。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阿之间产生了分歧,中国的专家都撤回来了。本来我是要带着这些技术资料重返阿尔巴尼亚,可没想到是我去机场接他们回来。我很惊讶,也很遗憾。
我觉得,中国撤回专家是很不幸的事,对双方来说都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主要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对此,我还没有回国之前就有所感受。中国驻阿使馆的领导同志经常到工地来看望我们,因为我们在那儿有550名专家,其中搞生产的专家就有250名。在外国有几百名中国专家聚集在一起搞一个大工程是少有的,非常少有的。所以,使馆的领导同志来看望就经常说,现在中阿关系有点不对劲,问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说,我们忙于技术忙于现场建设都来不及,哪儿还有功夫想这些事情啊。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些公路两边的山坡上面都竖了好多大的标语,这些标语就是讲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暗指中国是修正主义。这些在国外搞外交的同志能够感觉到。那么,中国国内呢?其实,人们也感到了有些不对。比如当时有一些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在中国的钢铁厂里实习。我们的几个大钢厂都有大礼堂,经常放电影。当时有一个纪录片电影就是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接见尼克松。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看到这个镜头后就全体起立退场,而且还唱阿文歌曲。中国人听不懂,有时候还给他们鼓掌,后来明白了他们唱的是修正主义完蛋了,霍查是革命的旗手,这才恍然大悟,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了。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中国,人们普遍有中阿关系有些不对劲这样的感觉。当时中阿关系的政治气候不好,国内外都有反应,估计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也接到了他们国内的指示。否则,他们怎么会看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尼克松总统会站起来退席,而且还要唱修正主义完蛋了的歌曲呢?这大概是中阿彻底分裂的前奏曲吧。
另外,中阿分裂还有一些原因。当时,咱们国内在搞批斗,阿尔巴尼亚也明确表态支持中国搞批斗。这是一个国家干预另一个国家国内的事情,这样做不妥,有失外交风度。当时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已经很多了,涉及到各个领域。我统计一下,钢铁方面有两个大的企业,有矿山,有制造采矿用的装备工厂,有铬铁马利列合金厂,有氮肥厂,有生产篮球足球排球的三球厂,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很好运动啊。此外,中国还援建了针织厂、啤酒厂,铜冶炼厂,还有很多很多。也就是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了很多很多。光爱尔巴桑这个冶金联合企业,如果把国内的投资算上至少是六亿人民币。六个多亿,投资是巨大的。可是,阿尔巴尼亚后来又提出一个更大的清单,要求中国继续给予援建。中国当时只派了一个考察组,考察组的成员我们也见过。我跟他们交谈问他们来到阿尔巴尼亚干什么,他们说新项目要考察一下。据说这些项目都没有成立,没有批。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复出了。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阿尔巴尼亚要的东西中国没有给,两国关系恶化可能和这个也有些关系。所以,中阿关系后来就破裂了。当时,霍查认为阿尔巴尼亚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他是举大旗的旗手,可能跟这些都有些关系。不过,这些都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我说他们的事情是说不清的。
总体上说,我们搞生产的总希望工程质量要保证,保证工程质量才可能开工顺利,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对质量把关非常严格,一点不客气。由于严把质量关,爱尔巴桑的每一个援助项目的开工建设和投产都是顺利的,一点质量问题没有。好几年的施工和生产,我们生产系统没有死过一个人。你知道,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的范围有260公顷,这么大一片工厂车间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死过一个人。在建设过程,中方没死一个人,阿尔巴尼亚方面死了一个人,但完全属于意外。他在屋顶推独轮车,不小心从屋顶掉下来。在安全施工、安全生产上,爱尔巴桑工程做得很完美。这么大一片地方同时开花,上下都开花,甚至立体的工程都出现,没有伤亡事故,这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工程可以说是完美的。
费民孚: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就睡在办公室
1972年10月-1975年10月,我在上钢五厂援外组(科)搞筹建工作。在这三年中,我主要是做出国的技术准备,重点是应对自动化仪表的更新换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我国的自动化仪表都是以电子管线路为核心的,七十年代初逐步改成晶体管线路。援外要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所以,设计的援阿自动化仪表都选用当时最先进的刚投产的晶体管线路产品,有些还是仪表厂的试制品。
1975年10月,我被派到阿尔巴尼亚,作为援阿专家参加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自动化仪表调试和投产工作。知道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消息之后,尽管任务很艰巨,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当时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非常友好,中国那时候最友好的朋友就是阿尔巴尼亚。毛泽东当时写过一封信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到阿尔巴尼亚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调试全自动2吨燃油快装锅炉,它是一种自动化的小锅炉,产出的蒸汽提供给高炉投产用。因为高炉12月份要投产,所以,我们就是参加高炉投产的准备工作,从高炉点火到铁水出炉的几天里有关中方专家都在各自的岗位通宵值班,要为高炉投产保驾护航。我通宵值班的工作就是保障锅炉系统正常运行。当时,所有援建的中方专家都是非常辛苦的。当时,侯厂长都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比我们还要辛苦,工作时间还要长。我们那时候困极了还可以打瞌睡,可以在凳子上眯一眯。但是,他不行的,因为他是总工程师,整个生产的技术工作都要请示他。所以,侯厂长很忙。经过日以继夜的奋战,高炉终于1975年的12月份左右投产了。
在援阿的岁月中,许多日常生活细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刚到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待遇很好。阿方招待我们,吃得都蛮好的,吃的东西也很多。阿尔巴尼亚的货币叫列克,我们每月就是两百多个列克,合40块人民币。中国援外的专家,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职务大小,都是拿这么多钱。阿方说,他们请西欧专家要付几百几千美金,中国专家拿的钱这么少,那就多给你们吃些好的吧。所以,每天餐桌上都有鸡,猪肉,虾和水果罐头。阿尔巴尼亚人以前是游牧民族,喜欢吃羊肉,吃猪肉的人少,阿方称呼虾为虫子,是不吃的。中国人喜欢吃猪肉和虾,正好互补。每周六晚饭由中方人员下厨烧中国莱,还供应酒,非常热闹,一周的工作辛劳都洗净了。相比当时处于十年动乱的中国食品供应的匮乏,我们感到非常幸运和满意,我在阿工作两年体重增加了十五斤。
在工作方面,由于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是边投产边建设,工作条件很艰苦,还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路,下雨后非常泥泞,鞋上都是泥,走路很困难。我和金福鸿在仪表车间焦化仪表站工作,负责焦化车间,能源车间,后来还有烧结车间等几个车间的仪表调试,这些车间的自动化仪表中有大量的DDZ-2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还有防爆的QDZ-2型气动单元组合仪表,我俩要对这些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冷调试、热调试、检修等,还要手把手地培训阿方人员做这项工作。阿方的仪表组有十个人,有两个组长原本是电工,来中国接受过仪表培训。我每个星期给他们上一次课,一次半天,给他们讲那些仪表专业知识,把基本常识、维修的主要技能告诉他们。
就这样,一边生产,我们一边教技术给阿方同行,一直在一线和阿方人员一起工作。爱尔巴桑钢铁厂投产之前,我们本来住在爱尔巴桑城区的中国专家大院里。大院是有围墙的几幢新造的工房,两三个人住一间,离厂区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估计有十几公里。投产后,我们在第一线的生产指导专家就搬到厂区里面住。阿方把厂区里面的办公楼简单地改造一下,我们生产的专家就住在里面,24小时为生产正常运行保驾护航。如果在下班后生产出现问题,他们就打电话,我们就马上到车间去工作。最初的几个月我们都是这样工作在第一线,住在厂区的那个办公楼里面。后来,阿方人基本掌握了生产操作技术,我们就逐步撤回镇大院里了。
在阿两年中,我们与阿方同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们对我们也都挺客气的,我们都相互递香烟。他们对我们技术水平特别佩服,因为我们用的仪表他们基本都不懂,希望我们给他们上课。不过,我们与阿方人员关系虽然比较好,但也不能走得太近。那个时候有规定,我们与阿方人员不能私下接触。我们不能到他们家里面去,他们也不能到我们宿舍里来。我们住的地方都有警卫,除非是特邀人员来开会什么的,一般人不能进我们大院。白天,我们在马路上碰到阿方人员,也就是点点头,不能多讲的,这方面有外事纪律。在生活中,我们不能与阿方人员有太多联系。他们邀请中国人跳舞,中国人都是不参加的。我们和阿方工作人员之间互相都不留地址,相互之间是不能够联系的。
我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两年,当中在1976年9月回国探亲过一次,1977年10月回国了。我不是1978年7月大部队撤回的,而是个别探亲回国的。我回国主要是因为任务完成了,因为焦化站最后一个烧结车间在1977年3月投产。我把自动化系统都调试好了,就跟我们专家组长说,我回去后就不来了。我们组长向阿方的车间主任征求意见,车间主任说,生产任务调试设备虽然完成了,但我讲课讲得很好,希望说能不能再回到阿尔巴尼亚来,多讲一点课,让阿方人员多学一点相关技术。所以,领导叫我可能还要再回阿尔巴尼亚去,连行李都没带就回国了。不过,我回国之后,中阿关系就很紧张了。上面领导说,你既然完成了仪表调试任务,讲课就不一定再去了。后来我就没有去,行李还是人家给我带回来的。
回国之后,我们援外的老同志也会在一起聊聊,相互打听一下阿尔巴尼亚那边的情况。后来,我们了解,爱尔巴桑的镍钴提纯厂没有投产,那个钢铁厂没有原料,就停掉了。实际上,那个钢铁厂是我们国家很大一个包袱,当时设计投资是二十多个亿,相当于十个上钢五厂的投资。设备是我们是按最低成本价卖给阿尔巴尼亚的,其它费用都没有的,什么安装调试费、设计费、专家费都是没有的。不仅如此,设备钱还是20年以后再分期还本,并且没有利息。钢铁厂开始投产时都是用中国的铁矿石,那时候用远洋轮船通过苏伊士运河运到那边。轮船过苏伊士运河要交过路费,1吨就1个美金。我们每年运往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矿砂,一年下来费用相当于广交会一年的外汇收入。把外汇都用光了,我们国家也负担不起,严重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1975-1977年这段时间,中阿关系已经紧张了。但实际上,阿尔巴尼亚的老百姓不太关心这个,主要是搞政工的人在宣传说中国是新的修正主义。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阿尔巴尼亚的报纸就有些这样的言论,公路上也有这类标语。但是,老百姓也不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阿尔巴尼亚跟中国有些分歧。另一方面,我们援阿专家内部也有政治学习,通过传达的上级指示,我们也知道阿尔巴尼亚对我们国家有意见,说中国拉拢美国,不反修了。所以,我们内部也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在工作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曹松庆:我们是最后一批撤离阿尔巴尼亚的
我当时是由上海冶金局派出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主要负责机械方面的工作,具体说就是负责电器仪表机械。当时负责整个爱尔巴桑冶金项目电器仪表工作的是三个人。但在国内筹备时总共有五六十个。当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援阿组,里面还分为一个工艺组,一个设备组。我当时在设备组,主要负责采购电器设备,跟设计院联系,设备入册、分销到阿尔巴尼亚去。
援阿之前,我在上海冶金局设计院工作,从1972年就参加援阿的筹备工作。几年下来,我把相关设备的各项数据都搞清楚了。当时,国内一共有四个人做电器仪表设备工作。但是,我们不知道谁会被派去援阿。到1974年年初的时候,领导才告诉说是我去。我当时比较年轻,才29岁,还是单身一个人。我们工作单位没有太卷入文革,我可以一门心思搞工作。所以,在国内采购设备时候,我就拿盖着一机部、冶金部和外交部的三个图章的介绍信全国各地跑。我每年要参加两次订货,采购的都是援阿的设备。
当时中国有三大援外对象,第一个是坦赞铁路,第二个就是阿尔巴尼亚,第三个就是越南。1971年中国进了联合国,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阿尔巴尼亚等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所以,中国人都觉得她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国内在这方面的宣传还是很强的。当时,我觉得选派我出国,是组织对我的培养。当时人的思想比较单纯的,组织能够选上你,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当然也是自己勤勤恳恳工作的结果,主要看你工作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能力。领导当然有好几个人选,但在电器仪表方面就选派我一个人,另外两个人,一个负责机械的,另一个是临时负责现场的,一共就我们三个。其中一个人休假,平时就我们两个人。当时,上海冶金局承建援助阿尔巴尼亚有两个大项目,一个是轴承厂,另一个就是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
我们最初的印象是阿尔巴尼亚很穷。我当时出差的机会比较多,走的比较多,就像刚才说到的要全国各地找设备。我看到的是它整个经济在欧洲确实是最穷的。但是,跟我们国内比,除了上海之外,阿尔巴尼亚并不穷。比如,当时中国的农民都是赤脚干活,但他们的农民都是穿着套鞋干活。
我是1974年6月份去的阿尔巴尼亚,一直到1978年8月份才回来,是最后一批离开的援阿专家。在这两年多时间中,我们跟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平时开车外出的时候,上海冶金局自己培养了很多翻译,但都是以生产为主。像我们搞设备的人,时间久了都是连说带比划,与当地人的沟通也基本都能应付。很多情况都是通过互相交流解决的。从我的工作角度看,有时会出现某些设备找不到了,对工程进度产生了影响。于是,我就要核查,是中国那边没有发货,还是货到阿尔巴尼亚之后又发错地方了。实在找不到的,我就跟中国专家联系,看看什么东西可以代用。这种问题很多,不少都是我们在现场解决的。
在上海冶金局派去的援阿专家中,多数人在阿工作时间不过三四个月,而我在那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刚到的时候,那里还是平地一片,见证了轧钢厂从建设到投产的全过程。在联动调试之前,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比如,为什么不联动试车,只是搞单体调试?这个时候我们国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如天安门事件,中美建交,毛主席逝世等等。中阿两国的关系逐步疏远。对此,我们从当地报纸上了解到一些。但是,我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当时都是有组织纪律的。我们的组织生活会的记录都全的。我当时组织生活属于包头钢铁厂。撤离的时候,我们接到指示要全部走。本来我们还要待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工程分一期跟二期。把轧钢厂建好后,应该说一期工程就结束了。按道理说,我呆了四年时间,是最长的,应该换人了。可是,我的主管,他是包钢派来的,叫我不要走,因为后面还要建设钢管厂,希望我们这些熟悉的人继续留下。我们正在谈走还是留的时候,使馆的信息过来了,要我们全部撤离。所以,我一听到就跳了起来,对他说,这事不要谈了,咱们全部都要走了。
我们撤离阿尔巴尼亚用了几个月。开始时,我们还有些担心,怕双方人员关系变得紧张。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吃得甚至比原来更好了,原来吃什么,还照样有的吃。方方面面,阿方对我们的供应没什么变化。当时,我们有些资料可以留给他们,有些不能留。许多资料都烧掉了,个别人把马桶都烧坏了。私下关系好的话,留给他们一些也难免,就像当时的苏联专家撤退时的情况一样。当时,中国援阿的设备都是最好的,我们回国后发现,国内企业都没有这样好的设备,但阿尔巴尼亚却有了。
中国援阿专家撤离阿尔巴尼亚,主要是由于中阿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对普通百姓影响不大。我们离开爱尔巴桑的时候,有许多市民街头送行,没有人刁难我们,我们那里有些阿尔巴尼亚服务员都哭了。的确,我们在那儿待了几年,同他们也有一些感情。平时我们生病什么的,他们就给我们一些药之类的东西,相处得还是不错的。撤离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决定,阿方工作人员肯定也知道了。我们最后一次到现场的时候,告诉阿方人员说明天我们不上班了。我还记得,当时在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专家,其他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当时,我们国家是从最坏的情况着想,去安排。其实,就是在地拉那机场,连开包抽查什么的都没有发生。我们离开的时候,阿尔巴尼亚服务员和我们还打过招呼。他们也都能够理解,因为撤离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送我们去机场的车全部是阿尔巴尼亚提供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我还得到了一个有霍查签字的劳动奖状,是三等奖。最高的是金质奖,第二是银质奖,我得的是铜奖,所以,我们关系还是不错的。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人员,市民也好,服务员也好,翻译也好,都跟我们挥手道别。整个阿尔巴尼亚只不过两百万人,爱尔巴桑只不过几万人的事情。看到我们的车走了,出来挥手。这是确实存在的。
撤离的时候,我们按上级指示每个人都在清理资料。什么东西能留,什么不能留。有趣的是,平时我们都有巧克力,不舍得吃,要带回来,但又怕阿方不给面子要开箱检查,所以有些人就没敢带。我记得,当时最后撤离的几十人分乘三架苏联产的飞机,在机场什么都没有发生,很平稳地离开了。这次我们是直接从地拉那飞回中国。我最早去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匈牙利,从匈牙利再上飞机到阿尔巴尼亚。
孙忆新:我为援建爱尔巴桑钢铁厂培训翻译
1959年,我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班。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只有少数同学去苏联留学了,我和一些同学到了北京大学俄语系继续学习。1962年,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国家高教部选派到阿尔巴尼亚留学。在阿尔巴尼亚学习期间,由于中国驻阿使馆人手少,我上了大三之后时常被使馆调出为国内来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代表团做翻译,不仅为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而且为铁人王进喜、大寨党支书陈永贵做过随团翻译,参加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当时,周总理嘱咐我们:“你们在国外学习,是小大使,是传播文化和友谊的使者。他们要注意学习当地的文化、风俗,多多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你们还年轻,祖国的未来将在你们手中改变面貌。”
1967年3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被迫离开使馆回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所以,我回国后被下放到在农场劳动改造,前后长达四年之久。1970年初,我的一个在总参三部工作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在301医院培训15名阿尔巴尼亚军医。但是,他找不着翻译,他问我有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可以到他那去,但是借调时间只有半年。这样,我就在301医院给阿尔巴尼亚医生当了半年翻译。这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杭州,但杭州外办还是没有给我安排工作,说让我等几天吧。我就只好等。过些日子,他们告诉我说:“你的运气还不错,上海冶金局要你去工作。”我吃惊地问:“我怎么能到上海冶金局呢?”外办的人对我说,你赶快走吧,留在这儿你只能扫大街。其实,外办的那些工作人员挺好,很同情我:“别说你是从阿尔巴尼亚学习回来,我们的翻译都在扫大街,人手还不够。你赶快去上海吧。你还不赶快走,万一走不成你还得扫大街。”
于是,我赶快拿着行李去上海报到,接待我的就是后来宝钢厂的王佩洲厂长。
我第一次到上海冶金局报到,他们很快给我办好了一切手续,发了工作证。我拿到工作证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时已经是1970年8月份了。我是1967年回国,到1970年才拿到工作证,有了正式工作。在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回家看我父亲母亲,因为他们都被关起来了。到冶金局外援组报到的时候,王佩洲厂长跟我谈了话。他说,小孙啊,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周主任都跟我们说了。你在经贸部的一些同学都跟我们谈了你的情况。你放下思想包袱,我们不相信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好好地在这儿工作。我说,王厂长,我很久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了,我可以回去看看我的父亲母亲吗?他说可以啊。过了两天,我们家里来信了,说我们家里父亲母亲都解放了。于是,我就拿着那封信去找王厂长,对他说,王厂长我不是走资派子女了,我父亲母亲解放了。王厂长说,从周主任跟我们介绍你的情况时起,我们就没有相信过你是什么走资派的子女。好,你就赶快回家吧,快点儿回来啊,我们这边还等着你呢。我就回了一趟家。你们想想,我是1962年离开祖国,到了1970年才回家看父母。当时,他们刚刚解放不久,见到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百感交集啊。我父亲母亲听说我分到上海冶金局工作,而且还能用阿尔巴尼亚文工作,他们高兴的要命。他们说,哎呀,真是不得了啦,你现在还有工作,多少知识分子都没有工作啊。所以,他们让我就赶快回上海。
到了上海冶金局以后啊,我真像找到了家。我们那个援外组的组长是王佩洲厂长,他是陈毅当市长的时候被评上的上海劳动模范。所以,他对陈毅元帅,对周恩来总理,对老干部都有深厚感情。他告诉我,他本来是一个炼钢工人,后来被提拔为上钢二厂的厂长,陈毅当市长的时候又把他树成了上海的劳动模范,后来送他到上海科技大学读书。所以,他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才让他来主持上海援外组工作。他对我们这些所谓的走资派子女格外好。
我去了不久,他就对我说,你先不要当翻译。我们就靠你一个翻译,完成不了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爱尔巴桑钢厂的任务。我们派到那儿的专家有500名。爱尔巴桑这个钢厂是一个联合企业,从采矿到炼铁、到炼钢、到轧钢都得有。他还告诉我,阿尔巴尼亚要派2000个实习生到上海冶金系统的一厂、三厂、五厂来实习,那个时候还没有宝钢。这样,我们首要任务是培养翻译。所以,他让我先去当老师,当阿尔巴尼亚语的老师,有重大的翻译任务再叫我回来。
所以,我去上海冶金局报到以后我就去教书了。我们一共办了三期阿尔巴尼亚语的培训班,培养的学员大概120多名。但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选拔学员有多困难?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当中,哪有学生啊?初中给关了,高中没有,大学没有。能够找到初中生到我们这儿去考试,写的字都歪歪扭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多小啊,根本就没念过书,更不用说懂外语了。我曾经选拔了三期阿尔巴尼亚语学习班的学员,最得意的一个门生是第三期的,他是上海吴淞煤气厂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办公室厨房烤面包的一个小师傅。当时,我给上海吴淞煤气厂的那些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去讲课,那里有第一期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当翻译。你想啊,中文就那么差,都没念过什么书,跟着我就学了半年的阿尔巴尼亚文就去当翻译,你说大的课他们哪会上啊?他们只会去帮着去干活,把这个东西抬高一点,那个低一点,向左,向右。只能说点这样的话。真讲起一些流程时,他们不会翻。所以,冶金局领导还是让我去当翻译。
所以,我为援助爱尔巴桑钢铁项目培养了三期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他们后来和我一起都到了阿尔巴尼亚去工作。另外,我们还在钢一厂、二厂、三厂、上海吴淞煤气厂、上海机修总厂等单位培训了两千个阿尔巴尼亚的实习生,他们回到了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都成了各个岗位的生产骨干,技术骨干。
接着,以王佩洲厂长为首的上海500名专家赴阿尔巴尼亚,来到了爱尔巴桑。那时候,整个爱尔巴桑还是一片空地呢,上海的基建局,我们的冶金基建公司,武钢冶金基建公司等单位在半年之内,把那些高炉、转炉全都建起来了。然后,那些生产专家就在那儿调设施,培训阿尔巴尼亚员工。上海培训的2000名技术骨干远远不够,我们还得在现场培训。就这么紧赶慢赶,爱尔巴桑钢厂从考察到最后高炉投产用时很短。高炉投产的时候,谢胡亲自剪彩,当时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是很轰动的,陪同谢胡的是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新权。刚开始的时候,王厂长是援助爱尔巴桑项目的上海专家组的组长,专门负责生产。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冶金部又派了副部长级的韩清泉去当大的组长。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上海的专家,还有宝钢的专家,有武钢的专家,全国各地优秀的钢铁专家都派去了。所以,冶金部就派了一个副部长在那儿带队。副部长要有一个核心组,成员有技术秘书,有生活秘书,还要有翻译。我就是他那个核心组的成员,给他当翻译。500名专家组,我培训的那三批专家组的翻译,在爱尔巴桑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援助队伍。
1975年初,我也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到了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王厂长他们早就去了。在爱尔巴桑工作期间,我们专家组驻地是阿尔巴尼亚盖的专家楼。所谓的专家楼,它比现在的房子要差远了,条件很艰苦。我们一天的伙食费八块钱人民币,但我们已经很满足。那时候,我们在国内的工资还拿,也都是几十块钱。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期间一个月的工资40块钱。从阿尔巴尼亚休假回国的时候,我就给亲朋好友带一盒无花果,这已经不错了。中国援建的毛泽东纺织厂卖的白布,帮助援建塑料厂卖的脸盆,我们就往国内带脸盆,白布。阿尔巴尼亚的橄榄油很好,但我们都舍不得买,带一瓶橄榄油那是很高级的礼物,我最好的朋友,也只能送一盒无花果。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时,真的是日以继夜。
援建阿尔巴尼亚钢铁企业,对中国来说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阿尔巴尼亚的铁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虽然年产只有25万吨,但困难重重。为什么呢?因为阿尔巴尼亚铁矿石不好,含镍和钴。这两个元素对炼钢炼铁简直就是敌人,必须把它们除掉。所以,必须先得有一道工艺,把铁矿石中镍和钴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以后,镍和钴又是战略物资。当时,中国老一代革命家真是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着想。阿尔巴尼亚是个穷国家,帮助它把镍和钴提炼出来,它就可以将它们卖到国际市场,不就可以挣钱了吗?剩下的铁矿石,再按照常规的那一套办法先炼成铁,再炼成钢,再把它轧成钢材,所以,为了给阿尔巴尼亚搞出一套提取镍钴的工艺,冶金部领导下的各个科研单位,如上海的一些研究所,武钢、鞍钢全部都参加了,花费了多大力气啊。
冶金部派第一个考察组到爱尔巴桑考察铁矿,要追溯到1965年,钢厂1976年建成。你想,1965年到1976年,我们国内做了多少工作。镍钴提纯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工作。镍钴提纯得用氨,而氨对人体的损害太大了。我们那些工程技术人员用液体氨把镍和钴提出来,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有一个援阿的工程技术人员是马钢的,名叫张宝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此外,一些老工人和一些老工程师们,因为从事这项工作,后来都是长期的肺部不好。
在冶金界有一个职业病,即矽肺。就是长期在钢铁行业工作的人,最后老的时候粉尘把肺堵上了,就像纱窗的纱窗眼全都给堵上了。工作条件那么艰苦,文化大革命期间物质条件又非常贫乏。我曾经去鞍钢出过差,钢厂里去看那些工人们。你都知道他们吃什么饭?拿个铁饭盒,两个窝窝头,一小点儿酱,一根大葱,几块咸菜干,就吃这种饭。当时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把经过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试验出最好的工艺拿到阿尔巴尼亚去,把他们的铁矿中的镍钴提炼出来,然后把铁矿砂运到钢厂进行筛选,然后进行烧结,然后炼铁、炼钢、轧钢。
500个中国专家在爱尔巴桑日以继夜的干活,这还不包括国内事先做的前期工作。我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结识了很多工程技术人员,感到他们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高炉的专家,炼钢的专家,轧钢的专家。我跟他们谈,你们在国内都是专家了啊,真了不起。我是学阿尔巴尼亚文的,让我再到这儿来工作也特别高兴,这不仅是旧地重游,而且能用阿尔巴尼亚文来干一件有益的事情,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建一个钢厂,我也觉得特别光荣。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还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方毅部长就讲要把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工艺流程和把最好的专家都放到爱尔巴桑的钢铁工地上去。所以,500人的专家队伍汇集了中国冶金界、钢铁界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这真不是吹牛的。大家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到阿尔巴尼亚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发扬的也是国际主义精神,那真是一点也不假。当时,方毅部长说,你们工程技术人员也好,翻译同志也好,都要想阿尔巴尼亚人之所想,急阿尔巴尼亚人之所急。尽管自己也有困难,但是,我们把困难留给自己,要把最好的一个钢厂奉献给阿尔巴尼亚人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所以,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那么多优秀的专家,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本来是是学俄语的,后来又学了阿尔巴尼亚语,基本上是和文学和语言打交道。在上海的时候,王佩洲厂长跟我谈,你现在是给冶金行业服务,要了解冶金生产的全工程,要知道怎么把矿石投到高炉里,烧结,走焦炉,烧结炉,到高炉里烧成铁水,铁水怎么变成钢锭,钢锭怎么轧成钢。这个全过程你全都要知道。我第一次到的是铸造车间,铸造车间是最苦的。那里的粉尘飞扬,工人最后得矽肺的简直太多了。我到那儿一看,哎哟,我今后打交道的场所就是这里呀,跟我大学里学的莱蒙托夫的诗,普希金的诗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时,走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欣赏着美景,那多优美啊。可是,看看这里,这么脏,到处粉尘。不过,我马上就转变过来了。我在农场也挑过大粪,现在不过是转到了一个工业战线而已。我必须了解工人是怎么干活的,今后要给他们当翻译。不懂这些工艺流程,不能跟这些工人同样流大汗,我怎么能够把他们要表达的东西真正翻译过去呢?我怎么能把中国工程师们设计的那套先进流程翻给阿尔巴尼亚人呢?后来,我就慢慢地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就特别热爱这些钢厂。上钢的一厂、三厂、五厂等重要的钢厂,还有煤气厂,机修厂等等,我都走遍了。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武钢、鞍钢、包钢等等。在这些钢厂的熏陶,和这些工程人员的交往,对我后来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后来又改学英文,工作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经常出差到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到加拿大、到大洋洲。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在英国看伦敦塔、看大英博物馆,在巴黎看埃菲尔铁塔、罗浮宫,在意大利看罗马、梵蒂冈的大教堂,在纽约看自由女神,外国的这些优秀文化当然也给我很大震撼。但是,我想到的是我们那些在钢厂工作的人们,他们拿着那个铁饭盒,怎么吃那两个窝窝头,怎么吃那些咸菜,怎么大葱蘸大酱,怎么在那里辛苦地劳动。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人们觉得钢铁工业多么的壮观,像火龙一样的铁水流出来,火花四溅,多么的优美,多么的壮观。可是,当真正走到现场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有多辛苦!所以,我在上海冶金局、在阿尔巴尼亚、在爱尔巴桑钢厂工作的前后这七年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的精神财富了。
中国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以后,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撤回那一经历我没有赶上。但是,王厂长和一些援阿专家回来以后告诉我:“小孙,你知道,我们在离开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那些工人还有当地的居民都排着队送我们,个个流眼泪。”我说,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时候,我们500个专家住在爱尔巴桑城里,离钢厂有一段距离,大汽车每天拉着500个人走,浩浩荡荡地开到钢厂,真是壮观极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阿尔巴尼亚人说,500个中国人在这儿呢,节假日也听不到他们的吵闹声,他们都在钢厂里工作呢。爱尔巴桑城里只有4万人,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在钢厂工作。这些在钢厂工作的阿尔巴尼亚工人说,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干起来是没白天没黑夜。平时在城市里的时候,中国人也安静极了,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也听不见他们的吵声。我们的工作作风跟解放军一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所以,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离开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热泪盈眶,默默地给这些工程技术人员送行。
1977年,我从阿尔巴尼亚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冶金部外事司工作。这样,1977年底我就到了冶金部外事司,参加了最后一次中阿冶金方面的谈判。这次谈判的阿尔巴尼亚冶金代表团是矿产部部长率领的,而中国代表团是冶金部副部长率领的。那次谈判从1977年年底谈到1978年的3月,最终以失败告终。开始谈判的时候,双方还热情洋溢,像春天一样,盛赞中阿友谊。但谈到具体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很不愉快了,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谈判结束以后,冶金部外事司的司长找我谈话。他说:“小孙哪,现在阿尔巴尼亚文也没什么用处了,派往阿尔巴尼亚的专家都撤回来了,我们也不会再到阿尔巴尼亚搞什么项目了。你呢,第一外语是俄语,但现在俄语也没什么用。你看你怎么办?你做什么工作呢?要不你就做行政工作吧。”当时找我谈话的是司长、副司长和党委书记三个人。我说,三位领导,我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做行政工作,这是第一。第二,您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已经找好了学英文的地方,我英文学好了以后回来仍然是你们的英文翻译。他们说,你行么?一年你就能当英文翻译?这样,我就到冶金部下属的有色金属研究院参加英语速成班,学英文去了,当时我已经38岁。以后的事,就与阿尔巴尼亚,与援助阿尔巴尼亚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