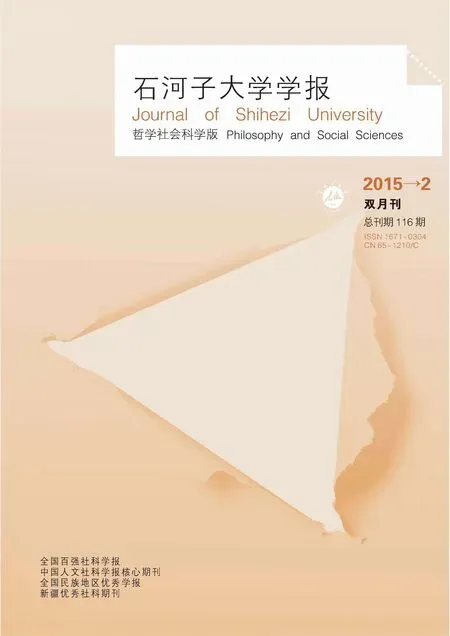感恩行旅的热度与限度:20世纪80年代王蒙小说中的新疆叙事
杨新刚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一、“新疆是个好地方”
对于王蒙而言,用“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歌词来形容他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在新疆16年的感受应该再准确不过了。同时,新疆对处于人生低谷的王蒙来说的确是一块福地与宝地。王蒙研究专家温奉桥先生认为,“新疆之于王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情感和心灵的‘原点’,更是思想‘再出发’的驿站。王蒙的一生,‘拐点’多矣……而其中最大的‘拐点’——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还是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层面——是新疆16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的‘换心的手术’是在新疆完成的。”[1]而施战军先生则说得更加形象与富有诗意,“新疆伊犁可以说是王蒙先生一个文学‘新房’,……和文学结婚的那样的新房”[2]287。在新疆他不仅做到了全身保命,“文革”期间未受到非人的待遇与冲击,“至少在伊犁,大多数人对‘文革’只是旁观和虚与委蛇”[3]305,而且他还收获良多。他不仅饱览了边地风土人情,了解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信仰,而且也开阔了视野,净化了灵魂,提升了境界。因此,当若干年过去之后,谈起卜居16年之久的新疆,感恩之情犹充盈胸中。“此时全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已经斗了个天翻地覆,一个个都是大祸临头,心惊肉跳,狼奔豕突,朝不保夕,而我跑到了远离政治中心,遥远啊遥远(苏联歌曲名)的地方,暂时过着太平小日子,我简直得其所哉,除了王某,谁有这个运这个机遇这个尴尬中的浪漫!谁能想象得到王某人是这样在伊犁的杨树林间,清清的渠水旁,洁白的雪峰下面,距离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和少数民族弟兄一道吃着串烤羊肉,喝着土造啤酒迎接索命追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263蛰居新疆,对王蒙来说,实乃人生之大幸。
1958年,王蒙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是年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区农村,参加劳动锻炼。1959、1960年又分别被下放到京郊农村两个不同的地方劳动。1961年,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1962年9月,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在中文系做教员,并发表了《眼睛》与《夜雨》两篇短篇小说作品。这一年秋天,王蒙应中国文联之邀参加了当时在北京西山举办的读书会(主要是反修)。正是在这个会议期间,他从文联领导人的讲话中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大风大浪,决定躲开时代的暴风骤雨。“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3]2181963年,王蒙经过与家人的沟通商议,决定举家奔赴新疆。
王蒙之所以选择远赴新疆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希望避免悲剧的重演。王蒙远赴新疆,有自我流放的意味,也有避乱全生的想法,“经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3]217其二,希望开阔自己的眼界。“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晴雨雪,我渴望爱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3]220其三,响应领袖的号召。“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3]218
1965年4月,王蒙遵照自治区文联领导同志的意见到巴彦岱公社参加劳动锻炼,并担任公社副大队长。他在巴彦岱一直工作了6年,直到1971年离开到新疆乌拉泊文教“五·七”干校劳动。
相对于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的王蒙,新疆无疑是个神秘无比充满魅力的地方,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新疆则是边疆省区。当旭日从东海跃升照耀着故宫的金顶碧瓦的时候,帕米尔高原上还是群星闪烁,新疆不仅与北京相隔数千里之遥,而且生活的节奏似乎总是显得从容而缓慢。但新疆又有着中原抑或北京所匮乏的得天独厚之处,牛羊成群,雪山连片,吐鲁番的葡萄与哈密的瓜,可谓物产丰饶,尤其是在物资紧缺的时代;新疆生活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回等民族,他们“大杂居、小聚居”,大家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和谐共存,仿佛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民族兄弟姊妹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可谓民风淳朴厚道。
1966年开始的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潮波及新疆,但王蒙当时在新疆却并未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他与淳朴可爱的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及回族等少数民族农民兄弟生活在一起,王蒙不仅未被当作批判的对象,相反各少数民族兄弟姊妹对从北京来的“老王”优待有加。当“文革”期间自治区文联所谓的“大联委”下达对王蒙的处分命令时遭到了他所在公社的自觉抵制,“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我,文联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他们无权向公社下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所谓冻结王蒙存款的语句。他们明确地说,王在这里,并无不良记录,他们不准备对王下手。”[3]323这令王蒙百感交集,他在暗自庆幸的同时,更加以真诚回报真诚,以心换心地回馈各少数民族的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关爱。因此,他不仅更加热情认真地学习维语,而且更加积极投入到当地的生产活动中去。在担任巴彦岱大队副大队长期间,由于他的真诚努力与全心全意地付出得到了各族乡亲的高度肯定。
二、沉入民间:以自然和人民为师
新疆的生产与生活经历让王蒙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对社会与生活的认识,提升了人生境界,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思想及创作素材方面的基础。新疆当地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在王蒙内心留下了深刻映象。首先,他被戈壁滩上顽强抗争严酷自然环境的各种植物所折服,“戈壁滩上的植物令人肃然,梭梭柴,骆驼刺,红柳,沙枣,胡杨,它们生长得坚硬,不规则,枯干,疙里疙瘩,伤疤斑痕,多棱多刺。它们绝无江南植物的柔润多汁,婀娜妩媚,它们只能以旱抗旱,以枯御枯,以歪就歪,以稀而瘦减风,以绝不艳丽柔媚而和光同尘,知白守黑。它们是置之死地而后活,置之不毛而成为戈壁滩的稀疏毛发。它们仍然是戈壁滩的生命的象征,而灰色的铁青的碎石才是永远绷着绝对无情的脸。”[3]231-232其次,他被高与天齐的崇山峻岭的雄伟姿态所折服。“我走过的南疆地区大致位于天山之南与昆仑山之北,两边的山都不大看得见,又总是模模糊糊地看着远方的山影。”[3]232“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无法不感到个人的渺小,不感到人与人携起手来的必要,不感到一味自吹自恋自怨自我循环自我按摩的没劲。”[3]232这一切冲击着他的心灵,这种感受久居都市的王蒙从未体验过。再次,不仅乐器、花帽、皮靴、铜壶、地毯、毡子与莫合烟等新疆特有的风物吸引着王蒙,而且当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深深地吸引着着王蒙,特别是维吾尔族文化。他觉得维语是世间最为美妙的语言之一,他拜维吾尔族的老者甚至孩子为师,向他们学习维语的发音与实际用法。“当人们尤其是外国人问起我究竟在新疆干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是在那里学习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再两年,不正好是博士后的学习培养吗?”[3]251在认真学习维语的同时,他还虚心认真了解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可爱的民族。他积极融入当地各族民众的生产与生活之中,他与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回族等少数民族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着他们的痛苦与忧伤,也分享着他们的幸福与快乐,践行着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我学的不仅是语音词汇语法,我学的是声调,是场合,是心思,是文化,是格局也是方式,我贴近的是维吾尔人民的灵魂!我也把大量汉族的历史传说幽默故事用维吾尔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给他们听,其中包括《东坡志林》上的一些轶事与机辩,深受人们的欢迎。话换话,心交心,话与心放到一起,我此生最快乐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赢得了维吾尔人民的友谊与信任。”[3]270
王蒙的身上有着独特知识分子的情怀——深入民间,感受民生疾苦,与他们甘苦与共。与同时代被下放的“右派”知识分子相比,王蒙并没有将流放当作天大的苦难,“他很可能是极少数的始终保持着少共情结的作家,当然,因为他的胸怀的宽广和思想的敏锐复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少共情结不是直接和硬性的理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对美好的永不放弃的肯定。”[4]18他曾满怀豪情地把奔赴新疆视为新生活的开始,“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3]222。因此,他不会把自己视为落难的“贵公子”,内心油然而生一种高贵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不仅不会自视甚高,相反,他抱持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甚至还有些兴奋的心情,看待到新疆农村的劳动锻炼。劳动间隙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濯足泉边听水声,饮茶瓜下爱凉棚。乳牛傲客哞哞里,雏燕多情款款中。”(其一);“蚕豆花开苦斗锄,蔷薇花谢马兰疏,家家列队歌航海(指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户户磨镰迎夏熟。”(其二)[3]246这表明他真正放低身段真正沉入民间,即使当地的各族乡亲把他视为北京来的“老王”。因此,当别人慨叹命运不公一味哀怨悲叹之时,一味保持一种知识分子或曰小布尔乔亚式的清高之时,他与当地的民众却打成火热的一片。“我劳动,我喜欢麦场上的工作尤其是扬场。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如虹如瀑布如雨点如精美的几何线段如臂膀的延伸,瞬时落成一堆,转眼成小山中山大山,麦秸麦麸与尘土随风而去,飞腾如烟如雾,肌肉紧弛,上肢伸展屈,姿势衔接,心情舒展,不是体操,胜似体操,不是舞蹈,胜似舞蹈。”“我也喜欢装车卸车,包括高轮牛车、胶皮轱辘和卡车。”[3]263他更是将下乡劳动的巴彦岱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将其视为再生之地,灵魂的升华之地。也正因如此,他才与房东阿不都·热合曼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也正是由于他与当地少数民族乡亲做到了真诚相待,他们才会向他敞开心扉,将他视作可以信赖的乃至推心置腹的朋友。当然,友谊是相互的,他也从少数民族朋友那里得到了尊重以及热情而真诚的帮助。王蒙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与他的“少共”情结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他因“右派”问题,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但他依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因此,正如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中唱的一样,“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呀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相信自己的言行经得起党和人民的考验,辛勤的付出能够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一句话,他相信。“因为相信。五十年代,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间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相信歌曲,相信领导,更相信人民,相信青春和微笑,相信春天和花朵,相信红军和军号,相信马恩列斯毛泽东直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相信建设新生活的愿望,相信历史,相信历史的运动即使呈现螺旋形,总的趋势仍然是向前进步。相信历史的曲折终将跨越,个人的不幸毕竟算不了什么。相信爱情也相信文学,相信电影也相信大报告,相信作家协会与人民公社,相信劳动创造世界,相信品格,相信道德和修养的必要性,相信光明的快乐的公正的生活终将变成永远的不可逆转的现实。”[3]246
王蒙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信仰及其由此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与生活方式。他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父老乡亲善良淳朴,过着与世无争恬淡而宁静的日子,他们每个人各自守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不急不躁,乐天知命,承受着当下的一切,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生老病死,蹇涩通达皆不论,几乎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当地少数民族大都有着虔诚的信仰之心与独特的人生哲学。其中维吾尔族关于人生的“塔玛霞儿说”与“伟大说”,深深地影响着王蒙。“维吾尔人喜欢的一个词儿叫做‘塔玛霞儿’,可以译作‘漫游’,但嫌文了些。可以径直译作‘散步’,但嫌单纯了些。可以译作‘玩耍’,但嫌幼稚了些。可以译作休息,但嫌消极了些。可以译作娱乐,但嫌专业与造作了些,娱乐是有意为之,塔玛霞儿却是天趣无迹。塔玛霞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像 play也像enjoyment,像relax也像take rest。维吾尔人有一句相当极端的说法:‘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是塔玛霞儿。’”[3]280“对于人生的理论除‘塔玛霞儿说’还有‘伟大说’。有天晚上,热合满与我谈天,他大谈人生是乌鲁克(伟大)的,他说应该知道,星期一是伟大的,星期二也是伟大的,那么星期三更伟大了,星期四是伟大的,星期五尤其伟大(按周五名主麻,是伊斯兰教的祈祷日),然后周六周日都是伟大的,然后每月从一号到三十号每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是伟大的,他讲得非常兴奋。我不能详解,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讲法。人生的每一天,本来就是伟大的呀!”[3]281王蒙长达十多年的新疆生活阅历,使其逐步了解与认识了当地各少数民族民众的人生智慧与人生哲学,并从中汲取了面对人生逆境的强大力量。因此,赵一凡先生认为,“老王写起新疆来,情感充沛,题材丰富,无人能比。”[5]5王蒙之所以具备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其来有自,16年的新疆生活不仅给予了王蒙丰厚的生活经验,而且也向他展示了新疆各民族的通达的人生哲学。
三、乐天安命:初心永在 本真自在
王蒙曾经说,“光在北京,哪怕在北京远郊区,更不要说在高级机关与文教单位工作上十年八年,你不可能了解国情,你不可能明晰实际,你仍然高高在上,你仍然凌空蹈虚,你仍然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去新疆的另一方面的体会。”[3]229这些体会,成为王蒙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初到新疆,王蒙担任《新疆文学》的编辑。1964年,他在《新疆文学》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他还写过反映当地民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红旗如火》与《买合甫汗》,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1973年,他任职于新疆文化局创作研究室。1974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1978年,王蒙发表了“文革”后的第一部作品《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其党籍得以恢复。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在伊犁》(系列小说),包括《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好汉子依斯麻尔》《虚掩的土屋小院》《葡萄的精灵》《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逍遥游》《边城华彩》。1990年代,发表《萨拉姆,新疆》《故乡行——重访巴彦岱》《伊犁,我没有离开你》《心声》《奶茶》《永远的美丽》《又见伊犁》《无花果》《宰牛》《四月的泥泞》《我们大队的同事们》等散文,以及《雪满天山路》(之一、之二)《木卡姆》《回新疆》《塔什库尔干》等诗歌。2013年,发表了以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伊犁地区阶级斗争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王蒙有关新疆文学创作可视为中国传统边塞文学在当代的显现,但他的创作又不同于既往的边塞文学。因为许多边塞文学的创作主体与边塞及世局于此的各民族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而王蒙则不然,他曾经在新疆生活过16年,对当地居民的文化心理及生存样态基本上做到了了如指掌,而且很好地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之中,并成功地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另外,新疆16年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来说,不仅仅是拓展了叙事内容,同时也在叙事手法与叙事艺术方面有着重大的启发作用与意义。李敬泽先生提醒人们注意,“他(指王蒙先生,引者注)在80年代初,一系列的小说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小说艺术,语言风格的令人炫目的创造性,绝不仅仅是来自于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可能一直不是太留意,他同时也深受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影响。”[6]276吴义勤先生在评价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时曾谓,“他的叙事语言和整个表达方式,深得维吾尔语言的妙处。”[7]286应该是说王蒙先生小说语言叙事的独特性的形成,与他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密切相关。王蒙抱持着感恩之心完成了其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新疆叙事,这带来了两种效应:其一,他会比其他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的作家看到相对更为全面的新疆;其二,他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新疆边地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予以遮蔽,而这则直接影响到其该时期新疆书写的广度与表现的深度。
系列小说《在伊犁》充分体现了这个特征。该系列小说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核心,表现了伊犁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具有中国传统志人小说的突出特质,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与《虚掩的土屋小院》是《在伊犁》系列小说中,最能够体现边地民众初心永在,本真自在生存的两篇小说。
小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的穆罕默德·阿麦德本是一位回乡的知识青年,其内心丰富细腻而又宽厚善良、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渴望爱情,渴望新生活的维吾尔族农民。也正是由于他所具备的这些与其农民身份似乎不十分相符的特质,让他在乡村中显得较为特别,甚至与他人格格不入。王蒙将穆罕默德·阿麦德自“文革”到新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变化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生动可感的文学形象。在农村还实行薪酬计时制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只出工不出力,手持一个小的“耳挖勺”似的砍土镘,一副“软、懒、散”的作派。他善良热情,家境并不富裕但还是邀请“我”到其家中做客;他在村里经常被人嘲笑与打趣,而且经常和女性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显得有些过于活泼;但他却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的人,他向“我”表示,自己爱跳交谊舞、爱看电影、爱看书、爱唱歌跳舞,“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随着与穆罕默德·阿麦德交往的加深,“我”越来越了解到他鲜为人知的一面,从大的方面看,他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注意民族团结,“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从小的方面看,他极为顾家。父亲患有疾病,家里的很多事情母亲又做不好,又没有能干的年龄相当的姐妹,因此,他就把家里的一些“细活”承担起来,如做拉面,整理房间。这让周围的乡亲特别是男子汉们所看不起,因为在当地民众看来,男女有别,“细活”家务事应当由女性来做,而他却做了女子应该做的事情,丢了男子汉的脸面。他热爱文学,极为喜爱阿衣别克著的《纳瓦依》中所表达的思想,“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因为它正直,//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因为它弯曲。”他也非常喜欢书中的女主人公狄丽达尔。“我”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充满了感激,“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8]320他渴望爱情,但却因为贫穷拿不出体面而昂贵的彩礼,也就不能与他喜欢的玛依奴尔结合。他帮助玛依奴尔逃婚,并指责玛依奴尔父亲将女儿当作商品卖掉、无情地毁掉女儿终身幸福违反婚姻法的做法。但最终玛依奴尔还是嫁作了他人妇,令他徒唤奈何。在玛依奴尔与他人结婚时,他举止失常,甚至有些癫狂,表明他身陷巨大的痛苦之中。“文革”中,他因一句玩笑话被“斗批改”宣传队打成现行反革命成员,差一点就身陷囹圄。后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将小砍土镘换成了特大号砍土镘,积极肯干。70年代初期,他与病病殃殃的来自南疆的女子阿娜尔古丽结婚,但等到她的病治愈,身体彻底恢复,特别是她的家乡南疆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之后,她带着穆罕默德·阿麦德给的三百块钱回了家乡,在周围的人看来,阿娜尔古丽将一去不返。面对阿娜尔古丽可能不归的结局,穆罕默德·阿麦德没有抱怨,而是充满了感恩,“‘那有什么意思,强拽过来的还能是狄丽达尔吗……她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大儿子了,这家业也是她帮助我挣下的,即使她不回来,也算对得起我了……何况,我在这里的名声……不太好。’他满眼是泪。”他告诉“我”如果阿娜尔古丽真的不回来,他就将孩子交给母亲带着,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流浪。他拿下都塔尔,拨动两根琴弦,唱起来了,“我也要去啊,我也要云游四方,/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我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我要越过高山和大江。/安拉会佑护我吗?能不能平安健康?/我愿能够归来,或许能回来,/回到我个生我长我的地方,/回到我亲爱的故乡!”[8]335
《虚掩的土屋小院》刻画了“我”的房东——一对维吾尔族夫妻——女主人阿依穆罕与男主人穆敏。“我一想起穆敏老爹与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二十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文化知识,却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能的厚道与含蓄。”[8]441阿依穆罕平素酷爱喝茶,她之所以嗜茶如命,是因为她将喝茶当作了精神寄托。阿依穆罕有过两次婚姻,曾生育过6个孩子,但均夭折了。内心无比痛苦的她只能通过饮茶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下,我们又说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8]413看似乐天知命的话语中,折射出其内心的酸楚与无奈。她对穆敏非常关心,为他烧水做饭,不论多么辛苦毫无怨言。令“我”先是不解继而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丈夫并未如期归来。她走到街心眺望,之后又添水烧开,“又往外扒拉扒拉火,走出门去迎接。如是搞了好几次,也没有把老爹等来,只是费了许多水又许多柴。”[8]409中午依然没有等到丈夫,晚上也同样如此,但她做着同样的事情,并无怨怼,“吃晚饭的时候老爹也没有回来。大娘又是烧开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伫立着眺望通往庄子的那座架设在主干渠上的木桥,前前后后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烧干了一锅又一锅的水,耗费了一把又一把的柴。”[8]410这看似简单的举动中,蕴涵着阿依穆罕对丈夫穆敏的款款深情。当得知穆敏一定要回南疆探亲时,她又惴惴不安,担心会失去穆敏。当穆敏从故乡回来之后,她又笑逐颜开。男主人穆敏为人诚实,辛勤耐劳,在公共事务方面是个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是非分明敢于仗义执言。同时,对信仰有着一种虔诚与认真,经常思考彼岸问题。当得知多年未曾联系的弟弟的下落之后,他兴冲冲地踏上返乡之路,但现实却与他开了一个玩笑,老人的一腔热情遭遇了弟弟一家人的冷淡。但他并不口出恶言,而是默默地承受一切,面对“我”的询问,他的回答极为平静和自然,“我想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经去过了,就回来了。”[8]438心中纵然有委屈,有痛苦,只是自我默默地吞下消化,让时光抚平内心的忧伤。
不论是穆罕默德·阿麦德,还是房东夫妇都是不忘初心,本真自在生存的边地民众。
四、独出机杼:非常岁月的别样人生智慧
穆罕默德·阿麦德与房东夫妇都是不忘初心本真生存的人,但边地民众中亦有独出机杼的“好汉子”,《淡灰色的眼珠》中的马尔克与《好汉子依斯麻尔》中的依斯麻尔就是这样的人。
《淡灰色的眼珠》中所谓的“傻郎”马尔克木匠是个黑头发大眼睛高鼻子大手大脚的“美丰仪”的“伟丈夫”。马尔克的妻子阿丽娅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不久就离了婚,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了一位令人垂涎的美丽富孀。她整整过了十年独身生活后,遇到了高大英俊流浪到本地的木匠马尔克,与之结成夫妻,相濡以沫共度人生。马尔克富于生活的智慧,总能够找到他人看不见的生路与机会;又由于他富于生活的智慧,因此他具有他人所不及的伶牙俐齿,“文革”期间,他张口语录,闭口语录。紧张的麦收时节他要到城里卖掉他做的木制品被执勤的民兵阻拦时,“我”见识了他的“辩才”。“马尔克衣冠整齐,精神焕发,虽然受阻,但是并不急躁,而是耐心地、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地与小民兵辩论。他说:‘……亲爱的兄弟,哦,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你的阻拦是完全正确的,是的,百分之百正确。我们的夏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错,我应该参加会,不参加会是不对的,它是我的缺点,它是我的错误,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诚恳地检讨,坚决地改正。但是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之官则思。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心群众生活,打击贫雇农,便是打击革命。而我呢,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雇农,我来到毛拉圩孜公社时候,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我是用土坯作枕头的。那么,是谁,发扬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了我呢,亲爱的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那就是你的阿丽娅姐姐呀!当然,这是党教育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帮助的结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8]343-344“我”十分惊讶于他的能说会道能言善辩,“马尔克诚恳地、憨直地、顽强而又自得其乐地一套一套地讲个没完,他的目光那样清澈,天真无邪,又带有几分狂热。他说话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一个正在钻木头的钻子,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他的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胳膊,特别是两只大手的拙笨的姿势,使你无法对他说话内容的可信性发生怀疑,何况那是一个除了怀疑我自己,我不敢也不愿怀疑别的一切的年月呢。”[3]344在“我”和众人的说合之下,执勤的民兵最终不得不在夏收大忙季节放走了拿小摇床到伊宁市前去交易的马尔克,他依靠“辩才”取得了胜利。
马尔克是个极为出色的能工巧匠,他的木匠手艺虽不能说鬼斧神工,但在当地首屈一指,做出的成品精美绝伦。他热爱生活,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却有着将生活艺术化的内在追求。作为木匠,他极力反对粗制滥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8]352马尔克知恩图报,由于“我”替他说情,外出回来之后,邀请“我”到他的家中做客。“暮色中我看见他的小院门和小门楼修得整整齐齐,木门上浮雕着几个菱形图案,最上面正中是一颗漆得鲜红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心镶嵌着一个特大号的料器的毛主席像章。小木门似乎还有一点特殊的机关,他左一拉右一按,没等我看清就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又自动关上了。”[8]348登堂入室之后,“我”有了更多更大的发现,“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墙龛里放置着一盏赤铜老式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地上铺满深色的花毡子。有一张木床,床栏杆呈优美的曲线,每一个接榫处都雕着一朵木花,四条腿像四只细高的花瓶;床上摆着厚厚的被子、褥子和几个立放着的大枕头,靠墙处悬挂着一个壁毯。我知道,这张堪称工艺品的床定是马尔克的得意之作,我也知道,维吾尔人家的这张床一般不是为了睡人,而是为了放置卧具和显示自己的富裕、自己的幸福生活的。”[8]350
对于女性,马尔克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让你死……”[8]352-353这表现了马尔克绝无大男子主义,他对女性极为尊重与热爱,这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妻子阿丽娅的态度上。阿丽娅与当地的裁缝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她收留了四处漂泊流浪的马尔克,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我”见到的是人到中年的阿丽娅,“她亭亭玉立,穿着透出嫩绿色衬裙的白绸连衣裙,细长的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锁骨显示出她的极为瘦削,鹅蛋圆脸,在灯光下显得灰白、苍老,似乎有一脸的愁雾。乳黄色的头巾不知是怎样随意地系在头上,露出了些蓬松的褐黄色的头发。鼻梁端正凝重,很有分量,微笑的嘴唇后面是一排洁白的小牙齿,可惜,使我这样一个汉族人觉得有点别扭的是,有一粒光灿灿的金牙在汽灯的强光下闪耀。但最惊人的是她的眼睛,在淡而弯曲的眉毛下面,眼睛细而长,微微上挑,眼珠是淡灰色的,这种灰色的眼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它是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包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她用她的丰富的阅历和特有的敏感观察了我,然后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语气词回答了我的问候。”[8]349马尔克对阿丽娅用情颇深,尤其是他当着“我”的面夸赞阿丽娅,“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第一号。’”[8]353当阿丽娅得知自己即将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之时,她提出要与马尔克离婚。因为她希望丈夫马尔克能与年青健康的爱莉曼生活在一起。她不能说动马尔克,希望老王出面帮忙说合,“我”劝告他为未来的日子打算,但马尔克对“我”的好心却表现出极大的反感,“‘瞎说!如果阿丽娅没有了,还有什么‘以后的生活’!’这个健壮的大汉当着来来往往看门诊的病人及家属,呜呜地哭起来了。”当“我”进一步向他提出要他接受爱莉曼时,他竟然突然愤怒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去!离我远一点!如果你不是老王,我会扭断你的胳臂,割下你的舌头!’然后他松了手,自己打起自己来,把我吓坏了。”[8]365他倾其所有给阿丽娅治病,最终马尔克也没有与他的阿丽娅分开,直到她离开人世。马尔克不仅心灵手巧,心地更是淳厚善良,而且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
《好汉子依斯麻尔》中会讲多种语言的回族汉子依斯麻尔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三区革命,有5年的民族军军龄,是个三等荣军。在平时有些小小不言的缺点,如爱吹牛,爱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事情等。但他也有一定的优点,如卓越的组织能力,在率领村民参加建设大湟渠大会战时,他赏罚分明,创新劳动技能,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工友的拥戴。基于虚荣与实惠的他极想当官,“文革”起来后,他积极加入造反派,但他并非真得要“造反”,而是借“造反”之举实现做生产队长的梦想。当上队长之后,他骑着高头大马“检查工作”,对普通农民指手画脚,利用职权打借条从生产队里支取现金、利用权力挪用集体财产并役使他人为自己建房等。他能屈能伸,面对沉着老练的对手王吉泰,他绝不硬碰硬而是拿捏适度,既要保持自己的威严,又不要与王吉泰把关系搞得太僵硬。“好汉子依斯麻尔”真是一个难以做出简单评判的人,他真实而“本色”地生活着,他或许是一个将生活当作演戏的演员,极为容易地游走穿行在生活与戏台之间,极易入戏,也极易出戏。“他好像一个演员,上台演戏的时候有声有色,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等散了戏,卸了妆,收起了行头,便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地穿上最普通的衣服,融化在普通的人群里去了。”[8]398-399
不论是马尔克,还是依斯麻尔,他们的言行足以展示出非常岁月中别样的人生智慧,他们没有大奸大恶,面对非常岁月只有“幽他一默”或耍点儿小聪明。
另外,小说《葡萄的精灵》回忆了穆敏独特的酿造葡萄酒的方法,而《爱弥拉姑娘的爱情》则不仅绘声绘形地描述了图尔拉罕对养女爱弥拉的疼爱之情,也叙写了爱弥拉人生的遗憾。当教师的爱弥拉与丈夫自由恋爱相结合,但她的婚事并未得到图尔拉罕的祝福,因她不愿养女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吃苦。而爱弥拉在如何处置养母图尔拉罕遗产问题上与哥哥及姨母又吵得不可开交。《逍遥游》一方面描写了“文革”期间“我”与妻子在伊宁市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描绘了“我”与共处一院里的房东和租客们之间的交往。在这里“我”既目睹感受了“武斗”的惊心动魄,又体验了多彩的人生。愤愤不平感到晚景堪忧老无所依的老房东茨薇特罕、同为租客赠予“我”馕的不知名的维吾尔族老年女性、瘦小枯干声音尖利的哈萨克族老太太及其神秘的“病狮”儿子、对孩子极为溺爱的满族的白大嫂、来自湖南的最年青、最富有朝气最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年轻夫妇、叫得最欢质量最次既想推销掉手中的奶皮子又想做中间人捞好处的“卖奶皮子的”、头脑越来越活泛的年青小伙子瓦里斯江……动荡的时代中,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不怨天尤人,不指桑骂槐,只是静静地等待该来的一切,不回避,不躲闪,“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都安之若素。“多少迷人的生活和大地!当动乱的忧烦成为过去以后,一切会更加美丽!”[8]529《边城华彩》既描述了“文革”期间对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无端与滑稽的批判,又塑造了一位沉稳幽默的民兵队长艾尔肯,当造反派问他持有何种观点时,他的回答堪称机智。“燕子与猫”则记述了给“我”带来好运、排遣寂寞、感悟自然之道的芳邻——一对燕子。房东阿依穆罕认定“我”是一个好人,功劳就在于燕子,“按我们维吾尔人的说法,只有善良的人住的房子里,才会有燕子栖息。这个小屋是我故意留了那么大的门缝的,但两年来燕子一直没来。您才来,燕子就来了,您瞧!”[8]537在伊犁农村曾经有“花儿”与匹什卡克两只小猫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前者带来的是安慰与惊诧;后者则是无比的震惊——能够从七八公里之外被遗弃的地方跑了回来。“长女”描写了维吾尔族女孩莱依拉,她不过八岁左右,但却是“母亲的助手,母亲的知音,母亲的艰辛怨怒的替罪羊”,“弟弟妹妹的保护人——童年只属于弟弟和妹妹”[8]541。“夜半歌声”,回忆了各具特色令人终生难忘的喀什噶尔民歌与伊犁民歌。“我从来没有听过像喀什噶尔民歌那样温柔、又那样野性的歌。它充满了野性的温柔与温柔的野性,唱完听完后你觉得全部生命、全部身心都得到了尽情发挥。”“我从来没有听过像伊犁民歌那样忧伤、又那样从容且甜蜜的歌。它充满了甜蜜的忧伤与忧伤的甜蜜,唱完听完以后你觉得你已经体验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你已经升华到了一个苦乐相通、生死无虑的境界。”[8]549
王蒙20世纪80年代以新疆为表现题材的小说,不仅表现了新疆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现实,描述了各少数民族各自的信仰、文化、风俗及其生存样态,也塑造了边地各少数民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虽然该时期王蒙小说中的新疆叙事,带有浓重的感恩色彩,给其表现的深度带来某些限制,但《在伊犁》系列小说依然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1]温奉桥,温凤霞.从伊犁走向世界——试论新疆对王蒙的影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1).
[2]施战军.王蒙依然年轻[C]//温奉桥.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3]王蒙.王蒙自传:第1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4]陈晓明.历史的前进性与多元文化的交融[C]//温奉桥主编.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5]赵一凡.王蒙的“中段”[C]//温奉桥.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6]李敬泽.“这部书有多方面的非常重要的意义”[C]//温奉桥.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7]吴义勤.穿越历史的写作姿态[C]//温奉桥.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8]王蒙.王蒙文集:第1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读温奉桥新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