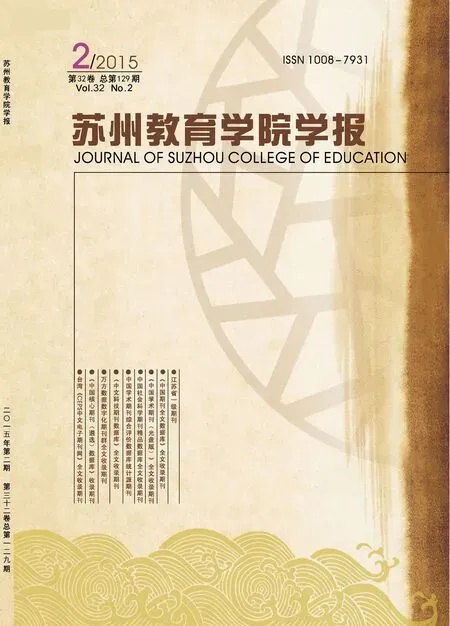1980年代作为“现象”的《故事会》:新时期的文学价值回归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社会思想得以解放。1979年《故事会》第一期去掉刊名中的“革命”二字正式复刊,并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期,直线上升的发行量一度占据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形成期刊界的“《故事会》现象”。究其原因,除刊物自身因素外,主要还与1980年代对传统价值的回归有关。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2-0029-03
收稿日期: 2014-12-15
基金项目: 2014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_1208)
作者简介: 马圆圆(1990—),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
The Stories as a “Phenomenon” in the 1980s: The Return of Literary Values in a New Era
MA Yuan-yua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1980s, social thoughts were liberated with the end of the “Ten Years’ Chaos”. In 1979, the fi rst issue of The Stories came out without the word of “revolution”, which signaled its re-publication and started the fi rst period of its prosperity. During the time, the magazine’s circulation soared and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he cultural product market,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The Stories Phenomenon” among various periodicals. In addition to factors related to the magazine itself, the phenomenon can also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return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1980s.
Key words:1980s;The Stories;new era;literature;return of values
1979年《故事会》去掉刊名中的“革命”二字复刊,直至1985年短短七年时间,发行量由1979年的267 933册直线上升至1985年的6 280 000册,完成了刊物的第一次飞跃,并占据了期刊界的半壁江山,形成期刊界的“《故事会》现象”。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了“80年代”的开始,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有所放松,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故事会》作品基础上,根据历史承接规律,结合“五四”文学直至“文革”前的文学史,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并非是文学价值的“重新确立” [1]109,而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期,并为新时期文学迎来了第一次辉煌。
一、“人的文学”复兴
十年内乱对人性的长期摧残,人们信仰的破灭和权威的崩溃,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个性解放、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成为文学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潮流,这无疑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思想的回归。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继辞世以及“四人帮”下台,全国范围内的悼念与庆祝活动此起彼伏,民间文学期刊《故事会》1979年第1期刊登征稿“启事”:“我社拟编选一本以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爪牙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所造成的流毒与影响” [2]的杂志,“故事创作与活动笔谈会”栏目随之刊载《写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故事创作的光荣任务》《努力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等两篇文章,这一度奠定了《故事会》复刊初期的基调,以悼念老一辈革命家为主题的故事题材为人们打开了情感的闸门。1979年第1期首篇《人民广场的一面战旗》以周恩来总理逝世为背景,讲述人民自发地与行将就木的“四人帮”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接着,故事创作开始转向对普通人的遭遇、命运和情感的关注,以1979年第3期《巧姑娘招亲》为开端,依次于第4、5、6期刊登《如此恋爱》《“女状元”与“一刀准”》《一个青年姑娘恋爱的故事》等,反映新时期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爱情故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类故事仍采用人们熟悉的“才子佳人”模式,只是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区别于以往风流才子与名门小姐,而是转变为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断拼搏奋斗的有为青年男女。这一模式符合人们“有头有尾、布局周到”的阅读要求与心理期待。因而,刊物在发行后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这一时期的《故事会》强调“人的文学”,极力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定程度上宽慰了人们久被压抑、践踏的内心与尊严,究其实质仍与精英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相关。中国在近代史上出于对西方的抵抗和对先进文化的追赶,表现在文化方面则带有明确的现代国家意识。这一追求含有明显的民族性,“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将民族具体化为“人的意识”。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意识以压倒一切的态势占据了中国的社会思想阵地,但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思想文化大量涌入,“国家意识” “民族意识” “人的意识”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出现了“走向世界”的大潮流,文学界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逐步迈向“多元化的新世纪文学”。这一时期的《故事会》率先在复刊初期引入外国民间文学的内容:1979年第5期《故事会》首次刊登了日本民间故事《贫穷神》。并从1980年第1期开始不断增加外国民间故事的数量,由原来的1篇增至3~5篇不等,在刊物尚未有固定栏目的情况下,“外国童话” “外国民间故事”于1981年第1期即确定下来。随着1984年国家提出实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策开始,中国重返世界大家庭,逐渐走上“正常化”国家的轨道,《故事会》栏目设置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反映新时期世界各地人民和谐生活的“新故事” “外国民间故事” “妈妈讲故事”等栏目逐渐固定并形成刊物品牌,其比重占整个刊物的50%以上,至20世纪80年代末上升为70%(剩余30%分别为笑话、漫画等)。外国文学作品比重不断增加,刊物内容呈现多元化态势,这意味着历史的震荡在1980年代后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安宁平和的市民生活成为文学的主题。
二、文学主张的回归
综观1980年代的《故事会》,都会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即其所颂扬的人物,都具有较为典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个人奋斗的目标。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中国文学必须遵循的“纲领性”文件,政治宣传成为文学的重要功能,1949年后社会主义运动又将之发挥至极致,这一功能自然而为新时期文学所承继。具体而言,一方面它顺承儒家的观点,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以载道”,文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利作用;另一方面,为结合革命宣传的需要,毛泽东的《讲话》旨在突出将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教义的载体,突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不仅要求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的政治形势、政治任务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在具体工作步调上,要求与政治完全结合。复刊后的《故事会》明显保留着这一文学主张的痕迹,如1979年第2期论及故事创作问题时指出,故事创作要积极配合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要恢复传统,为实现‘四化’服务……正确理解故事创作与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 [3]。1979年第3期《巧姑娘招亲》中,良种大队老队长女儿阿巧贤淑温柔、聪明能干,“使山芋藤上结出番茄,蓖麻树上开出棉花,大六月里吃到花菜,十二月里种出西瓜”,其追求者踏破门槛,然而她却偏偏喜欢地主出身黑不溜秋的“闷葫芦”实验员阿顺。由一起做实验培养出来的深厚感情,因阿顺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断受到外界的阻挠,但为了响应国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故事发展的高潮将笔锋一转:像阿顺这样积极上进的青年即使出身不好但仍可被吸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个人的命运遭遇无不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息息相关。再如,自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后,全国范围内陆续掀起对“四人帮”的批判活动,1976年11月,由《诗刊》编辑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联合主办了“纵情歌颂华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朗诵演讲会。1979年作为《故事会》的复刊年,第2期《花脸孙亚雷》、第3期《巧姑娘招亲》、第4期《马蹄铁和老槐树》等故事均是对“纵情歌颂华主席”这一主题的深刻反映,而“愤怒声讨‘四人帮’”则几乎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
然而文学为政治代言绝非仅仅是为了宣传国家的政治政策,其更深层次的功能是对于民族性的建构,最终想要建立的是“民族独立和民族防卫的屏障意识” [1]132。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一支,它所要述说的是来自民间、能够体现民间正义与智慧赋予参与者的不可战胜的伟力,更确切地讲它是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生动再现。作为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仿真”写作,对民众更具有亲和力和可信性。例如,故事对“四人帮”人物和人民英雄形象的区别,均是这种道德理想的具体体现。《人民广场的一面战旗》 [4]中,“四人帮”的头目和其跟班均有着狰狞的面孔和可鄙的名字,马天水及其同伙“歪鼻头阿国” “三寸丁小爬虫”贪婪、残忍、凶狠、狡诈,他们是对另一个群体构成伤害的形象符号,也是旧模式中恶人形象的“四人帮”版。相比之下,舍小家为大家的人民警察马天民,在仅有的一天休假中不舍得回家陪伴妻子和刚刚满月的孩子,选择帮助一位怀抱婴儿的聋哑女人找到回家的路。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好警察身后相应地有一位体贴入微的好妻子,在自己孩子满月的当天路遇执勤的丈夫竟没有一句怨言。 [5]所谓只有无私奉献,没有个人杂念,无疑是共产党人必备的道德品质。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6]而文化领导实际上就是“文化和道德”的领导,在通俗的大众文学的民族性叙事中,又被赋予了诗性的色彩,流血牺牲、视死如归、公而忘私等品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都是被极力倡导的。新时期的《故事会》在保持“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还集中了大量此类题材的作品,一方面传递道德力量,配合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树立,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扬起希望的风帆,更为自身的生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农村文化趣味的延伸
一份刊物的风格往往能从其“征稿启事”中找到蛛丝马迹。《故事会》的稿约一直强调作品的民间性,无论是题材还是创作方式均要求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对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奠定了民间文学的农业文化基调,1942年“为工农兵服务”的普及,使之成为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 [1]152因此我们可以粗浅地将1940年代至1980年代的“人民”概念外延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新中国建立,对于执政者而言,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采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入时间表;另一方面,基于长期革命的历史经验,继续推行“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即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状态,是葆有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本色的途径。它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思想文化、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城市倾向,于“十年动乱”期间被发挥到极致。当动乱戛然而止,这种倾向仍旧潜藏于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处。相比之下,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则被看作人无边欲望的反映。从1979年第1期《磨盘山》开始,每期均有以乡村生活风貌为主题的故事。尽管有些作者对城市生活十分熟悉,但鉴于历史记忆,对新时期仍有着深深的惶惑与迷茫,即使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对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例如,《九枚硬币》讲述江南小城里一位爱乱花钱的工人薛亮,因平时大手大脚,在与女友首次约会时仅剩九枚硬币。他囊中羞涩却又不愿丢面子,故而开始编造谎言,为圆谎而不断地制造新的谎言,以致在女友面前频频出丑。终以薛亮坦诚相对、道出实情才成就了一段姻缘。而结尾所引用的一句顺口溜“艰苦朴素是正道” [7],才最终在真正意义上点明了故事的主题。
当这些带着淳朴气息的作品进入城市时,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的新“奇观”。但其实际上带来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即“依靠人民政府才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唯一保证”的观念。如故事《关怀》讲述20世纪50年代初陈毅、张茜夫妇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不仅为国家事务日夜操劳,而且还在百忙之中对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线的工人杨云及其家庭关怀备至。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所蕴涵的国家对人民新生活的关心和对生动健康生活的积极倡导,带给人们以想象与憧憬,在情感复归的1980年代,正是(下转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