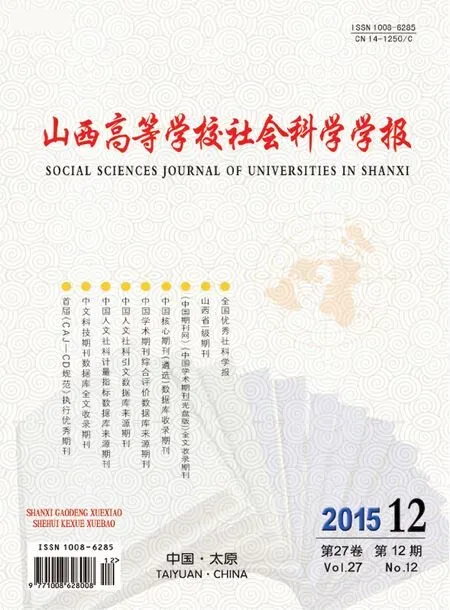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送别诗”认知诗学分析——以《送元二使安西》《别董大》为例
陈 晖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08)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送别诗”认知诗学分析
——以《送元二使安西》《别董大》为例
陈晖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08)
[摘要]从认知诗学角度出发,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送元二使安西》与《别董大》进行了分析。图形—背景理论通过自身关系的调整与转化,不仅营造了诗歌的整体美感来凸显意境,而且在不断地分离转换过程中形成新的意境焦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与感知诗歌文本的深厚韵味与丰富蕴含。
[关键词]图形—背景理论;送别诗;认知诗学; 《送元二使安西》; 《别董大》
一、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兴起于20世纪末,继承了认知活动是基于人类对世界、周围环境感知与对自身经验的总结这一基本观点,并在此观点基础上将文学视为人类普遍的认知活动的一种。简言之,认知诗学是将认知科学应用于文学阅读的一门学科,是探索文学作品的工具。苏小军认为,认知诗学是理解语篇运作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比较全面的重新审视[1]。Stockwell认为:“认知诗学是一种基于认知科学的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不单是文学的写作技巧, 或仅仅是在世界知识基础上对文学语篇的理解, 而是一个更自然的阅读过程。”认知诗学提供一种方式,探讨如何精确把握文本的脉络走向与意境;同时, 强调文学阅读的体验性、互动性和文学语境性[2]。梁丽认为,认知诗学强调读者在文学语篇理解过程中的在线识解心理机制,读者在语篇理解过程不断形成新的理解与回应过程[3]。蓝纯将认知诗学理解为根植于语言的交叉学科,对文学的研究根植于读者的普遍认知活动,对文学的研究根植于对人类世界知识与普遍知识的研究[4]。熊沐清探讨了认知诗学的任务,将其任务归纳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够理解读者的文本解识过程与特定的理解效果,还有助于进一步验证认知诗学理论在文本中的阐释力以及其在营造文本效果中的作用[5]。认知诗学的研究发展离不开其最基本的理论:图形—背景理论。
二、图形—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理论是一种以突显原则为基础的诗学认知观,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凸显”的图案上而忽略了周围其他的图案。该凸显的图案即为图形,而其他图案则为背景。在此基础上,Stockwell探究了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并将他们的关系概括为:将有相对静止,在其他事物的前部、顶部或上部,比其他部分更细节化,有完整边缘,处于不完整背景的一部分,或凸显出来的总结为图形;而将无固定形状,无清晰轮廓线,细节未分化,起衬托作用,无已知的时间空间特征的总结为背景[2]。其后,图形—背景理论被Talmy应用于句法研究,他将图形—背景理论应用在句法结构上,阐明了该理论对复杂语法结构的强大阐释力,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到儿童的二语习得研究中。Langacker将背景—图形理论应用于更为细致的介词与小句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据感知的凸显程度创立了认知句法[6]。在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中,Stockwell强调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理解与关注在于不断地被新的关注点所吸引,并通过背景—图形的转换不断形成新的关注点[2]。
国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图形—背景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介绍与概述,如熊沐清指出:认知诗学是文学与语言学的新界面,图形—背景理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文本解读机制[5]。高娟[6]、匡芳涛[7]等也有类似的研究。从研究方向来看,近期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背景—图形理论在诗歌的翻译对比研究及其现实化方面。李蓉运用该理论对同一诗歌的不同译文进行分析,指出准确识解不同译文中的图形,对指导读者准确把握不同译者对诗歌意境及原作思想的理解有重要作用[8]。梁丽强调了背景—图形理论对诗歌现实化及其意境表达的作用,认为读者对诗歌意境的理解,即对图形—背景的认知关系发生了转变,形成了新的焦点,是一个不断形成新的理解与回应的过程[3]。熊沐清指出,在背景—图形理论的现实化过程中会发生背景—图形的分离现象,即随认知环境的变化与焦点的转移,在图形—背景分离过程中具备背景特征的物体可能在另一次分离中成为图形,起到焦点与营造意境的作用[5]。从研究内容来看, 一是以对中国古典诗歌为研究内容,如蓝纯以唐宋古典诗歌为对象进行的研究[4],黎萌以唐代山水田园诗为对象进行的研究[9]以及朱海燕以杜甫诗歌为对象进行的分析[10]。二是以外国经典诗歌为研究内容,如文慧以外国经典诗歌《苍蝇》为例进行的分析[11],李瑶琴以华兹华斯诗歌为例进行的分析[12]。
从研究方向来看,国内学者关注点相对集中于背景—图形理论在诗歌的翻译对比研究及其现实化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背景—图形理论的现实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意境营造的作用。从研究内容来看,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宋词及外国经典诗歌分析较多,以唐代送别诗为例进行的分析相对较少。故本文尝试在图形—背景理论框架下对唐代送别诗进行认知诗学分析,以期验证图形—背景理论的认知阐释力并试图探究其对送别诗意境的作用。
三、图形—背景理论下《送元二使安西》与《别董大》认知诗学分析
唐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使得“送别诗”成为唐诗的一大类。本文从《唐诗鉴赏辞典》中选取了盛唐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与高适的《别董大》为对象进行解析。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送友人出使西北边疆的诗。前两句写景,景中有画,画中有情。“渭城”“朝雨”点明了送别的地点与时间,一个“浥”字诗化了轻尘。在古老的咸阳城下,古道旁,清晨的细雨润湿了路旁的尘土,清新的雨后气息弥散开来。在这样一个清丽的背景下,“客舍”与“柳”作为细节,更集中、更明亮的图形被凸显了出来,客舍旁的棵棵绿柳,雨后更加翠绿。而“客”字暗含了离人,“柳树”的“柳”与“留”谐音,暗喻“惜远离别”与不舍,天因愁离而落雨,杨柳依依而惜离别之情便全部蕴含在其中,为下文的抒情做了渲染与铺垫。作者像一个高明的剪辑师,将镜头从景中有画的环境渲染中剪切到送友人离别的酒宴上。此时,图形—背景关系发生了转变与分离,写景意境中作为图形的“柳”在寓情意境中转换为背景,而“酒”则凸显出来成为了图形。但随后焦点再次发生了转变,作为图形的“酒”转换为背景,而“更尽”的“这杯酒”则转为了图形。“更”字说明酒已过多巡,但仍然有千思万绪汇在那“更”尽的一杯酒上。既有对友人西出阳关、跋山涉水、羁旅边塞的担忧,又有千言万语的叮嘱与不舍;既有想劝友人再喝一杯将其多挽留一刻的难舍,又有此次别离后友人无“故人”一起把酒言欢、不知何时能再相见的感慨。作者通过柳从背景中的图形到背景的转换,更新酒的图形—背景关系,将读者的关注点成功地吸引到后文中动态的“更尽”的一杯杯酒中,营造了天愁离落丝雨,故友更尽杯酒难离别的意境。图形—背景理论通过自身关系的转化,在其不断地分离转换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关注点”,以强化整体的意境效果。
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别董大》是唐代诗人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诗歌前两句晦暗寒冷的送别景色,正契合作者困顿不达的人生际遇。诗歌的后两句,借慰藉同样处在不达际遇出京远行的友人,抒发诗人的豁达豪迈之情。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将其所见所感、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作为“背景”,将自己特定的此时此地此感作为“图形”凸显,既有对友人远行的依依惜别之情,又展现出诗人洒脱豪迈的胸襟。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诗的前两句与《送元二使安西》相同,同为写景。诗人用黄云、落日、北风、白雪、南飞雁五个密集的意象营造了诗歌的整体意境。落日余晖下的黄云为静态意象,北风呼啸、白雪飘洒、大雁南飞为动态意象,静态意象构成的背景与动态意象构成的图形通过空间组织原则创造了整体意境上的美感。在静态意象构成的图形中,相对完整和具象的“雁”成为了图形,而很难找到界限的自然现象北风、白雪成为了背景。在第一次图形—背景分离中充当图形的意象在此次图形—背景分离中变成了背景,“雁”作为图形得到了“凸显”。雁南飞、人别离,诗歌的意境通过图形—背景的分离由苍茫广阔的旷野转向了别离之情。
通过对上述两首送别诗的分析,图形—背景理论在送别诗歌中的阐释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图形—背景理论通过自身关系的转化,不仅营造了诗歌的整体美感来凸显意境,而且在其不断地分离转换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关注点”,形成新的意境焦点。《送元二使安西》通过由送别背景—柳—酒的关注点的转移,营造了春日雨后—友人难留(柳)—把酒话别—故人难再见的意境焦点的转移。新的关注点的形成即意境焦点的营造,意境焦点的层层推进,全诗再尽杯酒难离别,叮嘱担忧说不尽,故人何时再相见的惆怅与悲凉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同《送元二使安西》相同,《别董大》通过图形—背景的分离,诗歌新的关注点为“雁”,新的意境焦点为离别。在第二次图形—背景的分离过程中,作为图形的雁(离别)转为背景。然而,同《送元二使安西》不同,此次作为图形的却不是更细节化、更具象的物体,而是更意象化的作者的景中所感。诗人之感,既有对远行友人的宽慰,又有对友人的鼓励,也有对自己与友人走出困顿挫败境遇的超迈豁达之感。这一不同从另一角度证实了图形—背景理论的强大阐释力,也反映该理论本土化与现实化的进程中,对意象化的唐代诗歌而言,背景—图形理论的特征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尝试在图形—背景理论框架下对唐代送别诗进行认知诗学分析,探讨了图形—背景理论在唐代送别诗歌现实化及实现诗歌意境中的作用。图形—背景理论通过自身关系的调整与转化,不仅营造了诗歌的整体美感来凸显意境,而且在不断地分离转换过程中形成新的“关注点”及新的意境焦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与感知诗歌文本的深厚韵味与丰富蕴含。
[参考文献]
[1] 苏晓军.国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J].外国语文,2009(4):6.
[2] Stockwell, P .2007.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3] 梁丽,陈蕊.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J].外国语,2008(4):31.
[4] 蓝纯.从认知诗学的角度解读唐诗宋词 [J].外国语文,2011(2):39.
[5] 熊沐清.语言学与文学的新接面:两本认知诗学著作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4):299-305.
[6] 高娟.Talmy图形背景理论概述[J].文教资料,2008(18):48-50.
[7] 匡芳涛.图形背景的现实化[J].外国语,2003(4):24-31.
[8] 李蓉.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J].外语教育教学,2011(7):69.
[9] 黎萌.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山水田园诗的认知分析[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3.
[10] 朱海燕.运用图形—背景理论解读杜甫诗歌 [J].语文学刊,2012(3):6.
[11] 文慧,李宏鹤.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苍蝇》分析中的应用 [J].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10(2):149-152.
[12] 李瑶琴. 图形/背景理论与汉英诗歌语言对比研究[J].语言应用研究,2014(8):158.

Analysis of the Poem aboutPoemsofFarewellfrom Cognitive Poetics
based on Figure and Background Theory
——AcasestudyofAFarewellSongandFarewellToaLutist
CHEN Hui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TaiyuanInstituteofTechnology,Taiyuan030008,China)
[Abstract]The figure /background theory is introdu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which was appli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Farewell Song and Farewell to a Lutist.The approach intended to unfold the poetic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e poems by the adjustment of the figure and the background.Moreover,it could form the new focus to attract the readers′ attention, offering an effective way to visualize the literal meanings 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poems.
[Key words]figure and background theory;poems of farewell;cognitive poetics;A Farewell Song;Farewell To a Lutist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12-0093-03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12.026
[作者简介]陈晖(1986-),女,山西太原人,太原工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诗学。
[收稿日期]2015-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