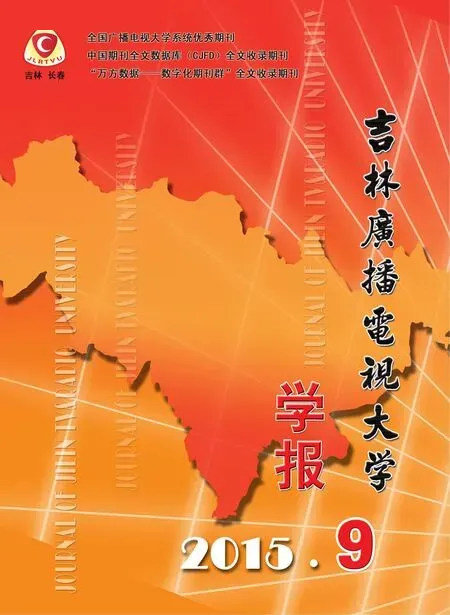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选择
刘小宇 王 柬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1982年,罗大佑在自己发行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里,有一首传唱至今的经典,《鹿港小镇》。歌词里写到,“台北不是我的家”,但“台北的霓虹灯”和“水泥墙”却在开疆扩土,向家乡“鹿港小镇”大步挺进。“鹿港小镇”成了只能追忆而不可返回的“遗失的美好”。可以说,在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基调上,2005年《额尔古纳河右岸》和1982年的《鹿港小镇》是精神上的连体婴儿,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此消彼长的现代化浪潮中,罗大佑和迟子建的情感指针坚定无移的指向前者。这种知识分子的乡愁与焦虑,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产物,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对于“湘西世界”和城市文明的两极化书写,是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
村上春树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①现代化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以辗压性的姿态将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样板向全世界推广复制,在现代化这座坚固、冰冷、充满工业气息的高墙面前,各种充满人文气息和历史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样式,命运都如同脆弱的鸡蛋,不堪一击。站在“鸡蛋”一边,便成了大多知识分子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大佑与迟子建,在处理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关系上时,都旗帜分明的表明立场,他们是现代化的批评和讨伐者,是古老乡村文明和民间文明的凭吊者和记录人。
2008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在授奖辞中写到,“(小说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但实际情况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对话姿态。对话,双方应该是差异性的存在,而小说从头至尾,作者就致力于将自己的叙事立场和价值坐标向“我”最大程度的靠拢和同一化。迟子建是一个鄂温克文明的代言人形象,而不是站在两种文明之间的反思者和探究者。
一、叙事立场的选择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②,迟子建选取了以“我”做为叙事视角,一大原因是“我”的生命贯穿了百年来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在场者,所以以“我”为视角是一种叙事的必须。但以“我”为视角,不一定意味着作者对“我”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态度的全盘接受。八十年代对现代化的盲目乐观是一种幼稚和短视,而如“我”一般对现代化的全盘否定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偏执,而对文化冲突双方任何一个方向的简单认同,都会妨碍小说的叙事深度和反思力度。然而,遗憾的是,在小说中,作家的立场与“我”的立场几乎未做任何切割,作者几乎是以“我”的代言人的身份,为我们描摹了一个民族日暮途穷的文化悲剧,并将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简单化的推给现代化,而且在涉及到现代化与鄂温克文化相互关联的段落,几乎全部采取负面的态度。
如果小说是以两种文明的“对话”为基本目标,依莲娜的成长经历无疑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她生于乡村,长于城市,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使得依莲娜对山内山外两种文明既有感性的体验,又有理性的比较。夹在两种文明之间,她成为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无根之人,一方面想向乡村引入现代商业模式,一方面又认为金钱污染了原有文明的美好。感性上对民族文化的依恋和理性上对商业文明的认同,使得依莲娜成了一个永远生活在别处的人。可以说,依莲娜思想与情感上的纠结和矛盾非常典型的折射出两种文明之间的断裂感和冲突感,这一角色无疑更具有“对话”的价值。
但是,依莲娜的样本意义不仅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反而成了被单向度批判的对象。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当依莲娜自食其言,将做完的两幅皮毛画带出山外时,“我”冷眼旁观,“她那样子,就像要给她的两条狗去找个好主人。”③这可能是,全书中“我”说的最刻薄的一句话,送给了她最爱的外孙女儿,仅仅是因为依莲娜试图在两种文明之间架起一座商业的桥梁。
“我的故乡有广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时间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炉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园、晚霞,这都是我童年时最熟悉的事物。”④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资源对于作者来说,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是,做为汉族的迟子建,可以毫无障碍地切换到鄂温克族的文化语境,不会有汉族作家为少数民族代言的隔膜感和违和感。但劣势是,作家与所要表现的文明没有拉开一个可以静观,反思的距离。
二、对年青一代命运的整体观照
如果说,出于对民族史诗回溯的需要,以“我”为叙事立场是一种结构上的必须,那么当小说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对年轻一代性格和命运的整体观照依然以“我”的价值坐标为准绳——即以在现代化和鄂温克文化之间站队的方式——来对年轻一代施以褒贬,这就多少带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固步自封。在新一代中,大概也分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别,被城市文明完全带坏的一类,在小说以沙合力和帕日格一对双胞胎为代表。沙合力少时便是乡里一害,大了勾结了几个刑满释放的山外闲人砍伐山里的自然的保护林,卖黑材,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其实沙合力的故事,并不太具有民族属性,放在一个不争气的汉族孩子上也是成立的,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双胞胎是由“我”来抚养的,算是比较早的“留守儿童”,隔代抚养对于孩子来说,本就容易滋生很多的心理问题,当然,这个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帕日格所犯的“罪行”则更加轻微,他只不过是将城市里的时尚、流行的唱法和舞步带回了山里,在“我”看来,也是矫揉造作得很,全无以往的天然纯朴(八十年代初,老一辈看不喇叭裤和蛤蟆镜,认为邓丽君是靡靡之音,这与“我”的看法如出一辙,与其说是年轮人的堕落,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代沟)。将年轻一代的所有堕落和不争气都推给现代化,似乎成了小说的标准答案。
第二类别,被认为是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希望所在。这一群体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天性纯良,带些傻气的安草儿(在迁徙时,唯一和“我”留在山上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以吃树皮为乐,立下宏愿要为鄂温克文化造字的西班。
前两类人似乎都各走极端。第一类有很浓重的丑化意味,在描写上也是速写式的勾勒,作者拒绝或者干脆不屑于走入他们的内心。但客观来讲,在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走出大山,走进城市,追求现代化的便利的生活,不管你接受与否,这都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迟子建把传承鄂温克文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不染城市文明尘埃的安草儿和西班身上,亦不现实,因为憨傻和纯真的确能够抵挡城市文明的诱惑,但这只是个例,不具普遍意义。西班对民族文明的坚守虽然是理性的选择,但也有隐患,从西班的心性上看,他具有一种隐士的品格,这种品格可以让他安于山林和孤寂,如果只是个人选择,已然足够,但西班虽然隐忍,但他对文化传承是有野心的,这种对城市文明完全垂下眼帘的态度是否有利于他野心的实现,也是值得商榷的。没有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激活,碰撞,西班的宏大志向会不会沦为闭门造车,这也是未知之数。毕竟善因未必结善果,文化的传承除了心性,还需要学识、修养、见识和眼光。
第三类别,便是在上文提到的依莲娜。在现实中,不管是小说家乌热尔图,还是歌唱家乌日娜,他们其实都是第三类人,代表鄂温克人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体系里获得世俗的成功和认可,然后再用他们取得的声望、地位和社会资源反哺民族文化。但在小说中,迟子建不仅将依莲娜的艰难探索和心灵裂变设计成死局,而且也改写了人物原型的死亡方式(现实中依莲娜的原型,画家柳芭是失足落水,而依莲娜却是主动殉葬于文化)。
作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依莲娜的死亡上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最后她的尸体在“河转弯处的几棵茂盛的柳树拦住了”⑤,这让“我”对那几棵多事的柳树憎恨不已,“因为依莲娜就是一条鱼,她应该沿着贝尔茨河,一直漂向我们看不见的远方的。”⑥“多事的柳树”就象征着原始文明对都市文明的拒绝,在河流看来,从依莲娜跨出山外的那一刻,她就不再属于山林与河流,这一身份的泾渭分明,连死亡也不能为之跨越。从某种程度上说,依莲娜自投死路,可以说是自己对文化皈依后的心灵平静求之而不得的绝望表达;也可以说是以已之命,向那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民族文化献上祭品。但贝尔茨河做出的回应是不接纳。这个不接纳的态度对于依莲娜是残酷的,但如果文化有灵,那这个文化是否也过于洁癖和保守了呢。
三、对于鄂温克文化的态度
“面对这一困境(传统文化的转型危机),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⑦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一直为人诟病,但在对鄂温克文化近乎穷途末路的挽歌书写中,迟子建再也“温情”不起来,反而有了“悲情”的倾向。为了达到最直击人心的悲剧效果,作者采用的途径就是将现代化与鄂温克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无限简化和对立化。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东西越美好,毁灭所产生的悲剧力量越巨大。在此逻辑下,小说里的现代化一无是处,而鄂温克文化则是一切人间至美的集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
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一切文化习惯和文化模式都是有因果,有缘起的。特别是像鄂温克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了了“生存”的烙印,在当代人眼中的诸种美德和“天人合一”,其实不过是彼时彼地鄂温克人能够取得最大生存机会的理性化选择。比如,鄂温克人不贪财,因为常年搬迁,财产只是累赘;鄂温克人爱护环境,因为环境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今天乱丢的垃圾,明天却有可能成被驯鹿吃入胃中,而驯鹿做为鄂温克人的生命之舟,任何使其生病和死亡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如此分析,不是贬低鄂温克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只是反感现代人动不动就把“文化”一词上纲上线,使劲拨高,拨到不食人间烟火,万民敬仰和追慕的境地。古代人,鄂温克人和现代人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语境。以彼时彼地的鄂温克人的行为习惯,来批判现代文明的贪婪和无敬畏之心,自有其参照物的价值。但如果一味的扬古抑今,便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了。
物质决定意识。在传统向文明进化的历程中,我们都曾经是身处鄂温克人的处境,所以他们的经历我们亦能感同身受,对于其文明的覆灭也会痛彻心扉。鄂温克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由于其特殊的生存方式,一直以一个化外之民姿态的遗世独立。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驯鹿的步伐和铃声将他们的生存范围划定在大山之中。这种化地为牢,是文化之幸,为人类保存了这样一块未受现代文明侵扰的人类活化石。但是,与其说是鄂温克人选择了山林,不如说是山林选中了鄂温克人。这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如果鄂温克人没有驯鹿,他们也许早就走出大山,汇入现代文明的大江大海,和我们一样,一边须臾不可离开现代文明诸种便利,一边抱怨和痛骂着现代文明的诸多副产品,然后发思古之幽情,遥想“天人和一”、“复归自然”的美好。
文化无绝对,不能将包括鄂温克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古文明,绝对的美化和神化。对于警醒现代人的野蛮和粗鲁,无畏和鲁莽,这些古文明是一剂良药,但如果将其做为否定现代文明的终级价值,就进入了另一种武断和蛮不讲理。毕竟,真理是有限度的,向圈外跨出哪怕一步,真理也会向谬误无限靠近。而且,这种美化和神化也是一种自欺欺人,毕竟现代文明已经和我们势如骨肉,再难分离。
注 释:
①村上春树林少华译.“高墙与鸡蛋”——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J].东京:文艺春秋,2012,(4):6.
②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3.
③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67.
④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1):17.
⑤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112.
⑥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66.
⑦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0,(7):45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2]谢元媛.文明责任与文化选择——对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事件的一种思考[J].文化艺术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