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文/本刊通讯员 孙明 蔡金刚
史海钩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文/本刊通讯员 孙明 蔡金刚
在上世纪40年代末那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开始执行撤退台湾的计划。由于知识分子的去与留,牵动整个社会对于新旧两种政权的信任与支持,当时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积极争夺高级知识分子。朱家骅在1948年底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紧急命令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劝说大陆籍知识分子来台任教,因此有许多科技界人士赴台与傅斯年的鼓动有关。

傅斯年(立排右二)与著名学者陈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钊(立排左四)等人合影,此后他们便天各一方。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负责执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有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陈雪屏(时任代理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其中北京(时称北平)方面由蒋经国、傅斯年、陈雪屏组成三人小组,“教育部”、“交通部”、“青年部”、“国防部”及“华北剿总”等予以协助。
当时平津战役正处于关键阶段,三人小组把计划南撤的北京文教界人士分为四类:一、各校、院、会负责人;二、中央研究院院士;三、与官方有关的文教人士;四、学术界有贡献者。以上计划人数约三、四百人。根据上列四原则罗列名单,如冯友兰、饶敏泰、毛于水、杨振声、罗常培、张政娘、沈从文等著名学者,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教授居多。
从1948年12月起,三人小组陆续派专机载运平津地区的学者南下。15日,将胡适、陈寅恪、张佛泉、张伯谨、王聿修、王冀怀、刘祟钦、黄金鳖、毛子水,侯墦等人运抵南京;21日,派两架飞机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夫妇、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窖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北大教授张颐及赵梅伯等人接出;1949年1月7日晚,又将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北大教授毛广水、钱思亮,及清华教授顾崇钦等60余人接出。
很多著名学者如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等不愿南下,即使送至南京的学者中有一些后来又回到北京。被列为“学人抢救头号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首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工作照
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立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后,经常以校为家,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刻休息。他一面在校内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采取强硬措施裁汰冗员;一面积极延揽人才。当时岛内各校延聘师资普遍存在人情与官方的压力,未能真正聘到所需的专业教授,傅斯年则用人唯才,不讲人情,很快聘任钱思亮、郑通和、余又荪为台大教务长、训导长及总务长,从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几乎都在台大兼课,并开始陆续修复台大战时受损的建筑,采购图书仪器设备,以及延聘师资。另一方面根据《边远地区服务人员奖励条例》,对于1949年1月起自省外来台大的新聘教员,于到校之月起提前发薪一个月,有眷属者发放两个月薪金的津贴,以补助其到职旅费,以示优待。由于他过于劳累,终于在195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倒在校长的位子上,享年仅54岁。
大陆学术传承得以在台湾延续
据资料记载,1947年初时,台湾大学内日籍教师仍占20%;其后来自大陆或留学欧美的教师逐渐增加。到1949年5月底,已有专职教员531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大陆,台湾籍教师不及5%,不再有日籍教师,教学内容与质量也随之发生根本改变。
接任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是前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思亮。任内他殚精竭虑,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首先从健全台大的教师聘任制度着手,高薪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任教,同时有计划地大量派遣在校教师赴外国进修,以提高台湾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跟上世界科技与文化发展的潮流。他非常重视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极力纠正轻视大学一年级课程的传统偏见,约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教授任教。加上他所推行的新生入学与学生转学制度的改革,使得台湾大学的教育质量逐年提高,良好的校风得以形成和巩固,成为台湾的一流大学。
由于这一时期许多大陆学者陆续来台,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学术传承一并得以在台湾延续。以历史学相关的发展为例,在日本投降之初,岛内仅有台湾大学设有历史系,其后的1946年,台湾师范学校也开设了史地系,其中大部分师资都来自大陆,如傅斯年、姚从吾、方豪等。
再以考古学为例,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日本考古学者逐渐退出了台湾考古界的舞台,而在大陆以发掘安阳殷代都城遗址闻名的一批考古人员,包括李济、董作宾、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他们的到来,使得因为日籍教师撤离而濒临中断的台湾考古事业重新获得了生机,对今后这门学术的存在和成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事实上,到1949年底国共内战结束后,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的有相当一大批内地的优秀科技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尽管此后海峡两岸处于长期隔离状态,但彼此的科技事业都是在继承了前辈科学家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的基础上各自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同属一脉相传;甚至到后来,也因这种共生关系而一直相互影响着。那种由师生、同学、密友、同事之间长期建立起的纽带联系,任谁也割舍不开。
大批内地年轻学生辗转入岛
在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国民政府为了与共产党争夺人才,要求许多邻近前线的大中学校师生辗转迁移。例如1948年9月,山西大学奉教育部电令,要求文、法、工学院及医学院医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均迁到张垣上课,校本部及一年级学生迁到北平。10月底,河南大学奉令迁到苏州;同时,从河南郑州、开封撤退的40余所中学约5000余师生,教育部指定迁至皖南,开办临时中学收容。教育部还派专员到浙江海宁进行安排,以收容鲁豫流亡学生。12月,要求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农学院迁至成都。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岌岌可危,开始游说这一地区的大专院校迁移。由于遭到教授及学生自治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北平辅仁大学首先表示不迁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也表示原地不动。1948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召开教授会,校长胡适主持,出席教授105人讨论迁校问题,数分钟即通过“北大从未考虑迁移,今后也绝不迁移”的结论。12月8日,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不得不宣布:平津地区国立学校及重要文教机构原则上都暂时不动,只有唐山工学院迁移。
平津地区迁校不成,国民政府又试图游说南方学校迁移。1949年初,中央大学接获教育部迁校的电文,但大多教授表示反对,教授会主席郑集明白表示:“学校经不起搬移折腾,一迁已甚,何以堪再。西迁是因为日寇入侵,不得已而为,而此次是国内战争,根本没有搬迁的必要。”
同年4月29日,即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派总务司长贺师俊来沪口传密令,要求上海地区学校紧急疏散,首批为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15所高校,限于30日前疏散。迁移事宜由上海市警察局严格监督办理,如有借故拖延者,则强制执行。但这项要求也遭到各学校的反对。
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秘密串连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朱垣壁、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等人,商定决不迁校,留在上海。继任教育部长杭立武亲自来沪,要他到教育部当次长,再转赴台湾,他拒绝了;给他赴台湾的飞机票,甚至准备了专机,让他和几位大学校长一起走,他又拒绝了。由于章益抵制迁校和拒赴台湾,蒋介石下令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下达对他的通缉令。
但当时仍有不少北方的学校,包括一些中学师生受到国民党的宣传鼓动,他们大都不清楚这场战争的正义是非,只是担心战火会毁坏校舍,害怕危及生命,希望寻找一个安定的求学读书环境,因此纷纷奉命南迁。特别是很多年少的初中学生,他们没有多少自主性,只是盲目相信带领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妥善安置上。然而国民党当局此时正穷于应付战事与经济问题,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与精力顾及他们,这批流亡的学生只有少数得到稍好的照顾,大多都颠沛流离。由于战火不断向南延伸,许多迁移的学生也随之不断辗转,被迫一迁再迁。
据统计,1948年9月,流亡在湖北汉口的河南学生只能靠同乡热心筹款度日,经重新登记合格的学生共3800余人,在汉口有亲属未准登记的另有2800余人。也就是说,当地政府仅可收容合格的学生1000人,其他2800余人必须自己设法想办法。另有些流亡学生在逃难途中,因国民党当局没有统一安置办法,只能靠社会善心人士临时筹募的款项度日。然僧多粥少,有些学生甚至加入难民行列,沿途募捐乞讨。《大公报》记者采访到1948年11月从郑州到吉安的流亡学生,谈到当地教育部所设的招待所每人每天仅配发2角钱,而当地买一碗面是8角钱,根本不够用。
此外,挤车的危险镜头每天都上演,使原本先天不良的铁路更加拥挤,京沪铁路及浙赣线特别严重。有一段时间,浙赣线为疏运豫、鲁、苏、皖四省流亡学生,停开普通客货车列车,专供学生搭乘,有时加挂车箱运送学生,一个多月才稍为舒缓。
1949年2月22日,山东济南地区的流亡学生200多人到上海,其中100余人找不到负责人,最后由当地社会局安排住在山东会馆,并派施粥车运粥到山东会馆。毕竟是临时救济,长期饮食几乎无人负责。山东临沂中学遭遇甚惨,借住在农仓里,只领到棉衣200套,未分配到的只好裹着棉被上课。他们每天只能领到少量钱做伙食费,当时物价飞涨,连稀饭都难喝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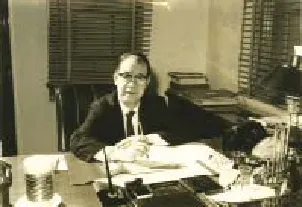
接任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前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思亮
钱思亮(1907~1983年)
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生于河南淅川县,其父钱谨庵为中国近代法学界元老,1931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获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32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再获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应聘至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学生授业解惑,是该校以教学质量著称的七教授之一。1945年抗战结束,曾被委任为经济部化学工业处处长,1946年复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后任化学系主任。1949年1月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之聘,任该校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曾一度代理台湾大学理学院院长,成为傅斯年的主要助手。在此期间,钱思亮致力于新生招考制度及转学制度的改革,为后来台湾实行的大专院校联合招生制度奠定了基础。1951年3月,接任已故的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同年任在台湾复建的“中国化学协会会长”和“中国科学振兴学会理事长”。
1957年,钱思亮与梅贻琦等5人受聘为台湾中研院评议会第三届评议员,1959年任台湾“长科会”委员,1964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1970年被任命为中研院第五任院长,1971年兼任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委,1983年9月病逝于台北,享年76岁。在他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主张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并重,推动许多新兴领域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扩展,如设立地球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及资讯科学研究所,并增设生物医学、统计学、原子与分子科学三研究所及分子生物学综合研究室筹备处等,对该院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及后续发展贡献良多。为纪念其多年来的业绩,中研院将化学研究所新建的一幢大楼命名为“钱思亮馆”。
由于国民党军逐渐败退,平津地区流亡到南京的学生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只能寄读在当地的学校里。广东中山大学为了接纳越来越多的流亡学生,校方特别制订暂时收容办法,要求寄读学生来校登记时需呈缴原校证明书及历年成绩单,而且寄读生不设寄宿,并须填写保证书。这些规定让当时这批流亡学生深感寄人篱下。
不少流亡学生随国民政府撤退机构,最终辗转搭船来到台湾。有些无法集体来台,只得临时被拉参军入伍或成为随军服务机构的员工眷属。其中一批来自山东的流亡初中学生,因为岁数太小,经过多方交涉,被分派到澎湖防卫司令部成立的子弟学校,最后落脚在彰化员林,算是一个特殊的实例。
据台湾官方统计,1949年台湾岛内受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突然增加甚多,1948年高中以上者为132,984人,1949年为227,505人,增加了近一倍。此与大陆学生及大量公务人员的迁台有关,因为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受中等及高等教育者居多。岛内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在1949年也比以前增加许多,1948年大专院校学生数为1914人,1949年为5906人,增加将近3000名学生。1949年第一学期岛内大专院校的教职员人数为383人,学生数为2914人。到了下学期,教职员增为922人,学生数为5906人,增加了2992人,这些增加的学生大多来自大陆地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陆各地年轻学生加入到台湾当地的建设中,后来中间出现许多优秀的人才,加速了岛内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1949年前后,还有不少大陆公营和私营企业奉命迁台,其中又以台湾最缺乏的纺纱厂数量最多。如华南纱厂由上海、宁波装运纱锭3000枚来台设厂;台元纺织公司由于吴舜文力主迁台,搬迁1万锭的机器来台;雍兴实业公司于1948年底迁台,中国纺织公司将华南各地的物资迁台,成立纱锭1万枚、织布机300台的台湾纺织厂。此外,申一纺织厂、嘉丰纺织厂、万宝纺织厂等三家超过100台动力织布机厂商从上海迁台,针织厂部分有超过一半以上由上海、青岛迁台,其中较著名的如来自上海地区的远东针织厂公司、建国棉织厂和庆祥棉织厂,以及来自青岛的六和棉织厂,不论是纺织厂数量还是设备的规模都在逐渐扩增,对于台湾后来的纺织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国民政府兴办的公营企业如齐鲁公司、天津恒大公司、济南兴济公司、沈阳益华公司、安徽农产公司、上海树华公司、永业公司等也相继迁至台湾,对台湾的橡胶业、棉织业的发展也有很大助益。在青岛拥有多家工厂的尹致中于1947年来台创立大东工业公司,建立造纸厂、自行车厂等,对台湾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基于《罗宗洛日记》(1945—1946)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