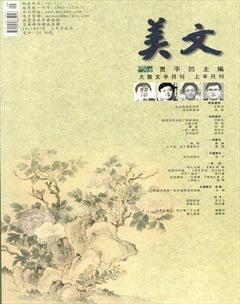毛姆与中国 (下)
罗宾·吉尔班克

整天我都在船上顺流而下。就是沿这条河,张骞曾逆流而上去寻找其源头。航行多日到一地,见女子织锦,男人役牛。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女子把她的梭子给他,并告诉他回去把梭子让筮师严君平一看便知。他照做了,筮师马上认出此乃织女之物,还说在张骞拿到梭子的那一天和那一刻,他注意到有客星犯牛郎星和织女星 。是故,张骞知道自己是到了银河的深处……
这时,我突然感到,面前茫然触动我心扉的就是我寻找的浪漫。此感有别于它,乃艺术引发之激情,但此生我说不清,也道不明,缘何会有这样的奇感。
——节选自《在中国屏风上·浪漫》 毛姆 著 1922年
显而易见,世事可怜,此女来中国是为嫁人。然而更悲催的是通商口岸的所有单身汉对此心知肚明。她身材高大,体型欠雅,手大脚大鼻子大。她的五官确实大矣,但那双蓝眼睛到是美目盼兮。或许对此她亦有那么点自知自明。而立之年的她金发碧眼,白天穿上得体的靴子、短裙,戴上宽边帽,还是蛮有风韵的。但到了晚上,当她为了衬托自己的蓝眼睛,穿上不知哪个土裁缝照着时装图为她剪裁的蓝色丝绸连衣裙,试图展现自己的妩媚时,却让人觉得大煞风景。她对所有的单身男人百依百顺。当有人谈起打猎时,她显得兴致勃勃;当有人说起运输茶叶时,她也听得很入迷。当人们谈论下周的赛马时,她像个小姑娘一样拍巴掌。她死缠着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跳舞,让人家答应带她去看棒球赛。但实际上跳舞并非她的唯一爱好(再好的事久了也会腻味),当她和一家大公司的代办,一个单身老男人在一起时,她就只喜欢打高尔夫了。她乐意让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的小伙子教她打台球,同时也把活泛的心思花在那个和她谈论银子的银行经理身上。她对中国人兴趣不大,因为这个话题在她厮混的圈子里不吃香。但作为一个女人,她会情不自禁地为中国女人的遭遇鸣不平。
“大家知道,她们对自己的婚姻大事说不上话,”她解释道,“一切都是媒妁之言,男人在婚前甚至没见过姑娘的面,诸如浪漫等情怀无从谈起。至于爱情……”
她说不下去了。她本性善良至极,那些单身汉不论老少,娶她都会得到一位贤妻,而她对此比谁都清楚。
——节选自《在中国屏风上·最后的机会》 毛姆 著 1922年
1920年冬,在沿长江旅行时,毛姆迷上了一个地方,那儿的古老与神奇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他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经过四川的这个地方,就在那儿,据说博望侯张骞乘槎泛舟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地球,来到了把牛郎和织女隔开的银河。牛郎和织女夫妻当时在天空的位置就是西方天文学家眼中的牛郎星和织女星。毛姆对此异事完全可以不屑一顾,这可能是向导或翻译讲给他的。但他没有,而是离开众人回到船舱,独自沉思这个神秘的故事。夜气袭胸,作者的脑海里闪现出的是世界上自己游历过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强烈的浪漫气息”让人陶醉。再次走出舱门,物是人非,心境全无。他独立舟头,“就像一個把蝴蝶撕碎,要找出美它在何处的人”。
《在中国屏风上》,这本毛姆有关中国的微型散文集,里面类似这种纯净、如过往烟云的宁静瞬间颇多。对于作者而言,有些地方体现的是灵魂的升华,其硕果乃文学作品。这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称之为“灵地”,这里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仿佛贴得很近,合二为一,给人一种超自然的顿悟。毛姆的高度认识富有浪漫气息,在本质上和宗教不同。其笔端带有一种忧郁的回潮,正如《最后的机会》一文所示,当说到外国侨民不得不玩婚姻游戏时,作者的心情跌到了最低谷。与牛郎和织女那纯洁的神话恋情相比,这位可怜的女同胞沉湎于自娱,徒想钓到一位理想的外国人为夫。她的举止甚至没有莎士比亚笔下“黑美人”的朴实魅力。莎翁的描述是:
我也承认,我的情人举手投足之间,
没一点儿让我想起天仙下凡。
——节选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30首
从英国移植过来的东西平淡无奇,清汤寡味。若言中国人妻乃婚姻之奴隶,那这位英国女士就更加可悲,其乃前程的奴隶。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谈到过毛姆在《苏伊士之东》中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描述。我认为在抨击这些在异国他乡定居者的心胸狭隘和装腔作势时,毛姆的主要武器是冷嘲热讽。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对当地中国人的处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不清楚他是在延续流行的东方种族原型,还是在狡猾地重构他们。他先前剧作中的瑕疵在《华丽的面纱》中依然如旧,当然这部小说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重复了《苏伊士之东》中的三角恋情节,不过是加了些《在中国屏风上》的猛料而已。通过对这部小说和更多散文的通读,拙作将致力于解析毛姆如何在自己的作品里把传统文化元素与哲学糅合在一起,以及这对他的英伦创作风格有何影响。
从本质上讲,《华丽的面纱》是一个有关感情错位和复仇的故事,小说的结局完全出人意料。小说曾三次被改编为电影,每一次改编都明显有其时代特征。最早的一部电影主演是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影片上映时距民国时代的结束还有几年时间,影片富有东方奇景的色彩。银幕上的两位恋人在一座庙前约会,庙里盛大的舞龙仪式演得很是到位。但毛姆本人曾错失机会没有看到舞龙,他也不善于赶时髦用文字来描述画面。二战后的重拍(1957年)似乎更加谨慎,对两位有私情的主人公的塑造比原作更加苛刻。出现这种道德意识上的约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殖民地香港已经处于共产党领地的包围之中,制片商不希望让自己的对手觉得香港这块飞地是个滋生淫乱的温床。第三次改编是在2006年,填补了毛姆作品中的许多不足和空白。通过把故事背景从香港移到上海,影片展示出全中国人的民族躁动日益强烈,其寓意乃任何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殖民干预意向。至于影片是否有那么点超越了原作还是有争议的。
《华丽的面纱》铺设直白,将近而立之年的姬蒂·贾斯丁,迫于在社会上攀爬的母亲的压力,加之羞于妹妹已有了未婚夫,不得不接受了细菌学家沃特·费恩的求婚。虽然她无心于丈夫的爱,但还是陪他到香港来履职。在香港,她和风流成性的副领事查理·唐森(Charlie Townsend)闹出了婚外恋。沃特知道她和别人上床,他给她的最后通牒是要么离婚嫁给唐森,要么随他处置。而她太天真,从未想到自己的情人怕个人仕途毁于流言蜚语,不久就抛弃了她。她得到的“惩罚”是跟着沃特去了内陆远方的梅德福镇,那里霍乱流行,她丈夫受命前去救助。
事后想来,可悲的姬蒂似乎和《在中国屏风上·最后的机会》一文中那位剩女的故事如出一辙。毛姆描写的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老处女现象。那些无法在英国找到配偶的人便不得不到英国的殖民地去寻亲了。殖民地的外交工作岗位实在安全,侨民生活圈的婚姻生活让人感到知足。作家E·M·福斯特在《印度之旅》中有同样的描写。他说上了年纪的穆尔太太带着阿德拉·奎斯提德到次大陆去,就是为了看看她是否和其在当地为官的儿子能否婚配。当年英国中产阶级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娶不了英国的,就娶香港的”。就姬蒂本人来说,她很清楚那儿的男人都是二流货,要是在伦敦,她社交中来往的男人永远也不值得被邀请参加她母亲的晚会。
更为切实的是,这部小说里有浓郁的以前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里的味道。一本《在中国屏风上》在手,读来就如同是在看描写外国人对中国内陆有兴趣的地方志。困在霍乱流行的地方,姬蒂来往的外国朋友只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女,一个是古怪的英国领事。毛姆先生赞扬过天主教修女们的坚韧(见《在中国屏风上·陌生人》一文),她们和自己的同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不同,选择长年在脏乱的中国内地城市安家,而不是在酷暑到来时就躲进凉爽的山里。基督教新教鼓励传教士多生儿育女,这样孩子的需求也就成了他们过几年回欧洲休假的理由之一(见《在中国屏风上·上帝的仆人》和《在中国屏风上·恐惧》)。而天主教传教士信奉独身,其生涯有可能再无踏上故土的机会。毛姆描绘的法国院长嬷嬷(见《在中国屏风上·修女》一文),就是放弃了在比利牛斯的舒适生活来到了中国。显而易见,梅德福镇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就带有这位法国院长嬷嬷的影子。
这些修女意志坚定,甚至宁愿面对霍乱带来的死亡,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教使命。毛姆对此观察很仔细,通过一位修女的话,他注意到修道院孤儿院里做针线活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被人遗弃的。家里人遗弃她们因为养不过来,或者就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她们在这里接受教育,信奉天主教,法语和汉语一样流利。
这种介入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殖民行为,因为这些遭遗弃的孩子被灌输的是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价值观。《华丽的面纱》制作人在2006年的重拍中则把这演绎得更细致。当姬蒂·范尼在家里的餐桌上赞扬修女们无私的纯洁精神时,沃特的反应显得很激烈。他指责修女是在把“这些孤儿培养为小天主教徒”,其言外之意是说,孤儿对获救的感恩最终将会转化为对上帝仁爱的感恩。毛姆的批评从不这样直截了当,但有两个因素让电影脚本觉得有必要加上这一笔。首先,这部电影的后台是中国的官方,毫无疑问官方期望通过美轮美奂的镜头,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影片的拍摄地桂林去观光。另外,为了迎合中国的标准历史观点,有必要想法巧妙地认可中国在“百年屈辱”时被奴役的处境。除此之外,毛姆的作品充斥着微妙的旁敲侧击,草草读之则浑然不觉。电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为了让观众参透,必须选择更大胆的色觉冲击。
电影中被删掉的(理由很明显,虽然原作中有引用)是毛姆在旅行中见到的最具恐怖联想的“弃婴塔”,人们会把不想要的孩子扔到这里。在《在中国屏风上·小城风景》一文中,毛姆曾描述说洞里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他还提到这些西班牙修女花钱让人把孩子送到教堂,而不是抛进那死亡的深渊。毛姆厌恶的景象在别的外国人笔下也有流露。在1900年出版的《漂泊在中国》一书中,康斯坦丝·戈登·库明女士(Constance Gordon-Cumming)描述了她造访宁波时的情景:“(玫瑰和金银花的)淡淡香味,掩不住到处袭人的恶臭,臭味污染了傍晚和风的清新”。她的游记提到了孩子被遗弃,埋在在塔外面,有的甚至被野狗撕咬。
汉学家瞿理斯 (Herbert Giles)不提倡弑婴,他对此事的看法是,外国人描述这些轶事有点想制造轰动效应。在第一个例子中,戈登·库明和其他人的描述并非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常态。在食物稀少的地方,孩子多的人家会把孩子让家族其他成员或邻居收养。他在宁波附近住了四年,得知的情形是这些弃婴塔有人定时清理,所有被发现的遗骸都得到妥善的掩埋。他就从未听说过有过路的人同情刚刚被遗弃的婴儿,并带回家抚养。
瞿理斯在演讲中涉及此话题,他說在英国人们当然从未听说过弃婴,另当别论的只有罪犯。他没有提到相关的法律条文,但在违反《人身保护法》(1861年)第二十七条(此法到现在未废除)规定:任何人遗弃两岁以下的孩子就是犯罪,最高惩处为五年监禁。回到那个时候,由于害怕被起诉,英国父母会把自己养不起的孩子送进无人监管的孤儿院,或是送给养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养母成了“育婴妇”,个个心肠歹毒,收养没人要的孩子都收费,然后又故意不管不问,致孩子于死地,以便有利可图。时代变了,现在英国的妈妈几乎没有人因为遗弃孩子而受到起诉,旧法规的影响明显还在起作用。2014年初,广东地方政府设立了“弃婴保护舱”(俗称“弃婴岛”),为那些出生时有残疾,或出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婴儿提供庇护。类似的东西绝不会在英国出现,因为1861年的法律依旧有效。
回到《华丽的面纱》,范尼女士不喜欢在中国不卫生和不体面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她协助修女们的人道主义工作。和这些行善的人相反,维廷顿先生则相对做出一副冷漠的神态。虽然他不失同情心,但却刻意于在自己的官位上不越雷池,装着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他给姬蒂解释“道”就是:
道乃道行,是众生永恒之道,但道非人为,自身为道。道是有,道是无。道演化万物,万物遵循道,最终归于道。……道法是无欲无求,顺其自然。
——节选自《华丽的面纱》第十章
说完这番话后是一阵自贬式的干笑,他的话虽然语意含混,但“在我喝了半打威士忌酒看星星时”倒也说得过去。尽管如此,要是这番话的确代表他的个人信条,这似乎可以解释这个怪人为什么会在一个相对孤独的地方存活了这么久。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学会了(不像《华丽的面纱》和《在中国屏风上》中的外国人)从不失望,也不动怒。即便是在小说写到悲情的高峰,就是费恩医生和刚刚身怀六甲的妻子达到了互信互爱时,他却染上了霍乱,但悲伤没有击倒他。
不知毛姆有没有意识到,他手头就有密码,可以解读为什么除了维廷顿,大多数外国人都努力想在中国有一种家的感觉。一天午后在乡下,精心读瞿理斯 (Herbert Giles)翻译的莊子,遗憾的是他感到不受启发反受其扰:
……他的书是好读物,尤其适合在雨天闲读,常让人不经意间有所触动,遐思万千。然眼下的想法犹如涨潮时拍岸的波浪,缓缓浸入人的意识,吸引你抵御古代庄子的思想。尽管你欲悠闲,但还是坐在了桌前……驾轻就熟,下笔如行云流水。活着真好!
——节选自《在中国屏风上·雨》 毛姆 著1922年
再往前三十年,当庄子刚被译为英文时,奥斯卡·王尔德就提醒人们说,此书中的哲学思想将会给英国社会带来冲击波。这位古代哲人强调的是“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其思想与当今政客和说教者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写道:
显然,庄子是个危险分子,在他离世两千年后用英文出版其作品乃不成熟之举,可能会给很多享有名望和勤奋刻苦的人带来痛苦。修身养性也许真的是庄子的人生目的,是其哲学体系的根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所需。当今世界,大多数人过于热衷教化他人,实际上无暇修身。但这样讲是否明智呢?在我看来,要是我们一旦承认庄子颠覆性观点的力量,我们便早该审视一下我们自命不凡的国民习性了。人一旦做了蠢事,唯一的慰藉便是对此事的自吹自擂。
——节选自奥斯卡·王尔德《中国圣贤庄子》
身为爱尔兰人的奥斯卡·王尔德总是拿英国文化开玩笑。英国人的天性是能看到其他民族的短处,满脑子的帝国霸权思想。尽管毛姆本人与英国的统治阶级走得很近,但他流露出自己喜欢这样的批评。《在中国屏风上》所显出的主要技巧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殖民者过分专心于教化当地的中国人,但却全然忽视了自身的毛病,使其膨胀得可怕。梅德福镇的修女们内心有种自我满足感,因为她们清楚修道院是自己徒手建起来的,几乎不需要捐款。2006年版的电影制片人觉得应当沃特·范尼表现出一种反殖民意识,从而保留住了原作人物的自负形象。他责备当地人缺少感恩,对自己把神奇的西药带给他们没有任何表示。但他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践踏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甚至是在给当地人灌输恐惧。如为了水源不被污染,让人家搬祖坟;要人们放弃传统的挺尸祭奠,甚至让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强迫人死后要立即埋葬。
除此之外,庄子给人的启发就在毛姆的手头,但他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就是能让自己走出殖民怪圈的利器。毛姆书写中国最有趣的一篇文章是《哲学家》,文中的对象是文弱但口出狂言的辜鸿铭,辜当时住在成都一处弥漫鸦片味的小屋里。毛姆只是听说过他的名气,要是毛姆先前知道辜鸿铭对他的讥刺,他就不会那么急着和辜鸿铭见面了。几乎从一开始,辜鸿铭就认为来访的毛姆不过是文坛的一个暴发户,而他则是高贵的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他最让人沮丧的话是“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这句不祥的言论预示着后边的话更厉害:
当黄种人也可以造出跟白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的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节选《在中国屏风上·哲学家》 毛姆 著1922年
中国对《在中国屏风上》的批评文章不多,其中一篇是宋淇写的(Stephen C. Soong)。他的指责比较温和,说尊称一位很多中国人觉得让人尴尬的清朝孝子贤孙为“哲学家”时应当谨慎一些(见宋淇著《我的父亲与毛姆》)。我相信毛姆用这个尊称部分原因是为了不让辜先生难看,让人们觉得他是整个清朝的替罪羊。在英国,称人为“哲学家”有时候是一种挖苦的恭维。被冠于该头衔意味着这个人的思维过于抽象,难以在当今世界苟活。或者是说虽然此人相信不切实际的空话,但却有一定的独到见解。
过了近乎一个世纪,辜鸿铭当时的预言没错。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全球的力量稳固崛起——但不像辜鸿铭想得那样是在军事上,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和出口商品。比如,中国不再需要当年沃特·范尼进口的药物,因为就西药来讲,中国一直在削弱其国际市场,同时却在保护自己的传统医学。这些成就并不是靠恢复了辜鸿铭梦想中以前大清朝的体制,从这一点上讲,老先生是落伍了。
说到底,人们会注意到毛姆和辜大师之间有奇异的相似之处。辜鸿铭盲目效忠大清,对其弊病视而不见,以至于牺牲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可信度,留给自己的是一个凄惨的晚年。而毛姆则是毫不留情地痛斥自己的同胞,以至于永远也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他无法成为道德权威的化身,因为他不过是这块人人为家的土地上的一个过客。另外,他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驾驭都是很肤浅的,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种机智的尝试方法,揭露自己同胞扭曲的自我观念。只要看一看他对辜鸿铭的警告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出毛姆思想上的困惑。在《苏伊士之东》中,毛姆借博学但却可憎的李泰成之口,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的英国殖民主义观点。说到底,像他那样的英国人无力反击辜鸿铭抨击,只能堕落到在文字上恶搞其观点,也许是嘲笑辜鸿铭的妙论。但在我心里,这不过显示出的是错位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