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野信太郎:精神故乡的面影
王升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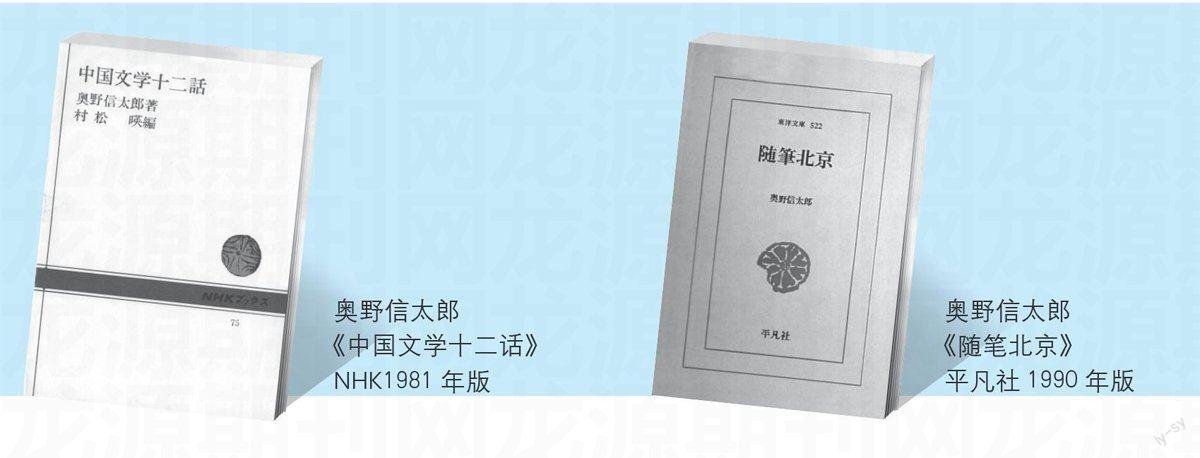
在日本的中国学界,虽曾有“西之吉川,东之奥野”一说,但二人的学术理路与旨趣实有不同。如果说吉川幸次郎继承了京都学派严谨、缜密的考据功力;相对而言,奥野信太郎(1899-1968)则对压抑感性与欲望的实证主义敬而远之,追求生活情趣,似乎更近于“享乐主义的感觉派诗人”。当然,从陆军中将之子、子爵外孙的身世和“山手良家子”(山手为东京富人区)的生活环境而言,奥野随性、潇洒的个人享乐本也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但作为学者,若将烟酒、购物和搓麻将等也视作评价他人的标准,恐怕就独具异彩了。在早庆(早稻田与庆应)中国学会第一届会议上,奥野信太郎在向与会学者介绍爱徒村松暎(村松梢风之子)时就说了句令四座无不咋舌的话:“此人搓麻将,就是通宵彻夜也在所不辞。”
世事无常,奥野的不幸在其二十一岁进入庆应文学部后接踵而至。入学当年及翌年,双亲先后谢世;三十六岁时妻子坂东智慧子病逝。而就在同年(1936),奥野得到了国费留学北京的机会,身份:外务省在华特别研究员。
认为奥野文学成就了北京多少有些夸大其辞,但说北京成就了奥野文学似乎并不夸张。佐藤一郎曾将奥野文学的主题归结为表现文雅、幽艳的都城精神,事实上,这里的“都城”主要指向了其故乡东京和北京。中日战争爆发后,北京作为“大东亚建设的基地”而受到了日人的广泛关注,北京沦陷区统制也为日人来京提供了可能与便利,种种以北京为背景写作的游记、观察、评论、报告文学和小说等向内地邦人描绘着“东亚古都”的诸种面影与动向。而奥野的魅力则在于,他向日人展示了一个漫步者看到的北京胡同之声色及其中氤氲着的都城精神。在奥野看来,北京的情趣并不存在于一般旅人所出入的金殿玉楼之中,而是平凡而又难以捉摸的一种情韵。
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虽为日人带来了收音机、电视、自行车和飞机等近代设施,但传统东京的灰飞烟灭却使“老东京”们失却了精神家园。其后的东京在喧闹、污染与变动中,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这一体验使奥野初入北京时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最初,在我就如同被吸进那巨大的城墙中一般走进去时,自己首先发现的是,一种像进入了极为寂静的树洞中一样、与一切噪音突然隔绝的感觉。”而这种感受与横光利一的所谓“嫣然而笑的尸体般”之感截然不同,奥野在静谧中找到了回归童稚、找寻老东京的时光隧道,北京也因此成为追溯其个人成长轨迹的最佳参照—“北京再次作为鲜活的现实,让我生动地触摸到了东京急剧的变化而使我自幼忘却了的精神。耽于追忆或许有时会明显阻碍人类的进步,我在北京触摸到的绝不是追忆的精神之美,不过是作为现实,北京巧妙地使我在时间意义上后退了一下。从后退之处老老实实地逐渐注视着自己的成长。”奥野又认为自己始终是作为异邦人观察着中国,而通过注视着独自混迹于中国人中的自己,则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取重返童稚精神的自己再次在成长中出发的过程。而我所关注的是,到底是哪些要素成就了北京作为奥野“精神故乡”的“考古”意义。
与其他“中国通”一样,奥野行文也有引经据典成癖的倾向,“抚今”之前先作一番“追昔”遥想,并试图以此姿态表现北京传统文化中贯通古今的“不变”。在奥野的北京书写中,有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そのまま”(原封不动),若将这一词汇置于具体时空论述之中,则近乎于“亘古不变”。在薰夫人(奥野的第二任夫人)看来,奥野“一旦外出,就似断了线的风筝,去向不明”,我想,若在东京,大致放浪形骸于酒馆、妓馆;在北京,你大可在旧书肆、小吃摊、戏院、湖畔池边和胡同等处寻到他的踪迹,因为这些是观察北京之“不变”的最佳去处,因为在这些地方可以找寻到东京已经不复存在的风致。或许,这就是将风筝吹断线的那阵清风。
为论证中国人的食欲旺盛和注重饮食生活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作者援引了某杜甫研究家的议论—杜子美的诗魂发于“饥”又归于“饥”;胃袋空虚直接成为寂寞诗魂的哀叹,食味满足又是其精神的愉悦、将人间描绘为理想国的要因。而北京成为饮食风味的中心“历史地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反之,正因北京乃“古老之都城”,方成为中国饮食之渊薮(《燕京食谱》)。奥野认为,饮食中最能代表都市风韵、涵养都市人情致的当属小吃。在东京,自幼常吃的许多小吃急剧衰亡,遂使北京小吃成为作者想象古都风情轮廓的现实标本,而联结其间的是“季节感”或一朝夕的生活断片:酸梅汤会使人联想起北京的炎炎夏日,商贩叫卖萝卜的声音会让人想到冬夜里幽暗的胡同。关于北京小吃能否永远存续,奥野声称自己不敢断言,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当地人的保守,若非借他人之手将不会有什么新的作为。这就使“保守”这一中国人的国民性成为“不变”的注脚之一(《小吃之记》)。在东京,与传统小吃一起消逝的还有种种街巷声音。“尽管场所与事物有所不同,但今日北京与往日东京的街巷声音,其中充溢的情趣却如出一辙。”北京胡同成了声音传播的管道,也为倾听这些声音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送水独轮推车的吱嘎之声、金属棒轻捋剃头镊子的慵懒之响、卖油翁或打更人敲梆子的感伤之音,或哀伤、或孤寂的余韵让人沉醉。(《街巷的声音》)这些声音触发的感动在小田岳夫的长篇小说《北京飘飘》中也有极为相似的表述。想来,或许讲求“物哀”与“幽玄”的日本传统美学修养使日本文人与种种低徊悠婉的街巷声音产生共鸣,为之流连难舍并非偶然。
当然,都市生活永远是“变”与“不变”的交错。五四运动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以及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北京城市生活的某些侧面不得不由“不变”而开始“不得不变”。令奥野终生难忘的变动无疑是一千四五百名日本人长达半个月的“北京笼城”(日语中“籠城”乃坚守城池、闭门不出之意)。作者在《北京笼城回想记》和《笼城前后》中详细地讲述了在京日本居留民从收到笼城指示起三小时内的集结,笼城期间的忧郁、愤恨的情感体验,以及其间居留民之间相互礼让、秩序井然等令人感动的一幕幕。以上这些为今人理解那一时期敌人内部情状提供了颇为生动的历史记录,值得一读。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另一“变”,即奥野对北京社会变动中的女性所给予的特别关注。对于这一视角的择取,你可以理解为其作为放浪文人的“秉性难移”,也可理解为其作为学者的“匠心独运”。怀恋传统使奥野对五四运动的激烈批判不难理解—在他看来,“五四”对传统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其建设性的一面,理性的缺失使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当局的煽动下转变为炽烈的反日、排日的意识。而“五四”两位著名女作家石评梅与庐隐的悲剧人生及其创作则不幸成为了奥野的论据。后者指出,庐隐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值得赞叹之处,只是“五四”青年无轨道的混乱生活之记录。在《女人剪影录》文末,论者颇意味深长地评论道:“讽刺的是,古都燕京是闲雅静谧之都,充溢着与年轻女性挺身而出、狂热乱舞并不相称的氛围。我总感觉那凸字形城墙的一角,作扭曲之相,在那些牺牲者们之上讽刺地嗤笑他们。”此外,在《燕京品花录》中,奥野又引经据典,介绍了北京妓馆的层次及其历史流变,并历数京都香艳之绝艺,对诸名妓京剧唱腔之高下一一点评。或许,信太郎所追求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文人情趣”,即如东坡之于琴操,如柳七之于青楼群妓。但值得关注的是,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北京妓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并加速了其兴衰更替。试举两例:在往昔清吟小班中,妓女(与跟妈对话时)颇具“异国风情”的楚州话逐渐被只言片语的日语所取代;东洋妆盛行开来。来北京寻求“古都情趣”、“文人情趣”的日人奥野对此变动述而不论,其中奥妙唯读者诸君断之。
有多少个作家,就有多少个北京形象。旅行指南与游记的北京介绍难免千篇一律或浮光掠影,虚构作品中的北京形象又似乎真假难辨,奥野以漫步者的悠闲步调和“中国通”的学识描绘、讲述了北京的声、色、颦、笑,并在后来出版的《北京留学》中将这段生活视作“一生中不会再有的幸福日子”。尽管由于战争悲剧的发生,来京寻找“精神故乡”面影的奥野似乎又有些不幸,但种种幸与不幸的交杂无疑丰富了其北京体验与表达。至于生动与否,非邀诸君一读而未敢妄言,但因了斯人是作,北京城又至少多出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游客—阿部知二。阿部氏在为《随笔北京》写的寄语中及自家小说《北京》的跋中对奥野表达了谢意。他说,奥野氏是数年前使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人。没有与奥野氏的交往,便不会有自己的拙陋小说《北京》的问世。说起来,在关于中国的方面,奥野是他的老师,他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