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想象的逆镜像
李欧
乌托邦想象与叙述在西方文化中可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当代西方乌托邦理论研究者,常将西方乌托邦叙述追溯到《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古罗马普鲁塔克的《来科古斯传》等等。当然,众所周知,“Utopia”观念的正式定型来自16世纪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以及康帕内的《太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而这些“近代”的乌托邦叙述,与西方古代相比,神话思维与神话想象大大减弱,理论设计的性质普遍增强,而且可实践性也大大增强,似乎是人类社会即将实现的蓝图。19世纪的西方,文化的主调是乐观主义,相信人类正在向“天堂”前进,科学会帮助人类战胜困难,“伊甸园”可以甚至即将达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乌托邦文艺风云际会,几乎泛滥成灾。有人统计,在19世纪最后十年,就大约有一百多部乌托邦小说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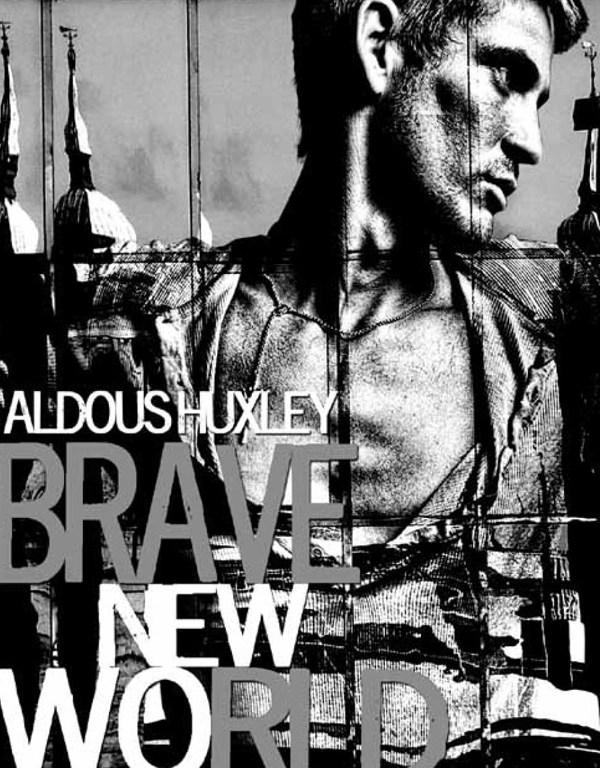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灭绝,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人类似乎不是在向天堂前进,而是更趋近于地狱。残酷的现实,导致悲观主义大流行,文艺基调大逆转,于是“反乌托邦”文艺开始盛行。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各种“乌托邦(Utopia)”的反面概念术语,不断被思想界创造出来。像“颠倒的乌托邦”(reverse utopia)、“非乌托邦”(non-utopia)、“丑恶的乌托邦”(nasty utopia)、“讽刺乌托邦”(satiric utopia)、“反乌托邦”(anti-utopia)、“恶托邦”(dystopia)、“批判的乌托邦”(Critical utopia)等等,一般简而言之统称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这是20世纪西方文艺的主潮之一,即或是非典范的“反乌托邦文艺”,也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反乌托邦”的意味,如系列电影《黑客帝国》等。
其实,反乌托邦文艺还可追溯到19世纪及以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未来世界”就已经开始悲惨,只不过没有形成气候,不过是乐观主义画面上,一两抹忧郁的色块而已。“反乌托邦”文艺在20世纪上半纪主要表现在小说,下半纪主要表现在影视,进入21世纪,势力稍减,但在网络文艺、卡通、漫画等文艺领域,却繁荣起来,看来21世纪的西方也不会是乐观主义的世纪。
在小说领域,首先是所谓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美丽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从文学性、审美性来看,《我们》与《美丽的新世界》谈不上多么高明,叙事策略平常;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他先前写的《动物庄园》,都可以称得上20世纪的文学经典。可惜他英年早逝,未得诺奖。不过,能称之为“三大”,其意义在于这三部小说共同奠定了、甚至确立了反乌托邦文艺的主要观念,甚至是主要情节、主要性质。后面紧随的反乌托邦文艺无论有多么多样化的发展,仍只是这三部小说所建立的领域内的变化,所谓“丸不出盘”而已。包括影响极大,甚至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经典,如威廉斯·戈尔丁的《蝇王》,伯吉斯的《发条橙》,艾拉·莱文的《这完美的一天》等等;因此,当代研究反乌托邦文艺,仍是以这“三大”为核心而展开。另外,重要的“反乌托邦”小说还有美国的《记忆传授人》,加拿大的《羚羊与秧鸡》等等。
20世纪下半纪,反乌托邦文艺最大发展是在电影领域。电影作为20世纪文艺的“灯塔”艺术,虽然“反乌托邦”并没有构成其主流,但一些重要的反乌托邦电影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一九八四》,1954年被改编成电影,1984年再次被拍成电影,评论者认为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还有曾被评为“历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首位的《银翼杀手》以及影响较小的《罗根逃亡》等,这之后,伴随着“反乌托邦”小说的逐渐衰落,“反乌托邦”电影却日渐兴盛,如《巴西》等等。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不断问世:《撕裂的末日》《人类之子》《V字仇杀队》……还有近年来在中国上映的《雪国列车》,虽然它是韩国电影,但却是高度“西化”,而且是韩国电影试图融入“国际”的一种努力。
当代西方“反乌托邦”文艺还不时出现在漫画、卡通、lT游戏中,如标准的“反乌托邦”电影《V字仇杀队》,实际上先是小说,后被改编成漫画,最后才改编成电影。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反映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变化,究其原因,首先是对人类文明与人类生活必然会不断“进步”的观念的怀疑,对人类终将战胜自然,终将战胜自身的愚蠢,而终将走向“伊甸园”这一信念的怀疑。无论是政治大革命,还是科技大发展,确实使人类在不断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上带来的生产效率,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人类“进步”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人类“幸福”?反思审视人类20世纪的生存状况,就如当代加拿大人类学家隆纳·莱特(Ronald Wright)在《进步简史》中深刻忧虑地指出,人类已经陷入“进步主义陷阱”中,而且无力自拔。因此,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弗·詹姆逊曾评论道:“对乌托邦的冲动的邪恶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已经变成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很多当代西方一流思想家与学者都直言不讳地对乌托邦观念进行抨击。如波普尔、哈耶克、伯林等,他们甚至认为对乌托邦思想的误用,是造成20世纪人类社会诸多灾难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反乌托邦文艺风生水起,不足怪也。
当代西方的反乌托邦文艺作品众多,但是其主题、内容,甚至主要情节却大致相同,主要有以下内容情节。首先是“未来社会”不是近于天堂,人人快乐、自由、平等和幸福,而是几乎一致地认为将要出现“极权社会”,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的权力控制之下。《我们》中的“大一统国”封闭在绿色大墙内,每个人的每分钟都被严密控制:
每天早晨,我们几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准确: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然后去讲演厅、去泰勒训练大厅,最后回去睡觉……
只有在“性活动日”时,人们才有权利放下窗帘,遮挡在玻璃房上,使人们有了那么一丁点儿的隐私,然而,这一行为却是需要凭“票”进行的。
先由性管理局的化验室对号码们作全面检查,准确确定血液中性激素的含量,据此制订出相应的性活动日期表。然后人们就可以提出申报,自己在哪些日子里愿意和某某或某某号码发生性关系,并有权得到一个粉红票子小本子。至此就万事大吉了。
这一切的背后是高度发达的科技力量。科技发展,其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而在极权政治下,科技成了强大的邪恶力量,支撑着恐怖。电影《雪国列车》,得以维持运行,依赖高度发达的科技,而《一九八四》中无处不在的监视,也是依赖高技术的支撑。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受着科学技术的控制,生育、性别、身份、职业,甚至性快感、语言都由高技术来全面控制。在妊娠期中每个胚胎就被编程设定了各种条件,即在胚胎时期就“命中注定”拥有不同的命运、职业、爱好、从事的工作甚至思想。可以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些反乌托邦文艺作品,实质上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质疑:幸福感、快乐和稳定一定要以压制自由、个性、创造激情为代价?科技无节制地发展,是否是让人类登上了欲望号列车,向深渊极速前进?为科技发展所依赖的工具理性是否会必然导致人会异化为机器?当生命被仪器所包围,人格是否也会被淹没而窒息?……在小说《记忆传授人》中,为了更好地“控制”,连每个人的记忆都应消失。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天渊之别。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些反乌托邦文艺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则完全否定和压抑人的自由、自由思想和个体性。如《我们》中称:“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即或是人们生活无忧,快乐立即可得,如《美丽的新世界》中通过服用“唆麻”,难道这是人类所奋斗追求的世界?这无疑是反乌托邦。
其实,反乌托邦文艺,在一定意义上是乌托邦文艺的一种发展,一种逆转性的发展。除了外部环境,时代境遇的刺激外,乌托邦文艺与反乌托邦文艺在内在逻辑上有相通之处。莫尔构建的理想社会,人人追求为大快乐放弃小快乐!为他人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但是再向前走一步,“我”就成了“我们”,以社会名义牺牲个体;权力集中就成了恐怖宰制,个体的人则沦为喂养国家这个怪物的食料。《太阳城》中规划的全体居民的“作息时间表”,就是《我们》中全体社会绝对步调一致的生活秩序的先声。可以说,反乌托邦文艺是乌托邦文艺的一种逆镜像。
反乌托邦文艺,并不仅仅是某种绝望与恐惧的情绪表达。可以认为反乌托邦文艺的生产者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表现了直面惨淡人生的批判意识,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暗含着对美好未来的强烈的诉求,即在恐惧甚至绝望中仍有坚守。乌托邦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否定性,对现实中丑恶、异化、灾难的否定,以“将来”的光明来烛照现实,从而促使人们去改变现实。但是已有的“乌托邦”工程的失败,乌托邦观念的一些具体实现反而导致人类更大的灾难,因而对乌托邦思想的厌倦甚至反感就必然产生,反乌托邦文艺必然会泛滥。但是反乌托邦文艺并非全是绝望情感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反乌托邦文艺的种种凄惨画面中,作者有意识甚至可能是无意识地总有一丝亮色留给世人。在《雪国列车》的结尾,地球温度开始回升,仅剩下的两个人:尤娜和小男孩,还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保罗·蒂利希曾对“乌托邦”做了深刻的思考,他指出:“如果乌托邦并不同于无价值的幻想,它必定在人自身的结构中具有一个基础,因为归根结底只有在人的结构中具有基础的事物才会有意义。”他斩钉截铁地强调:“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反乌托邦文艺是乌托邦文艺的“逆镜像”,是对虚假、变质的乌托邦思想观念的否定,实质上仍是一种乌托邦精神,一种乌托邦冲动。“战胜(虚假、变质)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