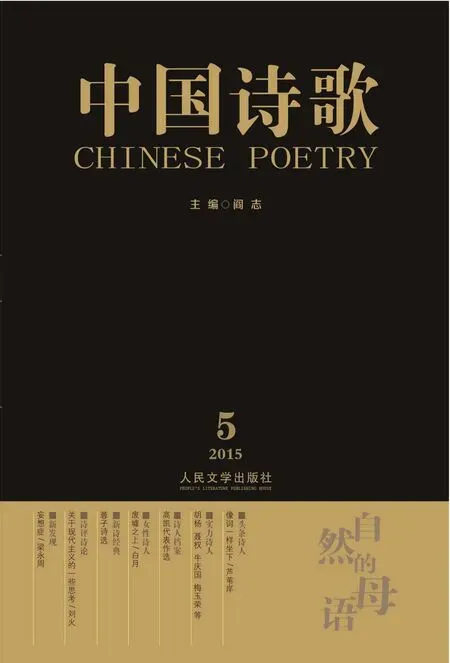高凯代表作选
高凯代表作选
村小:生字课
蛋蛋鸡蛋的蛋
调皮蛋的蛋乖蛋蛋的蛋
红脸蛋蛋的蛋
张狗蛋的蛋
马铁蛋的蛋
花花花骨朵的花
桃花的花杏花的花
花蝴蝶的花花衫衫的花
王梅花的花
曹爱花的花
黑黑黑白的黑
黑板的黑黑毛笔的黑
黑手手的黑
黑窑洞的黑
黑眼睛的黑
外外外面的外
窗外的外山外的外外国的外
谁还在门外喊报到的外
外外——
外就是那个外
飞飞飞上天的飞
飞机的飞宇宙飞船的飞
想飞的飞抬膀膀飞的飞
笨鸟先飞的飞
飞呀飞的飞……
苍茫
一只苍鹰
把天空撑起
一匹白马
把大地展开
一条阳关大道
在一个苦行僧远去的背影里消失
一粒金沙在天地尽头
高出戈壁
凝神眺望
不是月亮就是敦煌
躲闪一块刀疤
一个黑影一个
脸上带着一块刀疤的陌生人
与我突然相撞进而
与我对抗
所有的表情
早已被那一刀全部杀死
两道目光
像两把刀子一样
寒气逼人
我的歉意被狠狠
刺伤一块刀疤
让我心跳了一千次后
又跳了一次
亮堂堂的大街上
我像躲闪一把锋利的刀子
躲闪着一块伤疤
刀疤深刻着残忍
和仇恨我差点躲不过去
一块刀疤比一把刀子厉害
刀疤比刀子
更容易伤人
老照片
一个瞬间
就这样在时光里老了
尘埃落定
几位亲人已不在人世
此刻我和已故的亲人们
聚在一起
我注视着我们
我们注视着我太意外了
其实大家是面面相觑
从前我们
怎么把所有的日子都过成了黑
或者白
一层薄纸生死两茫茫
我看了正面
又看背面
打鼓
造鼓的人
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掏空
就是一面鼓
剩下的几截骨头
成了别人的鼓槌谁能攥在手里
谁就是打鼓的人
不过造鼓的人
还是把自己许多不平静的心声
平静地放在了鼓中
所有的鼓看上去都是空的
但每一面会响的鼓
又都是内容丰富
鼓不打不响
打鼓的人用力鼓舞灵魂的动作
就是打鼓
生我的那个小山村
秃岭上齐刷刷的庄稼
是村子的头发
半山腰里睁开的窑洞
是村子的眼睛
呼哧呼哧喘息的烟囱
是村子的鼻孔
咯嘣嘣吃东西的石头磨子
是村子的嘴巴
阳坡坡上院外的墙角落
是村子的耳朵
古旧而灵巧的生产工具
是村子的手和足
大槐树下的那口老井
是村子的肚脐
一根盘来盘去的羊肠小路
是村子的肠肠肚肚
老虎下山一张皮
是村子的穿衣
社火里那个最热闹的日子
是村子的生日
操场上常年插着一面国旗的小学校
是村子的首都
草莽童年
那时天上风起云涌
地上就风吹草动
明处的小蜜蜂口蜜腹剑
暗处的黑蝎子心狠手辣
而毒蛇和黑蝎子又是一对亲姊妹
那时勤于打洞的老鼠昼伏夜出
蚂蚱整天腰里挎着两把大刀
蜻蜓一身轻功会水上漂
毛毛虫摇身一变就成了迷人的蝴蝶
那时兔崽子狡居三窝
黄鼠狼岁岁不忘给鸡拜年
螳螂捕蝉黄雀紧随其后
金蝉总能巧妙地脱壳而逃
那时天下草木皆兵
遍地的冰草在春风里挥舞着双刃剑
周围的枣树一年四季浑身都是利刺
就是看上去花枝招展的喇叭花
在村里又是牵牛又是打碗十面埋伏
有一天我告诉手无寸铁的父亲
好男儿应该现身江湖
做一个草莽英雄
母亲在风中生火的情景
风雨如晦又有一股风
一口把母亲划燃的火柴
给吹灭了
母亲蜷缩成一团
惊恐万状像护住自己的一个孩子
把最后一根火柴紧紧抱在怀里
那个样子就像是弱不禁风的母亲
为黑暗而冰冷的窑洞
重新怀上了火种
生我的母亲
能在几十年的风雨中生出一大堆儿女
就能在一阵风中生出一堆火焰
母亲往往是在一家人绝望的时候
扑哧突然和火柴一起含泪笑出声来
让一家人心头为之一亮
舅舅家的路
一直向西
沿着国道走八九百里
再沿着省道向西走六七百里
穿过一个深深的大峡谷
爬上一个累死牛的黄土高坡
就是远近闻名的黄土残塬
养活了母亲的一大家子母亲出嫁了
舅舅从生到老一直守在这里
在塬上向北走四五百里
又向西走二三百里下一个大坡
过丑家川马莲河赵家沟门
再向西走百十里地的样子
越过野人岭叫花子梁和秃子峁
然后连跨三个崾岘向北走八九十里
再连跨三个崾岘
那些像驴脊梁一样的崾岘可危险了
继续再向西北方向走六七十里
又爬上一个屁股大的小县城
那个小县城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鸡鸣三省过去是兵家必争之地
出县城向北又是朝下走的乡间小路
在金黄金黄的油菜花
和绿油油的麦地之间走四五十里
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坝时再向西
过一座独木桥钻一个人工凿的山洞
看见一个药王庙再向西
接下来的二三十里都是羊肠小路
遇见一大片枣树林要向西
遇见一个三岔路口又要向北朝上走
经过一个没人住的小村子千万不要进去
再向西北走十里路的样子
隐隐约约看见一个芝麻大的黑点
就是舅舅家的村子了这时
可以在路边找一块石头坐下来
歇一歇慢慢地抽一支烟
听母亲说她第一次回娘家走到这里时
倒在地上后差点爬不起来呢
缓一口气向西再走八九里
拐一个大弯子后
再走六七里又向北兜一个小弯子
走到一堆老坟跟前再向西走四五里
而后向北二三里的地方有一棵大槐树
大槐树下有一个大粪堆
大粪堆旁卧着一只大黄狗
大黄狗的身后就是村口
大黄狗是村长家的
人不惹它它就不会咬人
谁穿得像干部它还给谁摇尾巴
进了村子还要走一里路的样子
再向左拐走八九十米后再向右拐
直走六七十米再向左拐
最后再走四五十米就是塬畔
塬畔下面又是近千米深的一条坡
坡底两孔坐北朝南黑眼窝般的窑洞
就是舅舅的家
药方
古道一条
三十三道弯六十六道梁九十九道坎
坦途三千有鹰的天空九万里
艳阳一轮明月半块星光一片
日子年年三百六十五天
其中疾风六十一天
雷电六十二天雨雪一百一十五天
霾二十天晴一百零二天
雪上加霜五天
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渡河十三年
坐北的窑洞三孔或朝南的瓦房三间
门符门画对联窗花常年一一贴满
掌灯一盏而且重圆的破镜一个
柴万担米万石油万缸盐万袋醋万坛
酽茶乎烧酒乎旱烟乎神仙三宝随便啦
但《本草纲目》须是完整的五十二卷
当然还需干净的黄土一锨
若有条件再搭配唐诗宋词各三百首
元代马致远的散曲三十一篇
和自家创作的自由体乡土诗十卷
以上统统一锅亲自文火煎熬半辈子
再坚持天天早晚口服七七四十九天
内心深处那些久治不愈的伤痛呵
必然消失这服良药就是时间
思想者
亲爱的
你知道我是怎样思想一个人的么
或者直接说你知道我是怎样思想你的么
我就像一尊题为《思想者》的雕塑那样
思想着你
我始终独自一人
一丝不挂赤裸着身子
半跪着头颅低垂沉默不语
一只手支在下巴上
目光停留在一处
思想着你
亲爱的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寸步不移一丝不动思想着你
我浑身上下被爱神仔细雕琢却全然不知
血液骨肉五脏六腑和灵魂
顽固地凝结在一起
内心一片欢腾
思想着你
打铁
打铁的人
在趁热打铁
在打铁人的手中
铁是软的
跳出火坑
呛一口冷水
反复挨打没有骨头的铁
浑身都是骨头
恨铁不成钢呀
打铁的人才使那么大的力气
打铁的人和铁之间
爱恨交织
打铁的人
本身就是铁打的人趁热
用自己的一块铁改变自己的另一块铁
就是打铁
俯仰
一只鹰
被我让在了高处
而我
被一只鹰让在了低处
一只鹰
让我看见了天空
而我
让一只鹰看见了大地
城里的鸡叫
一只鸡突然叫了
黎明时分从来没有鸡叫的城里
几声嘹亮的鸡鸣
把我从睡梦里唤醒
在一个很压抑的城里
不要说是一只鸡即使是一个人
平时也都是很难放开嗓子
吼叫一声的
而且城里人不相信
一只鸡会天天为别人操心
城里人每天的时间
都是由一种叫钟表的时光机器
一分一秒制造的
一只久居城里的鸡
可能错把城市当成了乡村
突然看见天边的鱼肚白之后
就情不自禁喊出了声
不过这只雄鸡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里
可能只叫醒了我一个人
几声酷似乡下的鸡叫
在一个让我失魂落魄的地方
没叫我的名字就把我的魂儿
从身外叫了回来
一盒火柴
从前最害怕那一盒火柴
在漫长的黑暗中突然消失
一盒火柴一把能种出温饱的种子
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一家人黑灯瞎火
伸手不见五指
从前一家人在黑暗中
伸手摸一盒火柴的过程
是一家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
更是一家人在黑暗中
寻找一家人的过程
从前一家人在摸到一盒火柴之前
往往会先摸到彼此摸火柴的手指
那一根根碰到一起的亲骨肉
总是先齐心捅破一层一层的黑暗
然后再摸到那一盒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