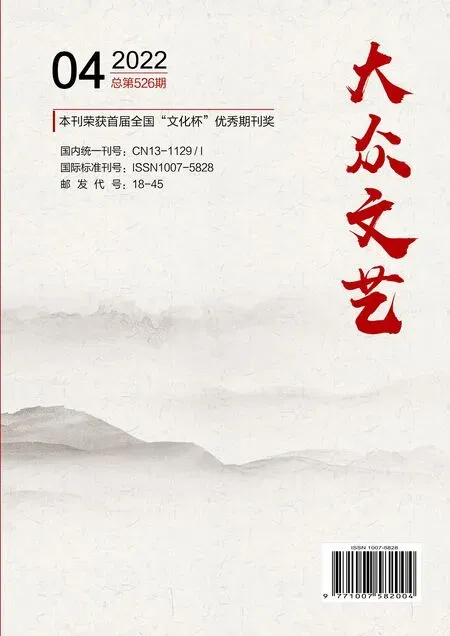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关于沈从文小说的一点思考
杨利香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1065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关于沈从文小说的一点思考
杨利香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10650)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一种“美”的离心力,表现在人物在各自具体的行动中“安宁”生存着。这是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奴役下所形成的习惯心理,使他们没有了是非观念,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折射出“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缺失。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叙述和描写反映出了这位30年代非主流作家的可贵的社会关怀。
沈从文;安宁;自我意识
课题项目: 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体育类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3A252)
“美”是沈从文小说中的重要命题,但是,读罢他的作品,悲凉之情、内心隐痛总是挥之不去。这种悲和痛是小说中的乡村人、事的一种生存状态,与他所倾心和执著的静穆和谐之美相反,构成了他的心灵世界和作品世界的悲凉内涵。
一、几种人物群像
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群“看客”。看什么呢?不只是看城里人的头发、皮鞋、起棱的薄绒裤、洋服衬衫,还看被捉的一对青年男女,而且是奔走相告地去看。例如小说《夫妇》 《巧秀与冬生》中 都有相关的情节描写。《巧秀与冬生》中的描写更是淋漓尽致,村民们可以“欣赏巧秀妈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族祖口里不住地说“下贱下贱”,却狠狠地看了几眼;族长也“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健康光鲜鲜肉体。”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用笔,“欣赏”“光鲜”,如此让人觉得舒服、唯美的词,用在这个“看”的场景中,简直是神来之笔,留给读者的不只是对“被看者”的同情,更有对这些不同身份、地位的“看客”的愕然和隐痛。
除了上文所说,这群“看客”们还饶有兴趣地看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一种特殊之事——杀头。沈从文的小说中非常真实地描绘过杀人的场面。《我的教育》中的有一个被杀者,结结巴巴地说自己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士兵们“看”那汉子下跪的姿势却看出做匪无经验,觉得他不懂做匪行规,不是啥角色。这真是一段揪人心肠的可悲描绘。作者用这群看客的“谈资”来消解“杀头”的悲凉,结果“看客”也成为了读者的“悲”的对象。
除了“看客”,沈从文的笔下还有“等待者”。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代表作《边城》中的翠翠。尽管小说的人情美、自然美、风俗美打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但小说的结尾交代:“还不如在碧溪岨等”,一种命运的无奈和忧伤油然而生,笼罩全文。另一位等待者是三翠,她虽然知道她的生活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存在,但是浑然不觉自己是可以选择的,于是在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等待着不知生死的丈夫。
沈从文的小说中的还有每天点名、发签子,按工头分配工作去做事的工地农民,有白天忙乎的肮脏的妇女、铺子里的屠夫、船上的短工、水手;有只关心二毛六分钱工钱、贫血体弱、一天要做十三个小时的工厂童工;还有做同样的事,在旧时代被称为“英雄”,在新时代却被视为“疯子”的老战兵。他的描写和叙述是令人心寒的,这些人如虫豸般卑微地活着,然而,他们又是何等的满足和平静呀!
“看客”的形象我们早已不陌生,在鲁迅的《示众》、王鲁彦的《柚子》等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等待者”的经典是荒诞之剧《等待多戈》。这两种形象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出现得并不多,但是,夹杂在他的“美的乐章”中,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沈从文笔下的“看者”“被看者”“虫豸般的人”多半都是最低层的人物:工人、农民、士兵。为什么本身就处在最底层的人,面对同为底层人的“被杀”“被捉”“被沉潭”的情景无动于衷,激不起半点同情和怜悯?而是得到了观看时的“趣味”“刺激”“欣赏”和“满足”呢?他们面对这些人事是心安理得的、平平静静的、与己无关的。翠翠和三翠的生命在“等待”中消逝;村民、官兵在“看”中打发每一天;萧萧在“看”中延伸她的命运;三三和她的母亲在“梦”的躁动之后,又复归生活的平静;那些虫豸般的百姓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感知世界和占有世界的行动是如此的简单和惊人的类似。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那么,黑土地上的这群子民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呢?
二、人物的精神重荷
沈从文在《摘星录》中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这所谓命运,正是过去一时的习惯,加上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而形成的。显然,沈从文笔下的“看客”“等待者”等的人物群体的行为就是“习惯”的作用,也就是一种“安宁”的生存状态,作者不是要说他们他们遇事泰然处之的成熟心态,而是暴露出他们内心的软弱,精神的匮乏。这是长期以来,在战争动乱,压迫剥削之下,在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下,所形成了的一种习惯心理,渗透到了这群子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习惯”麻木了他们的意志和思考能力,扭曲了他们的是非观念。《夫妇》中,为了处罚那一对年青夫妇,大家提出了各种办法,而当官的练长也无需裁定大家的办法是否得当,因为在他的头脑中“众人的裁判是正当的”;处罚巧秀妈的是“老规矩”——沉潭;阿金的爱情夭折和贵生的爱情告吹,就是因为妇人太美,麻衣相书上写明克夫,或者金凤八字怪,斤两重,不是夫人就是犯人,克了娘不算过关,后来事情多。“众人的意见”“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宗法社会的规章制度,迷信思想,其合理与否,正当与否,这些行动者并没有思考和衡量。“习惯”的势力是相当强大的,早就阻止和麻痹了他们的思考和判断,而只有遵循和相信。
“习惯”更使他们失去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以翠翠为例,我们可以被她的清纯美丽倾心,但是也不得不认识到她在爱情面前被动的言行是其爱情苦果的根,“争取”爱情的途径仍旧是平静的等待。萧萧应该说比翠翠勇气要多点,她想过与花狗一起逃,但当“母以子贵”救了她的命之后,这点勇气也早已烟消云散,且浑然不省地看着大儿子的童养媳娶进家门,有一个小女人走上了自己相同的路。
由此可见,“习惯”的势力是强大的,它甚至可以主宰一个人的命运,使人失去思辩,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个性,沉沦于“众人”当中,处在了“众人”的独裁统治之下了。这种缺乏思考、缺乏抗争的“安宁”使这些子民自以为是的满足的活着,水手柏子的逍遥自在,及时行乐就是一个典型。但是,如此,可以给他们带来永恒的幸福和欢乐吗?谁能保证柏子不会如天保一样在闯滩中意外身亡?翠翠即使等到了爱人的回来,恐怕也是物是人非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存在是偶然的,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但这并不是说它事实上不存在,而是说它缺乏存在的意义、目的和必然性。他们生命中的一切行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未来,均成为了盲目的热情和无效的劳动,性格上的软弱,精神上麻木愚昧的宿疾让他们有的依附他人活着,有的让别人延续着或循环着自己的日子,有的一味的重复着自己的日子,对于这些看客、等待者以及其他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似乎活着就是能呼吸就好,至于是不是还可以活得更好、是不是还可以争取到更好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比自己好一些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就是一种工具、机器、甚至可以说是卑贱的虫豸,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人”、更称不上坚强的、勇敢的“人”。或许他们自己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与他人的生存状态的区别或者思考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中国宗法制度的奴役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在湘西这块荒蛮闭塞之地,他们承认、遵循,甚至坚守了这一切。
“人究竟为什么而生存?”这是三十年代沈从文思考的哲学般的人生问题。“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只不过是沈从文所谓的“生活”,是肉体的存在物;而“怀抱向上或向前的理想并为之受苦”,则是他所谓的“生命”,这才是精神的存在者。“安宁”的生存着的子民们正是前者,他们只有“生活”,而无“生命”。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缺失造就了他们的悲剧,这就是这些中国子民的精神重荷。
三、结语
20世纪的很多中国文人用文字揭露过中国知识分子、农民的国民劣根性,而沈从文也在他的乡土题材的作品中对闭塞之地的底层人物有了这些深刻揭示。“五四”时期高扬和呼唤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里无法找到蛛丝马迹。沈从文所追求的“生命”在这种无形而沉重的“习惯”的精神重荷下是无价值的,且最终会被它压垮。对这群子民的行动描述流露出了作家的生命意识忧患。在这里,谁又能说新文学对国民性的探索对沈从文毫无投影呢?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揭示了人的生命中有着一种“不能承受之轻”,即人一方面可以经受生活上物质性的匮乏的苦恼,可常常承受不住现实世俗生命的“安宁”。沈从文认识到了这种“安宁”对人的生命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于是通过笔下的文字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怀——沈从文对湘西的“美”有着“鲁戈挥日”的真诚和固执,而“美”的离心力的对立存在却更好地显示出了20世纪20、30年代一位非主流作家可贵的社会关怀——重塑国民性格,因为美与丑,存与弃在这种对立中有了答案。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4.
[3]杨利香.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J].文学教育,2008(4).
[4]赵园,王珞.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A].沈从文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杨利香(1974—),女,湖南宁乡人,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高职文化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