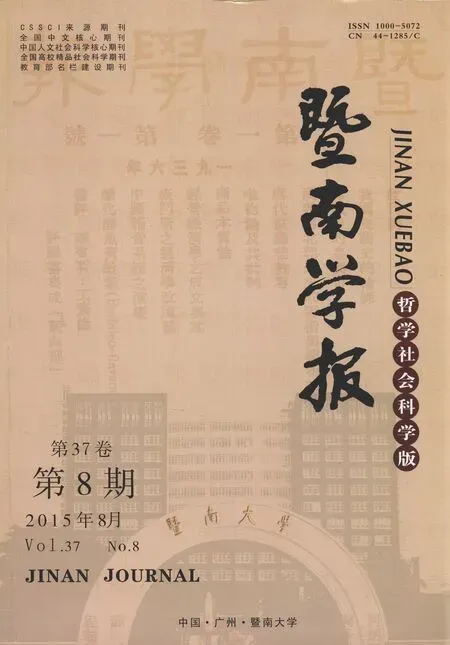论宋人婚书的文体形态与文学性
邬志伟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论宋人婚书的文体形态与文学性
邬志伟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婚书在宋代广为使用,宋人文集中多有收录。宋人婚书既为婚姻事实之契约,具有法律意义,又是具有私人书写色彩的书启,有文学意义。婚书的文体为书启文,婚书一往一答即构成男女双方对婚姻事实允诺。婚书作为一种文体,其文体远源因素可追溯到《仪礼》中婚辞,而六朝时期的皇室、贵族婚礼中的“六礼文”为后代文人婚书写作提供了文体与文辞借鉴。真正文体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婚书在唐代出现,唐人婚书为单书或复书形式,宋人则发展为叠幅形式,叠三幅为一封,是晚唐宋时书启叠楮之风的体现。婚书不见于唐人集中而见于宋人集中,宋人婚书正文为四六文,文体典雅,辞令优美,大量用典,不再是简单的实用礼书,成为文学作品。宋人婚书以其文体要素体现了“合二姓之好”的婚姻观念,也展示了宋代文人对自身家世风范的体认与彰显。
宋代;婚书;文体形态;文学性
“婚书”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有两种指称。其一,合婚占卜之书。古代书目中收录有“婚书”,如《通志·艺文略》“五行类第八”即记载“《婚书》一卷。《姚陈议婚书》一卷”。《宋史·艺文志》“蓍龟类”也著录“《校定京房婚书》三卷”。这一类作品属古代阴阳五行之学,内容大致为根据历法和阴阳五行,推步合婚吉日。其二,指男女议婚、成婚往来之礼书与文字凭证。在合同婚书出现之前,婚书主要指男女议婚过程中往来的各种书、启、札、帖等礼书,这些礼书从文体上看,为书牍体,但它们并不仅是普通的书启,同时具有为古代法律所承认、约束婚姻成立的意义。本文研究所指的“婚书”即上述第二种概念。
关于婚书,已有学者予以了关注,但还未将着眼点放于宋代婚书作品的具体写作与文体形态上。宋代婚书的写作,颇为丰富生动。宋人总集、别集中收有婚书作品,宋元类书中也大量收集婚书范文及格式范例。宋代婚书突显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婚姻过程中的礼书与契约,而且是一种文学作品进入文集之中。本文将对宋代婚书的形态、文体特征、文化内涵及其与婚礼程序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
一、婚书起源与宋前婚仪礼书的写作
(一)从《仪礼》“婚辞”到“六礼版文”
古代婚姻,从议婚到成婚,男女双方要通过媒妁不断接触往来。婚礼古有“六礼”之程序,据《仪礼》所记,士婚礼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礼》“士婚礼”在对六礼仪式进行说明之后,还特别记载了六礼过程中每一环节所使用的“婚辞”。据郑玄注,婚辞为“摈者请事告之辞”,即女家摈者与男家使者在仪式中互致问答之辞,男方致礼辞,女方答礼辞,一问一答。如纳采的时候,使者说“吾子有惠。贶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纳采。”摈者则答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双方的说辞客气谦逊,郑重严肃,是一种仪式用语。
魏晋时期,六礼仪式中开始出现记录于礼版之上的“礼文”。杜佑《通典》在论及“公侯大夫士婚礼”的历史沿革时,提及后汉与东晋婚仪中的“六礼辞”。“东晋王堪六礼辞,并为赞颂。仪云:于版上各方书礼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纳采于版左方。裹以皂囊,白绳缠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无官言贱子。礼版奉案承之。”从上述记载可知,晋时婚姻六礼之中使用“六礼辞”,记载在“礼版”上,版左方写“纳采”,正中写有男家父亲之名、媒人之名,并书有礼文。从其封章所书“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来看,这种版文已具备了书启文的基本要素。这种记录于礼版之上的六礼辞,其文辞来源于《仪礼》婚辞而略有变化。在南朝时期,除了贵族士大夫,皇室婚礼也有“六礼版文”。《宋书》卷一四《礼志》详细记录了晋穆帝升平元年(357)纳后时王彪之所定的“告庙六礼版文”,“六礼版文”表达的意思也同于《仪礼》婚辞,但是措辞明显华丽典雅,使用四字句式,音节整饬。
魏晋南朝时期的“六礼版文”可以视作后世婚书的起源,虽然此时版文还只具有“礼”的意义,表示东晋南朝高门贵族士大夫礼风之隆。但它从《仪礼》的口述辞令变为记录于“版”的文字形式,并且初步具备了书启文的文体格式。其措辞风格、语体范式都为后世婚书所继承,这种男方、女方一问一答的形式,也与后世婚书的一来一往的形式相同。王彪之所定的皇室“六礼版文”,成为后世皇室婚礼礼书的样本,而为唐、宋、元、明、清各朝所承。
(二)敦煌书仪中的唐代通婚函书
真正法律意义与文体意义的婚书在唐代出现。唐代婚书的写作,不再是高门贵族之行为,已经进入民间社会。《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明确提及“婚书”,并且作为婚姻成立之法律要素。但唐五代的传世文献中并未见有具体婚书作品。不少敦煌书仪却保留了婚书的格式及婚礼程式的说明,《书仪》(p.2619)《新集吉凶书仪》(p.2646)《吉凶书仪》(p.3442)等书仪中都载有婚书范本。敦煌书仪中的婚书也为一往一来的形式,通婚书(又称通婚函书)为男家致女家求婚书,答婚书(又称答函书)则为女家应允婚事的答书。敦煌书仪所载婚书有复书和单书两种。现仅以杜友晋《吉凶书仪》(p.3442)所载通婚书(复书形式)为例:
月日,名顿首顿首。阔叙既久(未久,虽近),倾属良深(若未相识云:藉甚徽猷,每深倾属)。孟春犹寒,体履如何?愿馆舍清休。名诸疾少理,言展未即,惟增翘轸。愿敬德(厚),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名白:名第某息某乙(弟云弟某乙,侄云弟某兄弟某子),未有伉俪。承贤若干女(妹侄孙随言之),令淑,愿托高媛,谨因姓某官位,敢以礼。姓名白。
不论通婚书或答婚书,都是“两纸真书”,即用楷书书写,写成两纸,两纸都具有书启文格式,前有日期,前后都有“顿首”或“白”这样的书信具礼格式用语。从其内容看,第一纸为寒暄问候,第二纸才表达真正的通婚之意。从其语言风格式来看,通婚函书用语并不华丽,不事典故。其单书形式则将两纸内容合并为一纸,去掉重复的两重首尾用语,基本文字内容不变。
综上所述,婚书作为婚姻六礼仪式中往来礼书,其文体形式为书启,至唐代,已具有约束婚姻成立的法律意义。其文体远源则为《仪礼》中的六礼婚辞,婚辞从一种口头问答发展到书面报答,其中“六礼版文”是发展中重要一环。
二、宋代婚书文体形态与婚礼程序
(一)宋代婚书作品存录与婚书文体形态
至宋代,婚书作为婚姻程序中往来之礼书已被普遍使用。宋人总集、别集、类书中大量收录有婚书作品,名称各异,文体为书、启。宋人总集《圣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元类书《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以下简称《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以下简称《启札青钱》)也收录有宋人婚书。据笔者统计,宋人在别集中收录有婚书作品的有: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赵鼎臣、张守、李光、汪藻、李弥逊、张纲、张嵲、王洋、洪皓、朱松、王庭珪、孙觌、郑刚中、陈渊、王之望、程颐、朱熹、周必大、吕祖谦、楼钥、洪适、韩元吉、杨冠卿、廖行之、黄榦、周南、李廷忠、刘宰、陈亮、李刘、方大琮、刘克庄、谢枋得、林希逸、陈著、马廷鸾等40家,三百多篇作品。这些婚书作品不单有为自己的子孙所写,也有大量代别人而写。可见,宋人婚书写作的普及与对婚书写作的重视。
宋人婚书采用的是叠幅形式的书启,称“叠幅启”,三幅为三纸,叠放一起。宋人陈元靓辑有《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以下简称《事林广记》)录有三幅婚书的格式,称“婚书第一幅式”“婚书第二幅式”“婚书第三幅式”,《翰墨全书》《启札青钱》等类书同样收录。《翰墨全书》称“婚启”而不称“婚书”,《启札青钱》则称“聘启”,这三种类书所录格式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词略有所不同。现以《翰墨全书》所录格式(如下图)为例,抄录如下:
婚启第一幅常式:
某启:孟春犹寒,共惟
某官亲家
台候,动止万福。某即日蒙
恩,谨启申问
起居,不宣。
忝戚某郡姓某启上
婚启第二幅常式:
某启:不审迩辰
台用奚似,未由

参晤,伏冀
顺时倍加
崇重。某下情无任祝颂之至。
忝戚某郡姓某启
婚启第三幅常式:
忝戚某郡姓某
右某启:兹凭媒议,伏承
亲家某郡某官(称呼)以第几院
令爱小娘子与某某男某缔亲,兹
行系定者(聘云纳聘者),言念云云。
谨奉启以
闻,伏惟
台慈,特赐
鉴念,不宣,谨启。
年月日忝戚某


婚启三幅式,其中第一幅、第二幅用来寒暄问候、祝颂,而且辞令随季节变迁,略有不同。第一、二幅启要将文字写成六行,又称十二行启。按《翰墨全书》说明:“按启有三幅,一寒暄,二启事,三祝颂,今人系臂定聘启皆用之,除启事正幅外,寒暄祝颂,俗谓十二行启,每幅止六行。”《翰墨全书》等类书收录有从一月至十二月(甚至包括闰月)的用于寒暄祝颂的第一、二幅启式,以便使用者随时套用。
婚启的第三幅才是真正表达通婚意愿的婚书。第三幅启中以“某郡某官(称呼)以第几院令爱小娘子与某某男某缔亲”字句正式写明婚主官位姓名及其结婚子女姓名。“言念云云”云云表示省略了一部分正文内容,这是类书格式套的惯常表达方式。省略的这一部分婚启正文内容,是婚姻双方的不同状况而写,所以在《翰墨全书》、《启札青钱》等类书中,分门别类列举代表性作品。如《翰墨全书》下列通用、宗女、阀阅、族姓、世婚、姑舅、两姨、乡邻、师友、科第、农人、工匠、商贾、幼婚、晚婚等20多种类别,以便不同身份不同情况的人学习使用。
宋人文集中收入的婚书,就已经去掉了前面的第一、二幅式的套语,包括第三幅格式也去掉了,仅保留了中间四六文的内容。《翰墨全书》中作为格式范例收录一则婚书正好说明了这一现象,如下图:
具位姓某
右某伏承
亲家某人许以第几院小娘子与某
男议亲,言念蠲豆笾之荐,聿修宗
事之严;躬井臼之劳,尚赖
素风之旧。既
令龟而叶吉,将奠雁以告虔。敬致
微诚,愿闻
嘉命。伏惟台慈,特赐
鉴察
年月日具位姓某定帖
其中“言念”二字后面的文句,全文来自吕祖谦《东莱集》中婚书《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启》,其全文如下:

蠲豆笾之荐,聿修宗事之严;躬井臼之劳,尚赖素风之旧。既令龟而叶吉,将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诚,愿闻嘉命。
可见,婚书在收入文人文集时,已经掐头掐尾,只剩下中间正文内容了。下面再举收入文人文集的回婚书为例。韩元吉集《南涧甲乙稿》所收《回吕氏定婚书》:
宋鲁通盟,声子尝闻于继室;郭崔论契,伯深亦记于续婚。顾惭旧族之余,叠奉高门之贶。伏承令侄孙,宗教从政,早传世学,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运判位第三女五十一娘,未习妇功,恐粗闻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将鸣凤以重占。盛事衣冠,既婚姻之是托;百年琴瑟,庶茀履以咸宜。
选入宋人文集中的婚书正文,已经没有了“右某启:兹凭媒议,伏承亲家某郡某官以第几院令爱小娘子与某某男某缔亲,兹行系定者”。这样的格式套语,而直接是一篇四六文。这一部分内容正是可以展示文学才华的地方,也是使婚书具有家世个性特征的关键内容。
类书与文集收录同一人的婚书作品,其形态不尽一致。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人书、启、笺、帖、札等文体都有其固有格式与载体形式,但进入文集之后,这些固有格式与载体形式即被忽略。在民间社会中,婚书具有礼法意义,民间类书收录婚书注重其形态完整,其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被突显,而收入文人文集时,其文学才华、个性特征则是其关键。很显然,婚书第一、二幅式作为一种格套,可以随时令身份不同而套用,因缺乏独创性,文集中一概摒弃不录。
民间社会注重实用操作,除了婚书文体形态与格式外,其包装封套、载体等形态也是其关注的内容。《启札青钱》中录有婚书“可漏式”即可漏子(指信封封套)的格式,并有说明“右公启(即婚启第一二幅式,笔者注)一幅,聘启一幅,叠卷同一可漏,礼物状自作一可漏子,两封谓之鸳缄”。《梦粱录》也记载“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据上述记叙可知,婚书三幅启为一封,礼物状为一封,名为双缄,又称鸳缄,这种双缄的封装也寄寓了民间对婚姻成双成对的美好祝福。
从形式上看,唐人使用婚书为复书形式,即有两纸,一纸寒暄问候,一纸表达通婚意愿,而宋人则变为三幅,在形式上更为烦琐。这种叠幅的形式,一方面表示婚书作为婚姻礼书的隆重性;另一方面,也是古代书启文形式演变的体现。唐末启札写作已经开始有叠幅启的出现,《云麓漫钞》引《北梦锁言》云“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宣政间,则启前具衔,为一封,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别叠七幅为一封。……庆元三年,严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唐末以后,三幅启开始流行。官场应酬中甚至出现“别叠七幅为一封”的形式,这是一种官场虚繁应酬之风的表现,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婚书用三幅启正是此风之影响。
(二)宋代婚礼程序与婚书的使用
婚姻六礼之程序,宋人已经简省为三礼,即纳采、纳币(又叫纳征、纳成)、亲迎。《宋史·礼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定婚娶仪制,品官婚礼依然按照六礼程序,但士庶婚礼则“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朱子《家礼》对婚礼程序的记载中也只记录了六礼中的纳采、纳币、亲迎这三项。《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也记载了宋民间婚礼程序,可以与《宋史·礼志》《家礼》相互印证。大概说来,纳采即民间所谓“报定”“系定”“言定”;纳币即民间所谓“聘定”“送聘礼”“下财礼”。
据《梦粱录》,三幅启加一礼物状的双缄是在纳采时用。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纳采”条下记“交授书”,并解释说“书者,别书纳采问名之辞于纸,后系年月日、婚主官位姓名。止宾主各怀之,既授雁,因交相授书……”朱熹《家礼》“纳采”条下亦提及纳彩礼中婚书的交换。
纳币环节,双方也有婚书的使用,《家礼》纳币条下记载:“具书,遣使如女氏,女氏受书,复书,礼宾。使者复命,并同纳采之仪。”《梦粱录》也记载“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聘启即前所言婚书,礼状即礼物状。前引《翰墨全书》所载婚书范例格式中即有“兹行系定者(聘云聘定者)”之句,意思是,如果是系定(纳采)则写“兹行系定者”,如果是聘(纳币)则写“兹行聘定者”。
由此可见,宋人婚书在“纳采”“纳币”两个环节中都有使用。这也就可以解释文人文集中出现称呼各异的婚书作品的原因。宋人文集中婚书作品,有称书,有称启,文体形式基本一致。男家致女家的有:婚书(启)、求婚书(启)、请婚书(启)、定婚书(启)、通婚书(启)、求亲书(启)、问亲书(启)、言定书、定书、聘书(启)、求聘书(启),纳币书(启)、下礼书;女家回男家则有:答婚书(启)、许婚书(启)、许姻书(启)、许亲书(启)、回定书(启)、回聘书(启)。由前述婚礼流程可知,求婚、请婚、定婚、求亲、问亲、言定等书启为纳采环节使用之“定婚书”;聘书、纳币书为纳币环节使用的“聘婚书”。但这种题目的划分也不是十分严格的,到南宋后期,两类型的婚书题目划分比前期要更为清晰,如刘宰《漫塘文集》“婚启”一目中,就分为“定某氏”“聘某氏”两类型的标题,其中“定某氏”为纳采时使用,“聘某氏”则为纳币时使用。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中对婚书启文写作方法的介绍也分“定婚启”和“聘婚启”两种。这种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也是宋人对婚书文体独特性认识的过程。南宋后期,文人文集、总集中“婚书”单独列目的出现,正说明宋代婚书其文体形式的独特性被人认可。
三、宋代婚书文体特点与文学色彩
从法律上看,宋人婚书既是婚姻事实成立的一个依据,具备契约性。与唐人一样,宋代婚姻事实的承认,也以婚书为据,《宋刑统》记载:“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婚书、私约、聘财三者皆是约束婚姻成立的依据。从文体上看,宋人婚书属于书启文,可视作书信的一种,具有强烈的私人书写色彩和个性特征,它不同于出现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婚契。从婚书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作者对双方家世风范、人生态度、婚姻观念等的表达与评判,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志趣,作为宋四六文的一种典型文体,其文学性也是宋人在写作婚书时孜孜以求的。
(一)合二姓之好的婚姻观念与文体表达
婚书正文内部结构可以分为起联、接联、叙年德中联、结联几个部分。其中,起联和叙年德中联为婚书四六文之特色。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部分对“定婚启”与“聘婚启”的写作方法进行了介绍,其中定婚启的写法为“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婚书中第一联即起联往往就双方姓氏、身份、交谊进行叙谈,这也就是《文筌》所说的“合姓”。《翰墨全书》“婚姻活套警语”中列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起联活套——“就姓用事”“借意说事”。
就姓用事,即就两家姓氏运用典故写作起联,宋人刘宰《漫塘集》中婚书就有许多例“就姓用事”的起联:
起草庐之顾,赫奕家声;分藜杖之光,寂寥世裔。(《定诸葛氏》)
传中郎之业,夙仰名门;校东观之书,有惭末裔。(《回蔡氏定礼》)
刘宰在这三则婚书中对联姻方诸葛氏用了诸葛亮之典,蔡氏则用了蔡邕之典;对自己的刘姓使用了“东观校书”“藜杖”等词语,都是使用汉代刘向校书的典故。婚书作品除切合双方姓氏用典外,也大量使用二姓合好的词语与典故,如“潘杨之睦”“雷陈之分”“朱陈之好”“秦晋之欢”“管鲍之交”“韦杜之姻”。这种合姓起联的使用,既是婚姻意义“二姓合好”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晋宋南朝高门氏族自矜门阀之风的承继,同时也是宋时书启中大量使用姓氏典故的体现。婚姻的意义,《礼记》所言“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在古代,婚姻是两个家族联姻,门当户对是婚姻的前提。婚礼古有“问名”之风,借此机会,双方都会对自己的家族进行一番褒扬甚至炫耀。宋代婚姻虽然不再以门阀为重,但在婚姻事实中,“二姓合好”的意义深入人心,因此,对对方家族进行称颂是婚书中首要内容,起联即以双方姓氏为切入点。与此同时,这也是宋人诗歌、启札写作中爱用姓氏的典故的表现。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南宋启札盛行,骈偶之文务切姓氏”。宋人不但婚书中使用姓氏典故,在其他四六文以至诗歌创作中,也以使用姓氏典故贴切而为人津津乐道。
(二)婚姻双方家世风范的体认与文人情怀的彰显
婚书起联的另一种写法“借意说事”更为清楚地在婚书中传达了婚姻双方的家世信息、家门风范与人生志趣。所谓“借意说事”是指对双方身份、交谊的叙谈,以拉近双方关系。《翰墨全书》《启札青钱》等类书中往往会就不同身份如“世婚”“师友”“科第”“乡邻”“异乡”等进行分类列举活套。而在文人写作的婚书中,则往往贴合自己与对方的关系而写。如:
雁塔题名,夙讲同登之契;凤占叶吉,兹谐嘉耦之求。(楼钥《次女许郑氏书》)
三十年之莫逆,岂云势利之交;四千里为流人,敢有婚姻之请。(李光《答潘舍人求婚启》)
楼钥为次女许婚郑氏所写婚书则“雁塔题名,夙讲同登之契”表明自己与对方家长是同登科第的关系。李光在答潘舍人求婚时以“三十年莫逆”表明双方交情之深,并用“四千里流人”自述被贬之处境,非常生动。
最为典型的是婚书中联,这一联称为“叙年德”,即明确指出婚配双方为谁家第几子或第几小娘子,并且需要对婚配男女双方的品德、操守、行止、学识、素养进行称叙。这是婚书与其他书启显著区别的地方,也是婚书文体之必备特征。对双方年德的称叙,文人士大夫一般会引经据典,使用来自《诗经》《礼记》《论语》《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称人品行的典故与词语。如以“采苹”“采蘩”“苹蘩之共”称扬女子能担当祭祀之仪,不失一家主妇之职;以“组纟川”“纷帨”“施縏”来称颂女子能工女事,守妇德,尽心侍奉家人;而“白圭三复”“弓冶之子”“箕裘之业”则往往用来指代男子不坠祖业,品质崇高,慎于言行。如苏轼为孙子苏符所写的《求婚启》:“轼长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质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风绵邈,庶几弓冶之余。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辈之爱女第十四小娘子,禀粹德门,教成家庙。”(苏轼《求婚启》)
叙年德中联为婚姻男女双方及其家世提供了一个简短的鉴定,这种鉴定正可以体现宋人对自身家世风范的体认与彰显,这正是文人人生态度的表示,如:
伏承贤第几小娘子,幽闲顺于保母,才德似其诸姑,闻之族姻,迨今笄岁;小子某,粗识嗜学,亦既胜衣。(黄庭坚《问李氏亲书》)
伏承令侄女,幼习妇规,颇著言德容功之美,而某小侄某,长闻义训,粗免骄奢淫佚之邪。(张守《为外甥定婚书》)
伏承某人令嗣,耽味简编,甚于寒素;而某女子,服勤鞶帨,安此清贫。(廖行之《回向氏许亲书》)
黄庭坚在婚书中肯定小子“嗜学”,张守褒扬自己的外甥“无骄奢淫佚之邪”,廖行之则肯定对方之子守“寒素”,自己之女安“清贫”。从这些品质的肯定中,不难窥探宋代文人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叙年德之外,婚书结联等其他话语中也不难看出双方家长的人生志趣与意愿,如“好事到门,窃为吾儿吾孙之喜;遗书满屋,愿纟由乃祖乃父之藏”(方大琮《回宋》)这是书香之家的自矜;“为国而啮雪旄,言旋是望;入门而会冰玉,语笑何如”(方大琮《林回徐》)这是爱国之心的表露;“两翁相语,俱为陶令归来之人;二姓其昌,好毕尚平婚嫁之事”(马廷鸾《庐山谢氏求聘启》)这是对隐逸情趣的向往。婚书中的这些表达,很好地为我们勾勒出宋代文人群体的整体风貌,无怪乎黄庭坚指称婚书“皆家传”。
而对女子,婚书作品中基本上以品性幽娴淑婉、勤事女工、姆仪雍容、谨守妇德妇教等传统社会女德规范来评判,也有个别婚书中借用中郎之女蔡文姬才学之富、谢安之侄女谢道韫林下风范对女子才学气质进行肯定,但似乎没有一篇婚书对女子美丽的外貌进行过描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儒学价值体系中,对女性的要求以德为主,外貌则被忽视。
(三)宋四六之风的体现
唐代婚书语言简质、不事骈偶,也不大量使用典故,而宋人婚书用四六文。这与宋代四六文兴盛的社会风气有关,宋代虽有古文革新,古文写作一再被倡导,但在朝廷公文、礼仪文书等实用文领域,四六文使用非常广泛。宋人婚书行文上也具备宋四六的一些特点,如大量虚字入联、大量使用长联。试看以下两联:
幸邑里之相邻,而声猷之素洽。是以致求婚之请,亦既闻报可之音。(廖行之《谦子定刘氏书》)
齐大非吾偶也,虽莫遂于牢辞,平固长贫者乎,或可酬于垕德。(杨冠卿《为帐幹与王氏书》)
第一联“是以致”“亦既闻”以虚词带动句势流转,有散体单行的感觉;第二联“非……也”“虽莫……”“固……者乎”这些句式纯是古文句式,却嵌入了四六骈文之中,使得骈文并不板滞,句意也有散行气势。再如长联的使用:
鱼轩象服,岂敢期异时家室之荣;竹杖芒鞋,便可结两翁山林之伴。(李弥逊《问亲书》)
伏承某官,世胄实江左衣冠之表,家声犹鲁国洙泗之余。以某侄女,固尝袭荆布而傃贱贫,可以执箕帚而奉洒扫。(孙觌《答曾氏问亲》)
这种长句在一联中的使用,依然保留了骈文的对偶感,但却瓦解了四字六字句交替使用的固定四六句式,不但很好地表达了内容,更制造了一泻而下的气势。宋人婚书四六文用典讲究,试举洪适《第五子婚书》为例:
三世连姻,旧矣潘杨之睦;十缁讲好,惭于朅末之间。宋城之牍岂偶然,渭阳之情益深矣。伏承令女,施鞶有戒,是必敬从尔姑,第五子,学箕未成,不能酷似其舅。爰谋泰筮,用结欢盟。夸百两以盈门,初非竞侈;瞻三星之在户,行且告期。
这篇婚书,无一句不用典,无一联不用典。第一联,“三世联姻”“潘杨之睦”,指潘岳与杨绥的情谊,典出《文选》中《潘安仁杨仲武诔(并序)》;“朅末”来自于《世说新语·贤媛》谢道韫语“群从兄弟复有封、胡、遏、末”。第二联“宋城之牍”典源唐朝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关于韦固遇月下老人翻检婚牍的故事;而“渭阳之情”语出《诗经·秦风·渭阳》,指代甥舅情谊。第三联“施鞶”“学箕”等词语出自《礼记》。结联“夸百两以盈门”语出《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的诗句,“瞻三星之在户”则出自《诗经·唐风·绸缪》。这篇婚书的用典颇为讲究,基本上用《礼记》语对《礼记》语,《诗经》语对《诗经》语,六朝语对六朝语,传说对传说。而且所用典故均围绕“世婚”“甥舅”展开,典故与典故之间也相互呼应。上引洪适作品可以让我们一窥宋代婚书写作之讲究,文辞之典雅。
宋人婚书喜欢广引典籍,广采经、史、子、集中关于人物品评、婚姻逸闻与传奇故事的典故,“坦腹东床”“卜凤求士”“天壤王郎”等关于择婿的逸闻典故频频出现在婚书之中,而“月老”“丝绳”“宋城之牍”“种玉得妇”“种白璧”等具有佛道色彩的姻缘前定的典故也为文人所喜用。杂史逸闻等典故的使用,为庄重严肃的结婚契约增添着几许的飘逸浪漫美丽的文学色彩。这也是宋人婚书成为可赏鉴可品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婚书作为一种文体,从唐代出现到宋代繁荣,其文体的渊源因素可以追寻到《仪礼》中婚辞,而六朝时期的皇室、贵族婚礼中的“六礼文”为后代文人婚书写作提供了文体与文辞借鉴。唐宋人婚书均为书启文,唐人为单书或复书形式,宋人则发展为叠幅形式,叠三幅为一封,并与礼物状一起合称“双缄”,具有成双成对的美好寓意,叠幅婚书的出现,也是受晚唐宋时书启文写作叠楮之风的影响。唐人婚书简质,不用骈偶,不事典故;宋人婚书正文内容部分则使用四六文形式,文体上具备宋四六的典型特征,文体典雅,辞令优美,不但采用儒家经典著述称叙婚姻双方当事人品行,而且广采杂史逸闻典故,使婚书典雅庄重又具有浪漫美丽的色彩。可以这样说,唐人婚书还是一种实用礼书,主要起到通婚报答的作用;而宋人婚书则不再是简单的实用礼书,而是文学作品。因此,婚书不见于唐人文集中,而宋人文集中则大量收录。对大量宋人婚书品读可以发现,宋代文人在婚书撰写过程中以其文体因素突出了“合二姓之好”的婚姻观念,又以其“叙年德”的独特文体要素集体展示了其对自身家世风范的体认与彰显,不单具有文学意义,更具有文化史意义。至元代,婚契出现,婚契作为合同婚书的方式逐渐成为民间婚书的主流。明清时期,婚书发展出现二线分立,合同婚书形式成为民间婚书的主流,逐渐发展为今天的结婚证书,而婚启、婚札则依然成为纯粹的文人的书启,用于婚姻中礼书往来。
[责任编辑吴奕锜责任校对王桃]
I206.2
A
1000-5072(2015)08-0092-09
2015-03-22
邬志伟(1982—),女,湖南娄底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批准号:10&ZD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