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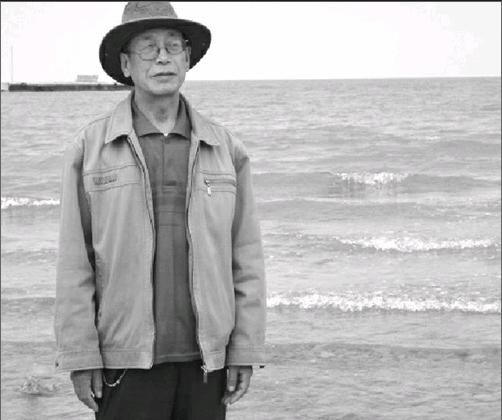
1
乌碑岘的水家三姊妹——金兰、银兰和铜兰出奇的漂亮。而更为出奇的是,命运似乎就因着这些响亮的芳名,将她们拉开了明显的等次。
金兰虽说只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可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市军分区的曹司令一眼就相中了她。夫贵妻荣,她自然就是贵夫人了。银兰和大姐金兰相比,是次了一些,却也过得随心如意。她在乡上的中学里当教师,而丈夫是校长。
这三姊妹中,铜兰就有些相形见绌了。上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离世了,母亲病倒了,两个姐姐又出嫁了,她只好辍学来伺候母亲。三折腾两折腾,就到了出嫁的年龄。可她哪有出嫁的权利?她得为水家接续香火,只有走招女婿这一条路。女儿出嫁是由着自己拣选,而要往进招一个拣选权就不属于自己了。不过拒绝权还是有的。凡找不上女人的男人,不是这里有缺陷,就是那里有破绽,铜兰又是那么漂亮,哪里能看得上!她从十六七上张罗着招女婿,到二十六七上还是女光棍一条。
铜兰二十八的这一年,庄间人把和她年纪相仿的石忠仁介绍给她。这石忠仁父母早已离去,哥嫂都分开各过各的日子,他穷得盘不上家,就情愿倒插进水家的门。
铜兰根本就看不上石忠仁,只是因为母亲一年不如一年,她一个人忙乎不转,就勉强答应了。这石忠仁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既“忠”又“仁”。他一进水家门,就只是干活。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干。其时,铜兰的母亲已睡了床,水火不送。石忠仁给她端屎端尿,洗衣濯身,比亲生女儿伺候得还殷勤周到。
三年之后,当铜兰母亲的坟鼓堆在萧瑟的秋风中一锨一锨撩起来时,一座无形的丰碑在村人的心目中高高挺起:铜兰两口儿是乌碑岘里千古第一孝啊!
2
这话传到大姐夫曹司令耳朵里,他立即打起了他们俩的主意。原因是他父亲害脑中风,已瘫在炕上三年了。家政换了怕有成十个,至今仍架在空档上。
曹司令把这个构想提出来和金兰商议时,金兰刷地脸都黑了。她和铜兰的疙瘩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娘家时结的。那时铜兰还小,看着刚刚订婚的姐姐,手腕上框着个黄澄澄、亮晶晶的宝贝镯子,就羡慕得要死。她恳求姐姐容她戴一天,只一天。“一霎儿都不行,还一天!”金兰俨然是骄傲的公主,不可一世。“这是无价之宝,你能随便戴吗?你有这个命没?”铜兰碰了一鼻子灰,又装了一肚子气。金兰每夜睡觉时,就把那宝贝用手绢包好,压在枕头底下。有一夜跑地震,金兰只顾命就把那东西忘了。铜兰却没忘,她把那东西悄悄地藏到了填炕窑的驴粪里。地震是轻微的地震,并没震出什么。而真正的地震却到了第二天。那天清晨金兰才察觉到她订亲的礼物不翼而飞,便挖破地皮地寻。寻到后来,她就把目标瞅到了铜兰身上。铜兰开头不认账。金兰气急败坏,一把就撕裂了铜兰的耳朵,血流如注。铜兰招架不住,只好如实“交待”……她就一直记恨着她,哪怕一根断线头子,她也决不让铜兰沾着。可她左思右想,要寻像铜兰两口儿这样可靠的家政实在难,于是松下脸来,勉强同意了。可在商议待遇问题时,又卡了壳儿。曹司令提出土地和庄子白送,另外每月付上一千块零花钱,并且伺候得实在好了,再奖励一万。
金兰不仅脸黑了,喉咙里还“吭吭”的,像有个骨头卡在那里吐不上来,又咽不下去。她说不出自己是妒是怒是恨还是醋,不觉地就有些失态:“就干脆连你一个司令都搭上吧!”
曹司令正色道:“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吧!”
金兰又立即变了态度,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是和你说笑哩!给我妹子填得再多,我能不高兴吗?”
3
司令家的这个待遇,对多少有点本事的人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如今的农村人出外打工,一年挣个六七万是家常便饭,谁还稀罕你这么一点点“待遇”!
可这对铜兰两口儿来说,就是财神寻到门上来了。这石忠仁也就是个天生伺候人的材料。他出去打工,工钱要不上不说,还太惜家,一个月不回来一趟就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活儿自然也就没力气干了。铜兰见他这般没出息,就自己出外打工,把男人留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她回家一看,男人瘦得没了人形,像不久于人世的人。她吓得不轻,就再也不敢出去,也不敢打发男人出去,两口儿死守住几亩薄田苦熬。现在摊上这么个差事,用眼下时髦点的话说,就是“互利双赢”了。曹司令的老家——曹家河畔,四五口人的水地就够摊价了,而那一院金殿一般的住宅,恐怕要往二十万那边说,再加上每月的一千零花钱……铜兰自然没打任何推辞,就带着全家人告别了乌碑岘,来到了曹家河畔。
曹家河畔和乌碑岘相比完全是两个天地。这水川区的农民靠着种植业和养殖业发面盆似地富起来,家家都盖了一砖到顶的新房,里里外外都贴上瓷砖,锃锃明明,亮亮堂堂,就跟进了天堂一样。而在这所有的房屋中,曹司令家的又是鹤立鸡群,独揽风骚。因为别的都是平房,唯有曹司令家的是两层楼,显然就分出了层次。曹司令原来打算退休之后回到故里安度晚年的,可后来在市里建了一栋小别墅,便改了初衷,并且把先前的打算冠以“农民意识”而彻底否定。
这“农民意识”却给当农民的妻妹铜兰带来了好福音。
铜兰就把大姐夫两口子感激到骨子里去了。她想要不是他们俩的垂顾怜悯,拿她和石忠仁的那点本事,恐怕八辈子都挣不出这么赢人的家业来。
铜兰感激过姐夫姐姐之后,又觉得决不能忽视已经卧床三年的这位垂危老人。是他把他们两口儿与这个豪华的乡村富宅、与这赛如天堂的曹家河畔牵连起来的。就凭着这想都不敢想的丰厚报酬,她得把曹家的老人当做自己的亲爹服侍。
曹司令的父亲才刚奔古稀,按现在人的寿数并不算年纪太大。他害的是“富贵病”,能吃能喝,就是不能动。铜兰两口儿进到他屋里时,一股恶臭打住了气。铜兰一问才知道,在这之前伺候的人,到顿数上只给他戳上一碗饭,——只一碗,怕吃多了,麻烦事更多。平常嫌老人脏,就躲到另一个屋里,或者出去串门。老人自然只有常在屎尿炕上栽着了。铜兰初来乍到的这一夜,就和男人忙碌了一个通宵,该洗的洗了,该换的换了,屋里还点了卫生香,洒了香水。铜兰给老人做了他最爱吃的饭——莜茶面疙瘩。老人吃了三大碗。吃罢后,就哭,是感激的哭。他说他三年来第一次把肚子填饱。铜兰和石忠仁也都陪着他哭,他们真没想到赫赫有名的司令父亲,竟然睡屎尿炕,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从这一个夜晚开始,铜兰两口儿就给曹姓人当了孝子。他们俩确实是孝子,任多忙,屋里总要留下一个陪伴老人。
他俩来到曹家河畔之后,虽说像一步登了天,而付出的艰辛却比乌碑岘不知要大多少倍。人常说,一个人躺下要四个人抬。对于一个瘫痪的病人来说,两个人换着伺候就够满负荷了。而他们俩还要作务庄稼,喂养牲口,照料孩子……乡村中看不见的活儿随处都是。铜兰两口儿再也没个囫囵觉可享受了,到忙月时就常常通宵不眠。如此这般地过了几年,铜兰就苍老了许多。逢年过节,曹司令两口儿压着小车,象征性地给老人来敬孝时,庄里人常把比金兰要小到十岁的铜兰说成金兰姐。铜兰心里就颇不是滋味。
她和男人这样苦熬了十年,总算把司令父亲伺候下场了。
铜兰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4
司令父亲安葬过的这天晚上,铜兰忽地觉得自己疲惫成一摊泥了,躺到炕上没上半分钟,就呼呼地睡沉了。
铜兰正睡得香,男人用指头把她捣醒说:“二楼上叫着哩!”
二楼上那一间装修得最阔的房子是曹司令两口儿的专有卧室。不过给铜兰也留着钥匙。过一段时间,她得打扫屋子,翻晒被褥。
铜兰走进司令姐夫的卧室时,这里显得非常热闹。两个姐夫和两个姐姐都在场,加上警卫员就是五个人了。大姐夫、二姐夫并排坐在三人仿古沙发上,两个姐分坐于两侧的单人沙发上。他们一边谝闲,一边喝酒。酒是纯正的五粮液。高级大理石茶几上摆有五香瓜子、香蕉、芒果之类的杂食。警卫员在另外一张桌子上点钱,那是事情上收来的情钱。他边点边捆成扎子,码了一座小山。屋里笼罩在一种酒的馨香和上层人物特有的富贵之气交织着的氤氲之中。
铜兰素常里跟姐夫姐姐在一起,就觉得很不自在,很是自惭形秽。而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她就更是自卑。大家都热情地招呼他们两口儿坐下,她左看右看,寻不到一个合适的坐处。大姐夫和二姐夫礼貌地站起来,让他俩坐到三人沙发上来。三人沙发坐五个人绰绰有余。可她能和司令平起平坐吗?惶悚之中,她就把屁股拓到席梦思的边缘上吊腿坐了。石忠仁走到哪里都是看她行事,和正统的夫唱妇随恰好相反。他像被人养顺了的猫,圪蹴到铜兰腿旁,把脊背靠在床帮上。银兰说:“他三姨夫,你到沙发上坐,要不就到床上坐起,那么蹲得住吗?”石忠仁看了一眼铜兰,憨憨地说:“二姐,蹲住呢!我拔麦时就这么一天往黑蹲,这是光坐着又不用力!”司令使用点小幽默说:“这里可没麦地里那么软!”惹得大家哈哈笑了好一阵。
铜兰心里就浮上一丝挥之不去的酸楚。她本来想尝尝一瓶上千块的五粮液是啥个滋味,这么一刺激,她就一点兴趣也没了。当警卫员向她敬酒时,她抿都未抿,并且用眼角向蹲在地下的丈夫使意思。石忠仁也就心领神会,滴酒不沾了,只是又说了一句太实在的话:“我喝惯了凉水,这猫尿见不得!”屋里再度掀起哗笑。铜兰开始缓和的心境又扬起久久不息的波澜。
这时警卫员点清了情钱,一扎一扎装进一个上面标有“观音王”的敞口尼龙袋子里,双手拱到曹司令面前说:“十八万八千八百元。”
铜兰就惊得半晌合不上嘴。他们乌碑岘人过一场事情,情钱过千也就被人喝红了。“这……啧啧!”
大概因为这钱数中冒出了三个“八”,预示着司令一家将红运高照、前途无量,大姐两口子的兴致就顿然高涨起来。司令又从警卫手中要过酒,亲自斟了来敬大家,好像老人并没有“千古”,而是带了重金厚礼给他们铺排锦绣前程去了。
金兰敬到妹子铜兰面前时说:“这酒没喝惯的人喝不住,我就代妹喝了吧!”
铜兰觉得心上刷地一冷,下意识地躲了躲。
金兰倒提了高脚酒杯说:“铜兰,你们两口儿也真不容易哇!”
铜兰被姐的这一声体贴话说得好不心酸!对于他们两口儿所干的营生,别人不说什么,倒也觉得没有什么。你若说个“真不容易”,也确实真不容易啊!他们在乌碑岘时,常在鸡屁股里掏钱花,而到了曹家河畔,是在人屁股里掏光阴。司令的父亲曹老太爷到最后的那几个年头,几乎每次的大便都是石忠仁用指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那污物就常嵌进指甲缝里,洗也洗不净,什么时候都熏人。忠仁倒是习惯了那种气味,而铜兰常恶心得饭也吃不饱、觉也睡不香。“大姐,你说真不容易,那确实真不容易!”铜兰觉得泪水憋得眼眶胀疼,但她一想眼前所有这一切将是属于自己的,便又转了话锋说,“不过,要不是姐夫、姐姐特意照顾,这么好的差事还轮不到我俩呢!”石忠仁从旁帮腔说:“司令大的屁眼门能剜上的人……”铜兰立马用眼角剜得男人噤了声。“我俩常说起你们的好处!”铜兰看看大姐,又看看曹司令。
“只要妹妹、妹夫记着就对了!”金兰胖得发光的圆脸盘上洋溢出为人办了好事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自得自满,俨然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下凡了。
“哪能忘了?”铜兰这才顺了一口气,“恐怕再换上一次毛衫①也忘不了。”
“你不愧是我的好妹子!”金兰乐融融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铜兰——”金兰的大屁股刚落下来,曹司令又发话了。曹司令这时仰躺在仿古沙发里,把那大背头靠在沙发后背上,一只手端着高脚酒杯,不时抿一口穿心透肺的五粮液,一只胳膊架在沙发挡头上,白漂衬衫的袖子卷到肘弯以上,袒露出粗壮滚圆的胳膊。铜兰就不由把那胳臂和男人的小腿做着比较。这一比竟是自己男人输了。她就无形中感到一种威压,连呼吸也疙疙瘩瘩的不顺畅了。她心里骂自己贱,连当姐夫的也怯乎,可就是不由自己。她听人说当官的——尤其当大官的都有煞气,能把人镇住。这怕是真的。她每次和司令姐夫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借故避了。她撑不住那无形的威压。但今宵她不能避。她要聆听司令姐夫对他们两口儿十年煎熬的评断,就像一个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的穷学生要看自己的考试成绩揭晓一样。曹司令也许看透了铜兰的心思,他的态度就格外和气,也格外亲切,“鉴于你们两口儿服侍老人有特殊的贡献——铜兰你听清了吗?是特殊贡献!啊?如果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你们两口儿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孝敬父母的模范人物。不过我已打发记者将你俩的事迹在省报上登了,电台也广播了。有可能到年终你们俩要作为家政的先进人物受到奖励。在政府部门给你们授奖之前,我先给你们奖励一万!”
铜兰就惭愧得揪心。她知道司令姐夫奖励她是因为她的孝心感动了他。她为司令父亲送葬时哭得死去活来,连方下②都惹得流了不少泪。她是司令从坟园里硬拖起来的,并且他还掏出手绢给她擦了泪。她分明感到曹司令当时受了很深的感动,并且因此他深信她替他真正尽了孝。可事实上她借此哭自己的爹娘呢!扪心自问,她对自己的爹娘也没啥亏欠之处,只是相形之下,就显出截然的差距来。唉,人怎么能把该厚的不厚、把该薄的又不薄呢?她这样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暗暗一问,就戳到伤心处了……于是她很坚决地拒绝说:“姐夫,奖励我就不要了,只要把早说过的落到实处,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曹司令向警卫员招了一下手,“我说了奖就得奖!”
警卫很恭顺地站起身,到他刚才装好的那尼龙袋里去取钱,慌得铜兰腾地跳下床,竟撞到男人的膝盖上,反弹力几乎将她弄倒,好在石忠仁弹簧似地蹦起来,一把稳住了她。可铜兰站立稳当时却又踌躇不定了。她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自己这样一个土里土气、没见过世面的村妇怎敢去挨近那纤尘不染、文雅高洁如天使一般的人物呢?谢天谢地哇,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大姐金兰解了她的围。
“小任,要不你就把这钱暂不要给了!”金兰也用手势阻止了警卫,“我也要奖她一万,到时候一块儿给!”
“大姐,怎么好意思……”铜兰不知该说些什么,吱吱地咂着嘴又坐回到先前的位置上。
“铜兰确实不容易!”二姐银兰有点感慨地说,“我也要给铜兰一万。不过我没带钱,回去后我给你再给!”
“甭甭甭……”
铜兰心里就有点发急。她一急话语的那个领域纯粹变成空蒙的荒漠了,就只是把发酸的腰身扭来扭去,弄得屁股底下的床发出怪响,仿佛也替她着急似的。铜兰虽是四门不出的乡民,但她行事为人却有自己的原则:不占谁的便宜。大姐两口儿给她追加的两万,尽管她觉得烧手,但仔细一想,自个两口儿毕竟替他们尽了孝。现在的人讲究个“精神补偿”。“孝心”还不是个精神吗?精神的东西有时是无价观的。甭说两万,就是弄十万能买来真正的“孝心”吗?而二姐的一万说什么也是不能要的……铜兰心里头正活动着这些谁也猜不透的念头时,忽听得大姐金兰鼻子里“吭吭”起来。
铜兰立即集中了精神去看大姐。她知道大姐一旦有“吭”就定有难言之隐了。铜兰就很是惶惑不安了。难道他们再追加两万是舍不得这一院地方了?若是一院地方落空,那这些年她作务得有感情的水地也落空了?若是这样,再追加上十万八万,她和男人十年的工夫不就白搭了吗?当姐姐又一次“吭吭”时,她的心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她肯定了自己的推断。这“吭吭”就是变卦的前奏曲。她感到事出突然,无法应对。她只知道乌碑岘人置变卦者于死地的一句话是:你把自己■下的吃了再说。如果大姐两口儿真变了卦,她能说这话吗?……铜兰还没想出个渠渠道道来,大姐又“吭吭”个不止。铜兰就吓得头脑里一片空白。
“铜兰——”金兰终于发话了,不过出奇的柔和,“这些年实在多亏了你们俩。”
铜兰的情绪又好转过来,用脚尖启示呆若木鸡的男人。
石忠仁忽地站起来,讷讷地说:“大姐……还有大姐夫的恩……比乌碑岘的山……都高……”
金兰“吭吭”地打断石忠仁不连贯的话语说:“别先说报恩了!当然我俩以前说的话都算数,只是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无论如何得答应!”
“大姐!”铜兰笑逐颜开了,“你有要求就直说吧,当妹子的给姐有不能应承的啥呢?”
可当金兰说出那个“无论如何得答应”的“条件”时,铜兰却拧身走下楼钻进了自己的住室。
5
铜兰起初把大姐金兰的“条件”想象成一年供应些蔬菜、面粉、油肉之类的“进口货”,如今这些东西多得堆天塞地,但凡上市的没一样是真品了。无怪乎不少城里人开车到乡下采购“绿色食品”。铜兰想,她得了大姐这么多好处,即使大姐不说,她也会把这一切丰丰满满地供应给她家。可她哪里会想到大姐提出如此可怕的条件呢?那不是“条件”,那是五雷轰顶!
铜兰钻进自己的卧室时,还被“轰”得头里嗡嗡地响。她倒插到炕上就哭得声哽气噎,慌得石忠仁一个劲儿地在她微微颤动的瘦弱的肩背上搓来揉去。
金兰也动了肝火,从楼上追下来,直撅撅竖到铜兰炕眼前指责说:“你觉得冤枉了是吧?我屋里的钥匙就你拿、我拿、你姐夫拿,这金镯子你没拿,难道说你姐夫拿去了?”
铜兰忽地坐了起来。她想说句辩解的话,但终究口软得没说出来。她想起了遥远的往事。
金兰打断铜兰的思绪说:“我晓得你早就把那东西爱得不是一般。可你现在也不小了,该懂事了。这是我的订婚礼物,它象征着我和你姐夫的爱情天长地久哇!”
“……”铜兰就只是哭。
“你若实在爱得不行,我回去给你买一个送来总可以吧?”
“……”
“铜兰,你一定要不识人抬举,那就不要怪当姐的无情,这一院地方,还有那几亩水地,你休想沾一点!”
金兰下了最后通牒之后,就噔噔噔地上了楼。
不久,银兰两口儿又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铜兰面对二姐和二姐夫,就越发哭得一塌糊涂。
银兰把身子屈到炕头上,拍着铜兰颤抖的肩头说:“铜兰哇,你要理解大姐,那个金镯子可是她的命根子哇!”
二姐夫斯斯文文地在地上转着圈儿抽烟。他斯文够了,就压住步说:“铜兰,我看这事多话就没必要说了!拿钥匙的就你们仨,两个是自家人。自家人肯定不会偷自家人的。你跳到黄河能洗净吗?”
铜兰忽地一蹦子跳下炕,狮子一般怒吼道:“滚!你们给我全都滚!”
6
铜兰看到屋里再没了外人,就对呆若木鸡的男人说:“把孩子叫起来走!”
“这一夜子往哪里走?”男人闷闷地问。
“乌碑岘!”
“那我们这些年……”男人嗫嚅道。
“天晓得!”铜兰口气决绝,不容商量。
翌日,铜兰两口儿清扫好院落、正要下地做农活儿时,银兰惊惶失措地走进了乌碑岘。她告诉铜兰,大姐金兰两口儿在回市途中出了车祸,正在县医院进行抢救。
铜兰本来这辈子再不想见大姐金兰了,可这时那根深蒂固的血缘亲情又油然浮上心头,暂时压下了那搅得她一夜未能入眠的屈辱。于是,她二话没说,跟上二姐去了县医院。
姐夫、姐姐在高干病室抢救。铜兰看到大姐金兰满脸是伤,插着氧气,不省人事。一条紫白色的细软管从床旁金属架倒挂的一个透明药瓶里细蛇样爬出来,先垂直一段,然后绕了个弧形,咬住了大姐的手腕。就在那个地方半露着一个久违了的、黄澄澄明锃锃的东西。
哦,金镯子!
注释:
①再换上一次毛衫:陇中方言,意为再转世一回。
②方下:陇中方言,丧事上专门请来帮忙的人。
责任编辑 子 矜
孙志诚,原名孙自成,1944年11月生于甘肃省会宁县农村,高中毕业后曾在本村任过民教和村支书。1980年兰州师专毕业后,在会宁从事教学和群众文化工作。系甘肃民协会员,甘肃作协理事。
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中篇小说《野路》1996年在《飞天》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作品曾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二等奖、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