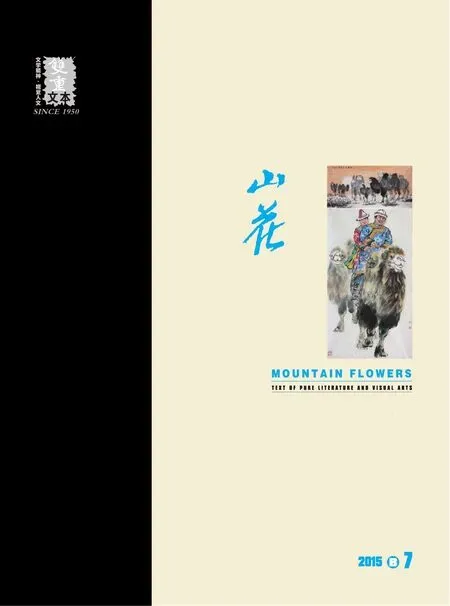从《普宁》看纳博科夫小说中荒诞的学院现实中的人文关怀
王春艳
从《普宁》看纳博科夫小说中荒诞的学院现实中的人文关怀
王春艳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普宁》是纳博科夫第一部引起美国读者广泛关注的小说,出版后备受读者欢迎。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普宁的俄裔美籍教授在一所名为温代尔学院担任教职期间的生活遭遇,反映了一个身处美国主流文化群体中的“他者”的困苦、挣扎与无奈。在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普宁遭遇了种种的冷遇和排挤,虽然他身处温代尔学院,却无法获得一个永久的教职;虽然他来到美国多年,却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虽然他周围学者云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普宁始终也没有找到归属感,行走似乎是他一直的状态。纳博科夫对普宁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体现了他对人类普遍困境的思考。笔者通过分析普宁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美国主流文化社会的遭遇,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冷漠和荒诞,以及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挣扎;通过对主人公普宁独特人物性格以及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分析,探讨了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怎样在荒诞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进而揭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普宁——“假”荒诞下的“真”自由
作为一个学者,普宁教授尽管性格温厚、学识渊博,却被塑造成了一位可笑的滑稽小丑式的人物。他言行举止在小说的“叙述者”看来十分不合时宜:老式的服饰、破旧的教科书、老古董式的上课材料、一口蹩脚的英语……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便是突出的一例:普宁教授应邀到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去做一次学术报告。而他却坐错了车,原因是他参考的那份火车时刻表是五年前印制的;途中不得不“丢掉行李”,而当他终于到达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站起来演讲时却发现自己带错了讲稿。在叙述者略带戏谑的讲述中,“搭错车”,“丢掉行李”和“带错讲稿”俨然使普宁成了读者眼中的笨蛋。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语言尽量标准,他打印了讲稿;为了早点到达克莱蒙纳以留出充足的时间,他参考了错误的列车时刻表;为了赶上演讲,不得不故意丢掉行李。普宁的笨拙和荒唐并不是因为他的糊涂,这一切都源于普宁作为“他者”在美国小心翼翼的生活。在美国,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自己触碰异域生活的禁忌而使自己陷入窘境。可他越是“谨慎”,在别人眼里就越“荒唐”。普宁作为一名教员,在课堂上的表现也不无荒唐。在讲课之前,他总会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可怕的黄牙”,再翻开一本“破旧”的俄文书;而后会因为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章节而惊慌失措;而终于找对的地方也是一些“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闹剧”。
普宁就像一叶孤舟,与美国的主流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普宁命运充满苦难,就像一颗“苦药丸”。但是纳博科夫塑造这样一个貌似“小丑”式人物并不是要为读者提供笑料,也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同情,他的真实用意是要通过普宁的“假荒诞”来反衬其生存环境的“真荒谬”。纳博科夫在1955年12月8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物……一个温柔、智慧、忠诚的爱人;他诚实正直的品格始终使他保持道德上的崇高。”这个全新的人物无疑就是普宁。作为学者和教师,他经纶满腹而又满腔热忱。他带着对俄罗斯语言文化无限的热爱,激情满怀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他不失时机地向学生传授俄罗斯的文学文化,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他不辞辛苦地收集资料,为的是实现自己编写一部“俄罗斯文化史”的梦想。他要在这个大部头里介绍俄罗斯的奇闻逸话、风俗习惯、文学轶事等诸如此类的事,前因后果的事件统统都要反映出来。作为朋友,他热情地帮助每一个需要他的同事,无私地向他们提供第一手的俄罗斯文化的素材,然而换来的只是嘲讽和讥笑。作为爱人,他不计前嫌,不计回报,无私地接纳和宽容前妻的一次次背叛和欺骗,独自忍受痛苦。甚至前妻带着与别人的孩子维克多前来投奔,他敞开大门并真诚地接受一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为自己的孩子。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普宁这个人物的高贵品格,那就是“真实”。“真”在他对身边人真诚的付出,“实”在他对工作、研究的一丝不苟和不求名利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普宁是一个高贵的美的形象,纳博科夫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合格知识分子的标准。他性格温厚却又举止怪诞,站在俄罗斯文学伟大的已故传统上与沾染了麦卡锡排外主义现在的美国学府格格不入,同事们嘲弄他,爱妻离开了他,而故纸堆的沉溺也许让他具有古典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深厚,却与轻薄的现代美国文明难以匹敌而狼狈不堪,他最终被排挤出温代尔学院。作为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他者”,普宁一方面努力回归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因为那是他不能割舍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努力地融入那个总是给与他冷遇的异国文化。从温代尔学院最终的离开,表面看来是普宁狼狈的失败,但这又未尝不是普宁通往自由的一次挣脱?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普宁驾驶的“小轿车大胆地超越前面的卡车,终于自由自在,加足马力冲上那条闪闪发亮的公路……”普宁拒绝了叙述者“老相识”要提供的虚伪帮助,不失尊严地踏上了那条“闪闪发亮”的自由大道。从某种意义上,普宁在虚伪的世界中守住了内心,坚持了自我,在荒诞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温代尔学院——象牙塔里的众生相
与普宁教授相比,温代尔大学的教师表面上显然是聪明无比,智慧过人;而实际上,纳博科夫则把他们刻画成是一群冷漠自私、缺乏学术创新能力的学术傀儡。无论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还是作为传承人类精神文明的学者,温代尔大学的教授们显然都是不称职的。劳伦斯·克莱门茨是温代尔学院的一名学者,“EOS是他讲授的那门最了不起的课程——‘意识的演变’(十二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可是连一名冷漠的信徒都没有),开场和结尾都是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滥加利用的词儿:意识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胡闹的演变”。还有一位是温代尔学院法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伦纳德·布劳伦吉,其实他既不懂文学也不会法语;可他却能够仅凭抄袭一些别人没有看到过的书上的内容作为讲稿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所谓的权威。这些也许是学生眼中应该受人敬重的师长却如此的伪善与不负责任。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大学校园里那些几十年教案讲稿都不变的教授们,用一成不变的旧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校园。当然书中也描写了一些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革新者,他们对高校教育模式的高谈阔论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哈根教授对现代教育发表了下面的高论:“你们也许会笑,可我敢说唯一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学生统统锁在隔音室里,干脆取消课堂……各门学科的讲座尽可能都给灌成唱片,供隔离开来的学生选听……”如此观点是如此地置教育的人性化于不顾,不但把教师当成了教育的机器,也把学生的知识接受当成了不需要掺杂任何情感的过程。这一观点绝不是小说人物独创的异想天开,现实的教育世界也似乎有不少人认同这样的解放教师的“理想”——有一天,学生们将面对冷冰冰的电脑屏幕,观看里面那个教授的手舞足蹈,聆听那不再亲切的谆谆教导。
作为大学里的学者,温代尔学院的教授们似乎更加的荒唐可笑。“一如既往,拿不出成果的教员靠写点文章评论他们比较丰产的同事们的著作成功地作为‘生产’;一如既往,一帮鸿运高照的教员正在享受或者打算享受年初荣获的花色繁多的奖金。”大学俨然成了一座“名利场”:教员们不再或没有能力追求真知识,真学问;金钱、研究经费、职称职位和各种闪光的物质头衔是更有吸引力的追求。在这座名利场里,大多数学者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和道德操守,遗失了那些最初最宝贵的品质。而像普宁这样老老实实的古怪学者,只会被这样现实的“学术环境”排斥——普宁最终失去了他期待很久也足以胜任的教职。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弗拉迪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自称是普宁朋友的人。尽管他极力为自己开脱“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职时,约定可以自行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辞聘请他协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普宁在得知取代他教职的是谁时,他曾经明确表示过绝不会在此人的手下工作。朋友可以自私地抢了朋友的饭碗,而却伪善地表明自己也曾经替普宁考虑过,如果真的是这样,他是否在接受这一教职时想过普宁会因此而失去工作呢?当他伪善地施舍时是否考虑了一位善良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呢?我们不得不为像弗拉迪米尔和布劳伦吉如此的学者感到汗颜,这样扭曲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学术观怎能利于高校的真正进步?
结 语
纳博科夫以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揭示了温代尔学院恶劣的竞争环境。同为大学教师,同事们嘲笑普宁,排挤普宁,为了一己利益明争暗斗。殊不知这种嘲讽和戏弄却更加凸显了普宁的高贵与嘲弄者本身的不堪。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中提出“天真的傻瓜”的概念。普宁教授无疑也是荒诞的温代尔学院派学者,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中一位“天真的傻瓜”。“‘傻瓜’类型的人物往往不谙人情世故,对标榜神圣崇高的各类情感后知后觉,懵懂不解。通过傻瓜的眼睛来看世界,世界就是这些崇高与谬误混乱一团的景象。‘天真的傻瓜’往往在不经意间剥去了所谓崇高权威,摘掉了假崇高的面具。”而纳博科夫正是通过观望普宁“傻瓜”的一举一动来影射了温代尔学院的荒诞。温代尔学院是当代大学的一个缩影,她浓缩了高校丑陋的芸芸学者以及学术百态。普宁是一位学者,一位俄裔的美国学者。在美国他的俄裔身份无疑为他的学者身份增添了悲剧的色彩,但真正悲剧的是他的“真学者”的身份。他的“真实”让他在那个“虚伪”的美国温代尔学院无法容身。《普宁》刻画了一个逼真的现代高校学术名利场:大学象牙塔内不再是一片净土,四处充斥着嘲笑、欺骗、自私、冷漠、追逐名利。作者通过幽默戏谑的笔触表现悲剧主题:在知识分子庸俗化、学术金钱化、教育市场化的荒诞社会中“真”学者的无奈和生存困境。作为置身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也批判,也戏仿, 但他并没有走向虚无。他以一位作家的冷静和审慎,剖析并诊断着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弊病,为人类的自由的抗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指明了方向。
[1]巴赫金.小说理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93-194.
[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普宁[M].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吕超.跨文化流亡的现实主义[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3):79-80.
[4]李莉.20世纪美国学院派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5]李楠.流亡者剪影[D].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
[6]刘娜.《普宁》的后现代主义解读[J].鸡西大学学报,2013(11).
[7]邱畅.纳博科夫英语长篇小说中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3(7).
[8]杨华.反叛的互文性——在《天路历程》中的体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8).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为“英语国家学院派小说研究”,项目编号为13C06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英美澳学院派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4YJC752030。
王春艳(1982— ),女,黑龙江省五常市人,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