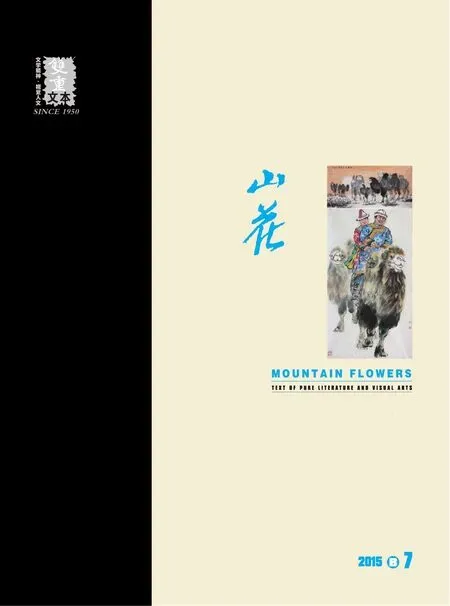蓝色妖姬背景下的失衡性
—— 分析卡内蒂的小说《迷惘》
马 蕾
蓝色妖姬背景下的失衡性
—— 分析卡内蒂的小说《迷惘》
马 蕾
《迷惘》是20世纪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以独特的坚定和鲜明讲述了一个荒诞、怪异、滑稽的故事。笔者认为,作品所塑造的类似疯人院的迷惘的世界和个人的迷惘状态源于失衡性,源于人的生存平衡的被打破。本文从贯穿作品的蓝色背景出发,用歌德的色彩学理论加以解释,揭示作品潜藏的失衡性及失衡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含义。
蓝色背景的妖魔化
《迷惘》沉浸在一片蓝色中,从幽灵般的苔莱斯的蓝色围裙、到基恩头脑里的蓝色阴影、再到基恩不时在梦中或自语时对蓝色的厌恶:“一成不变的蓝裙子,它显得刺眼,侮辱人和卑贱。”①“蓝色的裙子像一块岩石一样,僵硬地指向天空。”①“那影子是蓝色的,确实是蓝色的。”①“蓝色是最可笑的颜色,是无批判精神的人和一些轻信者喜欢的颜色。”①“阿伽门农是冥府中一个懦弱的蓝色阴影。”①这里的蓝色颠覆了和谐和自然的图景,是令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蓝色在西方传统观念里是被膜拜的颜色,它是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一种信仰。如歌德在《色彩学》中详细描述了蓝色的“吸引力”:蓝色犹如冷静的灵光,怀有无以名状的效果,是诱人的虚无,将人无法抗拒地引向远方。正如我们看到令人愉悦的事物在我们面前逃走,我们乐于去追寻它们,我们愿意欣赏蓝色,它不是向我们袭来,而是将我们吸引过去。②蓝色同样是幸福的诗意般的理想色彩:法国诗人兰波笔下“碧蓝的眼睛”,“夏日蓝色的傍晚”,“蓝天”,“蓝色的沧海”,“蓝色的波光”体现了自然原始的图景;尼采的诗歌里“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体现了静谧和幻想。
在《迷惘》里的肆无忌惮的世界里,天空纯净的蓝色降格为人间最为下流无耻的颜色,它代表的不再是真实和向往,而是无处不在的欺骗、愚昧和谋杀的凶残。在基恩对蓝色围裙的诅咒中,人们嗅到了蓝色中黄色火焰的腥味,如同肮脏的洪流、焚烧和理智的丧失玷污了纯净的蓝色。根据《耳中火炬》的描述,作品源于作者对维也纳和柏林社会的观察,而作品中的对话,也带有维也纳地区的语言特点,因此维也纳可被视为故事的发生地。维也纳常被喻为“蓝色浪漫之都”,真实的社会,却脱离了理想浪漫的色彩,打上了阴暗卑鄙的烙印,成了对蓝色的嘲讽和愚弄。从恶毒的看门人、贪婪的苔莱斯,到淫荡的鞋匠征婚人、自私的下水管道工人和小贩、见利忘义的驼背,无一不透露出阴暗和卑鄙。浸泡在蓝色世界里的《迷惘》呈现了一幅群魔图。
危机中的失衡性
1.语言的失衡
语言的失衡表现在交流中,个体无法让自己被别人理解,也无法理解别人,个人成为人为制造的封闭空间和自语的俘虏。小说开始的设置颇具精妙。开场是汉学家基恩和7岁小男孩的对话,这场对话显得与众不同:足足占了两页的对话一问一答,中间没有添加任何注解或修饰。接下来开始作者的叙述,包括基恩若隐若现的内心独白以及穿插的问路的对话。开场无间断的对话、基恩回顾式的内心独白、问路人的咆哮和被问者的木讷,使得原本以沟通为目的的对话本质上成为基恩内心独白的一部分,成为个人思考的延续,失去了对话的意义。它们从基恩的角度看是连贯的,但对于交际来说却是断续和无益的,因为对话违反了语言逻辑和常理,没有达到沟通理解的效果。它显示了人物相互交流的堵塞和失败。这种对话方式是孤立的个人的体现,意味着语言和它代表的意义发生了悖逆,导致语言的失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语言失衡发生在精通语言、终身以研究语言文字为生命意义的汉学家身上,“他讨厌一问一答,他习惯于用长篇论文来表达阐述自己的观点。”①对对话的拒绝也是交流能力丧失的前奏。人物的接触从语言的混沌状态开始,基恩之后步步落入邪恶之手,基恩精神上的迷惘愈演愈烈。在《私有财产》一章里,面对阴森森的面临生死的警察审讯时,同样,基恩的叙述只是使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模糊,完全无法使事情得到澄清为自己洗刷清白。语言的失衡还表现在称谓和事物的相互否定:基恩的弟弟眼中的地狱般的图书馆在基恩眼里犹如天堂;贴上“天堂”标签的酒店却是人间地狱,在天堂里出现的人物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对天堂一词的亵渎。
语言的失衡是人物的孤立状态和沟通失败的结果,它导致人际关系的迷乱。
2.人物角色的失衡
除了人的符号之一的语言缺失外,《迷惘》里的人物常以“蓝裙子”,“驼背”,“瞎子”,“跛子”,“一支粗笨的手臂”,“长发猴脸的小伙子”等带贬义的特征出现,它所叙述的人不再是完整、社会性的人,而是从生理到心理残缺的人,意在凸显人物的扭曲和失衡。
苔莱斯极尽伪装和谄媚,“书里有些污斑,我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搞掉……”,“我每一页都要读上十遍,否则不会有什么收获”,①“这下可上钩了,她思忖着”。①婚后,苔莱斯原形毕露,“明天没法做饭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本领同时干许多事情”,“……她摆出了一幅可怕的笑脸,眼角和嘴角都拉到耳朵边上去了,狭长的眼缝里射出两道浅绿色的光”。①她肆意对待基恩,强占房间,夺取图书馆,疯狂地寻找基恩的存折和他的遗嘱,直到将衰弱的基恩赶出家门。
驼背菲舍尔勒正如自己的外形那样令人厌恶。在肮脏的酒店里,他纵容老婆和嫖客鬼混,甚至利用老婆对嫖客敲诈勒索,完全丧失了伦理道德。他窥到了基恩轻信的弱点,编织谎言,策划犯罪团伙来骗取其钱财。驼背对他的几个“下属”布置任务时,“量材使用,区别对待。”①一切诈骗和谎言在驼背看来都是那么自然、娴熟,并且在利益分赃中他处于中心地位,对“下属”充分施展其权威,与“驼背”受人歧视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暴露了底层民众的贪婪和道德沦丧。
看门人普法夫“是个狡诈不可缺少的人物”。“那个凶狠的看门人天天守候在过道边的小房间里,……使那些指望在这幢大楼里得到怜悯施舍的人望而却步”①,“……冲着那个家伙训斥一顿,甚至把他打个半死”。①对待亲人他也如此。他让老婆和女儿做繁重的家务活,“要是老婆因为没做好饭而挨揍,那是她自己的过错……”①叫嚷“我是一只红色的雄猫,我要把这些老鼠全都咬死”。①作为苔莱斯的帮凶和姘夫,他虐待基恩,将他囚禁并强迫他跪在地上做看门人的活。
还有诸如没有弄清真相的众人对驼背的殴打,“必须恢复死刑,应该把残疾人统统消灭掉,所有的罪犯都是残疾人”。①影射了大众疯狂、失去理智的状态。
作品中从个人到大众都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人物仿佛异化了。这里没有人间的暖意,只有地狱的冰冷。
3.社会的失衡
作品里的地下酒店——通往理想的天堂,是整个现实社会的缩影:“……一股可怕的雾气迎面冲来”,“这家酒店又乱又脏,……柜台后面有一堆花花绿绿的破衣服”,“一些奇特的女人在后面大声尖叫……以前,整个天堂层布满了金色的星星;现在,大多数星星都被烟雾熏灭了”,“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使这个世界充满了臭气”。①在这样的场景下,弥漫着见不得人的勾当。道德和法制在人们的脑海里已荡然无存,男盗女娼、诈骗杀人俨然成为家常便饭。
苔莱斯残忍地对待基恩,全然没有夫妻情分,普法夫虐待妻女,也没有亲人之情,亲人间尚且如此,普通民众之间就更是尔虞我诈,失去了人性的根本。在这样的社会里,主人公的头脑和世界、书和生活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仁爱的丧失导致的“非人化”是与小说诞生的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的。作品刻画的不仅仅是极端的人物,更是极端变形的社会。《迷惘》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西方价值观陨落的年代,在无情的岁月里,孤独隔绝和恐惧不断上升,死亡成为政治的“发动机”,大众受到强权政治的蛊惑,呈现出堕落、沉沦的状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和纳粹势力逐渐走上权力舞台,利用社会、经济的动荡和民众的贫困境况,用谋杀和恐怖来贯彻纳粹反人类的理论。卡内蒂笔下令人费解和怪异的画面正是分崩离析的时代的反映,刻画了作为人类文明代表——一位知识分子在失衡社会中的不适应和混沌感。基恩在不断的自我保护的尝试中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毁灭成为对失衡的社会的一种暗示和警告,也为衰落的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
失衡性的深层次意义
如果将《迷惘》中的人物理解为木偶,他们的荒诞和怪异从而得到解释:现实世界中他们就是物化的、没有灵魂的人。在蓝色的背景下,《迷惘》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木偶剧。
基恩犹如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丑:“嘴巴如同一个自动切割机的槽口”,①“他的整个生活就是由这些情况构成的一根不间断的链条”。①他站在旧梯子上找书的情景如同踩着高跷的木偶。在警察审讯的章节里,“这个轻如鸿毛的瘦高个子……又倒了下去”。①如舞台上的滑稽戏,警察“对基恩那身骨架还有所怀疑,亲自动手给他脱衣服……他解开纽扣,仔细地看着基恩的肋间,那里确实什么都没有……应该把这种人送到博物馆去,而不是送到警察值班室来”。①他的妻子苔莱斯,一个肥胖的女人,整个身子由“蓝裙、汗水和耳朵”组成,歪着耳朵,从舞台上掠过,吃惊地注视着木偶主人。另一个木偶小丑菲舍尔勒,“这个人说话的嘴长在哪里呢?……他没有脑门,没有耳朵,没有颈脖,没有身躯——这个人是由一个驼背、一个大鼻子和两只安详而伤感的黑眼睛组成的”①,“他先把鼻子在墙上擦擦干净,然后伸到腋窝下嗅了嗅”。①驼背犹如爱慕虚荣的花花公子,为自己装扮,“黑白相间的格子外套,一双崭新的黄皮鞋,黑礼帽,……”①联想到圣母玛利亚、耶稣、美男子阿波罗,小说中人物的设置极尽讽刺。尽管也有蓝色的装扮、对耶稣学说的深入研究、对美的追求,但三个人物仅仅是披上了外壳而已,本质上与纯洁、高尚、救世主的形象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失去了灵魂,成为无魂之躯。外号“红雄猫”的看门人,犹如动物登场:“‘胡说!’一个猛兽般的声音吼道。接着出现了两个拳头,随后一个满头红发的脑袋从门里伸出来。”①直到基恩的弟弟格奥尔格赶来,才使基恩的境遇得到改善。但是,格奥尔格认为,“我们所理解的理智,其实是一种误解。如果还有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疯子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①“他渐渐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演员。他十分善变的面部表情能够适应一天中各种变化着的情况。”①“他成了他们的一份子,和他们完全融为一体。”①他将疯子看为正常的精神状态,自我判断和独立的见解对他来说无关紧要,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的失衡。
小说通过这些喧闹、踉踉跄跄的人物展现,打破了传统以来寻根式探索人和世界关系的小说的写法,用胖、瘦、粗笨、扭曲的木偶外形来体现一个失去存在基础的世界。主人公在失衡的社会里的病态化和所经历的失败,实则是其生存基础的剥离。基恩和他弟弟格奥尔格的态度为失衡的社会做了注解:他们更迷信科学,前者禁锢在科学研究领域,后者“他们要认真研究病人的那些胡言乱语,对此做出科学的解释”①,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将身体和灵魂、自然和文化、人和环境、男性和女性割裂开来,脱离了人和物存在状态的自然统一原则,造成了失衡。
灵魂在这些木偶般的人物中已荡然无存,爱的缺失是这里人物的共性,也是《迷惘》最震撼人的地方。而西方近代史对科技的极度依赖、追逐滋长了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忽视了人在文明社会中的作用,成为这种危机的时代背景。小说对社会和时代剥茧抽丝般的分析,揭示了混乱和荒诞的本质,即人物生存平衡的被打破,美和自然的状态被破坏,进而呈现出丑陋的景象。
注释:
①[徳]埃利亚斯·卡内蒂:《迷惘》(望宁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②Johann Wolfgang Goethe: Zur Farbenlehre. Didaktischer Teil, Bd 13, Hamburger Ausgabe, hg. Von Erich Trunz, München 1982 : 498, 496.
马 蕾(1977— ),女,湖北沙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德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