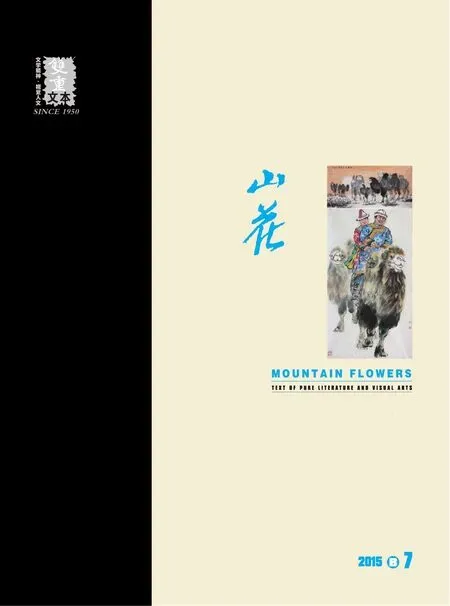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楚永娟
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楚永娟
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审美理念
日本书面文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全体的统一性,或者说“历史的一贯性”①。具体而言,文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理念不是以旧换新,而是旧中补新,持续发展。比如,短歌作为抒情诗的主要文学形式有超强的生命力,从八世纪的31音的短歌,到十七世纪以后俳句这一新的形式加以补充,二十世纪以来则常用长自由体诗型,直至今日短歌依然是日本抒情诗的主要形式之一。文学理念方面,上古时代的“真实”以其朴素性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的根本精神,进而演变为平安摄关时期的“物哀”、到古代后期,融入中世的“幽玄”、 “空寂”和“闲寂”、近世的“风流”(日语写作“粋”),成为日本不易的美学思想。明治以后直至近代,歌人依然重“哀”能作者求“幽玄”茶人尊“闲寂”艺人倾“粋”。 这些美的理念不是随着时代的终结而消失,而是被新的时代所吸收,与新思想并存,成为日本美学发展史的河床。
日本文化精神从萌芽初期,首先表现出以原始“万物有灵”的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 的朦胧意识。所谓“真实”, 既具有如实呈现的、写实的“实”,又蕴含着道德的、感情的“真”,是朴素的真实,原始的纯情,如童心般的境地。“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信仰上反映出来,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始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再经过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逐渐形成了“真实”的理念。这种重视真心和真诚的“真实”流贯于日本文学始终,成为日本美学思想的根底。
平安时期开始在“真实”意识中萌发“哀”的理念,逐渐演进为情趣化的“物哀”美学思想。记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所表达的对国家、民族、集团性质的“真实”感动,是对自然、神灵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 不是单纯个人的情趣,至《万叶集》后期,逐渐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情感,反映朴素的真情实意。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以反省自己为动因,表现自然的内观世界。紫式部以“真实”作为根底,深化了主体感情,创作的《源氏物语》被视作“物哀”文学的先驱,更新了上代的美学精神。这种“物哀”是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的喜怒哀乐诸相,是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的调和,涵有现实的理想化,成为当时美学理念的主流,又超出文学领域,影响到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规范。如日本人对大自然的钟爱如日本文学纤细、优雅的文风。平安时代中期,源于“真实”的“物哀”美学思想的完成,代表了纯粹的日本本土精神,确立了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
时至日本中世的镰仓时代,“物哀”融入了当时兴盛的禅宗的重悟性好闲寂的精神,当将带有神秘色彩的“悟”融为富有情趣的艺术来进行象征性表现时,便形成了这个时期美学的最高理念——“幽玄”。“幽玄”一词源于中国唐代骆宾王的“委性命兮幽玄”,其后包括佛法在内的一些文献典籍也用此词,以示幽微、玄妙之意。传到日本后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改变,日本最早见于平安时代《古今集》真名序中的歌学用语,当初被用作“超俗”“神秘”之意,以示和歌之风韵、雅趣。到了中世,被尊为新古今时代歌坛领袖的藤原俊成,起初把它当作超越“姿-词”的余情美,在此基础上,以藤原定家的和歌、心敬的连歌、世阿弥的能乐美学论为中心,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家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构建了中世的美学体系。“幽玄”开始成为日本文学精神后,它的内容有静寂-妖艳-优艳-平淡的变迁,与素材的写实相比,更重视抽象本质的把握和情调的折射,形式上重言外之意的余情、余韵,如同绘画中的生动气韵。和文学方面,和歌中所现的平淡与清新,军事物语中人生的虚无与哀怨,能乐中的情趣与幽邃,随笔中的平易与寂寥,都体现了佛禅的幽深、玄妙。这种余韵-余情-气韵生动是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方面,并渗透到日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本三弦音色单纯,但余韵悠长;舞姿舒缓简素,但富有张力,不乏流畅美。尤其是茶道,努力在狭小的茶室里,努力创造出一种枯淡、幽寂的氛围,使茶人充分享受‘无即是有,一即是多’的余情与幽韵”②,典型地体现了禅的精神与趣旨。幽玄扎根于“物哀”和佛教的无常观的土壤上,并与余情等因素逐渐融合成了以“幽玄”为中心的“空寂”美学理念,并将这种美学精神更深地引向“不易常住”的内面世界,乃至能乐的轻“词”重“心”,“以心传心”,深化“余情”的内面性,最后抽象为“空寂”的“无”的美学。
这种幽玄精神,与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的“闲寂”相通,是相似的情感象征,只是幽玄的情趣内容中有空寂-妖艳等的变化。而“闲寂”导出的哀婉的余情表现中蕴含着“余韵”“细腻”“轻妙”③,是“不易流行”。所谓“闲寂”是在中世以来的幽玄基调上,融入枯淡闲寂的情趣,经由西行、慈圆、宗祗的努力,终由芭蕉完成,树立了风雅、“闲寂”的蕉风,进入禅寂的意境。这种情调并非流于表面,而是作者基于实际体验的内心观照,所以即使华丽、美艳的题材也能渗入,将枯淡与柔美加以调和,达到虚实相生的余韵之境。这样,平安的“物哀”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以“真”“实”为基础,形成“哀”中蕴含“寂”,成为“空寂”与“闲寂”的美学思想底流。
日本人将茶道、花道都提升到一种艺道的高度,是因为日本人不仅满足于艺术性的追求,更因为他们将艺术视作与人生不可分割之物。茶道、花道之所以重礼仪、做法,是因为从严格的“型”和形式中可以象征性地体现本质的东西,寻找真的生命的精神,直观性与象征性相融合。这种经“型”来寻找白光般的纯粹,便是种“修行”,是悟“道”之心,成为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一面。将奔放的热情与才华融入“型”中进行锤炼,寻找内在的生命之光。他们相信即使有时重视机智的技巧主义,最终还要归于平淡无味的境地。“淡”便又成为一种重要的特质,不止于文学,也是日常生活中所要追求的境界。素雅的挂画、只插一两朵小花的精致花瓶都是一种平淡美,力求将七色的彩虹之光最终回归到白光,一切复杂的背后都有一种单纯美。“淡”不仅成为日常生活的规范,更是成为艺道批判的标准,成为中世以来艺术精神、艺术批判的中心精神。得道之人、达人的艺,都是无色无香但富有深度的艺,也可以说是悟透之后的老境之艺,归根结底是彻底的自然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境如同童心,只不过在心灵的成长方面一个是未谙世事前的单纯,一个是经历人生后的淡然。比如有“东有芭蕉,西有鬼贯”之称的上岛鬼贯(1661—1738)的俳句“庭前盛开白山茶”,根据欣赏的人心态不同,便有不同的韵味。童心之人看来只是一朵白山茶花而已,老境之人看来盛开的山茶花之白,内涵了一切缤纷之色,而且在单纯的白中觅到了人生的究竟。这种淡是真实的回归,素朴的“轻妙”(軽み,俳谐用语,松尾芭蕉晚年追求的以平淡美为基调的句式、句法和艺术境界)。 “淡”去了深重,附之情趣的东西便成为轻妙。
近代的日本社会,引入了西方“文学”概念,受到西方注重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日本传统的审美理念依然是日本文学发展的底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便是在传承日本古典“物哀”的美学传统上,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创造了哀怨、余情的文学,充满了轻淡的感伤和不尽的韵味。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正是既汲取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想象、象征、幽玄等营养,又积极吸收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化,才得以构建兼具日本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世界。当代人气作家村上春树文学的基调也依然是孤独与无奈,文字独具古典韵味,轻畅又寓意颇深。如前文所示,以直观的“真实”为根基,心物相接时的“物哀”、“幽玄”的空寂、闲寂、重“道”“型”的精神、爱“淡”“轻”的心境等,有一条纵观日本文学的持续主线,沿着这些精神的衍变轨迹可以探寻日本文学的精神史。接下来探究与之相对的日本国文学所隐含的民族精神。
隐含的民族精神
原始的“真实”美意识的背后,是日本人敬神爱国的精神。基于日本国土建成的事实与理想,上古的人们相信神建国土、自然、人类,通过诸神的交涉,最终由天照大神统一国家,天孙降临最终现实的国土成立,神皇作为神的后裔永久地继承、建设国家。这种国家的信念、民族的自觉贯穿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祝词、宣命、《万叶集》,经由《神皇正统记》和近世的国学精神发展起来。《古事记》《日本书纪》明确编纂的方针是“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以及“消伪定实,言意并朴”, 《万叶集》以天皇御制歌为开端,颂“君王是神明”的歌甚多。其所宣扬的是神皇意识和国家精神,其“真实”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尊皇与爱国、树立天皇和英雄的形象上,即以神皇道义为根本。天皇作为现世神,是国家最高的神格,皇室成为国家、国民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成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和源泉,不仅渗透到文学中,还体现在当前的集团主义民族精神中。
与这种敬神爱国精神相对,武士道则是支撑武士生活的精神,并成为中世的国民理想。重精神轻肉体的思想是武士道精神的源头,对经常直面战场的武士来说,肉体生命随时可能终结,因此便要重视精神的生命。战场上肉体的痛苦是为了名声而受,值得欣慰,不能有卑怯的有损声誉之事。对声誉的珍视,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名声,而且关系到家族的声誉,以祖先的功业为荣,以忠勇为耀。进一步延伸到主从关系中,对主人极尽效忠,甘愿舍弃生命。中世的军纪物语和近世的戏曲小说中洋溢着这种对主从关系的颂歌,与敬神爱国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并曾经升华为国民道德。当义理与人情发生冲突,常常需要牺牲人情,抑制小我,成就大我的人情。因此,虽然有理性的一面,但是不仅仅是“理”,而是被称为更高感情的“义”所统一。“义理”便成为表达日本道德内容最恰当的词,是舍己为家、为主、为君、为国的精神。近世一般道德场合的“义理”尽管有些许差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重精神与名声,轻肉体与物质,通过为主君效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所以为《太平记》中楠木正成的忠诚、假名手本《忠臣藏》大石良雄的精神所感动,这与读完《古事记》的感动是相通的,因为是日本民族的独特精神特质,与诸文学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日本精神和文学精神的核心。
忠君爱国的精神以传统的“真实”为根基具体呈现,与武士道的尊“型”重“道”的精神相容,表现出艺术之美。诸种审美意识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与渗透。单独考虑诸如“淡”其意义可能难以明了,但是经过“物哀”与“幽玄”再考虑“真实”“真诚”,就会发现其无限的韵味与深度。内在精神与审美意识相融合,共同贯穿整个日本文学。虽然由于具体的时代特征和生活环境,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由同一精神所统一,伴随着民族生活成长。从国土成立之初便被深刻在日本民族内心深处的纯日本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呈现,但是不变的本质贯穿在其发展历程中,多样性与统一性,变化与持续微妙并存。探究日本文学的本质,有必要意识到这种不变的民族的精神,并结合民族成长的姿态与文学的审美特征来理解。
注释:
①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上)》,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8、10页。笔者译。
②高文汉:《试析日本古代文学的特质》,《日本学刊》2002年第5 期,第121页。
③皆为蕉风俳谐的理念。“しおり”是作者心里的伤感自然表现在诗句的余韵中;“ほそみ”是种从内在深度中体现出的细腻的情趣;“軽み”是芭蕉晚年追求的以平淡美为基调的句式、句法和艺术境界。
本文为烟台大学青年基金“日本平安日记文学的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YZ01。
楚永娟(1982— ),女,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烟台大学日语系教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