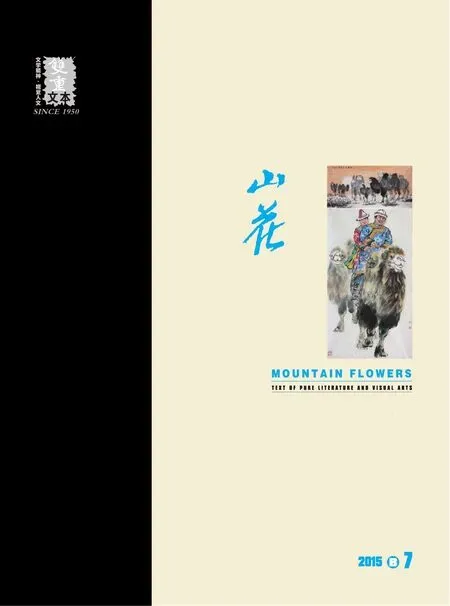村庄的轮回
李集彬
小小的村落
以前村庄对面山坡有一个小村落,只有三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和我们的村庄隔溪相望。如果那个村落还存在,该是世界上最小的村落,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那三户人家都姓詹——这个姓四乡八里极少,不知道从哪迁来的,又为什么居住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来历不明,去向倒是很清楚:一户搬到外面去了,两户迁入了我们村,说是为了躲避土匪袭扰。这是后来奶奶告诉我的。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现在一定还住在那里。
那个地方叫赤涂。我们家有一块地在那里,是旱地,赤土质,只能种地瓜和花生,有时种小麦。由于有庄稼地在那里,经常要到那里去:没有什么特别,坡上几块旱地,溪边几丘稻田,几棵龙眼树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几截矮土墙,已看不出当初的样子。一开始到那里去,见到那几截矮土墙,心里想,也许是什么临时房屋吧,比如生产队的仓库。没想到是一个村落。
一个村庄为什么会消失?
试想,月黑风高之夜,有匪来袭,隔着溪岸鸣锣呼救,土匪早已翻山越岭而去。这样的生活自然难以长期延续下去,只好转移投奔他处。况且几户人家居住在那样空旷的野地里,空洞而寂寞。我想,其实没有土匪袭扰,他们早晚也要离开那里:那个地方太寂寞。没有人能够耐得住长久的寂寞。
一个村庄,由于其小,经不起冲击,很快消失,人烟散尽,只留下一个躯壳、一段残垣,然后连这些也消失了,一切烟尘、声音、气息全都沉淀消散,一个村庄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里。有一天,老一辈人都消失了,这个村庄再无人提起,后人自然也就无从知道了。
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村庄,存在、迁徙、消逝,而在某一个地方又有新的村庄建立:一部村庄的历史就这样轮回。这之中充满沧桑和神秘。村庄里,人们在建房子挖地基的时候经常发现瓦砾、陶器碎片的大片沉积,可见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一片土地曾经有人居住过。这很正常,一个新的村庄总是建立在一个旧的村庄之上,一层层堆叠,形成村庄的年轮。只是有一点不清楚:不知我们所居住的村庄,建立在哪个村庄之上?
老井的秘密
井,我曾经无数次提起井。我之所以提起井,并非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我在一篇叫《井》的文章里说到的因为水,而是我想凭借它进入一座老宅——我们祖先已经消失了很久的房屋。它是进入这一座老宅的唯一通道。
那一座老宅是否确实存在过?不知道。只听祖母讲过:很大。小学,包括现在我们所居住的房子,都在老宅范围内。“当时因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村里人想见到李家的媳妇都很难。”不知为什么,说到后来,祖母又补上这么一句。我想,也许祖母一辈子都梦想着能有那样的生活吧。可惜她来得太迟,她嫁到李家时,那个庞大的家族早已败落,大部分人四处飘泊,房屋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院落,也已破败不堪了。祖母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充满着向往。其实她所向往的只是一种优雅的生存状态。在我的印象里,祖母女红不错,缝衣、刺绣都有一手。她还会剪纸,我曾经在她的小藤箱子里见到夹在册页里漂亮的剪纸,大概是喜鹊闹梅这一类图案。据说祖母小时候没有做过重活,嫁过来我们家之后也很少到地里去。祖母一辈子待在家里,即便后来到小学校帮厨,也没有离开李家老宅范围内。这是一件很值得琢磨的事。
那是祖母描画的老宅。祖母为了让我相信,提出证据:“那口井,是我们李家老宅里的水井。”一口井没有什么稀奇,上面没有文字,村里的老井不止这一口。“还有旗杆石,夹旗杆用的旗杆石。”她说。这就有分量了。要知道,在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才可以树旗杆,据说至少得七品。“我们家屋后小水沟上面用作桥梁的那一块石板。”她说。我一惊:一下雨,我就要蹲在那块石板上面玩水。石板上有一个圆形的花纹,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祖先叫李九官。”祖母说。我记住这一个名字。后来我在张家瑜先生那篇叫做《千年古县有遗迹》的文章里见到这一个名字:“古县李姓,系宋代富豪李九官三族亲后裔。”一切对上来了,我欣喜异常:那么,这一座老宅是存在的。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一口老井展开想象:
那是多大一座宅院?该有小学校操场一般大小。至于规模,依据村庄现存最大的老宅进行想象,我想,它该比它大,比它更气派。是的,它应该这样。我们房屋周围至今散落着几十颗石柱础。一颗石柱础代表一根木柱子,四五十颗石柱础代表四五十根木柱子,那该是多大一座宅院?!还有那块叫做潭子的菜地,也应在老宅范围里。也许是水塘,里面是否种有荷花?村庄最大的那座老宅里种有香蕉——我们家老宅里也有,就在原先祖父祖母居住的那一落院子里,可它绝对没有荷塘。这样想着,我满意地笑起来了。还有那块旗杆石,应该立在大门左侧。这样,祖先老宅的轮廓在我的想象里完整起来了。然而还是有点虚,我得一点点把它勾画具体了。只有零星构件,其余的呢?石砛倒是有,好几条,磨得光滑,搁在房前屋后,支在那里,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到那里去,躺在上面,沁凉沁凉的。屋瓦,门窗,装饰,家具,这些东西呢?我迷惘起来了。
一座老宅依然神秘。旗杆石是望不出什么来的。那一个圆形的花纹,里面一个神秘图案,也像一个谜,我只好去望那口井了。伏在井沿,井水幽深,一眼望不到底。据说有些水井里面有地洞,就在井壁里,通往远处去。我是受过这一方面启蒙的,比如地道战这一类故事。也许这口井里也有地洞,只是被井水淹没。这样想着,它变得更加神秘。我甚至想下到井里去探个究竟,只是不会凫水,这一个想法只好搁置。
因为穿越任何东西:学校、菜地、石柱础、石砛,包括旗杆石,都无法进入到我们祖先的那一个庞大宅院里,最后只剩下这一口井了。我想,这一口老井里一定有一个神秘通道,通往那座老宅里。一千多年过去,老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包括留下来的这些石质构件,最终也要被砌进墙里,埋入地下,只有那口井依然鲜活,澄澈透明,叮咚叮咚响着水声。也许它还要活下去,几百年,上千年。只是不知道若干年后,我们家族子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像我一样去留意这一口井,发现那一个秘密通道,像我这样去缅怀一个家族的光荣历史?
谁的庄稼地
这是谁的庄稼地?虫子们的庄稼地?鸟儿们的庄稼地?野猪们的庄稼地?它们一直和我们争夺这一片庄稼地。现在我们放弃了,成为它们的了。
我们流了许多汗,翻耕土地,种下庄稼。鸟儿们飞来,站在旁近相思树丛上叽喳喳叫,似乎在说,这些庄稼是我们的。你赶它,它飞走。趁你不注意,它又飞来,叼起一颗肥大的麦穗飞走。地瓜收上来,地荒着的时候,它衔一粒小麦从这里飞过,一不小心麦粒从嘴里脱落,掉落下来,它认定它是落在这一丘麦田里。那是一颗光滑饱满的麦粒,它想,一定长成一株茁壮黝黑的麦苗,结出一坨沉甸甸的麦穗。虫子们一直在这一片庄稼地里,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倒是人,来这里,撒下种子,施过肥,拍拍屁股走了。最多从这里路过,站在田埂上望一眼。虫子们记得很清楚,它们除了播种的时候不得不上岸,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一片土地。在它们心里,这是它们的家园呢。野猪自然更加霸道,在它们看来,山下这一片庄稼地哪一丘不是它们的?天一黑,它们就可以走进任何一丘麦田,吃个饱,在里面撒欢,打滚。
那时,村庄前后左右都被庄稼填满了。这一片山地里,除了房屋、树木、溪流和池塘,便是庄稼。庄稼把所有能站立的地方全都站满了,甚至挤掉乱石、野草和荒滩,整齐、优雅地在风中站立。春天时候,田园里多么热闹:小麦互相簇拥着,野花站在它们的脚下,一阵风来,一起唱歌,一起欢笑。鸟儿们飞来,站在相思树丛上,议论着:多好的天气!是啊,小麦结穗了,那么饱满,它们的心胸早已被芳香填满。虫子们在森林一般的麦丛里唱歌,跳舞,弹琴,从早晨到傍晚。这样的情景,鸟儿们一定记得。
野草荣了枯,枯了荣,虫子们换过一批又一批,风刮过来又刮过去,找不到以前的影子:这还是以前的庄稼地吗?
那些我们的土地,每一丘田园,它的结构和形状,土壤的颜色和肥瘠,甚至它的芳香和气息,岸边种什么树,长哪一种草,开什么花,闭上眼睛我们都能想起来。我还记得那些庄稼:稻谷割得把镰刀割钝了都割不完,地瓜大起来能把地垄胀裂,花生有小番薯一般大小。这一些,总和庄稼地里其他事物一起把我的记忆填满。
我们成功地逃离了土地,现在,这些土地全都荒芜了,野草、虫子、鸟儿、野猪把它占据。现在这些庄稼地已经不是我们的庄稼地,而是它们的庄稼地。
不老的池塘
如果说池塘是一轮明月,那么这个村庄环拥着那一口池塘便有抱月之势。如果说池塘是一面镜子,那么它便照亮整个村庄。
水,一个村庄是离不开水的,一个没有水的村庄便没有了泉和源,自然要枯死。一个没有水的村庄,只有金木土,是呆滞的,便也缺少灵性。水可以荡涤污垢,水可以洗亮眼睛,水可以照亮内心。
在我们村庄里,没有池塘的叫法,所有的池塘都叫潭:大潭,潭子。不知有多少口,分布在村庄和田野。村庄潭子多,星罗棋布。村庄大潭少,且是唯一。如果说潭子是星星,众多的潭子围绕着一口大潭便有众星拱月之势。我想,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我们叫它大潭,它是村庄的明月,就在村庄前面正中间那个位置,后面是一座三进七开间的古大厝。我想,如果纵横交错的小巷是村庄的经纬,那么这一口大潭便是村庄含着的一颗明珠了。穿行小巷,是劳作,是纵情的乐音激越;亲近大潭,是游戏,是闲散的余音袅袅:它们都是村庄生活的一部分。
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人,没有人不记得这一口潭。
炎热午后,狗吞吐着舌头,有朋友招你:走,大潭里洗澡去。那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到潭边,脱去衣服,噗通一声跳进水里,水凉得你嗷嗷叫,浸到水里再不肯起来。大人来喊,你潜进水里。水里是憋不久的,摘一个芋叶顶在头上,浮出水面。结果还是被大人看出来。“叫你藏!”一个土坷垃扔过来。你不得不乖乖上岸,跟他回去。村里孩子们的凫水技术大多是在这潭里练出来的。
从这个村子里嫁出去的姑娘,不会忘记这一口潭。早晨浣衣,傍晚洗菜,作为女人的一切本领都从这潭边得到启蒙。若干年后,嫁作他人妇,在他乡的井沿,一边揉洗着衣服——或者命好些,嫁到城里去,在逼仄的厨房里洗菜,一边就要想起光滑如镜的大潭:潭水莹莹如碧玉,掬一把泼到脸上,沁凉沁凉的;又掬一把,吸一口,甜丝丝的……想起好久没回娘家了,那时候,恨不得马上回到那个叫古县的村庄去。
这些村里长大的男子,长年在水里浸泡,性格开朗、坦荡。那些村里长大的女子,经过潭水的浸润,底子里纯洁和质朴。
池塘里的水是活水。据说潭底有一个很大的泉眼。每次池塘清淤,东边一架抽水机,西边一架抽水机,一起往外抽水,怎么抽也抽不干,潭底的水汩汩往外冒。我想,这也许是它为什么如此光洁、如此透亮的原因吧。
水面光洁如新镜,一个人俯在水面上,想撒谎都很难——你总不能欺骗自己吧。身体浸泡在水里,把身上一切污垢都洗去,灵魂仿佛也得到了净化。一个人在那样干净的水里,就连说粗话都很难,更不用说想到其他什么事情上去了。这样的池塘,便是一面能够照亮灵魂的镜子。
我想,村庄是需要一面镜子的,一面能够照亮灵魂的镜子。
吹过来吹过去的风
太阳沿着轨道行走,自东向西,按时起落,不敢越雷池半步。风最顽皮了,忽起忽落,忽行忽止,让你摸不着头脑。
风不来,云不来,雨不来,土地烤得龟裂,庄稼快要焦枯。太阳脸白白的有些不好意思,收敛了光亮,站到更高一些的地方去。
风赶着白云去了,就像赶着一群白色的绵羊。风赶着乌云来了,就像赶着一群黑色的山羊。风站住,连影子也看不到。风一动,就显出它的形迹来了。
风跑到地面上来,一头扎进村庄里,沿着村道,呼啦一声跑过去,转一圈,又转一圈。也许觉得好玩,潜伏下来。忽然卷起一阵尘土,打个旋,一个潮头往树上打去,树叶波浪一般起伏起来。在树梢站立一会儿,看看花圃里一株玫瑰开得正招摇,飞过去,从哪里咯吱一下,笑得玫瑰腰肢乱颤。风不想再和它纠缠,呼一声蹿起,耸立起来,见一个农人戴着斗笠匆忙前行,悄无声息从后面追过去,掀起斗笠,甩落地上,把它当作圈圈滚走很远。你去追,它走了,一边顽皮笑着,一边奔向田野,田野里的稻谷无止尽地起伏起来。
风纵身在旷野里奔跑,兴致正浓,云聚拢了,堆叠成峰,闷雷出其不意炸响,没有提防,措手不及,它吓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恼怒起来,骤然而起,直上九霄,把那一堆乌云缓缓推走。
地上、天上都玩腻了,风跑到海上去玩耍。无边无际的海洋,不似森林,可以和野花逗乐,可以和松鼠追逐,可以和麋鹿赛跑。广漠无边的海洋,就像一望无际的沙漠,太寂寞。顽皮惯了的风,推着波浪起伏,终究无聊,按捺不住,焦躁起来,聚拢一起,环环抱成一团,飞速转动起来,就像快速转动的齿轮,锯断桅杆,掀翻帆船。上了岸,变成一个巨大的熨斗,把庄稼熨平。席卷村庄,噼里啪啦,在街巷里穿行,把路人强行塞进屋里,关上门,关上窗,折断树木,掀翻屋檐。
风静了村庄便静了,风动了村庄便动了。当村庄沉默下来的时候,风就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