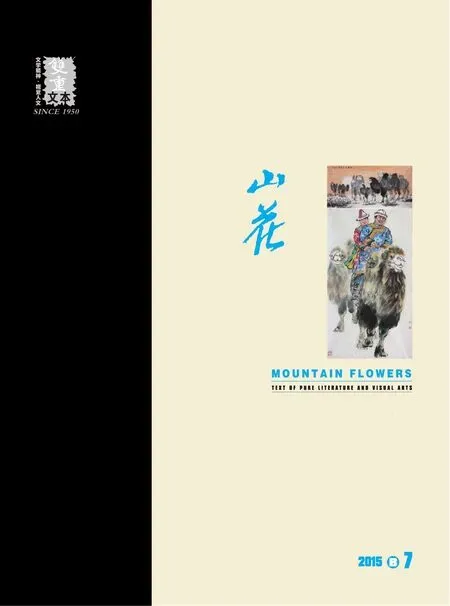保持对“无限”的热爱
钱磊+郑瞳
郑 瞳:前一阵,我刚收到你寄来的诗集《邮差笔记》,我说请放心,尽管很艰难,我还是会硬着头皮把它读完的。(笑)当然,这是玩笑话。这本集子里面收录的都是你早些时候的诗作,对于一位80后诗人,我不知道用“早期”这个词语,是不是会显得不太恰当,所以我说这些是“早些时候”的诗作。那我们就先来说说你最早的诗作,你还记得你写过的第一首诗吗?是什么让你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否让你觉得自己成了诗人?你会不会把这首诗选入你的诗集?
钱 磊:出版诗集似乎是一名诗歌写作者必然要做的事,我也不能免俗。这本集子收录的“早些时候”的诗作,确切地说是2013年以前的,算是对一个阶段的交代。写下第一首诗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也是刚接触到现代诗,当时觉得很轻松,分行的文字而已,恰好学校里举行关于“五四”运动的演讲比赛,就写了,大约十多行,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当时写的状态应该是很兴奋,尽管这首诗不能让我觉得就此成为诗人,但成为诗人的想法或许就是那时候升腾起来的。当然,这首诗不可能会收录其中,因为现在我也找不到了。就好像你看到了燃起的火焰,但却不一定会再去为火种感怀。
郑 瞳:你的老家在贵州西部的乡村,我看到过你发在微信上的照片,那里风景很不错。乡村生活给你带来什么?你是在这里开始你的文学启蒙的吗?能回忆一下你与诗歌的最初遭遇吗?
钱 磊:在别人的一些文章里,有时候会看到描述幼时乡村生活的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欺骗。在贵州西部,尤其是乡村,好风景意味着贫瘠与落后。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记忆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生活物质而奔波以及争吵,邻里关系人情世故更是将人性里的恶赤裸裸地展现在生活里,我常常想逃离,到乡村以外的世界,过与众不同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富人的孩子有自己的圈子,穷人孩子也有自己的伙伴和准则,这些东西造就了我早些时候敏感与内向的性格。
庆幸的是,我父亲于七十年代初期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家里除了农具,也有一些书籍,让我打发了幼年无聊的时光,我更愿意称之为是阅读启蒙,有了这样的启蒙,才会走上热爱文学的路。在这条路上,遭遇诗歌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相信在同龄人中,那时候读徐志摩、读海子、读顾城是一种时尚,除了阅读资源匮乏之外,或许还与当时的教育引导有关。在课本上读到现代诗时,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迷住了我,不能自拔。现在想来,确实有些可笑。
郑 瞳:后来你最终如愿离开了乡村,来到城市。现在你过着游刃有余的城市生活,你的诗歌更多是来源于乡村,还是来源于城市?
钱 磊:没有什么生活会是游刃有余的吧,尤其是城市生活,物欲纷繁以及生存压力下的各种困境,消耗着我们对生活的期许,我们只能是被它所裹挟。当然,每一种生活都有自己的明亮和缺陷,年轻一代摒弃乡村向往城市,也在情理之中。城市缔造的欢愉,更具诱惑力,我们在现实娱乐的景象下,逐渐忽略了这时代背后的粗鄙与暴烈,对于生活最初的目的和追求,一点点陷落,背道而驰。诗歌不可能拯救得了这一切,无论它来源于什么样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反感乡村赞美诗的,我们也没有去赞美她的权利,乡村的苦楚拒绝任何人的赞美。所以在诗歌写作上,我尽力避免乡村的生活入诗,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得取材于城市,在心理上我对城市生活也没有多少好感,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和讽刺,我想,我的诗歌更多的是用来平衡这两者在我生活轨迹里的冲突,它也源于这样的冲突,这种平衡不是游刃有余,而是一种无奈,在这宏大空间准则下的一种放逐。
郑 瞳:这些年,你几乎完成了从诗歌爱好者到80后代表诗人的飞跃。成为诗人,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钱 磊:是不是80后代表诗人这个不重要,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被代表。回归到诗歌,谁又愿意被代表?更何况诗歌至少包含了一颗自由的雄心。你所说的飞跃,倒是让我增添了写作的信心。成为一名诗人,是早些年的一个梦想,写到现在,反而觉得是不是诗人已经无所谓了。
在这些年的写作中,从对语言的痴迷,到逐渐清晰地对自己写作的反思,这意味着首先在对诗歌的某种认知心理上,我已经成熟了。我想,一个清醒和成熟的诗人,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去突破自己的写作界限?如何去触摸自我所处当下的困顿与焦躁?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当谈论一名诗人的时候,我更愿意谈到他所贡献出来的新鲜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悲愤、绝望、伦理道德,此时我们尽可能地省略诗中的修辞和技巧,而是去体会他的诗中说出了的我们共同的困境和羞耻。他仿佛是皇帝新装游行队伍中,那个无畏的小孩,喊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这秘密恰好是常识。
郑 瞳:让我们回到你的诗集《邮差笔记》,介绍一下这本集子吧。
钱 磊:诗集收录了我2004年至2013年期间的诗歌,由青春期至少年老成,也是我的写作从习作(模仿)到阅读(自省)的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诗歌中,拼凑和嫁接的痕迹成了硬伤,到如今,只好原谅自己。我以为那是一种天赋和灵气,使我走进了诗歌的殿堂,并坚持到现在。从选稿到成书,我删掉了全部诗歌的三分之一左右(其实还可以再精简),我看到了诸多的繁芜和虚蹈,这不是我想要的诗歌。
郑 瞳:现在你开始写作“简史”系列,这或许会是你下一本诗集的主题。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无限”的题目充满了兴趣?
钱 磊:“简史”系列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写的,当时也没什么规划,不知道要写到哪一步,最初是写《哑剧简史》,也难逃早期诗歌的毛病。而在此之前,我自己的写作遇到了瓶颈,如何突破固有的繁芜语言的滥用以及毫无节制的修辞惯性,成了我要思考的问题。而“简史”入题,也是我写作个人化的一种调整,一种实验,也是走出自我写作改变的第一步。“简史”让我确立了改变的方向,从史实的解构到现实生活的书写等等,大千万象,确实可以做到“无限”。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把之前的一种娱乐写作心态收紧了,不由得变得严肃起来。有时我在放大时空中的人与事,或把自己置入其中,或做一名旁观者,在这样的游离之间,解构也好,戏谑也罢,把自己的写作推向了纵深。在这个过程中,我享受到写作的另一种乐趣,对自身的挖掘以及对现实的关注更敏感,更低沉。在写作题材上也不断地尝试,包括一些现实事件、话题的关注以及个体尊严之类的入诗,丰富了写作的范畴。我想只有保持对“无限”的热爱,与所遭遇的一切较劲,才会使写作越走越远。
郑 瞳:很多人都认为“简史”系列标志着你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觉得是这样吗?这个系列你还打算继续下去吗?你是否会为自己的写作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
钱 磊:我不否认“简史”系列的写作让我收获了很多新的东西,对自己的写作系统化有了更高的要求。青春时期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如何使自己成熟,在每个阶段都能有所改变,保持写作的创造力,这比当一名诗人更重要。“简史”系列的创作,在语言、抒情、修辞、结构等方面做了诸多的尝试,我把阅读引发的思考,日常的是非,甚至是职业习惯杂糅在一起,凸显了写作上的生活痕迹,使自己更贴近于诗,而不是早些时候写作的滥抒情,或者说是凭灵性去写。这个阶段,我在诗中感受到了一种脾气,或者说,我在自己诗中注入了一种力量感。通过这样的力量感,去遮蔽其他的缺陷。我承认其实这是一种小策略和小野心。写作是一项持久的事,走得越远,越不相信什么天才、灵感之类的言说。“简史”系列写了几十首,其中《中国病人简史》是长诗,突破了我以往的禁忌,也差不多是时候停下了。至于以后的写作,随便吧,谁知道以后会经历些什么,反正还会在生活的大道上磨损掉更多的东西,尤其是激情和理想,肯定是最先湮灭的。当然,有写作规划是一件正确的事,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为人生写出一首正确的诗。
郑 瞳:你认为一首好诗是什么样的?你写出过这样的诗吗?谈谈你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吧。
钱 磊:记得以前和赵卫峰老师访谈时,他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一首好诗的样子应该是有语言,有思想,节奏合理,即语言、思想、节奏的有效统一,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显得粗鄙且无意义。其实关于好诗的标准,所有的争论应该都是无效的。一首好诗,它的基础源于诗人日常的修炼,自我辨析,情绪的积累以及生命过程里无数的郁结等等,一旦写出,我们能看到它隐喻背后清晰的指向,这必将会给我们呈现出一种丰盈的面目,能从中体验到一种普遍的沉吟和震撼,悲戚与欢欣。
我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诗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吧,就算有满意的作品,在同道面前,都会找各种借口挑剔,不愿意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出现在现阶段,而应该是出现在未来。我就是这样的,最多说是相对满意。好吧,那就谈谈我的“简史”系列中,相对满意的《白虎堂虚构简史》,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其实很简单,看新版的《水浒传》,我突然想起这样一个古代的权力机构,它有一套严格的登记审查系统,让人惶恐,这是它本身的威严散发出的震慑。有一段时间,我会常常在想象中凝视它,试图以一种冷静的审判来揣度其中暗涌的旋涡,然而这一切只是徒劳。我感知到了一种书生百无一用的无力,于是我写下了“进入白虎堂之前/你一定不/曾为死亡购买了门票”, 这种无力感一下子变得如此真实,当写到“你屡次怀疑自己患有小人之心/不然白虎堂的老虎/为何不对你显露一次真身”时,一切豁然明亮,剩下的部分,就交给读者吧。
郑 瞳:我曾经说你的诗作具备“藤蔓”的气质,它似乎呈现出一种发散和放射的状态,而且,和“藤蔓”极其相似,它具有一种缠绕的属性。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你的诗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形态?
钱 磊:差不多如你所说吧,尤其是早些时候的诗歌,这样的属性非常明显。我当作是诗歌语言的练习,由这样的修辞惯性,繁衍分枝,任其内在的逻辑推动诗歌的行进。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冒险的,设置了太多的阅读障碍,让人难以进入。在后来的“简史”写作中,我力图将这些障碍放开,在指向上变得清晰,在叙述上不再那么突兀,通过策略的调整,让语言释放出更明确的信息,让诗歌的空间松弛有度,富有弹性和张力。唯一的缺憾是,我的诗歌语言在之前的风格上,延续的痕迹依然还是很明显的,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我的诗歌特质。至于对自己诗歌呈现出来的气质和形态,我说不清,这个问题就交给你吧,反正你已经说出了“藤蔓”的气质,不妨再说一次。
郑 瞳:贵州80后,甚至90后,都不乏优秀诗人,你们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身在其中的你,如何评价贵州的青年诗人们?你们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你是否了解外界青年诗人们的写作?
钱 磊:贵州80后诗人,人数众多,诗歌的整体形态丰富各异。在全国,我认为已属优秀,但因地域因素以及本土的不自信,导致在一定的时期,外界对贵州年轻一代的诗歌没有更深入的认知。随着《山花》《诗歌杂志》等刊物的推荐,以及网络传播途径的多样与开放,这样的窘境,我相信会有所改变。
在现行的群体中,写作状态保持较好的冰木草,语言节制,精短的抒情,衔接了现实与诗性之间的矛盾;罗逢春长期致力于古诗的“翻译”,游走于书卷之中,吸纳当下,探究出现代诗的另一种可能性;罗霄山的厚重与深思,暗藏着尖锐。除此外,优秀的还有很多,比如木郎、黄光道、杨长江、顾潇,以及外地求学的方李靖等等,加之90后的突起,尤其是蒋在,诗歌与小说齐头并进,获得了外界的不少赞誉,这些都使贵州年轻一代的诗歌,以一种惊艳的方式,走向全国。
郑 瞳:我知道你周围有许多年轻的诗人朋友,作为一个群体,你们是否经常会有一些关于创作或思想的交流?他们的存在,是否促进了你的写作?或者这么说,你们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彼此的写作?
钱 磊:当然会有交流与探讨,我们会分享一本书或一首诗,也正基于共同的乐趣,在本省,我们一群人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走火》。在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下,有乐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汉语现代诗歌远不如唐诗宋词悠久,它的影响力仍然弱小,但同时却也生机盎然,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可能,吸引着我们。作为写作者的其中一员,年轻的诗人朋友交流起来更随意,更生动,这样的交流且不谈是否能有效地促进写作,它深一层的有效意义应该是在于激活了每个参与个体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不断寻找一种适宜的表达,来对抗真实的自己。
郑 瞳:所有的写作,大概都离不开阅读。介绍一下你的阅读,说说你在阅读中受到的影响。
钱 磊:阅读比较杂,早些时候读传统的文学,后来读哲学的,比如尼采,宗教的也读,外国的小说也读一些。这些阅读中,传统文学影响了我的诗歌语言,尤其是唐诗宋词,哲学影响了我的诗歌逻辑,在诗歌中,这些印记很明显。现在读得多的是诗集,国内外的都读,随笔也读。生活节奏影响,没精力读更长的了。国内的很多诗集很优秀,但胃口不对,温情的小清新,有取媚之嫌,我更愿意读一些有缺憾的,有脾气的东西。但愿在写作中,受到这种脾气的影响,让我的写作不会主动去回避某些问题,而是变得真诚和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