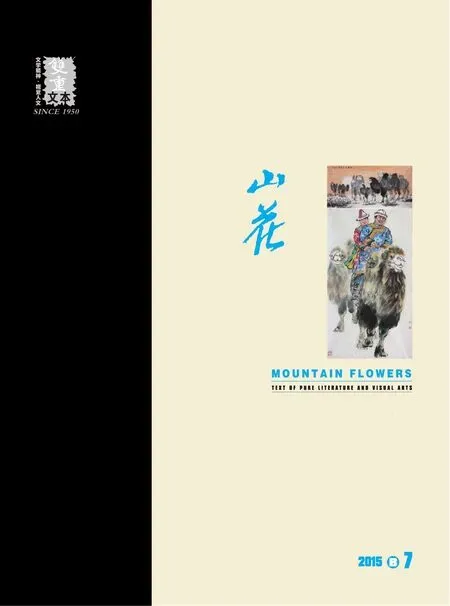从陌生到无限简史
吴萍萍
作为贵州80后代表诗人之一,钱磊并没有赶上贵州80后诗歌的第一个浪潮。当罗树、冰木草、熊焱、刘脏、汤成伟等人在2000年前后进入诗坛的时候,钱磊还没有正式走到诗歌这条道路上。十年后,罗树等人或偶露峥嵘,或销声匿迹,大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熊焱因为留居成都,也往往被归入四川的诗人群体之中,只有冰木草等极少数人依旧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创作状态。但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贵州80后诗歌的第二个浪潮悄然涌动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比以往更大的声势。稳健高产的冰木草、沉静博学的罗逢春、生猛直接的木郎、任性奔放的顾潇、厚重的罗霄山、忧郁的杨长江,以及庞非、冉小江、朵孩、非飞马……各具个性的诗人们令“贵州80后”这个抽象的概念得以生动起来。
钱磊正是这“生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位生于1985年的诗人,大约在2003年开始了自觉的诗歌写作,偶尔发表在一些报刊之上,这种平稳的状态持续到2009年。那一年,《山花》杂志发表了钱磊的诗作,并在之后的一两年内,数度作为重点诗人推出。可以说,当时刊物的推介力度之大,是许多名家都未曾享受过的待遇,却交付给了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强力的推介,必会引来更多的关注,因此,即便我们说,2010年左右,钱磊在诗坛横空出世,那也是不为过的。
读钱磊的诗歌,其实不能算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许多读者而言,这样的差使简直可以说是强人所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们总是喜欢生活在熟悉的气息之中,用经验来指导自己的一举一动,明确自己的去向。换句话说,人们对已知的世界满是眷恋,对未知的一切却往往充满敬畏之情。尽管人们也有着猎奇的天性,但从根本上来说,那实际上也离不开经验的支撑——经验一旦无效,人们就很容易茫然无措了,毕竟只有熟悉的,才意味着安全。不光是生活,在阅读中,人们也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怀旧的状态之中——如果在熟悉的表述中,读到几个新鲜的修辞,那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但是,如果你的阅读对象全然在你以往获得的经验之外,那种偏离就很可能带来迷失感和无力感。到了这个份上,人们就会选择把书本扔到一边去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诗人则理应偏爱陌生,假如生活被设置成为一个固定的框架,他们就要去追寻框架之外的东西;而如果语言表达已被固定为某种特定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就成了他们必须逃离的牢笼。
钱磊显然就是这样的诗人。
从一开始,钱磊就展现了他对语言和修辞的独特理解。他钟爱纷繁复杂的语句,甚至到了影响阅读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或许我们不能说他不渴望被认同,但至少可以这样说,他更加渴望展现某种不同。既然追求的是“不同”,那他自然要进入“陌生”。我们说“陌生化”,一般是摆脱那些司空见惯的情感和表述模式,代之以新奇感和惊异感,使人在猝不及防中被卷入到了作品的情绪里面。但“陌生化”说来容易,真要用起来,也自有其讲究。许多人受了“陌生”二字的迷惑,朝着与认知和常识全然相反的方向一路写去,语句也是唯恐不极端不惊艳,总想写点什么惊世骇俗的体验出来,而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钱磊则不然,有一种天赋的语感维系着他的写作。有时,他的诗作让我想起帕格尼尼演奏的《无穷动》,那些充沛的、跳跃的音符似乎反客为主,占领了琴弦,并且自行派生出了完整的旋律——音符反过来推动了演奏者。钱磊的诗歌也总是呈现出这样的迷局,文字像瘟疫一样铺天盖地掩来,裹挟着诗人前行,诗人在文字的高速旋转中,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文字汹涌而出,自己形成了诗歌。也有人说他的诗歌像藤蔓,呈放射状无边无际、遮天蔽日地生长,带着藤蔓那与生俱来的缠绕,即便是这样,那蔓延出去的枝叶,也早已不由诗人掌控。年轻的诗人似乎让自己退居到了被动的位置,只需要提供一个动机,剩下的事情,都成了一种自然而然。“我习惯于没有主语的夜晚”,“习惯于被词性主宰”,由此看来,诗人沉迷于这种被动的状态之中,还有些自得其乐。当文字的暗涌来临,“我把手指分开,不再拒绝阻碍的物质/在这幻想的旅途/如水草漂流而下”。
但同时我们又可以说,钱磊是主动的,他最终是自主地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代言。就像前面所说,他或许因此损失了一部分读者,但这其实并非是一种惩罚,他也乐于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虚浮的读者被他设置的种种障碍摒除,而另一些人——那些真正的读者,他们越过了最初在阅读中感到的不适,得以进入这语言的狂欢之中,这对于读者和写者,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像所有的诗人一样,钱磊最初的那些作品,不可避免地犯着幼稚的错误。这似乎是青春的代价,问题是,谁没有过青涩的年纪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总有那么多缥缈的空虚和忧愁被放置在面前,总有那么多清浅的情怀急于抒发。“浮躁的宋词小令为与生俱来的风花雪月/寻找一叶扁舟吟出愁绪/我习惯地说出: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曾经让诗人沾沾自喜的诗句,多年以后增添了诗人的“愁绪”,他说,“我看到了诸多的繁芜和虚蹈,这不是我想要的诗歌……”
懂得自省,这或许是钱磊最大的好处。这些年的诗歌写作,或许让钱磊得到了一些名声,也切实地让他拿到了一些奖项,但这些所谓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忘乎所以。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弱点,并试图寻找改进的方法,是的,唯有正视,才是唯一的、值得期待的途径——他在确定个人第一本诗集《邮差笔记》的过程中,删除了许多诗作,“我想用现在的减法,来赎回当时对词语滥用的罪”。
而对于过度繁芜的凌空蹈虚,他也开始警惕起来了。他开始自觉地由抽象潜入到具象之中,把那些飘在空中的意象,放到了坚实的土地上。这时,他开始写作他的“简史”系列。这将会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系列,足以包罗万象。“简史”类似于臧棣的“协会”和“丛书”系列(所有诗歌都以《XX协会》《XX丛书》命名)、或者阿翔的“诗”系列(所有诗歌都以《XX诗》命名),而且,有趣的是,臧棣和阿翔的文字风格正与钱磊类似,都是一种语言的旋涡。或许这就是具有相似质地的诗人?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一条通往无限的道路。
“简史”这个庞大体系的建立,正标志着钱磊的诗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他对于诗歌的根基,也越发地重视了起来。他意识到,如果不能从符号的表达、动机的衍生,迈入到对生活的坚实的建构,那么他的诗歌大厦将会摇摇欲坠。
看看他近两年的诗作,如《少年简史》,这首诗对诗人而言,是思考,而更多的则是感触和体验,里面容纳了对成长和消逝的理解、对爱情的向往和恐惧、对死亡和人生的认识。钱磊流畅地驾驭着繁复的语句,像是在热烈地自言自语,又像在喋喋不休地向人述说。“如果没有爱情,我们是否会更轻盈”、“可是爱啊,你不该就这样到来”、“如一首老成的诗,等我今天写就”,其中的激情和忧伤,从“所爱之物,渐次消逝”这一主题展开,又最终指向“所爱之物,渐次消逝”这一主题,这表明,诗虽名为“少年”,却不再是以往“不识愁滋味”、少不更事的青春写作。
所有向着“无限”进发的举动,最终都是与时间的交锋。在钱磊新近的《夜读布罗茨基简史》《白日梦简史》等诗作中,诗人比以往更加注重历史所呈现的复杂性,注重诗歌内在的质地。而从写作技巧上看,诗人也展现了比以往更好的控制力,诗意得以更多地呈现出来。
生活在有限之中,但内心却可以是无限的。一个寻求“无限”的诗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