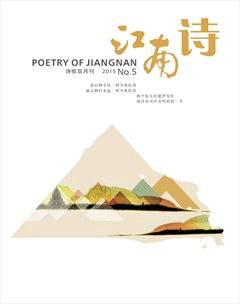冬天的胡琴
主持人语:
在60后女诗人中,冉冉是越写越好的不多几位之一。她说“凝神就会看见”,“由凝神带来的宁静、智慧和力量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也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所能得到的最好奖赏”。她凝神并穿越于诗歌和小说两个世界,从而有了双倍的收获和奖赏。诗歌在她是一种“祈祷形式”,是修为的证言和印记,而她的小说,也富有诗的敏锐、细微和内在韵味,《冬天的胡琴》就很有代表性。在2015“灿鸿”台风中,约浙江诗人慕白写了关于1994“弗雷德”台风的散文《风,从1994刮来》。他将个人亲历、新闻报道、网友回忆等融为一体,具有“跨文体”色彩。从经验主义角度来说,散文是对记忆的提取和拯救。(沈苇)
一
“我听见门吱的一声,那个人走出去,她去追。好一会儿,她一个人回来,翻箱子、柜子,边翻边哭。”
女孩说话的时候,身子不由自主地蹲下去,但并不看他。他是瞎子,看也没用。他端坐在他的小木凳上,架在腿上的胡琴早已没有了声音,皲裂的右手还拿着琴弓。
“是春天来过的那个人。我记得他的口音。”她记得他的蜜,那个养蜂客,花还没有开放就带着他的蜂箱从他的家乡赶来。她记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褐色的蜜、裸着脸在嗡嗡的蜂群中取蜜的养蜂客。
瞎子将拉远的琴弓重新往回推。太阳快要下山了,他身后的核桃树叶闪着暖暖的红光。风从远处的菜地吹过来,吹过他们又向前吹去。她站起来,从她站立的街头望过去,乡场的石板街就像梦里的空胡同一样安静,屋顶上的炊烟都是斜的。
胡琴又响起来,瞎子拉的是《 找牛 》,讲的是一只母牛和三只小牛,母牛在找它的小牛,小牛在雾中走,那雾比牛奶还白还稠。
二
天黑了好一阵,她和母亲还没有点灯。
风停了,雪开始下。一茬一茬的雪花从天空中飘下来,簌簌的声音像炭火在吮吸空气。
黑暗中,她还是看得见母亲的眼睛和牙齿,也看得见墙角堆好的布垛、幽暗的板壁。床上的被子仍然叠着。她们这间卧室是供销社的仓库,里面不能烤火。她们坐在木柜般的火桶里,腰以下被棉被紧捂着。
有笛声从远处传来。小学校的裴老师在灯下吹笛子。那战战兢兢支支吾吾的声音从窗户传出,升到操场上空,很快就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她不喜欢这声音,是因为不喜欢吹笛子时裴老师那涨红的脸。他第一次坐进她家火桶的时候,潮红的脸就像刚吹过笛子,他坐下,母亲的脸也莫名其妙地红起来,而他的手指像随时要去堵笛子的孔似的,不安地动来动去。
“你手里拿的什么?”母亲点亮罩子灯,轻轻问她。
她淡漠地看了母亲一眼。双手仍躲在棉被下。
她拿着一枚柿子。这个柿子她已摩挲了好多天。金红的带有雀斑的果皮下,能看见浆状的果肉和褐色的果核。
她知道母亲正在搜索鞋帮的声音。但远处的笛声还在响,时断时续的,像一个气管炎病人的喘息,焦急万分又竭尽全力。
有老鼠在移动。声音绵软而拖沓,仿佛是在用肚腹走路,从窗下一直走到壁脚。在那里,一只较小的老鼠兴奋地尖叫起来。
她从暖烘烘的被子里抽出了右手,去拿一支笔。左手还在棉被下。这是一支未削过的铅笔,多棱的笔身上,几个拼音字母细若发丝。像拿琴弓那样,她把笔横在手里。
“他不聋,怎么不说话?”她在说瞎子。
“他早聋了。”母亲知道女孩说给瞎子的话远比和自己说得多。
“他看得见我。”女孩把柿子举起来放在眼睛边,焐热了的柿子似乎变得更亮了,“你说,他儿子死的时候,他闭上了自己的嘴?”
“是的,那时他才三十多岁。老婆刚死不久。他看见儿子闭上了眼睛,自己就闭上了嘴。”
“不想说话,还是不会说话?”
“谁知道。”
“他那时瞎了吗?”
“没瞎。”
“他老婆死的时候,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是闭上了耳朵。”
“什么时候开始瞎的?”
……
女孩倏地把手缩进被子里,扭过脸,不再理会母亲。她觉得母亲的不想多说是因为那不成曲调的笛音,她认为裴老师和母亲是两个幼稚可笑的人,他们在她面前东拉西扯遮遮掩掩,既笨拙又有些滑稽。
笛子的声音果然听不见。凝神细听满世界都是雪花的声音。
漫天大雪。掌大的雪花,落在群山峻岭间,落在高高的盖子上,那里有被石板街贯穿的小乡场,有她和母亲的供销社。
三
雪下了一天,两天,三天。
雪收拢了大地上的白色群山。远处近处的山峦硕大而又清晰。曲折的石板街变得简短,街边,粗矮的木屋顶着雪白的屋顶。
稀疏的雪花又开始飘。指头大的雪,弯弯曲曲地、慢慢悠悠地飘落。街口,核桃树银白的树冠像一把巨伞。
女孩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瞎子也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穿得太多,蹲不了多久,她就站在瞎子的旁边。她站着,话已经说过,兴奋劲还没有退去。而端坐着的瞎子似乎也沉溺在倾听之中,上身一动不动。
“还有口琴,她吹过口琴就开始炒菜,吃饭的时候她又大声地哭……”
瞎子稍微有些疲倦,他将并拢的膝盖分开,端正的身板也开始懈怠。女孩反复讲的是同一个人,住在供销社隔壁,她会吹口琴,来自遥远的城市。
瞎子又在调他的弦。今天拉的几支曲子都半途而废。女孩不再说话。
女孩要说的和没说的他似乎都知道。但女孩想不明白,瞎子那干瘪瘦小的胸腔里怎么可以装下那么多排列有序、无休无止的琴声。
雪下得紧了些,掌大的雪花从天空奔涌而至,不一会儿,就落满了瞎子的双肩、双腿和膝头。低头看,核桃树下的小路在积雪下面秘密地游走,逶迤盘曲通往山脚。在路上,一条路又会衍生好几条,每一条路都在向前,每一条路都没有尽头。
四
石板街右边是临坡的吊脚楼,几十户人家整整齐齐的,宽大的屋檐连成一片,左边的房屋门前有高低不一的台阶,显得参差不齐。夜空下,熄了火的房屋就像幽暗的抽屉堆在石板街的两旁。
她和母亲捻小了灯,还没有睡。
裴也在。
裴也坐在火桶里,六只脚在棉被下,被炭火烤着。
她听得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母亲的脉管在突突地跳。而裴的五官像笛孔一样张开,无声的笛音四处逡巡。
她在冒汗。她太熟悉棉被下面的动静。
六只脚,每一只都在准备,每一只都在谛听。
她放下手中的柿子拿起了针。
她在缝制一顶帽子,这帽子刚好可以戴在柿子的头上。前几天她赶制的一双鞋,那鞋合体地装进了她的一对拇指。
缝了两针,缝不下去了。六只脚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但她逮住了母亲的目光,毫无疑问,她细而柔的目光像捻小的灯向裴投过去,裴低着头,假装没看见。
她不说话也不抬眼,帽子上的针脚乱七八糟。
有老鼠在布垛周围出没,一边追逐,一边欢叫。她想小解。
裴无意中摊开他的手,他的手掌宽大而红润。她想他可能要走了。他不走,她就不去解手。
咚!咚!
隔壁的人还没有睡。
那个会吹口琴的姑娘,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再次扔下去,咚的又是一声。
他们竖起耳朵,都在听。
“怕是又有三四个月了吧。”母亲说。
“她不要命了吗?”裴掀起棉被,真的要走了。
“作孽啊麻子。”母亲在诅咒,语气却像在挽留。这一次,她的目光就停留在裴的脸上,并不避开她的孩子。
“我在书上看过那座城市,”裴重新坐下,他开始安下心来。关于那座城市,他有许多可说的。那些车辆,那些建筑,那些码头和人。
女孩抿着嘴,烦躁地听着裴的讲解。实际上他说得很节制,很有条理,一点也不显摆。一座城市,它的饮食、服装,口音、排场甚至是厕所防空洞可说的实在是太多。女孩愤怒地坚持着,一方面不能打瞌睡,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他们去小解。
五
她和母亲躺在床上,肩并着肩。
这个夜晚没有客人。小学校那边稀落的笛声早已听不见。风还在刮。群山沟壑间奔走不止的大风。伏在山顶上的乡场一遇上大风就显得特别安静。
她听得见母亲的深长的呼吸,她知道她没有睡。吹大风的夜晚,她和母亲都睡不着。她们都有些兴奋,为那持续不断的风声。
在黑色的穹窿下,风跟白天是不一样的,白天的风松散飘浮,雾一样游动在山峦间,泛泛的冷但不刺骨,而夜晚的风持久而猛烈,像强光不停地扫过山岩树林和空地。石板街的屋瓦、板壁、门窗在风的喧响里也发出深浅不一的回应,但这些声音都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显得瓮声瓮气。
几只老鼠在被大风摇撼的窗户下打架,不是真打,像是调情,只一会儿工夫都发出了愉快的呻吟。
瞎子在梦中能不能看见呢?她听见自己在问母亲。
母亲也许在想她那些在阴湿的天气里发霉的布匹,或是在想从山下来的背脚仔打滑的鞋底,因为老是在途中摔倒,好些货物都被稀泥弄脏。孩子和她说话,她有些心不在焉,想到孩子会不高兴,她赶紧说瞎子原来并不瞎,看见的事全部存在脑子里等着做梦用。又说瞎子看东西不用眼睛。
用鼻子?用脚?裴坐在火桶里的时候,和母亲也是不对看的,但他们在看——有什么在流动和传送,她甚至不用抬眼就知道他们在对看,使劲地看。
门外的风弱下来。风从围墙的顶端滑到墙根。风吹墙根的声音很特别。扑扑扑,短促但不间断,就像一个人恼火地锲而不舍地吹一堆火,而火老是不燃,因为柴是湿的。
母亲开始讲瞎子的老婆,那是一个俊俏的女子,虽然牙齿有一点龅,但心灵手巧,在一大堆花布中,她总能指出哪一种最漂亮,这一点母亲特别欣赏。认识她的时候母亲还是姑娘,刚从县城附近的小镇上分配来。孩子对瞎子老婆的兴趣比较淡,一想到母亲以前也是一个胖乎乎有点笨的姑娘,心里就有点乱。她看过那时母亲在县城的照相馆照的一张相片,围着头巾,大脸厚嘴唇,丰满而又愚蠢。
母亲讲话的时候,孩子的耳边热烘烘的。母亲的嘴里有一股糯米的气味,青椒的气味,有时也会是红薯或者其他食物的气味,但她那口洁白的牙齿总是让她想到糯米。一个有着好看牙齿的姑娘,在偏远的乡场上,在供销社寂寞的柜台里,从春天到冬天,从姑娘变成妇女,有一个甚至是几个龅牙的女朋友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何况那个人已经死了。
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就该终身赎罪,至少他得用尽量窘迫的生活求得死去的人的谅解。不管怎么说活着比死去要强要便宜一些。一个俊俏的和母亲要好的女子中途死去确实可惜,但她对瞎子的老婆兴趣还是比较淡。她觉得瞎子理所当然地该和他的胡琴、和核桃树是一体,她不能想象她有老婆和孩子。
她想告诉母亲,她曾听见瞎子脱口说过一句话,当她有次蹲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虽然是很短的她没有听清楚的一句话,但她肯定他说了( 后来她再三要求,瞎子也没开过口 )。她记得他的嘴洞开,那话就冲口而出。她记得他的两片嘴唇,像仓库的两扇大门,她当时纳闷不知瞎子有多少话多少故事存储在里面。
她还想告诉母亲,口琴其实是吹不坏的,不像衣服穿着穿着就旧了,要打补丁,也不像胡琴拉久了弦会断;它应该像笛子,因为反复吹奏反复摩挲会变得越来越光滑,越来越好使……
一只口琴要多少钱呢?要积攒多久才够买一只口琴和去来途中的费用?想到钱,她的心就有些发紧。她瞅了一眼母亲,母亲的脸松弛地摆放在枕头上,头发乱蓬蓬的,眼睛似睁未睁,她闭上眼,赶紧装睡。
母亲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沉默中,风还在拍打门外的围墙,围墙外是牛背似的黑色山脉,此刻那些山在大风中起伏,在大风中倾斜。
有风的夜晚,两个相似的面孔和身体,在同一床被条下怀着各自的心事相对而眠。母亲伸出手,打算去摸孩子的脸或是掠开她脸上的头发,被她机敏地躲闪开。母亲讪讪地缩回手,转过身与她背靠背地睡去。
六
女孩积攒的钱也许还不够买一只口琴,也许可以买两只,谁知道呢?一只口琴值多少钱,要准备多少钱才可以上路,去有口琴卖的地方,谁又说得清?当初积钱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口琴,只是想暗暗地有一点自己的钱。一个小孩子自己有钱和没钱那感觉真是大不一样。
她的第一笔钱是替母亲打扫卫生时在供销社的门缝里捡到的。五分的硬币,上面有厚厚的一层泥。以后,她依然主动地多次打扫过柜台内外的清洁,但再也没有那样的运气。独自有了五分钱,那种喜滋滋的秘密的快乐让她幸福了好多天。但很快就不满足了。她喜欢变换的数字,比如去年是六岁,今年是七岁;去年的鞋子是二十三码,今年是二十四码;去年只识五个字,今年认识三百八,还有供应的粮食,去年是二十一斤,今年是二十三斤;还有布票,去年是八尺,今年是一丈。有好几天,她着魔似的在母亲放钱的抽屉边转来转去,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将手伸进去,摸了一张纸币塞进棉裤的口袋里。那是一张五毛的纸币,崭新的!她有些害怕,做了好几个晚上的噩梦,准备瞅机会把钱还回抽屉里去,当时正是月末,母亲每月一次的点盘下来,竟没有发现少钱。钱仍然待在她的口袋里,悬着的心也就慢慢地放了下来。以后再将手伸进抽屉,就多了一些从容和讲究,挑小的新的,贰分或五分,这么小的数目,母亲自然不会觉察。
也有正当的来源,比如赶集天母亲给她的零花钱,学期末节约的书本费她都一分一分地存着。
存款的数字在秘密地变化着,但那喜滋滋的快乐却再也没有了。怎样安置这笔钱是件伤脑筋的事。后来她想到了瞎子。瞎子待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她把钱藏在他床下的一只旧靴子里。她偷偷去查看过几次,每次都在而且是一分钱不少。瞎子知道吗?她宁愿相信他不知道,但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讲不会要。她相信他们有这样的默契。这个赌注她愿意下。
七
太阳挂在核桃树梢。阳光很红,但软弱无力,时起的风,把树枝吹得摇晃起来。叶片上的雪被吹得沙沙地往下掉。
有人挑着水桶往树下经过。桶里的水是泉水,氤氲着微微的热气。
瞎子的嘴唇是干的。露在帽子外面的双耳冻得出了血。那是两轮好看的耳朵。匀称、透明,像切开的两爿葫芦。因为通红,耳垂那里在流血。
瞎子的棉衣棉裤都是黑的。在白雪纷披的核桃树下显得洁净。
女孩在五步以外站着,今天赶集。她并不要听瞎子的胡琴,但她喜欢看来赶集的人从核桃树下走过去。
瞎子经常拉的几个曲目她都能够背出来了。她不喜欢听那苍凉而又嘶哑的声音。但喜欢曲目里的唱词,瞎子当然是不唱的,她听过别人唱。那个人啊……这是《 三月三 》的开头。在唱词里那个人绝望无依,冒着冷风,一个人左走右走,紧赶慢赶。每次听她都觉得心里发慌。
时辰还早。瞎子的琴声还没有开始。琴架在他的腿上,风吹过,无声的胡琴像沉默的风车。
她想起春天,在摆满蜂箱的田埂上,养蜂客拿着蜂巢,他的身前身后都是怒放的油菜花,他的头顶是盘旋的蜂群。蜜蜂是安静的,嗡嗡的声音仿佛是从蜂巢里发出的。就在油菜花旁边的人家里,一架老风车屏住吱嘎声,空气中除了菜花的芳香还有雀鸟飞过时留下的小粪便的淡淡的酸味。
胡琴其实可以说一说四月四,或五月五。在花地里,蜜蜂并不蜇人。养蜂客的眼睛总是眯着,被花和蜜滋养着,那双眼睛洋溢着春光和温情。女孩愿意把他想象成为自己直接或间接的亲戚。她对他的外地口音特别着迷。他是不唱歌的,话很少,寡言而又羞涩。
“他又来过两次……”她在说养蜂客,瞎子的头轻轻地侧了一下,不易觉察的,拿着弓的手还是松松的。他好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酝酿不知是好还是坏的情绪。
“天黑的时候,我看见他挑着箩筐……他给她劈柴,劈柴的时候,她在吹口琴……”
有人从他们面前走过,是一个男孩,穿着胶鞋。蹑脚蹑手地,背篓的口沿盖着一顶斗笠。
“他们喝酒,她对他说别喝了,他说不怕,不就是麻子吗?不就是仗势吗?我反正要杀人……”
又有人从他们面前走过,是一对夫妻。妻子手里提着一只色彩斑斓的公鸡,丈夫挑着的箩筐里估计是红薯糖,敲糖块的铁具发出叮叮叮的碰撞声。
“她又吹口琴,他一边喝酒一边哭……”她突然不想说下去,鼻涕和泪,加在俊美的养蜂客身上,就像在洁白的雪地上蓦地看见一个癞子,心里怪不是滋味。
这当儿,瞎子的右手已经在膝头上方来回拉扯了。还是《 三月三 》,缓慢幽怨的曲调里多了些诉说,那诉说仿佛是女孩格外添进去的,有种近距离的烟火的意味,说的和听的彼此都心领神会。女孩要说的还没有说完,瞎子要说的还是三月三,瞎子要说的谁又会仔细地听?
又起风了。风把过路的人的颈脖吹得短了些,她过长的刘海贴在了眼睛上,她抹开头发突然问:“杀一个麻子要几个人?”
有好几个人在他们面前驻足,他们的手揣在上衣口袋里,头上有汗,露着牙齿笑得很虚心。瞎子扬起下巴,不知是对她还是他们。三月三已拉到最后,那不尽的诉说里有赌气、怨怼、执拗和愤懑……
八
女孩病了,手脚冰凉,浑身盗汗。
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就黑下来。母亲坐在床边,床头的罩子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板壁上。裴也在。另一盏灯点在火桶旁边的抽屉上,裴在往火罐里塞纸。裴的影子和他的手在墙上动来动去。屋里显得很拥挤。
她想喝水。
她的头上压着湿毛巾,也许是烧得太厉害了,她想用舌头舔舔焦渴的嘴唇,但是舌头转动不灵。
母亲喂了她一些水,又把湿毛巾放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压上她的额头。
窗外的风似乎更大了。门外的院子里好像有几十双草鞋来回疾走,不远处的围墙上有人在用钝刀砍柴,墙边的棬子树在风中窸窸窣窣地落下豆大的棬粒……这样的夜晚适合打架,尤其是群架,拿着刀和绳子。
“麻子!”她大声地喊。
母亲吓了一跳,庚即转过头去,裴正抬起头,和她交换眼神。
“不要让她老跟瞎子在一起。”裴说。
“她喜欢跟他说话。”母亲想跟裴说这孩子有很重的心事,但她没有说出口。
小孩闭着眼睛,并没有睡沉,她听得见他们说话,甚至可以想见他们说话时眉来眼去的样子。她想重新坐到火桶里去,但手脚软得像棉花。
“瞎子命孬,孩子跟他学……”
“要是他自己的孩子不死……”母亲在叹气。
“是老婆先死,还是孩子先死?”裴比母亲后来乡场,他也是从县城附近来的。
“老婆先吊死。炸麻子的炸药孩子拿去当火炮玩被炸死。”
“养蜂客最近到处在找麻子。”
“有什么用?”母亲有些生气,只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她站起身,哗地一声把盆里的水泼到门外,过一会儿又在门外的水缸里舀水。
敷在孩子头上的湿毛巾几乎挡住了她的眼睛,但她还是看得见母亲的身影,母亲端着瓷盆从外边进来,裴迈出火桶去接,又把盆子放在火桶旁边的地板上。她担心母亲会在这时和裴坐进火桶里去,但母亲弯腰从地上重新端起了盆子。她坐在床头,再次揭下了孩子头上的湿毛巾。
频繁地更换毛巾,额头的烫减弱了。流了太多的汗,身体也变得轻盈。小孩感到母亲在小心翼翼地脱她的衣裳,一件一件地脱。光线逐渐明朗,周围一下变得很开阔,她像预备做操那样平举双手,脚边码着柴垛一样的冰。
有一点冷,是小块冰伸进后颈窝的那种,不进骨肉,却让人一激灵。又有一点,像不小心掉进了池塘,又湿又凉的衣裤紧紧裹住全身。更冷一些,衣服倒是穿着,但是太薄,又饿又委屈,风又大,天又黑,她的牙齿在咬什么,但总是咬不准……
打摆子。她听见母亲在问裴,裴几次伸出手在她的额头上测试体温。裴坚持认为是发烧。她看见他们说话的时候嘴里冒着寒气。她听见远处的风带着长长的哨音划过围墙,小格子窗不停地叩动着牙齿。
要……
孩子说什么,母亲听不见,她俯下身,瞅着孩子,眼睛里储满了泪水。
裴在母亲的头顶举起了灯。
女孩的抖减缓了,闭着眼和嘴,脸颊绯红,灯光下就像一枚发光的柿子。此刻,她的脑袋里灌满了糨糊,微弱的想法像半融化的果核似的在糨糊里游来游去。
我要……
母亲还是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已经在她的身上添了两床棉被,她感觉孩子的呼吸有些急促,就把手伸进被窝,支撑在胸口的位置,胸口压力太大,会做噩梦。
梦还是在做,只有孩子自己看见,是梦中梦。她梦见梦中的自己坐在火桶里,明火烤着六只脚。有两只严阵以待,另外四只老辣沉稳,极具耐心:谛听,试探,退让,小跑,拉拽,缠绕……火焰升起,腿上、背上、胸口、肩头到处都是火斑,不见母亲和裴的衣服,只见他们周身蛇皮样闪烁的火斑……
扯淡!
她喊起来,这一次母亲听清楚了,虽然古怪莫名,她还是破涕为笑。
裴认为母亲给孩子盖得太多,但暴热暴冷已经过去,应该抓紧时机给她打火罐。
九
孩子的病不是太重,但却拖延了一些日子。
母亲还不让她起床。已经过了正午,透过格子窗射进来的光线还是很暗。雪早停了。隔壁有人在舀水,过不久又在搓衣板上很响地刷衣裳,每隔一会儿,围墙顶的乌鸦就会呱呱地叫几声。
天花板上糊满了报纸,报头的字是鲜红的。大公报——报头字是草书,刚识字的时候,连估带猜,认为头上的报名就是大公鸡。报上的内容她看不清,也不认识那么多的字,但她急切地想知道报纸上说了些什么。她不想请裴告诉她,也不想让母亲读给她听( 天花板那么高,谁又能够看清楚那些小字? ),她渴望知道那么多张报纸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好多次,她仰起头,自己编故事给自己听。
“有一个人早上出门……”她还没有读出声,自己就笑了。这不像是读报纸,倒像是摆龙门阵,“有一个人早上出门,遇上另一个人,他们是仇人,但互相不知道,他们一起去赶集……”
有人在喊母亲买布。她床头的门通向卖布的柜台,门没有关严。那人扯了九尺白布、九尺蓝布、九尺青布。哪家死了老人。
“是王公公吗?”母亲问。
那人说是的,母亲说八十四了吗,那人说还没有到。
但他并不老,女孩记得去年冬天,王公公快步从街口走进供销社。母亲不在,他歪着头奇怪地盯视她和她身后的布匹。他的眉毛像带雪的松针,他的颈部有一个巨大的葫芦形肿瘤,那简直就是一把小提琴——她当时几乎叫出来!她真想把母亲的尺子当成弓送给他,让他在自己的肉琴上像瞎子一样拉出乐曲来。他死了。人的一生通过嘴说出的声音是很有限的、很单调的。她见过母亲和他说事,母亲唠唠叨叨地问,他只是简单作答。
“一个人早上出门,遇见了他的仇人,互相不知道,一起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姑娘?蒙面大盗?还是知道他们底细的老人?一个人只要出门,可能遇到的事就会多种多样,哪像躺在床上。
又有人走进柜台,踩着门前台阶上的积雪,踢踢踏踏地走进来,没有说话。那人伏在柜台上,肯定是裴!母亲说不定也伏在柜台上。
隔着算盘,柜台里外的两双眼睛在肆无忌惮地凝视。女孩都能想象,他们没有呼吸,只从眼里冒出热气。
柴胡。
裴终于说。
大青叶、贝母、枣皮……
母亲撕扯一页账簿在记他说的中药。裴以前曾经给母亲开过药方,从书本上看来的。女孩不能容忍他说话的口气,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好像他真的当过几年医生似的。从公道处说裴开的药倒比诊所的老中医见效。裴给好多学生的家长看过病,有家长直接央求他教孩子学医。
每样十钱!
母亲似乎乐意听裴的吩咐。隔着算盘,她在账簿上慢慢地写,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裴。她有十根灵巧的手指,两只手能同时拨弄算盘,而且是又快又准。
又没有动静。
孩子感到焦急。她烦躁地杜撰着她的故事。一个人早上出门,到处都是恋爱的人。一个男的问一个女的你什么时候生,女的说昨天,又问什么时候死,女的说随时……
隔壁的衣服还没有洗完,刷衣服的声音断断续续。她听见裴在说火罐。提到她的病,母亲开始忧虑,她担心的是她的体质,早有人说过这孩子长心不长身,柔弱的身体经不起折腾。
裴建议用鸡血藤泡酒给孩子喝,那样补血,又说他能搞到鹿茸,不过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用天麻炖鸡……
补得啊?小孩子!母亲说。
孩子突然觉得有些心软。隔壁刷衣的声音已停。墙上的乌鸦早已飞走。风还在吹,隔着柜台,裴和母亲的脸肯定冻得发紫。
“一个人早上出门……”,房间比刚才更暗了。但还是看得清堆在墙边的布垛的轮廓、抽屉的轮廓、火桶的轮廓和两口红木箱的轮廓。那两口红木箱装着她和母亲所有的宝贝和衣裳。如果一个人早上要出门最好不要选冬天,冬天要带的东西多,出门太麻烦。
街口的胡琴又响起来,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瞎子这次拉的是《 找牛 》。母牛张望着,四处找它的小牛。大雪天,四野的山牛犊一样静卧在雪被下,那雪比牛奶白比牛毛还要软。
十
女孩在夜晚想她的钱,牵肠挂肚地想。那钱好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几次在梦中,她点不亮灯,手指也合不拢,她就张开指头像瞎子一样摸索——她发觉钱是有脚的,像蚊足那样细的脚,但比人跑得快,它刚才还在这儿,转眼就到了别处。
钱,她是因为想到钱,才从昏睡中不断醒来。也许是病久了身体虚弱,也许是用药过度,她昏睡过几次,当她有力气下床,不等母亲同意她就来到了核桃树下。
瞎子在。仿佛等她似的。好久不见,他看上去更瘦、更苍老了。好像生病的是瞎子而不是她。
我的钱。她说。
瞎子今天坐的凳子比以往高,上身端正,腿显得比以往长。琴弓刚上过松香,空气中有淡淡的香味。曲子还没有开始,他的两只手却开始用劲,手背上的筋像几根麻绳。
我的钱。她说,声音比刚才高了些,但因为生过病,还是显得有气无力。
开始拉过门了。瞎子这一次拉的是《元宵》,喜庆的过门后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又是慢叙细说。仿佛鞭炮过后的岑寂,吆喝过后,寒暄过后,烤火的烤火,吃元宵的吃元宵,人们有一句无一句地说去年的事、前年的事或者更久的事。元宵节应该是欢快的,但它是春节的结束,加上春天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在淡淡的怀念和迷茫的憧憬里总有那么些伤感,那么些忧郁。胡琴,胡琴不比口琴,胡琴可以把所有的曲子弄得千回百转,柔肠寸断。
她听过隔壁的姑娘吹口琴,那是傍晚,养蜂客给她劈柴,她不停地吹,吹到后来就哭起来,养蜂客放下斧头去安慰她,她止不住的啜泣。但她觉得她吹的是些快乐的曲子、明亮的曲子。就像油菜花开的时候,空中那些零零碎碎长长短短的声音。那时,空气中的花香是一阵一阵的,在香气的间隙,有时是阳雀的一两声鸣叫,有时是枝条飒飒摆动的声音。
我的钱。她几乎要哭起来。
瞎子今天的表情有些奇怪。坐在高凳子上,上身笔直,两只眼睛凝视前方,面前的东西他看不见,他凝神的也许是遥远的所在,他的鼻翼在轻轻地扇动,嘴撮在一起像要吹笛子。
“我原来想要一只口琴。”女孩裹在围巾中的脸开始发烫,话说得又快又急。
瞎子重复地拉《 元宵 》,每一次都拉过门。元宵是正月里的元宵,风在刮,雪没有停,三三两两的人在火边有意无意地说自己或别人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买一只口琴。”她继续说。她的话在瞎子的琴声里显得含混不清。瞎子说的是一个场景,某个过程;女孩讲的是一件事情,一个愿望中没有发生的事情,两样都不在现场,都无法把捉,就像无数次在树下散开的那些音符,又像还没有拉出来的一些曲子。
“我的钱本来可以托她买一只口琴,在她回家的时候。”她在他的背后幽幽地说,她站着,没有像以往那样蹲在他的脚边。她说,在春天,我本来可以在油菜花中间吹自己的口琴。呜呜呜地吹,蜜蜂还以为是野蜂群……
瞎子扬起的下巴轻轻往回收,撮起的嘴也开始松下来。他的左手尚在琴身上滑动,右手的弓已经僵住。
声音的颜色就像蜂蜜的颜色……她仍在说口琴。听见自己的话响亮而又清晰,她意识到琴声已停。
“他们死了。”她用高一点的声音在瞎子耳边说。她告诉瞎子,养蜂客带着炸药到隔壁姑娘的屋子,喝了姑娘给麻子准备的毒酒,姑娘回家看见他死了,也喝下了剩余的毒酒。他本来想与麻子同归于尽。
瞎子的嘴呵着,眼睛望着远处,似乎不在听,只是歇息的右手又动起来。这一次他拉的是《 三月三 》。有风从远处的菜地吹过来,不一会儿就在他们头顶稠密的树叶间呼呼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