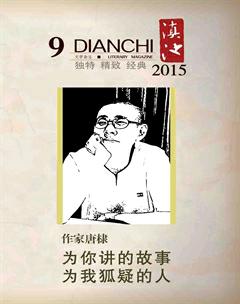剪刀过敏症
喻长亮
到家那天快到凌晨一点,妻子还没有睡,独自靠在床上抽烟,屋里全是烟味。她本来偏瘦,这时看上去脸色有些蜡黄,眼神忧郁。她不看我,固执地在思索着什么,又像什么也没想。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不安地问。“当然出事了。”她说,“你出门这段时间,出大事了。”我吓了一跳,感到脊背上凉飕飕的,僵硬地站在原地不能动弹。
“你坐下来,我慢慢说给你听。”她向我招招手。我挪开双脚,机械地坐到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
她说:“江小羽出事了。”“江小羽?江小羽是谁?”“江小羽你都不知道?我高中同学,我不是
跟你提起过吗?”我在脑子里搜索着,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你是说,江小羽出事了?”我重复了一
遍。“对,江小羽出事了。”她叹了一口气,好像等到现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我虚惊一场,终于放下心来。
接下来,她跟我讲起江小羽。
你走的那天下午,江小羽打电话叫我过去,说,赵家良有外遇了,说着就哭起来。我收起电话,匆匆打车过去。她家就在环城小区,不远,几分种就到了。
我推门进去,只见江小羽歪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浮肿,在不停地用纸巾抹眼泪。脚边的垃圾篓堆满了纸巾,有几片掉到了地板上,湿渍渍的,显然都是她用过的。
见我来了,她点点头,哽咽着说,坐吧。我默然坐下,想着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她却先开口了,带着命令的口气说,叫你来,是让你帮我出个主意。只见她抬手指着屋子的另一边,恨恨的说,看怎么收拾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惊异地发现墙角地板上跪着一个人。不用说,那是赵家良!他面向墙壁,身子伸得笔直笔直的。
我二话没话,跑过去一把将他拉起来。赵家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小声说,谢谢,谢谢好姐姐!我不记得他平时是不是这么叫我的,但这回他是这么叫的,还叫得挺暖心,可见他的确很能哄女人。赵家良一定跪了好长时间,双腿僵硬,无法站稳。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衡,却还是差点倒下去,最后一把扶住墙壁,才勉强撑住了。他弓腰抚摸着双膝,裂嘴倒吸着凉气,不时偷眼看一下沙发上的江小羽。我说,江小羽,你像话吗,哪儿有这样整自己男人的!
我这么说,本想给赵家良解围,没想到江小羽恶狠狠地瞪了赵家良一眼,说,给我滚回去!声音不大,却暗含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狠劲,惊得我身上陡起一层鸡皮疙瘩。
赵家良求救似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一脸痛苦地回到原地,小心地趴下去,老老实实跪在刚才的角落里。
江小羽告诉我,她是无意中发现他的秘密的。
前不久,她因生意上的事去了一趟北京,在那里前后呆了十五天。
北京,也是十五天。这么巧?
回来那天,她发现他的衣柜里新添了一条领带,说,哟,不错!哪儿买的?她无意中问。
赵家良迟疑了一下,含混地说,在中百超市买的。
你不是不打领带吗?怎么忽然想到买这个?
好玩呗,随便买了一条。
不便宜吧,还是个牌子?
也不贵,——几十块而已。说着,他转身出去了。
第二天,她去中百超市购物,在里边转来转去,忽然想起这事,却发现这里并没有领带出售。于是问服务员,服务员说,没有啊,这儿没有卖领带的专柜。
这事就过去了,她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下午,她去了一趟银行。她有定期存钱的习惯。
打开账户时她吃了一惊,里边居然少了五万块钱。有一笔还是前两天取出来的,一次就是三万!
她立刻想到赵家良,除了他,没人知道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前后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她想,赵家良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回到家里,她装作若无其事,该做饭做饭,该拖地拖地,一件也不落下。正好赵家良上厕所,手机落在茶几上。她逮着机会,赶紧翻看他的短信记录。
短信都删了,只保留着跟王鱼儿的对话,其中有这么一条:晚上我不来了,跟你如一姐在一起!
如一?她将手机放回原处,接着拖地。
下午,她找到了王鱼儿。王鱼儿是赵家良的哥们,过去常到她家蹭饭。
王鱼儿一见她,就知道没好事,说,嫂子,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我!
她说,王鱼儿,你家良哥欺负我,你居然敢当帮凶,你说你还是人吗?
王鱼儿躲闪着,说,嫂子,这话从哪儿说起,家良哥敢欺负你,我揍他去!他拿腔作势地挥舞着拳头。
王鱼儿,告诉你嫂子,如一是谁?她突然提高了嗓门,声音像尖刺一样,吓得王鱼儿一下子捂住耳朵。
嫂子,谁叫如一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江小羽指着他脑门说,王鱼儿,你有种,你以后别叫我嫂子了!说着就走。
王鱼儿愣了一下,赶紧上去拉住她,央求道,好嫂子,别生气,我真不知道啊,我骗你我
不是人养的。江小羽回头认真看了他一眼,说,哼,你要再不说实话,我真不拿你是你爹妈生的。
好嫂子好嫂子,您就别骂我了,我说了还不行吗?可是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要不家良哥非割了我舌头不可。
王小鱼告诉江小羽,那个女的叫柳如一,是赵家良在麻将馆认识的,已经交往两三年了。两三年?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江小羽心里一凉。
回到家里,正好赵家良回来了。她扔下包就叫了起来:赵家良,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敢背叛我!
赵家良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故作镇定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好,不承认是吧,那你说,我账户上少了
五万块钱是怎么回事?柳如一又是谁?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说什么呀?还嘴硬?你自己看吧!说着,她将刚打出的
银行小票扔了过去。赵家良战战兢兢地捡起来,说,真没有啊!那样子竟比哭还难看。你是不是拿我的钱养那个小婊子去了?说,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有!他双手捂着脸,竟然双腿一软,蹲到了地上。
还有,那条领带是不是那个小婊子给你买的?她上前去猛踢了他一脚,他浑身一哆嗦,跪了下去,地板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不是,——是,是啊!他真的哭出了声。那么,你们上床了?她咬牙切齿地问。——说啊,是还是不是?她又踢了他一脚。
老婆的故事还没讲完,我就睡了。临睡时我说,算了吧,我太困了,明天接着讲好不好?第二天,我打了刘玉意的电话,约她晚上在老地方见面。刘玉意是一个单身女人,租住在河堤街一个
偏僻的院子里。我们在一起有两三年了。两三年,又是这么巧?
我们约会的地点在城郊的一片小树林里。那是河边的一片坡地,上面长着一些零散的桃树,我们叫它桃花林。平常很少有人到那儿去,很僻静。一到晚上,河边总有很多人散步、遛狗,也有人在水边夜钓,在草坪上抽烟聊天。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在人群里走上一两圈,装作散步的样子,然后拐到另一条小路上去,借着城区路灯的余光,放慢脚步,边走边小心地回头瞧瞧有没有人,不久就到了桃花林。有时我先到,也有时是她先到,总之到了这里就放心了,不会碰到熟人。但我不太喜欢这种见面方式,曾试着在外面开房。她不同意,说更喜欢那种在野外的感觉。
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回刘玉意匆匆而来,神色紧张,一点也没有往日的从容。她告诉我,一路上,总觉得有人跟踪她。
我故作轻松地说,怎么会呢,这么久了都没出问题!
她说这些天她都有这种感觉,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而且还似乎看到过这人的脸,尖瘦,蜡黄,是那种病态却又刻薄的女人。你往前走时,她就在不远处跟着,那眼光就像刀子,插在你背上。当你猛回头去找她时,却什么也没看到。
尖瘦,蜡黄,病态。这是谁呢?我暗自思索。
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问她。
嗯,她想了想,应该是我们上次分手后的第二天,——大约十五天前吧。
又是十五天?我盯着她的脸,想知道这是不是她故意编造的谎言。
知道我要去北京,她约我在桃花林见面。以这种方式为我饯行,也算别出心裁。那晚她特别兴奋,不停地翻滚,尖叫,弄得我大汗淋漓。事后我说,你简直拿这片树林当你家席梦思了。她正在整理衣服,掐了我一把,妩媚地说,人家就是舍不得你走嘛。
你不知道,这些天我心特难受,就像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吞又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我感觉我们的事被人发现,而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老婆。
什么,你说什么?我心里一震。
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感觉,你老婆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她这么藏在背后,其实更可怕。
胡说,她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你太紧张了。我几乎叫了出来。
她仔细看了看我,说,我看是你太紧张了,一提你老婆,你嗓门都提高了,你是不是特怕你老婆啊?她嘲讽道。
后来,我们又说了一点别的,但是她的注意力总在跟踪这件事上,说话也不着调,一点也调动不了情绪。最后,我们不欢而散。
离开桃花林的时候,她故意落在后面,说,我可不想让你老婆抓个现行,还是你先走吧!
回到家里,时间还早,妻子还没有睡。
见我进了门,她说,这么早,你不是说晚上有应酬吗?每次跟刘玉意见面,我都会撒一个谎,比如陪客人啦,比如加班啦,无非找个理由晚点回去。
对,难得宽松一回,没喝酒,也没出去唱歌,可以早点休息。说着,我径直往洗手间去,生怕她发现什么漏洞。我在里边洗了一把脸,又在镜子里仔细照了照,才慢腾腾地出来。
我们接着讲江小羽的故事吧。说着,她点燃了一支烟。我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难道也是我去北京这段时间?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问我,要不要来一支?我摇摇头。她知道,我从来不抽烟。她说,昨晚我还跟江小羽打了一会电话,安慰了一下她。她这么说,好像是有意证明,江小羽以及江小羽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江小羽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怎么说呢,是发起飙来什么事都做得出的那种角色。也正是这个原因,她的生意越做越大,好多男人都让她三分。我一直想不明白,江小羽这么精明一个人,怎么就让自己的丈夫给骗了?
赵家良怕老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有时在想,也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他出轨?想想也是,成天面对一个母老虎,谁不烦啊。
这么说来,她遭到背叛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你说是不是?她打量着我,似乎在观察我。
我故意傻笑一下,摇头说,这事可别问我,我是医生,成天摆弄些刀子剪子的,只会做切除和缝合之类的事,哪儿知道这些名堂!说完,也偷偷瞟了一下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唉,也是,赵家良哪儿能跟你比啊,你要是也做对不起我的事,只能说男人这个物种太不靠谱。
我心里惭愧,重重地抹了一把脸上未干的水珠,掩饰道,那是,赵家良这家伙太不地道了。
那天赵家良把所有的事情都承认了。他告诉江小羽,那个叫柳如一的女人住在万家巷。
万家巷是一条老街,弯弯扭扭的街道两边是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在这不到半里长的街上,有十几家麻将馆,那些男人女人,整天都呆在这里打牌,麻将声哗啦啦此起彼伏,堪称麻将一条街。
柳如一没有正经职业,是那种成天泡麻将馆的女人。她跟每个麻将馆的老板都熟,往往从这家麻将馆出来,又进另一家。她长得漂亮,出手大方,走到哪儿,都被众星捧月似的。只要她走进哪家麻将馆,那里的人气就高涨,老板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一些人喜欢围着她转,特别是那些男人,去光顾哪家麻将馆时,都会先问一声,柳姐来不?老板马上堆下笑脸,说,来来,您坐呢,柳姐马上来,昨晚就预约好的。回头便打电话过去,好歹一定请来。因此,哪家麻将馆开张,或者生意撑不下去了,都会请柳姐撑门面。在他们眼里,柳如一是客源的保证。她不来,别的客人也不来,生意都会跟着她跑到别的地儿去。于是,那些麻将馆争着请柳姐压场,弄得她
比正经上班还忙乎,还有威信。当然,去也不是白去,得给出场费。出场费反倒成了她的正常收入。那些男人视柳如一为麻将明星,俨然把自己当作“柳粉”。在这条街上,柳如一的名气远远高过那些当红影视名星。
赵家良是万家巷的常客。江小羽忙生意上的事,成天不着家,到万家巷打麻将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与那些“柳粉”不同,他玩得小,经常跟一些不起眼的人瞎混,根本不引人注意。在柳如一眼里,万家巷里这种人太多了,连瞟一眼的工夫都没有。按理说,他们很难走到一块。
但事情也有出人意料的时候。那天赵家良手气特臭,时间不长就把钱输光了。他哭丧着脸抽了抽鼻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灰溜溜地准备离开。照着他的意思,输了就输了,认栽走人得了。
正当他低头往门外走时,有个女人叫他,说兄弟,怎么散了?
他抬头,是柳如一。
柳如一刚好进来,显然是来压场的,不过随便问一句。
赵家良心里一紧张,结结巴巴地说,手臭,输了。
柳如一抿嘴一笑,说,多大的事,姐给你,回去吧。说着,顺手从包里抽出一沓钱递过来。
屋子里的麻将声静止了,打牌的人都停下来,直愣愣地看着他们。
好!柳姐撑腰,多大的面子!有人叫了起来,有人拍起了巴掌。顿时,噼噼啪啪地满屋子的人都鼓起了掌。
赵家良交待这些细节时,一直跪在地上。江小羽说,她踢了他一脚,他就跪下了,是他软骨头要这个样子,自己压根就没有要他跪下去的意思。他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哽咽不已,有好几次都泣不成声。他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里钻出来,含混不清,带着哭腔,像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在哭哭啼啼地认错。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牌运都不好,一溜烟地输。每回需要钱的时候,柳如一都会不早不晚地出现在他身边,说,又不行啊,来,我支持你!他虽然输得难受,但有柳如一撑着,他有面子,也有底气。
于是,他跟柳如一自然而然地有了联系,比如还钱,借钱,再借钱,再还钱。
有一回柳如一悄悄跟他说,你打大一点,比如加码,比如换一个环境——跟那些赌得大的牌友一起玩,你会集中注意力,牌反而打得更好。他觉得有道理,听从了她的话。
那次他果然赢了一把,于是主动说,今天我请客,去来一回宵夜怎么样?柳如一说好啊,来一回就来一回。
准确地说,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开始。除了给他借钱,他知道,柳如一还为许多男人借钱。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并不是谁都能请到她去宵夜的。更何况是去来一回。来一回是什么地方?听听名字就知道,那是个暧昧地方。
他们在来一回吃完宵夜,就沿着河滨路散步,河滨路的尽头是一片野杏林,最后他们双双消失在这片林子里。
用赵家良的话说,柳如一不是那种放荡的女人,她仅仅只是将打牌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人嘛,总得找条活路不是?而跟他的联系,也仅仅只是出于感情的需要。在赵家良眼里,这个女人总是对的。这说明他是站在她那一边的,他跟她缠得那么紧。
与其说是柳如一将他拉进了那个麻将圈子,还不如说是他自己钻进去的。很快,他们便同场赌钱。打麻将,扎金花,猜九点。
不用说,他们之间形成了默契。比如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出一张牌,让她满贯听牌。比如,她也会吓走所有的对手,让他战到最后,独吞场上的钞票。他们会故意小输一两回,然后猛杀一把。得手后,去来一回分红。他们分得很公平,二一添作五,平分。她说合伙就得讲个公平。事实上赵家良心里明白,这是有意让着他的意思。这让他感激不已。然后他们会在小包间喝两口,聊聊天,——聊的内容当然跟赌钱有关,这会让他们在赌场上更默契。再然后,会去那片野杏林。
柳如一偏爱野杏林那个地方,她说那里的草地比酒店的席梦思更撩人。赵家良没有否认,他更迷恋柳如一的身体,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他明知这是见不得人的事,但乐在其中,从未想过对不起自己的老婆江小羽。
再接着说赌博的事吧。
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起赢了很多钱,也因此让赵家良赢了不少。于是,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几乎成天呆在万家巷。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赵家良找到了一种成就感。想想也是啊,当一个人很容易就能弄到大把钱时,还有什么会更令他兴奋!
江小羽在听赵家良讲这些事时,感觉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一下一下地割着她心口上的肉。
从头到尾,她都斜靠在沙发里,手指轻轻地拨动着指甲剪,眼睛无神地望着别处,看上去平静又无聊。赵家良的叙说,仿佛与己无关。与以往暴躁的个性相比,这个时候的江小羽多少有些反常。
找到柳如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万家巷不远,就在河边上。那是一片老城区,刘家庙,伍家祠,临河街,蚂蟥巷,都在那里,一条条古老的小街纵横交错,像一座巨大而幽深的迷宫。
来到这里江小羽才知道,这里分布着许多麻将馆,几乎每家每户都摆着一张麻将桌,每条街上都能听到麻将机呼呼拉拉转动的声音,当然也夹杂着男人女人的调笑和尖叫。较之新城区充满现代气息的繁华,这里滋长着另一种扭曲的热闹,比如污浊的空气,刺鼻的酒味,满地的纸片、烟头和瓜子壳,比如颓败、贪婪、色情等等。
在一家冷清的麻将馆,她坐下来,这时已有人客客气气地端来一杯上好的茶。
您面生啊!那是个中年男人。
是,我来得少。你这儿怎么没什么人?她喝了一口茶。
是啊,没人罩着,不就得挨饿吗!
她装作不解地看着那人。那人接着说,看看那几家吧,人多得没地儿坐,生意好得拿篓子装钱,为什么,不就是那个婆娘在作怪吗?
婆娘?
柳如一你都不知道啊?那几家都有她的股,你说生意能不好吗?
一个女人,哪儿有这么大能耐?
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上边有人呢。那人神秘地用手向上指了指,我们这些没名没姓的小麻将馆,动不动就叫人给抄了。她的那几家赌得大,一点也不避嫌,却平安无事。你说,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
江小羽并不否认她去过万家巷,她甚至承认,她在那儿还碰到过柳如一。柳如一从一家麻将馆出来,提着真皮包,像是出去办事,比如存钱或者取钱什么的,走得很快。经过江小羽对面,还冲她笑了笑,似乎她们曾经认识。她笑得妩媚,以至于江小羽都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直到她离开很久,她还深信,如果哪个男人对这样的笑无动于衷,一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也深信,自己的男人赵家良一定是叫这种风情无限的笑容给吞没了。
柳如一刚过去,上茶的那个男人指着她的背影不屑地说,瞧,这就是柳如一,你看,是不是个活妖精!
谁也不知道,那个上午江小羽在万家巷想了些什么,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总之,她对柳如一的憎恶一定达到极点。当然,也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晚上发生在万家巷的纵火案跟她有没有直接关系。是的,就在这个晚上,一场大火将万家巷付之一炬。之所以将这件事定性为“案件”,是因为在这片老街区的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这么凶猛的失火事件。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木质结构,街坊们生来就十分注意防火,即使偶然失火,也很快被扑灭,不会一下子烧毁整条老街。更要命的是,有人亲眼看见四五个地方同时起火,起火的位置都是要害部位,见火就着,人过不去,灭火也不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烧。人们分析,有人刻意要毁掉这条街,确切地说,是要烧掉街上的麻将馆。那么,麻将馆又跟谁有关?这么说就再简单不过了,这事是冲着柳如一来的。
纵火案后,柳如一就不见了。有人推测,那个晚上她是不是葬身火海了?但这种猜想很快就被推翻了,警察没有找到有关死人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次失火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柳如一到底去了哪里?有人说,这女人输了钱,亏大了,纵火为自己制造一个人死账灭的现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她卷了巨款,纵火后逃逸了。总之,这事跟她柳如一有直接联系。
事后,警察找过江小羽,但没有问出个头绪来。
再来说说赵家良。万家巷被烧了,柳如一也不见了,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私下里找过柳如一。他断定,柳如一并没有抛弃他,只是出了点小麻烦,比如钱的问题。到出事那天,她已经从他手上拿走了十万元。他认为这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可悲的是,直到这时他也没想明白,柳如一从开始就在玩他,她看中的只是他手中的钱。
他甚至认为,万家巷失火这件事如果真是柳如一所为,也是迫不得已。不错,她跟很多男人都有来往,都有金钱关系。如果真是拿钱走人,并制造这起纵火事件,在道理上说不通。她不需要这么做,以她在万家巷的信誉,一点小钱是难不倒她的,犯不着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无论怎么说,警察断定这场大火并没有伤到人,对他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说明柳如一还活着。
当江小羽发现这件事时,他都老老实实承认了。这里边不能排除他有后悔的成分。
小院一隅沐清风(中国画) 何阿平
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江小羽。她决定报复自
己的丈夫赵家良。一个背叛了自己的男人就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她报复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残忍。她要剪掉他的命根子。当她确定赵家良背叛自己后,这个想法就在脑子里固定下来。
于是,她准备了三把剪刀,床上当然要放一把,沙发上和洗澡间各放一把。
但是,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就在这个时候,赵家良不见了。他从外面打电话回来说,他找柳如一去了。他坦言,只有跟柳如一在一起,他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让江小羽备受打击,她认为这是赵家良的借口。他做错了事,死不悔改,反倒将责任归结到她的头上。赵家良是脑子进水了。
江小羽的故事还没有完,至于她和赵家良的恩怨怎样继续发展,谁也无法预料。讲到这里,妻子看着我,缓缓地说,哪天有空你去万家巷看看,整条街都烧没了。
我说,烧就烧了,我可没闲工夫去那个鬼地方。
你就不想看看那个叫柳如一的女人落了个什么下场?
不就是失踪了吗?我反问一句。
一条好好的老街因她而没了,你不觉得她就应该得到报应吗?
报应?如果赵家良、柳如一没搞在一起,还会有张家良、李如一,王家良、黄如一搞在一起,如果人人都因此遭报应,这世上岂不永无宁日?话没说完,我忽然觉得,自己已经心虚了。
你好像挺为他们抱不平?
见怪不怪了。再说,关我什么事!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去了那里。我想证实一下,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万家巷我很熟,几年前我们到河边小餐馆吃饭,经常路过那里。她的话一点不假,万家巷真的不存在了,毁于一场大火。我去的时候,几位工人正在收拾现场,看样子是要重建这条老街。
我悄声问一位闲坐的老人,知道柳如一么?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说,柳如一,我们这街上没有姓柳的,姓张姓李的倒蛮多。
我是说,这条街上麻将馆里有一个女的,很出名的。我不甘心,吞吞吐吐地问。
麻将馆,女的?哼,你是不是搞错了,这街上哪儿有什么麻将馆?真是!
我碰了一鼻子灰,恹恹地离开了。
从万家巷出来,我又去了环城小区,想打听有没有江小羽这个人。但在半路上,又放弃了:其实有没有江小羽这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妻子为什么要给我讲关于江小羽的故事,她是否发现了什么而有意为之?还有,柳如一,刘玉意,在她看来根本就是一个人?
晚上,我又打电话约刘玉意见面。
她说不方便出门,不出来算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走到哪里,都觉得那个女人跟着她,真是阴魂不散。我说,那好,我到你住的地方来吧。她连连说,别别,我现在发现她无处不在,你来了反而更遭。
这是什么逻辑?这事一定跟我有关系吗?我好说歹说,她终于答应出来,前提是我一定要先去桃花林等她,要不然她会更害怕。我只好提前半个钟头到了那里。她终于来了,还是那样紧张兮兮的。她说,你再别约我好不好,我都快疯掉了。
你真确定有这么一个人在跟踪你?我问。
可不是,我都不敢出门了。她像一个幽灵,我走哪儿她跟哪儿,有几回我几乎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回过头来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可怕不可怕?
没影儿的事,是你自己想多了!我不屑地说。
你不信?真是!这几天她变本加厉了,我躲在屋里不出来,她竟跑到我窗子下去了。我在屋里看电视,明明看到窗外站着一个人,仔细看
时,又没有。我不理她,一会她又出现了。尤其是在晚上,我把门窗都拴得死死的,她又来了,还在摸门摸窗,甚至听到金属撬匙孔的声音,弄得我心里直发毛。为此我整夜整夜睡不好觉,我感到自己都快给逼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中邪了?要不,是遭报应了?
报应?她也提到了报应,这难道又是巧合
吗?我问自己。什么报应!你又没做什么坏事。你说,我跟你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还不是
坏事!
废话,我们只不过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一点情趣,算什么罪过?我有些不耐烦了,差点叫了起来。
你说得轻巧,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我成天都在想,我们的事要么给人发现了,要么就是上天在惩罚我了。
她说着,竟咽咽地哭了。
我知道自己过火了,伸手抱着她,为她擦拭眼泪,说,你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身体出毛病了。
她固执地说,我没毛病,我好得很。说着竟从我怀里挣了出来。她生气了。待她稍稍冷静一下,我说,知不知道万家
巷?她点点头说,提它干什么?它被烧了,就在几天前。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还在生
气。
我知道,我们没法再谈下去了。我说,算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点别的吧。说着,我又抱住了她。这一回她很听话,温驯地靠了过来。我在她身上摸索着,手指慢慢接触她的身体。这样的夜晚,我们总得干点什么。不是吗?忽然,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女人到
底是谁?我感到,她浑身都在颤抖。我们再次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我又打了刘玉意的电话,想安慰一下她。但是,语音提示我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直觉告诉我,出事了。我急急忙忙地去了她住的地方,但那儿已经没人了。房东告诉我,她已经好多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还回不回来住。
我惊呆了。难道,她也失踪了?
跟上回一样,我回去得很早。让我意外的是,妻子已经睡了。
我悄悄去了阳台,临窗而立,呆呆地望着宁静的夜空。这时,我突然想抽支烟,于是又返回客厅,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当我将它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竟然觉得烟的滋味是如此美妙。在烟雾缠绕中,我清晰断定,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柳如一,也没有江小羽和赵家良。这么想着,我心里一惊,烟头差一点烫了手。
我又想到了刘玉意,她的变化让人捉摸不透。如果真有人跟踪她,这个人是谁呢?她失踪又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是死还是活?我越想越觉得害怕,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回到床上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轻手轻脚地钻进被子,准备蒙头睡觉。
怎么现在才回来?妻子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别人等你老半天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么?她埋怨着,一只手摸了过来,身体也靠拢我。
这些天你怎么了,碰都不碰我一下?她搂着我,嘴唇在我的脸上摩挲,气息热呼呼的。是不是在外打野食了,嗯?她挑逗着,用身体挤压我。
我努力应和着。许久,身体才有了反应。她敏感地觉察到了我的变化,动作更具挑逗性。我翻过身来,将她紧紧地压在下面,她快活地呻吟着。
我们疯狂地翻滚,席梦思发出吱吱的叫声。这时,床单下有一块硬物碰到我的手臂,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天啊,竟是一把冰凉的剪刀!
我惊得啊地一声坐了起来,突然感到下边一阵剧痛,像挨了一剪子似的。我本能地捂着下边,痛苦地扭动。
你怎么了?老婆松开我,不解地问。
剪刀,剪刀!我惊恐地叫着。
什么?哪儿来的剪刀?她疑惑地看着我,迅速在床上翻找。但是找遍每一个角落,什么也没有。床上怎么会有剪刀呢?她自语着,又跑到床下去找。
我蜷缩着身体,看着一脸茫然的妻子:我明明抓住它的,怎么会没有呢?
算了算了,不找了,快让我瞧瞧,是不是伤着哪儿了?她爬过来,焦急地想看个究竟。
我战战兢兢地松开双手,只听她说,没有啊,这不好好的?
这事还没有过去。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准备为病人做一例阑尾割除手术。更衣,消毒,检查手套衣帽,术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我举着双手平静地来到病人身边。这时,助手双手将一只白色的盘子递到我面前。放在往常,我会熟练地拿起工具,如剪刀——又是剪刀,或者手术刀,开始工作。是的,为病人切除痛苦就是我的工作。问题是这一回不同,当我将手伸向那把再熟悉不过的手术刀时,恍惚间它呼地一下飞过来,直直的插入我的身体。我的下边一阵剧痛,跟着双眼一黑,卟地一声直直地倒下去。
从此以后,我经常无由来地发病。一把叉子,别针,水果刀什么的,都让我剧痛钻心,生不如死。
我知道这种病的症结在哪里,我叫它剪刀过敏症。
我不能再为病人做手术了,只得请假在家休息。
当科室主任听我吞吞吐吐地说完请假事由后,疑惑地盯了我许久,才开口说话。他说,不对呀,最近我们科室有几个人都得了类似的病,怕铁器,怕药瓶子,怕化验单,发病时跟你一模一样,疼,钻心地疼,没药可治,来得快去得也快。来时疼得要死要活,去了又跟个好人似的,你说怪不怪?只说有花粉过敏,甲醛过敏,淀粉过敏什么的,还从没听说过见个什么就过敏的,这是不是太过敏了?照这样下去,我们这儿不是要关门了!
主任最后又说,他们来请假时,一再求我保密,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唉,有事请假,正常,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不过,你放心,虽然你没这么说,我还是要跟你说,我会保密的。放心好了!
我以为主任不高兴,在说风凉话给我听,为此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后来才知道,我又错了。
在家里呆了几天,我闷得慌,就给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陪陪我。
谁知他在电话里说,哥呀,我哪儿敢出门呀,我病了。
我说,放屁,哪这么巧,我们俩病到一块了!
他说真的,哥,我怕香水味,一闻到这东西我就身上疼,——知道不,就是下边这东西疼,疼得直打滚,那可真要命啊,我想都不敢想了。哥,你说这大街上哪儿没个香水味?这有女人的地方就有香水的味道,你说我还不犯病?你就饶了我吧,我还是呆在家里好,家里清静!
这回,我相信了主任的话。这么说,一定有很多人得了这种怪病。比如在我们单位里,比如在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地方,比如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隐藏着这种过敏症患者。他们大量存在,却又不为人知。他们像我一样,看上去好端端的,甚至仪表堂堂,怎么看都是一个再正常、再健康不过的人,而骨子里却是一个十足的病人,而且经常发病,苦不堪言,无药可治。
唉,难道这种病也会相互传染吗?要不,怎么会有那多人得这种怪病?
那么,我得的这种病,是他们传染给我的,还是我传染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