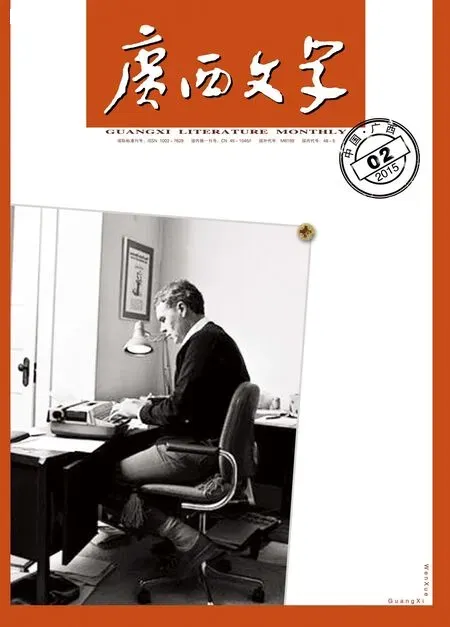距 离
短篇小说·苏 玫/著

我可能病了,杨可眉对子君说。她眼神无辜迷离,眉心微蹙。我心里有一团火,那火有时很旺,有时像火灰下的暗红火星,烧得我好一段时间睡不沉,食无欲,手有时无故地打抖。
十年了,杨可眉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狭窄、封闭的空间和子君说话,这个习惯随着子君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它在她心里越是枝繁叶茂。子君变成了一只耳朵,在她需要的时候,当她把心里的话说出声的时候,子君就在她脸颊边。她总能感觉到子君的温热和平稳的呼吸。她一个人说话,有时恨恨地说,有时调皮地说,有时哀伤地说,有时也会唱一两句歌出来,有时连自己也没听清,会重复一两次,脸上的表情总是随着倾诉和情绪千变万化、生动无比。
但我没疯,虽然我一直认为你不曾死去。我常常在人越多的地方,心神分散得越厉害,好像魂魄四分五裂地飘浮在空中,连人和我打招呼,我也只感到是一阵风掠过。这几个月这种状态时有时无,时重时轻。
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越来越喜欢一个人胡乱地开车没有方向地行进。在灌满车厢的那些无比忧愁和发散的悲伤音乐中,那些分散在空中的魂魄一点点、一点点地回归到我的肉身。
此时,南方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矮山土坡间已经有了浅黄、青黄、金黄等各种以黄色为主调的大片稻田在车窗外快速地出现消失、消失出现,黄昏的余晖渐渐湮灭在浓浓密密的桉树、枞树、榕树的浓密枝叶中……
四天,田子陪杨可眉在清远。两人在一起有时话很多,有时话很少。
在清远的最后一晚,微醺的两人在寒意逼人的夜里睡在一张白色双人床的两边。田子睡得很沉,发出小小鼾声。可眉和她在被子里保持着两个拳头的距离。
杨可眉好一阵睡不着,先想自己的悲酸,然后幻想身边的田子是个男人,其次承认田子是个女人,最后觉得即使田子是女人,她也很想让她抱抱自己。她只是想想而已。
没离婚的田子已经习惯了单身生活,她一人带着女儿过得很坚强。她很早就举例子说,她有个离婚的女友也很坚强。她越这么说,杨可眉越觉得必定是很难的事情要面临,一个人才要坚强。越那么想,杨可眉心里就越怕。杨可眉一直不敢对田子说出心底的怕,她怕田子不耐烦她的悲哀。
在杨可眉眼里,坚强的田子却是忧郁的、灰色的,那些忧郁和灰色从她的肢体、眼神、话语、褪色的头花、布满灰尘和划痕的皮鞋中散发而出。田子偶尔会说想逃离生活的那个大城市。
杨可眉和田子在一起,尽量把持自己的情绪。尽管如此,还是崩溃了两次,泪流不止。
每次流泪,田子都离杨可眉一米多,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看着杨可眉,连拍拍杨可眉的肩膀这样的动作都没有。
子君,我知道,田子其实是在看她自己。现在的我,不过是在走她走过的路。那些逝去的伤痛,又上演在她的眼前。她不靠前不说话,有些抗拒甚至有些嫌弃地站在那里,其实她害怕。
第一天,当金黄色的夕阳铺满清远的时候,田子站在旅馆的浴室镜子前。杨可眉看见镜子里那个一头清汤挂面般的长发里脸颊消瘦,下巴削尖,眼角有些下垂,但眉目依然清秀的中年女子,满脸涨红,有些羞怯地对自己说着黑裙子的秘密。
虚无,虚无的尽头还是虚无,田子叹息道。虽然悲哀和生气,但是田子并不打算就此放手和黑裙子有关的男人。她说,这年头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动情不容易。田子收紧有点消瘦的削肩,将两只手臂缠绕在胸前,眼神忧伤,直挺挺一动不动地站在浴室里。
杨可眉一把抢过田子揣在手里的那条黑裙子。那条一年没洗还带有一些印记和味道的薄如轻纱的黑裙子,一股脑儿被丢到了机械无情转动的洗衣机里。
田子像一个被突然抽走脚下地毯的人,狠狠地踉跄摔倒,脸色惨白。
看着在滚筒洗衣机里飘舞如黑蝴蝶的裙子,杨可眉突然有种想打破眼前镜子的冲动,这样镜子里的清秀女人和突兀出现的面无表情眉头紧蹙的女人就可以四分五裂了。但她也仅想想而已。她无力地僵直地站在田子身后。
那条脏了一年却被田子收藏的黑裙子洗过以后依然还是黑裙子。它的历史是无法洗白的。
两个人都像受了重创一样在浴室里喘息。
田子突然报复一样恶毒地说:你的子君呢?你收藏的是什么?他已经死了十年!
我站在那里,突然哗哗地流泪。田子看着镜子里流泪的我,无动于衷。拿起行李,我走出了房门。
哼,子君。我觉得子君你其实就是空气,相当于一个屁。我知道子君你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又是一脸的无赖。我曾经爱过你,子君,一个屁一样的无赖。就算你带着插入胸口的匕首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却在我的世界里得到永生,但永生以后的你是你又不是你,具体是谁,我也搞不懂。
我从没有握过你胸前的匕首,但我能感觉到手柄的纹路和刀锋的冰冷。他们说那把匕首有两个拳头的长度。
陈古深是睡过黑裙子的那个男人,他有家室。
子君,今晚月光如银。你猜我在黑夜的清远干什么,爬山!小镇的旁边有一座山,我对夜晚的山充满了攀爬的欲望。我不是一个人,还有房东的女儿,她从见到我的第一天就开始喜欢我。我唤了一声:走咯!我们爬山去咯!现在她一只手正拿巧克力放在舌尖上忘情地舔着,唇周一圈的黑印,一只手放进了我的手心,暖而柔嫩。
女孩十岁,介于懵懂和有知之间的年纪,脑子还是个小小孩,身体已经出挑少女雏形,高挑,胸前有一些微微的凸起。房东(她妈妈)很乐意让她陪我去爬夜山。女孩瓜子脸,额头有一些青春痘,马尾辫,眼角外挑的桃花眼大而明亮,很乖巧,腼腆,安静,不爱说话。我喜欢这样的女孩,我猜想她也有一颗敏锐柔软的心。
从到清远的第一晚开始,我和田子二十年的发小和闺蜜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之间多了一些真实的恶毒、刻薄和嫌弃。直到第三晚,我们都没有碰面,我多开了一个房。
她大概喝酒去了。像她那样看上去保守的女人夜晚去求醉,你第一次听到很诧异。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改变,静的时候像木乃伊,疯的时候像斗牛士对面的那头牛。当然她不是牛,我说的是那种疯劲,或者说像脱缰的野马,也很恰当。
夜晚的山深黛色,只有起伏的山影和浓黑的一片又一片的树林。路是石阶路,时缓时陡,没有扶栏。路边高过人的茅草长得很茂盛,一簇簇放射状的松针长在枞树的树枝上高高伸过头顶。淡紫色的小雏菊模模糊糊地这三朵那五朵地在两侧的矮草中冒出头来。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女孩闲聊。慢慢地我们的话语被喘息取代。
大声地喘息,我感觉到心脏在胸膛里快速收缩,汗水开始爬出额头、颈下、肩背。
我问我自己心里有没有在爬山的过程中因为身体的负累而心里感觉轻松了一些。人们常常用运动来提高自己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以提高体质和释放心理的一些负面情绪。爬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开始觉得这座山实在太高了,我累得不行。女孩告诉我,上到山顶要一个小时。
好累啊!我停下,弯腰双手扶膝,喘着大气对身边的女孩说。山间突然有白鸟飞过,快得像闪电,从一处树林飞入另一处树林。女孩骄傲地加快攀登的脚步:我觉得一点也不累,我超过你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被一个十岁的女孩挑衅,自然是无语的状态。我跟着女孩的身影,默默地随行。月儿半圆,明亮洁白。夜空里没有一丝云彩。
我想到了我为什么在田子提到子君你的那句话的时候,突然落泪,我自己也想知道原因。子君你的死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个伤疤。你的死期出现在你我幸福到来的路上,群生(我的远房表兄,介绍我俩认识的人)拿着你的离婚证一身血迹地敲开我的房门,说是车祸;可是多年以后,又有人说你的胸口插了一把匕首。一路的攀爬中,山风涤荡了山林,也涤荡着我的思绪,我此刻觉得自己为了一种沉重的情绪哭泣,是一件很让自己羞辱和恼怒的事。
子君你的在或不在,都跟你的肉体无关了。
田子陪我来清远的目的并不是为你。为了另一个正在消失的男性肉体,我愚笨到为了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肉体感觉自己似乎快失去了整个世界。我渐渐明白为什么要来到清远,也许不过就是让这次夜风涤荡心灵,责问自己: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被肉体所困住?为一条没有生命的黑裙子生气?为这个世界数不尽的罪恶中说不出单位的微小部分而愤怒?我一边爬山,一边独自默默地摇头,将心里的积怨转换成一声叹息吐露在风中。
山顶!阿姨你看!女孩看到山顶脚步愈发轻快起来,与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我又觉得自己不是为了涤荡什么心灵来到这里,所谓的生气和哭泣,都是那么的肤浅。也许,我自己就是一座山,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什么子君,什么另一个正在消失的男性肉体,他们都像山风一样,也许去了又来,但总归属于自然。我呢,不够独立和坚强。对,坚强,田子说得没错,坚强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才对,而不是让人惧怕。
女孩站到了山顶上,皓月当空,风儿吹起了她的长发和衣衫。她也不爱穿裙子,和子君你我的孩子一样,都因为身体的一些变化羞于穿裹住上身和裸露腿部的裙子。
子君,如果说你对我和孩子最大的伤害是什么,那就是你至死都不知道我和你拥有了一个孩子,她是女孩,也十岁了,和山顶的女孩很相像。
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没有我,子君你也许就不会死了。人生如能倒退关键的几步,人们都不应该被所谓的爱情所伤。可惜,人生路有去无回。
忘了吧,放了吧。蓝夜空,白月亮,黛山野,天地之间,只有我和女孩。我牵起女孩的手,要带她下山。她甩开手,要自己走。
啊!杨可眉!群生夸张地张开大嘴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我和田子面前。他胖了很多,头发少了,腮帮鼓了,眼睛小了,牙齿有烟垢,脚短了,肚子大了。十年了,他就像一个报幕员一样,时不时出现在我生活对面的舞台红幕布前,先是头、脚,才是整个身体的呈现。他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呢?表示他和我都存在于同一个时代?标志着一些故事曾经发生过?
子君,群生知道我的近况,他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来清远。我口未开,笑未出,眼泪就迸了出来,好像我眼底藏了一个随时溃堤的水库,它哗哗地奔流而下。群生身边有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两三个不认识的女人,他们被我说来就来的“哭戏”震住了,他们像被魔法定住一样围着我。
群生拍拍我,和离我一米远安静无语的田子打招呼,田子,怎么也来了?田子耸耸肩,为什么不呢?
群生伸手揽住我的肩膀,带我走出人圈。他问我,你还有多少路要走?我渐渐止住了眼泪的堤坝,说,应该快了。他说,那就别哭了,别为不值得的哭泣。我抽泣着说,眼泪好像也是一种药。群生咧开了嘴笑,傻样儿!我也傻兮兮扑哧地笑了。
群生欲言又止,田子……
我说,我知道,没事。群生疑惑地离去。
我和田子直到第四天的清晨,两个人才互相说了一些致歉的话语,然后像一对真正结伴同游的好闺蜜一样游览了清远。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我们该做点游客要做的事。
和田子走在一起,我还是无法忘记黑裙子。我和她也不能无话可说地游览下去。
我告诉她,我几个月前结婚了,有个男人接纳了我和我的孩子。田子很惊喜地看着我,热烈地恭喜我的幸福隐婚,重新用闺蜜的亲密眼光注视着我,好像我吐露了我的秘密,相当于重新接受了她到达我心里的位置。
我又告诉她,我准备离婚了。她一脸的惊愕。我耸耸肩挑挑眉摊开手,说,就这样。我想做出一个很轻松的表达,虽然说完了我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假。
像我以前一样吗?有人消失了?田子问。我告诉她,差不多。
慢慢会好的,田子安慰我说。我没有接话。我知道。我也知道一个精神王国毁灭具有的杀伤力。
我没有告诉她,我丈夫是陈古深。
我原来不确定黑裙子是不是她的,但田子的黑裙子真的很像陈古深手机照片里的那件。我一直不想知道答案,尽管这是一个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时代。
但到清远的第一天,田子已经告诉我了,陈古深是她的什么人。这个距离我一百公里,一年和我见面十来次,相好二十年的发小,我们之间的话题有些说有些不说,一起隐藏的话题里同时隐藏了同一个男人。陈古深的名字,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的时候,击中了我内心隐藏许久的炸弹,当时我和田子的身体相距两个拳头的距离。陈古深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不是没有发生故事的可能。
但是不管是不是田子,陈古深都一样要离开我的精神王国,他甚至比不上逝去肉身的子君你。虽然我依然悲伤,但我相信这是短暂的。
田子问,没事吧?我说,没事,我们去喝两杯吧。
子君,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里有一句话: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反抗不由我们选择的人类处境。我隐约觉得自己心里是赞同这句话的。
我偶尔还是会一个人驾着车在青山绿水间,犹如一道火光穿梭在时光里,但我逐渐不再喜欢这种身体被灵魂追赶的感觉。我想,有些东西需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