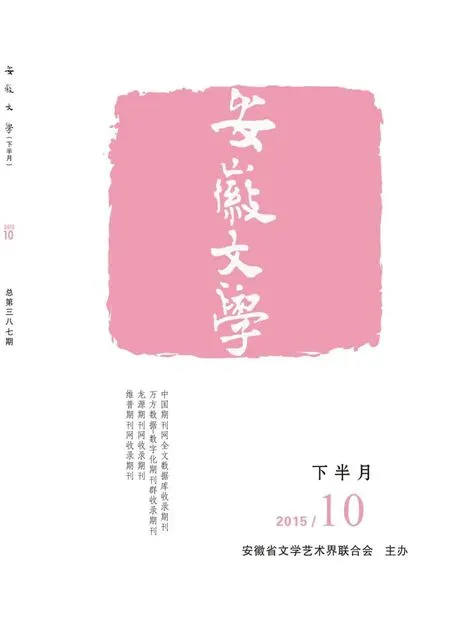从叙述距离理论角度分析茨威格短篇小说
胡晓萍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从叙述距离理论角度分析茨威格短篇小说
胡晓萍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摘要:本文以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叙述距离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茨威格如何在小说文本中采取多种距离调控手段以达到和读者的默契交流,帮助读者进一步把握作家的叙事意图。
关键词:叙述距离理论茨威格叙述技巧叙事意图
一、引言
布斯(Booth)说,作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消除隐含作者的观念与读者观念之间的任何距离”[1],但通常情况下,距离总会存在的。因此,在小说创作中,作家必须通过各种叙事技巧的精心设计,努力构建一个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三个叙述主体之间的理想距离,从而让作品为读者接受,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小说本质上就是作家对读者进行距离控制的系统”。布斯还提出了许多距离控制的具体方法,本文将聚焦于茨威格小说的叙事技巧,以及他如何控制叙述距离把读者引入他的虚构世界,帮助小说整体构思的逐渐展开。
(一)主人公反映自己故事的权利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以善于描写女性形象而著称。他的小说创作细腻地表现了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少女对一个浪荡子一见倾心,像妓女般地委身于他,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马来狂人》中的主人公由于内心愧疚及瞬间的冲动而不惜以生命徇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出身名门、年逾不惑的孀居女人,竟然为年轻赌徒的一双手神魂颠倒,以身相许,甚至想到与他浪迹天涯;《情感的迷惘》中享有声望的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个同性恋者,为情欲所逼竟偷偷出没在下流龌龊的场所,最后导致身败名裂。这些人物美丽多姿、感情奔放但却命运凄惨,即使从文学虚构的视角看也是极端的典型。如何说服读者接受故事中的人物,消除读者与隐含作者观念之间的距离是需要作家采用一定的修辞手段(即方法、技巧和策略)的。一般说,当人物被用第一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最近,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最近,因为第一人称叙述“使叙述者与人物合一,就使读者如听当事人侃侃而谈,内容均为叙述者的亲见、亲闻、亲感,故鲜明生动,真切感人”[2];第三人称,次之;第二人称,最远。作家对人称的选择,是决定叙述距离的关键要素之一。
茨威格喜欢第一人称叙述,“由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3]”,这是最典型的茨威格叙事风格。陌生女人第一次见到作家R就“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只对你的存在感兴趣![4]”长大成人后竟像妓女般地委身于他、抚养他的私生子达11年,最后儿子已经死去,自己也要离开人世之际,她写信给从未谋面的R诉说一切,只是请他相信“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这是怎样一个“陌生”女人啊!用常人的感情和道德准则来衡量她是不合适的。读者不禁会想,“这样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存在吗?”然而,读者却从未怀疑过它在陌生女人身上的存在感。笔者认为,这和书信体这种叙事方式不无关系。书信体小说的格局通常是由女主人公用书信文本以私下的受述者为对象,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佐证了女主人公内心感情真实酣畅地表达,字里行间充盈着最温柔的同情、最真切的理解和最后的光明,极具有感染力。读者看到了这个连名字都没有透露的女人不仅是最狂热和最痴情的情人,而且也是最温柔、最慈爱的母亲,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油然而生。在其他许多作品中,茨威格同样赋予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倾诉心底的苦恼,希望主人公的自叙能博得读者的信任和同情,拉近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二)不可靠叙述者
布斯是这么评论叙述者的可靠性:“当叙述者所说所做与作家的观念(也就是隐含作者的旨意)一致的时候,就可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可靠叙述者的行为、思想观念能代表着隐含作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较近;不可靠叙述者的观念则不一定代表着隐含作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较远。不可靠叙述者的加入不仅拉大了叙述者、隐含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也让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无形之中变大了[5]。
茨威格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品中不止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通常有两个或者三个,外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故事)内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形成了叙述层次,内部的叙述者则因为必须通过外围的叙述者叙事成了不可靠叙述者[6]。从叙事学上说,这种有叙述层次的叙事方式会产生一种拉开作者与故事、与读者距离的间离效果。不可靠叙述者在茨威格多部作品中都能找到,如为一个登徒子抚养私生子的卖笑女郎,头脑发昏到与赌徒浪迹天涯的老太太,被遣散到印度殖民地的“癫狂患者”医生以及未曾有过任何职业,没有固定住所的高雅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人等等。瑞蒙·凯南指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主要源于叙述者有限的认识,个人的参与以及有问题的价值体系”。不可靠叙述者作为叙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只能叙述本角色知道的内容;同样,不可靠叙述者的文本或评论也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他们对故事所作的描述并不是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如果让不可靠叙述者直接对读者叙事,他们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那么可靠叙述者的转述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和读者的接受度。布斯分析作者需要不可靠叙述者加入的原因:“如果说赋予主人公以反映他自己故事的权利便能够保证获得读者的同情,那么,收回这种权利而转予另一个人物,则能防止过分的认同。”也就是说,茨威格通过一个个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立有效地调节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帮助作者与他塑造的主人公划清界限,避免公众读者将作家与不可靠叙述者等同起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对该叙述者的距离相应地会发生变化,从最初的信任到不信任到信任,最后还是不信任,叙述距离的忽远忽近会产生“某种真实”的“效果渐变与叠加”,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不可靠叙述来达到讽刺的效果。
(三)作家的声音
布斯认为,在小说中提出行动本身就是作家的一种介入,完全去掉作家的声音是不可能的。“虽然作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在小说中存在着作家多种的声音,譬如提供事件的基本概况,从而营造一种真实的画面感,制造细节、发出评论、强化观念,从而突出整个事件的社会意义和写作目的。
作家很多情况下并不属于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评价或者感慨肯定会把读者从故事内带到故事外,读者与书中的人物自然地有了距离。假定故事内的叙述者刻意让读者无限接近人物,就会将作家的声音隐藏起来,或者降到最低值。我们知道,书信体这种叙事形式能帮助作家与主人公划清界限,避免公众读者将作家与叙述者等同起来。当陌生女人用书信追忆往事时,作家没有任何机会与主人公产生关联,也不能干涉叙述者的叙述,作家的声音被降到最小值;但作家并非不在,他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叙述控制读者对故事情感介入的深浅或情感距离的远近,控制着读者的阅读感受。当读者读道,“请耐心点,亲爱的,等我请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感到厌倦啊!”读者会惊讶于她的狂热和痴情,对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为了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过上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陌生女人卖身了,“我没有羞耻感”,“你不会鄙视我”,因为“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多么温柔、慈爱的母亲!读者得以在不受作者干扰的环境下和叙述者一起近距离地观察人物的一言一行,越来越投入到人物的情感中并引起情感的共鸣,读者仿佛也和R一样“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心头,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人隐约出现了。
当然,不是在每一部作品中作家的声音都是如此深地隐藏在幕后,作家有时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一种客观评价,将自己的观念和细节联系起来,从而突出事件发生的意义。当亨丽塔太太私奔事件发生后,游客们议论纷纷,有的似乎在为私奔事件开脱,“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因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有的则斥责道,“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正经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婊子,亨丽塔太太准是这类人”。还有的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既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明明存在着”。既然如此,“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依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这些评论正是作家的声音。作家声音的出现让读者猛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读到的故事并非原汁原味,而是一个加工品,经由一个全知的讲述者精心打磨而成。布斯强调说,“进行价值与观念的介入,对小说家具有特别的诱惑,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面,那具有哲学家神气的人在沉溺于不着边际的讲演”。
二、结论
距离产生美。作家之所以在文本中精心设计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从叙事本质上说是希望现实世界通过小说叙事实现创造性的变形,使之以一种不为读者熟悉的非常态形式出现,打破读者的接受定势,从而创造出读者对小说文本的审美距离[7]。茨威格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叙述以及作家声音的介入等多种叙事技巧进行文本的距离控制,深刻描绘人物的内心矛盾、挖掘和解剖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激发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同情之心,最大程度地接受作品,并获得不一样的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 (美)W. 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黄立华.虚构的权威:《紫色》中的“女性声音”品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9(6):138-141.
[3] (奥)茨威格.茨威格[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 (奥)斯蒂芬·茨威格.斯·茨威格小说选[M].张玉书,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5]孙宁宁,李高佳.叙述距离理论观照下的儿童文学汉译:《王子与贫儿》个案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80-84
[6]曹学庆.斯蒂芬·茨威格小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2012(13).
[7]白春香.小说叙述距离的审美本质及艺术生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