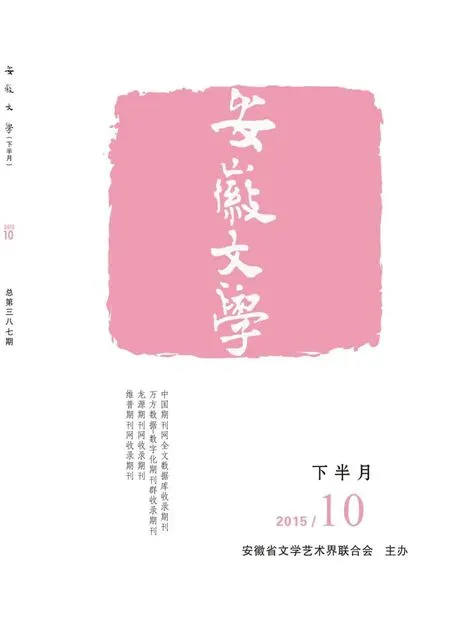《慈悲》中的互文性解读
肖书珍河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
《慈悲》中的互文性解读
肖书珍
河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
摘要:作为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于2008年发表了她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第九部小说《慈悲》,莫里森第一次把她的目光投向了十七世纪奴隶制还未完全建立的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投向了所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体现了她对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人生的思考,表明了莫里森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新探索。本文主要从小说《慈悲》和作者的互文性,历史的互文性,其他文本的互文性的表现形态来说明小说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慈悲》文化身份互文性
一、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标识性术语。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Prince)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互文性理论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强调不能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否则它也将落入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互文性理论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也可称之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地形式研究的层面,而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文学分析中互文理论的运用使文学评论跳出了文学本身,将作者、历史、文化等因素含纳入对文学作品的解读。
二、莫里森多重文化身份对《慈悲》的影响
莫里森的双重文化身份决定着其作品的创作目的。文化身份受到传统、语言、宗教、思维模式、社会价值观、地域、性别和美学等因素的影响,文化本身就是开放的,不断变的,双重文化身份指的是同时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身份。后殖民主义学者Edward W. Said(1991),Homi Bhabha(1997)均详细解析了多重文化身份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和负面影响。一方面,拥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人会有种身份危机感,他们不知道到底拥有哪种身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多种文化身份也能让他们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吸收新的文化。莫里森无疑把双重文化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一)恢复非洲文化和历史的使命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从童年时代就耳濡目染了无数有关黑人的故事,对传统黑人文化充满尊敬,为她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由于黑人长期受到白人的奴役和歧视,黑人们被强制学习和信奉殖民文化和宗教,他们的非洲文化和历史逐步被边缘化和篡改。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有官方书籍和文献开始揭示真实的奴隶历史。为了挽救她的同胞的身份危机和缺失,为了还原真实的黑人历史,莫里森不遗余力担负起宣扬非洲文化和历史的使命。莫里森始终关注着美国黑人种族的现实和未来。黑人如何摆脱心灵的重负,进而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自信,这是莫里森诸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一条线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莫里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慈悲》中,莫里森借助黑人奴隶弗洛伦斯和她母亲之口反复提到“羽毛”。“羽毛”和“鸟”象征着“飞翔”,“黑人会飞翔”是非洲一古老传说。弗洛伦斯出生和生长在新大陆,对非洲文化一无所知,但依靠骨子里存留的一点儿非洲文化的记忆,凭借本能,她竟能读懂只有非洲人才能读懂的标记,一次次转危为安,找回自己的非洲文化身份。莫里森想通过弗洛伦斯的故事告诉读者:只有那些回归传统文化的非洲人才能取得独立的自我。
(二)创作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能力
既然莫里森出生成长在美国,不可否认,白人文化对莫里森也有着极深地影响。如果说莫里森拥有的黑人文化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的白人文化身份使得她呼吁恢复黑人文化和历史的声音得以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得到认可。
作为一部较成熟的作品,《慈悲》反映了莫里森的许多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想,如不确定性和多重叙事等。在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影响下,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同时也无法确定谁才是主要人物。此外,拯救了女主人热宝贝卡卡性命和俘获了弗洛伦斯芳心的铁匠的名字自始至终是个谜;莫里森采用的多重叙事等都显示了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实际上,多重叙事的写作特点颠覆了主流话语的单一叙事,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人物都被赋予了讲述他们心声故事的权利。例如,《慈悲》中弗洛伦斯被母亲抛弃这一事件被Jacob,弗洛伦斯和她母亲三个人叙述,读者可以结合三个人物的叙述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莫里森同时是两种文化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这种多重文化意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三、与历史事件的互文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既没有完全超越时空,也没有完全再现了历史。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解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慈悲》中真实事件的移植
莫里森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女奴在向北方逃跑的过程中,为了免遭奴隶主的追捕亲手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咽喉。基于此,莫里森创作了《宠儿》,讲述一个被母亲杀死的女孩数年后又重返人间寻求母爱的故事。作为一个更成熟的作品,莫里森在《慈悲》的描写中,把这一情节作为作品的中心事件展开,移植到小说的两个故事中。她不仅关注着没有人身自由权利的黑人奴隶,还把眼光投射到每一被压迫的种族。弗洛伦斯被母亲抛弃这一情节是“杀婴”故事的第一次移植,因为被母亲抛弃,弗洛伦斯一直对母亲充满怨恨并忍受着精神折磨。直到文章最后一节,在弗洛伦斯母亲的诉说中,读者才明白为什么这位母亲央求雅各布把她女儿作为债务的一部分带走,为什么要忍受母女的永远分离。这位奴隶母亲自己遭受着庄园主的欺凌,当她觉察到庄园主又把目光投向她一天天长大的女儿时,这位母亲意识到唯一能保护女儿的是让女儿永远离开这里,尤其是当她在雅各布的目光中看到了和她的主人不一样的东西时,当得知雅各布要挑个奴隶抵债,她就把女儿推了出去。这种抛弃正是出于母亲对女儿的爱护,可弗洛伦斯却误解了母亲,母女在终生分离的痛苦中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现实中的玛格丽特和小说中弗洛伦斯的母亲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遭受到性侵之后生下的孩子;其次,他们都不得不选择和自己孩子的永远分离。唯一不同的是玛格丽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弗洛伦斯的母亲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在美国野蛮的奴隶制度下,母爱也被扭曲。
如果说弗洛伦斯和她母亲的故事表明了黑人奴隶所遭受的痛苦,那么寡妇伊令和女儿珍的遭遇则显示了美国奴隶制早期所有社会底层的妇女所忍受的痛苦折磨。寡妇伊令和她的孩子们拥有一片村里人垂涎三尺但实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女儿珍的斜眼疾被村里人视她为撒旦化身的罪证,如果珍是撒旦化身,她们一家的土地将会被剥夺,他们将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传统教义认为魔鬼是不会流血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女儿不是撒旦化身,伊令每日用鞭子抽打珍直到血流斑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和孩子,伊令不得不使女儿每日遭受肉体的折磨。这次移植显示了莫里森对美国早期残酷奴隶制的无情揭露。为了增加场景的真实性,莫里森在作品中穿插了历史事件。“六七年前,一支由黑人、土著人、白人和黑白混血人——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及契约劳工——组成的队伍发动了对抗当地乡绅阶层的战争。”战争失败后,“引发了一系列维护秩序、镇压骚乱的新法律的形成禁止解放黑奴,禁止黑人集会、旅游和携带武器;收于任何白人以任何理由杀害任何黑人的特权”。作为一位睿智的作家和思想家,莫里森同时关注着奴隶制下黑人和所有被压迫者的悲惨遭遇,显示了莫里森超越种族的思想。
(二)奴隶制度的再现
《慈悲》是一部历史作品,读者可以在作品中最大可能的了解当时美国历史。莫里森曾经说过“我试图将奴隶制和种族分开,看看它到底是何面目,看看没有种族主义影响的奴隶制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不相信那是人的本性,是人们来到这片土地的原因”。所以她塑造了十七世纪的一个多种族的大家庭:白人奴隶主,白人契约工人,黑人奴隶,黑人自由人,印第安人奴隶等。1619年,第一批运抵北美的非洲人最初并不是奴隶,随着奴隶市场的合法化,大部分黑人的身份慢慢蜕变成奴隶,但仍有少数黑人保持自由之身,文中的铁匠就是一个自由的黑人。由此看出,那时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黑人奴隶不仅仅遭受这身体的折磨和心理摧残,还忍受着缺衣少居的痛苦。《慈悲》中有诸多描写。雅各布曾经说“每当他罕见地与这些每天都要换连衣裙却给仆人们穿粗麻布的有钱人的太太们在一起时,他的丽贝卡对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更有价值。”此外,弗洛伦斯总是央求着穿鞋子,可那时黑人奴隶是没有鞋子穿的。自15世纪欧洲人殖民化美洲大陆后,很多印第安人被焚烧,烙印,遣散或被流放到偏远的北方或沦为奴隶,《慈悲》印第安人琳达的家乡瘟疫肆虐,士兵们焚烧了整个村子,幸存的琳达成为了奴隶。不仅是印第安人,许多落魄的欧洲人甚至是亚洲人都被运达美洲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由此可见,在美洲殖民早期,人的肤色并不重要,那时的种族主义还没出现。
(三)种族主义的显现
在美洲殖民早期,奴隶制是一种建立在对所有无偿劳力剥削的基础上的独立的体制,它早于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没结合一起。这种分离性可以从文中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种族主义的建立是为了保护欧洲贵族的既得利益和镇压奴隶和契约工人们的反抗。由于大量的屠杀和遣散,只有少数印第安人成为奴隶,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黑人被运往美洲并成为奴隶。由于遭受非人折磨。许多庄园爆发了反抗奴隶主的运动,给奴隶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加强奴隶制的统治,统治者制定了许多剥夺奴隶权利甚至生命的法律。所以,当弗洛伦斯承担起寻找铁匠救治瑞贝卡的任务时,她面临许多生命的危险。除了强制的法律外,统治者的教堂也被赋予了给民众洗脑的权利,人们盲目的信奉教堂教义,把患有眼疾的珍视为异类,把黑人奴隶弗洛伦斯看做非人的动物。“那些认不出我的眼睛,那些仔细检查我的身体以寻找一条尾巴…他们想看看,我的舌头是不是像蛇一样是分叉的,我的牙齿是不是为了将他们嚼碎而被挫得尖尖的”。所以大部分人的思想被教堂控制并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和统治工具。
其次,种族主义并不是美洲早期奴隶制固有的体制,它是由白人构造出来用于维护白人统治的。一些人并不赞同种族歧视,他们把黑人奴隶和其他劳工平等对待。所以说,他们接受奴隶制度但反对残酷的种族主义。《慈悲》中的神父显示了对黑奴弗洛伦斯的同情,寡妇伊玲和她女儿珍也是少数没有种族歧视群体的代表,在确认弗洛伦斯身份后,伊玲为最初的警觉态度向弗洛伦斯道了歉,并且给她拿来食物;女儿珍还帮助她脱离了危险。文中的情节表明:在美洲殖民早期,种族主义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固有成分,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抗奴隶主的压迫,为了离间一部分白人契约工人和黑人奴隶的联盟,建立在白人优越论上的种族主义形成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开始结合在一起。
通过分析《慈悲》和其他历史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影响小说创作的特定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清晰地再现了美国早期殖民历史。
参考文献
[1] Allen,Graham. Intert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2000.
[2]安玉恩.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契约工的形成及特点探析(1607-1775)[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
[3]高继海.“托尼·莫里森小说的叙述特色”[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4]胡俊.《一点慈悲》:关于‘家’的构建[J].外国文学评论,2010(3):200-210.
[5]姜泽甜.《一点慈悲》的新历史主义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1.
[6] Morrison, Toni. A Mercy. New York: Knopf,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