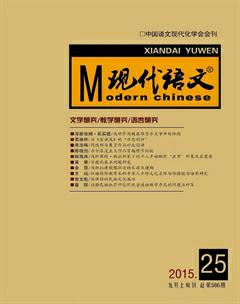论王孟“山水之志”及其山水诗的差异
摘 要:大唐盛世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化氛围,成为山水诗的沃土,代表诗人王维和孟浩然在各个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他们的山水之志不同,山水诗的主观投入不同;艺术造境方面,王维以诗情画意、清淡清幽取胜,孟浩然则以白描写意、寂静幽静见长。
关键词:山水诗 山水之志 主观投入 艺术表现
山水诗人的最大特点是诗人将主观情感寄托于客观山水中,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江河山川中寻找心灵的超逸和生活情趣,在自由闲适中,抒发隐逸之趣和理趣感悟。生活在盛唐,是诗人之幸。王维、孟浩然注重个体精神,他们的山水诗善于抒发主观情感,但在诸多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从“仕”看王孟“山水之志”
王维、孟浩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山水诗人,他们在艺术性上具有共性,又存在很多的不同。应该说,决定诗人创作倾向最根本的是个人的气质和精神内核,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会造成相应的诗歌风格,成为其独特的艺术标记。“仕”与“隐”是古代士人面临的普遍矛盾,由于每个人的背景、经历、思想不同,具体的表现也不一样。
孟浩然出生于耕读传家的中小地主家庭,由于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和儒家思想的洗礼,青少年时他热衷于博取功名,积极入仕,以展示自己不凡的抱负,并常以身为布衣为憾。如其诗《南阳北阻雪》写道“少年异文墨,属意在章句”,希望能像扬雄一样“一荐《甘泉赋》”,[1]用自己的辞赋才智,见赏于皇帝,然后一展宏图,建不世之功。他曾多次赴长安,寻觅进仕之路,然而他既没有考上进士,也没有得到援引获得一官半职。孟浩然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表明自己怀有济世用时的强烈愿望,“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而荣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之气。[2]他曾几次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干谒求仕,然而功名事业却终究无成,只能归返山林。献赋无成,一生求仕不得,务实济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于是,由秦京道返回渔梁州,由求取功名转为修身养性,在最狭小、最低的层次上表现最高的个体情操和主观人格。他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华,兼济天下的机会。他通过对宇宙人生的哲学反思和对物欲的超脱,来获取心理平和,走向超脱与精神自由。然而,他的诗中充满着未能遂愿的无限遗憾,他的心境从未真正平静过,他的诗中跳动着诗人那颗躁动伤感与矛盾的心。因而他的诗没有李白放纵不羁的张扬个性,没有杜甫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情怀,没有王维平静宁悟的禅心,他的诗在平淡自然真切的景物体会中夹杂着诗人独特的个性。他从山水景色、诗词歌赋、饮酒品茶、亲友交谈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王维少年得志,二十一岁中举,官居大乐丞,但之后王维经历曲折:先是被贬济州,然后重做京官,并参与张九龄的改革,随后革新失败,他再次被贬,于安史之乱中被俘,平乱之后又再历沉浮,终于在心静如水的境界中走到生命的尽头。王维在《献始兴公》中“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一句,是诗人对贤相张九龄“天下为公”“大济苍生”政治理想的拥护,表明自己也会像张九龄一样,施展抱负,造福苍生。[3]这种阅尽沧桑,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王维从中年就开始选择亦官亦隐,“以禅诵为事”的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是厌倦官场,追求悠游闲适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远离祸患的需要。王维与孟浩然的本质差别在于他已泯灭了入世之念,表面上看他亦官亦隐的行为方式似乎有些拖泥带水,而实际上他“心灵归隐”却比孟浩然来得利落干脆。佛教的无欲无为,随缘尽心化解了他内心的悲愤,所以王维的诗显得更为平和寂静,他看待世间风物往往带着佛家的“禅意”目光,用佛理观照自然万物,参悟其中的内在精神,显示出空灵敏锐的智慧。王维效仿佛门中人闲居静坐,任性随情,《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心境不为事累,不以物迁,一心只对山水作细致静穆的观照,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心有所思,宁心静悟山水的真谛。《鹿柴》《辛夷坞》诸篇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诗既是诗人片刻的审美体验,也是以物观物、全然无我的宗教体验,王维正是在这种极见山水之真性中,体悟着心中了无牵挂、清澈明净的心境。
在思想内容方面,孟浩然和王维的山水诗贯彻了以景物为中心的原则,建立了表现自然美的新格局。孟浩然诗中思想感情的抒发是他求仕不得而积极寻求机遇的表现,而王维诗中的思想追求则是基于诗人已在仕途,唯求世事公平,兼济天下苍生的愿望。王维看到社会诸多矛盾之后,内心灰暗,对仕途极度失望而自甘隐退,因此他的内心趋于平静淡然,在诗中呈现一种真正的恬淡美好,如《鹿柴》中,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充满生命活力的图景。而孟浩然在描绘山水、观照内心时,则明显地流露出一份抑郁和对社会冷淡的情调。
我们在讨论王孟山水诗差异时,必须以内心世界的不同、思想精神的差别为基点,牢牢把握诗歌创作内在本质的不同。王维孟浩然二人生活道路不同,家庭环境各异,但殊途同归,又交情甚笃,都逃离现实,隐居田园,寄情山水。《庚溪诗话》载:“……又如孟浩然,因王维私邀至内直,俄而上至,维匿之。”[4]他们共同举起山水诗大旗,形成了唐代诗坛独具特色和影响力的诗歌流派。
二、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
讨论山水诗创作时逃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我关系”。诗人以怎样的立场心态看待自然世界,直接影响到他眼中的山水以怎样的风貌呈现出来,“物与我”构成了诗人创作的首要因素,这种对待物我的方式往往在经年累月中化为无意识,变成直觉行为,而这种方式又与诗人的自然观密切相关。王维的很多诗中把主我隐藏得很深,或者说诗人把主观情感与自然景色和谐地融为一体,诗人的情感志趣便体现在景物中。而孟浩然的主观意识在诗中的体现则很鲜明,即使平静的自然景色中,诗人的个体意识也很突出地占据诗歌一角,使人无法忽略掉诗人的情感,这一点可以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5]王维是身与物同化,物我两忘;孟浩然是以己观物,物我共存,但物我都很突显。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在主观投入上明显不同。
孟浩然诗中物与景成为诗人寄情的载体,他的诗处处显现出主我意识,即使在清新自然的画面中,也时刻有诗人的感受在其中。考试落第求仕不得的抑郁心情,常常表现在诗作之中。通过景物描写,抒发羁旅的乡愁和仕途不顺的烦闷,流露出游子的漂泊之感,由于心情孤寂,山水也不免染上一层冷清的色彩。如《宿建德江》中,一个“愁”字把本来空旷无边,“江清月近”的景色染上一层思乡的愁绪,将羁旅乡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夏日南亭怀辛大》是孟浩然典型的自然淡雅的山水诗代表作,诗人在描绘了月下乘凉的闲适之情及荷香四溢,露珠从竹叶上滴落的清新之景后,表达的却是“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孤寂之情,表达了对故友辛大强烈的思念之情。诗人的情感纵使在恬淡的美景下依然强烈,景与情无法相融,诗人也没能融入景中。孟浩然诗中的这种表现与诗人一生不得志而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相关联,他布衣终生,悲愤可想而知,因此在诗中处处可见诗人的主我意识。
王维的山水诗以物观物,在于其情感的冲淡,他在诗中把自我隐藏得很深,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万物的禅意,体悟其中的生命意蕴,而又以佛理禅趣去体味山水。他的山水诗是在企图抛弃自我后,追求一种超脱空寂、物我合一的境界和富有禅趣的静态美,他从不把自然界拉到自己身上,作为自己情感的烘托。如《鸟鸣涧》中桂花坠落的细碎声,鸟鸣的清脆更衬托出山林水涧的宁静幽寂,作者把自己融入这鸟鸣花落的大自然中,感受到动静相衬的和谐与生命力。又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静谧的深山中,芙蓉花独自绽放凋落,不见诗人出现在诗中,却能从大自然中体会到他的人格精神,自然美与人格美和谐统一。再如《山居秋暝》,此诗洋溢着诗情画意,诗人在有限的篇幅中,选择最富有感染力的自然景色和山水风光,以灵活多变的手法交织成一幅清新自然、宁静高远的图画,很自然地表现出作者对山水独有的体验和感悟,表达禅的意境,使诗歌创作更倾向于纯粹的审美。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纯粹是一幅风景画,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全是景物,并未见人物。但我们很清楚,这些景物是作者精心安排处理的结果,是用它们来表达自己。在王维诗歌中,主体淡化通常使用两种方式来表现:其一,作者个人逃离,隐藏在他所描绘的画面之外,不断呈现景物,尽量不对画面中的现象作直接主观的情感判断;其二,作者写景的同时也有人物的活动,但这活动并不是由作者来完成,而是选取一些身份独特的人物,如隐士、村姑、牧童等。这些人物形象有个共同点,即远离尘世,具有闲情逸趣,这与王维的主体精神相一致。王维诗中的这种表现与诗人的经历相关,王维在仕途上历经的波折使他心中忧愤,诗人以禅自我安慰,希望隐居远离祸患,处处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体现在诗中,便是物我合一的境界。
三、白描写意与诗情画意
从艺术手法上讲,两位诗人的山水诗都有入画的特点。诗中的景色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幅清新自然、幽静深远的山水风景画,但两位诗人的画面差别也很明显。
孟浩然写诗“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他常常白描写诗,其诗往往字不雕琢,句不锤炼,始读之,给人以质朴疏淡的感觉,但细心体会又感到朴中含华,淡中有味。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通篇侃侃道来,句句如话家常,诗人把他浓烈的感情渗透到客观景物的描写中,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又如《武陵泛舟》:“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水回青嶂合,云渡绿溪阳。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此诗寥寥数笔便勾画出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清新自然,不事雕琢。总之,孟浩然的诗写的极为本色自然,以白描为主而较少刻画,喜用简单的笔调随意点染,自然天成。
王维书、乐、画兼擅,他在诗中借鉴了他作为画家所独具的绘画艺术技巧,将诗、画相互沟通,把文字作为绘画的线条和色彩来刻画山水,虚实相间、明暗配合,极大提高了山水诗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他以音乐家的听觉,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声响,将它们有机地组合成如诗如画的意境,使他的山水诗成为一幅有声画。
如《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人出汉塞后,放眼四望,只有不见首尾的黄河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壮阔但单调,突然见到一股烽烟冲天而起,诗人原先枯索的神经被视觉冲击而变得活跃,同样的又大又圆的落日,更激起诗人的视觉刺激,整体上看原来乏味平旷的背景突然变得鲜明活跃起来。诗人对单车问边或有所不满,但决不至于激愤抑郁,透过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个热爱大自然风光的诗人,他那颗敏感的心,正被边塞雄伟壮阔的风光所吸引并激起昂扬奋发之情。
四、寂静幽静与清淡清幽
孟浩然诗中的静是“寂静”,直写其静。如《夏日雨亭怀辛大》中:“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太阳落山了,月亮慢慢升起,诗人散开头发乘凉,打开窗户坐着,一切是这样的安静悠然。再如《万山谭作》“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这也是安静的环境,但作者并未用动态或声响来衬托。王维诗中的静是“幽静”,他善于以动写静,以有声衬托无声,如《秋叶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果落第之声都能听见,草虫的鸣叫声更加衬托出秋夜的寂寥。又如《过香积寺》诗中“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所以,“王孟”二人虽都是写“静”,但在静的意境表现上都有区别。
孟浩然的一生,总的倾向是隐逸且布衣终生,所以他写的山水诗常常怀着清淡的心情,表现冲淡的境界。孟浩然多用清淡的笔调表现恬淡的情怀,仅从用语上看,“清”字和与“清”字构成的景物在他的山水诗中不仅多,而且往往蕴含着远离官场纷扰、都市喧嚣的淡雅和淡然。如“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洗然第竹亭》),“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等,这正是诗人在自然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和心灵补偿。
同样,王维的山水诗中“清”字也用的很多,如“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清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山居秋暝》),但王维展现的清新之景不仅是意境优美,清新淡远的画面,其中更凸显着诗人冲淡到忘我状态的灵魂。他希望忘掉官场的挫折、人生的坎坷,一心向佛后,王维的山水诗充满着亲近自然、物我合一的禅意,在清幽的山水物境中充溢着诗人禅悟后清远宁静的心情。王维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具有空明的境界和幽静之美。孟浩然的山水诗则没有王维那样的超脱,而是更贴近于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常出现在诗中。孟诗中的景物也常常为自己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加修饰的特点,也就是说孟浩然的山水诗表现的更多的是儒家居世的“清淡”,而王维的山水诗则更多的是出世的“清幽”。
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创作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同样引人入胜,深入分析他们山水之志的不同与山水诗的差异,可以使人们进一步明白王之所以为王,孟之所以为孟。
注释:
[1]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卷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3]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4]陈岩肖:《庚溪诗话》(下卷),《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9页。
[5]王国维著,滕咸惠注:《人间词话新注》,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4页。
(赵雪珍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