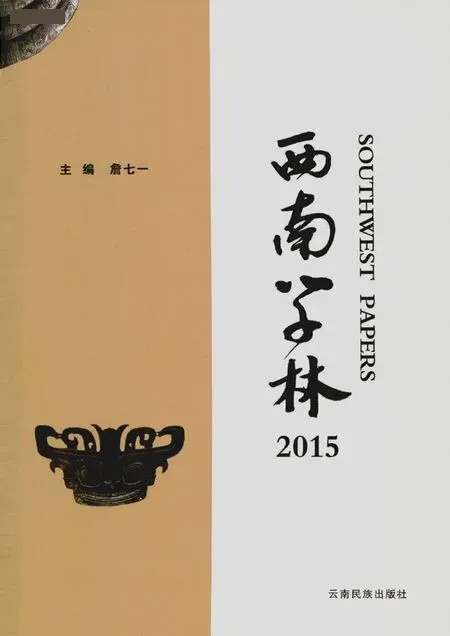从传统到现代①
——大理白族民间文学中的生态民俗呈现及其发展研究
(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由于全球性的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危机,“生态学”一词已成为普通人生活用语中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俗学工作者有必要对现代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变迁予以高度关注,发掘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有的生态情怀,合理选择和优化营构与自然相生相谐,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民俗生活模式。而这种可供参照的生态民俗资源,除了在汉民族文化系统内探寻外,一些少数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良好,更为我们提供了构建生态民俗空间的优良范本。例如,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生活于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作为一个拥有良好自然生存空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通过各种形式得以传达,其中,在神话、传说、歌谣、戏剧等白族民间口承文学样式中更得以生动地体现。本论文试图以与白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民俗学的视角,对其中所蕴藏的生态民俗文化进行系统考察,该研究除了对白族传统民间文学及传统生态民俗进行深入探寻外,还将关注现代白族民间文学、生态民俗的演化与发展。
一、历史视野中的白族传统民间文学与生态民俗
大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世代生息繁衍于此的白族人民创造出了丰厚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民间文学则是其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代表。白族民间文学形式多样,风格独特,从过去一直传承下来的传统民间文学按体裁可分为散文类、韵文类、说唱类三大类。韵文类如民歌、史诗、叙事诗等,代表作品有:以 “打歌”形式演唱、传承于洱源西山地区的创世史诗 《创世纪》、有 “白曲之祖”美誉的白族民歌 《泥鳅调》、叙事长诗 《鸿雁带书》《出门调》《青姑娘》等,这些作品或叙说白族先民改造自然的宏大理想、英雄业绩,或抒写传统时代白族民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散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代表作品有创世神话 《开天辟地的故事》 《人类和万物的起源》、图腾神话 《氏族的来源》《虎氏族的来历》、本主神话 《段赤诚斩蟒》《大黑天神》、龙神话 《白龙掌印》《小黄龙与大黑龙》、佛教神话 《赞陀崛哆开辟鹤庆》、风物传说 《风花雪月》《蝴蝶会》,历史故事 《火烧松明楼》、工匠故事 《锯子的来历》等,这些作品想象丰富,美丽动人,既反映了白族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也显示出白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对汉民族文化乃至外来宗教文化的广泛汲取、利用;说唱类如大本曲、吹吹腔等,代表作品有大本曲《辘角庄》《望夫云》《柳荫记》、吹吹腔 《血汗衫》《灵芝草》等,这些作品散韵结合、唱腔丰富,是历代白族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生态民俗学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普遍联系的有机体,人类的生产模式、文化习俗、思维观念等都与生态环境有着多维度的密切联系。白族民间文学是几千年以来白族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创作、传承下来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体现着白族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应对自然环境时采取的不同“生存策略”。白族传统民间文学中蕴含的生态民俗文化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经济民俗在白族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艺术呈现
经济民俗又称“物质民俗”,是民俗学的一大分类,即物质生产与生活方面的习俗。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是在其特殊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境内山川连绵,江河纵横,山地之间散布着当地人称之为 “坝子”的小盆地,洱海、茈碧湖、西湖等高原淡水湖泊点缀其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白族民众基于生存需要做出了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各种实践活动,形成了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渔业、畜牧业、林业、手工业生产为辅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村落经济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方面,白族历来以稻作生产闻名。稻作农业受气候变化、岁时更迭影响,农事活动的张弛有节取决于对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的准确把握及顺应、利用。流传于洱源西山的 《犁田歌》是大理地区最古老的白族民歌,歌谣这样唱道:“说来你们不相信,犁田我们用野羊,犁头用的白石头,犁的很平整”。这首古歌谣语言天真质朴,形象地描述了白族先民在农耕文明初期使用简单农具进行生产的状况。另一首流传于西山地区的打歌作品 《采花歌》用一年四季的花开花落串联四季的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民俗节日活动,其中不仅有对气候、农耕时序的总结,“山村活计要数二月忙,忙播种来忙烧荒。劈倒山林开荒地,点火烧荒人人忙”等唱词还反映出具有生态意义的白族传统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模式。除了民间诗歌,白族人民对于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更多是以农事谚语的形式代代相传。如 “早晨天赤脚,晚上大雨来”“有雨山戴帽,无雨山系腰”包含着天象、气候变化规律的知识;“早栽三天成谷,迟栽三天成草”“你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你一季”则告诫人们不要耽误农时。此外,白族人认为湖泊、龙潭中都有龙王,龙王是雨水的象征,而村社神 “本主”也掌握着生产丰歉,因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事祈福、禳灾习俗、农业祭祀习俗则更多的沉淀在本主神话、龙神话中。例如,大理挖色大城曲村本主神话中讲述沙漠神来到挖色坝大城曲村,教当地人种五谷并帮助人们兴修水利,因此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在其死后为其盖沙漠庙予以奉祀。大理地区著名的龙神话 《小黄龙和大黑龙》中暴虐成性的大黑龙造成水灾,淹没了大理坝子,正义的小黄龙在人们的帮助下打败大黑龙,从此大理坝子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人们给小黄龙盖了一座龙王庙,把它奉为绿桃村本主。每到生产节令,当地白族民众都要祭祀本主、龙王,祈求丰收。
除了农业生产,白族的渔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也较为发达。根据考古材料,白族先民早在4000年前就已使用渔网捕鱼,驯养鱼鹰捕鱼的历史也很悠久。“鱼鹰之家好风光,鲜花万朵喷鼻香,蝴蝶追逐相嬉戏,花间配成双”,自古以来,在波光粼粼的洱海上,洱海渔民划着木船唱着白族调,船舷上一排鱼鹰比肩而立,形成了一副和谐美好的生产画面。白族许多的传说、故事,如 《洱海月》《三月街的来历》(渔民阿善与龙王三公主阿香 “做月街”版本)等也映射了洱海地区民众的渔猎生活。
畜牧业在大理白族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大理是个好地方,羊呀肥又肥。大理是个好地方,羊毛长有三尺六”,西山白族打歌 《放羊歌》就记述了古代白族牧人的游牧生活。在长期的实践中,白族人民积累了大量的畜牧业生产经验,如白族民谚说的 “在家吃一斗,不如外边走一走”,提倡放养为主的生态饲养方式。
白族的手工业自南诏、大理国时期起就达到了较高水平,明清以来,依托当地优越的林业资源、矿业资源,大理石制品、木雕、银饰、扎染等手工行业迅速崛起。围绕着这些手工技艺形成了众多的白族民间工匠传说、物产传说,如 《鲁班传木经》《锯子的来历》《七十二道金花线》等。白族手工艺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农闲时外出务工—— “走夷方”的传统习俗,留下了 “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俗语。鹤庆首饰加工艺人也长期挑着担子在滇西、西藏、四川一带四处飘荡,鹤庆白族民歌中 “山高只要马得力,水深只要船行直”“(阿小尼)妹,隔山 (尼)听到 (嘿)铃铛响, (格是口罗我尼小阿哥),不知阿哥(尼)去哪里?”等唱词就对这些艺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外生活的艰辛、思念亲人的情怀进行了生动描述。
除了物质生产习俗,经济民俗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的习俗惯制,因其形成过程涉及对自然界物质能量的摄取,因此也带有其栖息地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印记。白族民间文学作品也对这些生活民俗的形成进行了相应的解说。例如,对于白族服饰中最有特色的年轻女性头饰的由来,“凤凰帽的传说”归结为白族所崇拜的神鸟凤凰赐给凡人的礼物,后来又有其代表 “风花雪月”四景的说法,当中透露了自然崇拜观念及自然湖光山色潜移默化地对白族人审美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白族饮食里迎宾待客的重要茶礼 “三道茶”在敬茶过程中唱念的俗语 “头饮香,二饮味,三饮渴”“酒满敬人,茶满欺人”“一苦二甜三回味”,既反映了白族民众善于利用各种本地饮食资源进行茶艺创造的禀赋,又寄寓着他们对人生哲理的智慧总结;白族民居从建筑取材、民居结构到居住习俗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白族人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观念,如大理民间有 “大理有三宝,石头砌墙不会倒”的谚语,指的就是当地民居善于就地取材,广泛采用大理海西一带所产青石为建筑材料的特点。一个白族村子一般都会立一个照壁,如洱源凤羽凤翔村中和大照壁,上书 “腾蛟起凤”四个大字,让人联想起金凤凰飞临凤羽坝子,把羽毛无偿馈赠给当地民众的古老传说。照壁这一建筑符号充分表现了白族建筑风格的环境适应性和民族性,凝聚着白族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交通运输习俗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白族马帮文化。大理历史上就出产良马,早在先秦时期,白族马帮就开辟了一条被誉为 “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另外,白族马帮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往北,将云南的茶叶运到北方的青藏高原,与藏族人民进行茶马互市,这便是神秘绝险的 “茶马古道”。白族马帮中流传有这样一些歌谣:“头骡选上枣骝马,二骡选上菊花青。识途还留老玉眼,十岁出头还健行……”形容马帮骡马安排选用的技巧,“横蛇直兔野鸡飞,三凶四吉五平安,早晨要逢乌鸦叫,晚上喜鹊报平安”则透露出马帮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特殊禁忌习俗。
这些传统白族民间文学作品深刻反映出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经济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当中既有对自然力的顺应、崇拜,又有对自然力的反抗与改造。
(二)生态精神民俗在白族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艺术呈现
精神民俗也叫民间信仰,主要指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社会民众中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其形成与特定地域地理生态条件和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白族地区宗教信仰较为复杂,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的白族本主信仰,所谓 “本主,本主,本境福主”,他是白族人公认的地区保护神。本主信仰既融汇了一些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佛、道教思想的渗透。本主信仰中包含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龙崇拜观念具有鲜明的生态文化内涵,而白族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对这些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深刻的诠释。
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对象”。大理苍洱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山河草木、奇峰异石都使白族先民产生联想,进而成为其崇拜的对象,于是,山有山神、树有树鬼,甚至石头也有灵异的力量,其中有些逐渐就演变成本主神。例如,洱源县凤羽铁甲村本主的来源,有一种说法为大树疙瘩。相传该村有一妇人上山背下来一个树疙瘩,来到现本主庙所在地歇脚后就再也背不起来。第二天,妇人和丈夫带来斧子想把树疙瘩劈开搬回家,结果连劈数斧都劈出了鲜血,两人大惊,空手而归。结果,当天晚上他们梦见树疙瘩说:“我是你们的本主,要盖庙祭祀我”。后来当地人就在该地建了本主庙。再如,大理上阳溪内光村本主为大石头。传说有一年洱海里滚上来一块大石头,滚进海边的田里,人们怎么都搬不走,后来众人给大石头烧香,它一点一点滚到上阳溪内先村,就再也不滚了,于是人们就盖庙祭祀将其奉为本主。
动物崇拜观念在白族本主信仰中也有鲜明体现。“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实体,而是低级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大理洱海金锁岛的本主相传是一只灵猴,它极通人性,能占吉凶。这只灵猴很喜欢未婚少女,有一次跑去和一户人家的女儿纠缠,结果被女孩的父亲打死,死后即被奉为本主。在农耕时代,白族还常常把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动物如水牛,视作有灵魂的生命个体,进而对其产生崇拜。大理海东下秧村本主是老水牛。相传老水牛帮人犁田,死后因主人掩埋其尸体不周而感到愤怒,欲降灾于主人家,后主人将其重新掩埋,从此保佑当地风调雨顺、清吉平安,因此被奉为本主,号称 “牛王”。
此外,大理苍洱地区江河湖泊纵横,因白族认为龙王即是水神,因此其本主信仰中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很多。洱源县漏邑村本主为九龙神龙王。相传其有八子一女,都是洱源县境内各村的本主。洱源茨充本主龙王段思平,相传他有九子九孙,古时蛟龙为害,其率子孙应募去和龙王搏斗,最后段思平钻进龙口,杀死蛟龙。
本主信仰展现了一副人神亲和、人神和谐的理想图景,其间接表达了白族人民对于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除了本主信仰外,白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及后来的佛教、道教信仰也多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这些在白族众多传统宗教神话、传说中都有相应的艺术表达。
二、现代情境中的白族现代民间文学与生态民俗
大理白族地区的历史沿革是一个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密切,且逐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大理白族人民在劳动生产、社会政治、文化娱乐、物资消费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与转型。与之相对应,白族现代民间文学与传统民间文学相比较而言,产生了一些新的传承方式与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大理白族现代民间文学的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白族传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星华前来大理,率先领起白族民间文艺采集之风。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整理出版的白族民间文学作品集有白族民间故事集 《玉白菜》(1957年)、《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1959年)、《白族民歌集》(1959年)、《白族大本曲音乐》(1986年)、《白族神话传说集成》(1986年)、《白族民间歌谣集成》(1997年)、《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2003年)……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保护白族传统民间文学遗产,传承白族历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是白族现当代民间文学形式的创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白族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民间文体艺术形式,或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内涵的民间文学样式,如新谚语、新歌谣、新说唱、现当代历史传说、都市传奇、网络个人叙事等。歌谣方面,大理现代白族歌谣的艺术创新,常依托电影、电视等媒体资源,在沿袭传统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融入当代音乐家、曲艺家的表现时代风貌的个人创作,其传承由传统的口口相传转化为 “口传——媒体——口传”的多元传播模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建国十七年经典少数民族电影 《五朵金花》的插曲 《蝴蝶泉边》《采药歌》《唱支山歌扔过墙》等,是当代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在广泛吸取白族传统民间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创作而成,而伴随着电影的传播又成为当代广为传颂的白族民歌的代表作品;传说故事方面,在20世纪上半叶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语境下,大理白族地区结合当地的革命运动涌现了一批革命历史故事,如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 《一块雕像石》,反映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经过洱海地区的革命故事 《红军攻打宾川城》《红军草鞋治痧症》,表现洱海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斗争故事 《沙溪大战》《解放云龙》《赵凤歧》等。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因素对大理白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在新兴的民族手工行业、民族商业、民族文化旅游行业都衍生了一系列新传说、新故事。例如,鹤庆乾酒有限公司借助各种报刊、网络媒体资源用 “鹤庆乾酒的传说”“鹤庆乾酒的重生”等富有民间传奇色彩的叙事积极打造产品的文化形象,从而在当地民众中形成了关于鹤庆乾酒的新传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白族民间曲艺的艺术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创作和演唱的大本曲有 《施上泽入社》《试验田中一枝花》《农家乐》《我是一只画眉鸟》《白州飞起金凤凰》《审村官》等。此外,1962年,大理洲白剧团成立,宣告了一个新的剧种——白剧的诞生,白剧在唱腔上以吹吹腔和大本曲为基础,内容上既有改编自白族传统民间传说、故事的古代戏,如 《望夫云》《白洁夫人》《苍山会盟》等,也有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现代戏,如 《情暖苍山》等。很多曲目曾获省级以上奖励,彰显出白族当代民间戏曲的朝气与活力。本章主要就白族现当代民间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新时代语境下的新的生态民俗文化内涵作分析探讨。
(一)生态经济民俗在白族现当代民间文学中的艺术呈现
作为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地区,大理自清中叶以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优势,衍生出一些重要的经济民俗现象,如现代商业、手工业、当代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于是,传统的以农耕为主体的村落经济模式开始向着村落农耕经济与城镇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方式转型。白族现当代经济生产、生活民俗的演变在其民间文学的创新发展中也留下了艺术的痕迹。
近代以来,在大理喜洲、鹤庆等地的白族民众中广泛流传着一些关于白族商号、商帮的传说故事。西南丝绸之路自秦汉以来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商道,其开拓、发展自有白族先民的贡献。清代中后期以来,白族商帮更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商业群体,不断推动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清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以前,大理白族社会中接连出现了裕和号、三元号、德兴号、庆顺号等商号,这些商号以贩运土特产和土地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发家,仍属于封建主义商业经济。而清光绪初年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大理白族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商业经济,例如喜洲的永昌祥、锡庆祥、复春和、鸿兴源四大资本家。这些对当地民众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商号、商帮的发迹史、创业史、家族轶事成为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例如,关于大理马久下邑村三元号的情况,有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一个就讲述了其创建者杨士元的发家史。据说,杨士元少时拜师学手艺不成,就随大哥的马帮到保山做小生意,在其寄宿的一幢“鬼宅”中获得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假借买卖托运 “瓦花”(从缅甸运来的棉花)之名,把银子安全托送回大理。这样,杨士元就发了大财,于是开了三元号做起了买卖瓦花的大生意。这则传说间接反映了近代以来白族商号对于大理白族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起到的解体作用以及对于城市纺织手工业及商业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多元的经济生产模式对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当代民间文学的发展则积极参与了大理地区新兴产业及新的生计、生活模式的构建。建国初期,大理工农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经历过一个对环境资源浪费性使用和低效转换的生产模式阶段,但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传统的资源浪费型工农业开始向着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方向发展。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积极反映了环保生产的新观念。例如,由民间艺人杨兴廷编导大本曲的 《促环保、建家乡》、由白族文化学者乐夫编导的大本曲 《审秧官》结合新农村建设积极宣传生态农村建设思想。而进入21世纪以来,大理州积极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积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了 “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白族文化产业的资源开发与建设。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白族文化创意产业多以旅游业为基础平台,在开发自然景观的同时,积极配合文化层面的旅游开发。于是,白族民间文学与旅游业的互渗发展成为了大理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例如,白族旅游文化精品节目——白族三道茶表演,在让游客品尝三道茶、品位人生苦甜的同时,还用新编的 “敬茶歌”向游客宣传大理山水与特产:“苍山茶绿洱水清,先吃苦来后享福,创业多艰辛……大理名产配佐料,捧来奉嘉宾。洱源乳扇油亮亮,漾濞核桃脆生生;补脾益肺安心神,古传确是真……”。此外,依托旅游行业而迅速发展的白族现代工艺美术行业,如大理石雕、木雕、草编、扎染等也在积极利用相关民间文学作品打造自身的文化形象。大理民族文化产业的兴盛发展,表明白族民众逐步调整生计模式,即从先前的功利化摄取向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摄取模式转变,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产业,而对于该产业的发展白族民间文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生态社会生活民俗在白族当代民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呈现
当下,在白族的各种社会生活民俗中,节日民俗的当代传承、发展、创新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节日是 “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大理白族的节日民俗活动丰富多彩,除了与汉族同样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外,还拥有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节日,如朝山会、葛根会、青姑娘节、太子会、朝花会、观音会、三月街、绕三灵、蝴蝶会、栽秧会、火把节、海灯会、石宝山歌会以及各具特色的本主节等。在节日的特定时间里,白族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得到最全面集中的展示。节日承载有大量的区域人文背景信息和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内容,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特别是伴随着大理现代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旅游资源的白族民俗节日及依附于其中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往往从传统的具有单纯的宗教意义和神圣象征意义向着世俗化、娱乐化的方向衍变。以大理 “蝴蝶会”为例,与其相关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古老的传说、有电影 《五朵金花》中阿鹏与金花的经典对歌《蝴蝶泉边》,还有当代旅游景点的歌舞表演,这些作品的民俗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具有较大差异——民间传说展现出的是传统时代白族人民在游赏春光时对大自然神奇景象的咏叹,对歌 《蝴蝶泉边》是对 “蝴蝶会”除游春盛会外另一个文化功能,即白族青年男女倚歌择偶的爱情盛会的现代阐释,而当下蝴蝶泉景点的歌舞表演作为民俗旅游的活动内容,基本已丧失原生文化中的仪式感和隐喻性,而主要发挥吸引游客的经济效益。当然,也有一些当代白族节日习俗及相关民间文学艺术表演依然渗透着生态因素,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民俗观光旅游的特质,从而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性。以洱海开海节为例,它在展现洱海周边白族渔民的祭海仪式、鱼鹰捕鱼、手撒网鱼、搬罾捕鱼等传统捕鱼技能的同时,配合以洱海渔歌、对歌、大本曲等民间文学艺术表演,特别是在活动周边地区举行的洱海渔歌会,都是由当地民间团体组织的,它用白族民歌对唱的方式使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用歌声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节日活动虽是现代旅游开发的选择,但相关文学艺术表演的内容仍是当地白族渔民因地而生、引情而生的产物。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表演配合着白族捕鱼文化习俗将大理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情及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向各地游客做了生动、形象的宣传,同时也扩大了旅游节自身的影响。
结 语
通过以上对传统及现代的白族民间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民俗事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理白族民间文学及民俗文化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对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和谐、平衡的期盼与憧憬。当然,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白族民间文学与生态民俗文化事象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其生存环境、传承方式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效用价值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白族民间文学传承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传承人的减少,年轻一代在现代生活娱乐资源丰富情况下逐渐丧失对传统民间文学的兴趣和关注;而生态民俗发展方面面临的危机则主要在于,生存方式选择的多样化造成了一些传统生存技艺传承的困境,以及在商业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地方旅游开发随意将白族的民俗文化内容降解为诉诸现代旅游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从而使其失去固有的文化指向……这些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着白族原有的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现实的环境危机表面上是自然的危机,其深层实质是人的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它不是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源自心灵的或观念的问题”。因此,在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下,在白族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中中,积极发掘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的命题,既具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发展,构建健康、环保的现代生活模式的现实意义,同时又能更好地促进白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