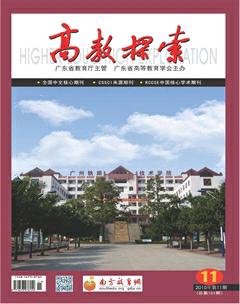论中国大学校训的品位之维
摘要:校训是一所大学的文化旗帜和精神坐标,是大学价值观最直观、最凝练的表达。大学校训的品位有高下之分。好的大学校训在思想源头、道德关怀、知识创新、气度境界和学术特色等方面都有卓越而独到的表现,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判识大学校训品位的五个基本维度。好校训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属于大学本身,更属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
关键词:大学校训;文化品位;评判标准
校训是什么?校训是激励、引领一所大学的精神坐标,是凝聚一个知识共同体集体意志的文化旗帜。如果说大学精神是海上灯塔,那么大学的校训就是灯塔中的光源,它集中代表了大学最具标志性的精神原点,集中体现了大学的育人智慧、教育品格和文化魅力。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大学校训文化价值的发掘,校训更加广泛地走入了公众视野。人们也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校训有没有高下之分?究竟什么样的校训是好校训?质言之,判识校训品位的标准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既有研究成果多有触及,但并不系统,似无明确答案。带着这一疑问,笔者拣选并深入分析了2014年中央电视台“校训是什么”和《光明日报》“校训的故事”两栏目公开推介的一批大学校训,试图从日益丰富且富有个性的校训之中,探寻大学校训的品位评判问题,为好校训到底“好在哪儿”找寻答案。
一、大学校训何以有品位之分
从逻辑上讲,要回答大学校训品位的评判标准问题,先须解决校训“何以可以比较”这一前提性问题。从表面上看,校训都是大学为自己“量身订制”而成个性化“产品”,只适用于本校的文化理念和精神特质,基于“适合本校的才是最好的”这一基本认知,评价校训就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而似乎不存在所谓“最佳”与“次优”的高下之分了。但事实上,人们对校训的比较和评价随时在进行,既然可以通过“我最喜爱的校训”、“什么是校训”或“校训的故事”等这样的项目来排名或报道,那么说明在人们心目中校训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最终往往只有极少数大学的校训通过排行榜或报道的形式被推介出来,也说明在公众心中校训的品位是有高下之分的。
一般来说,凡是可以用于比较的东西,既存在某种共通性,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无共通性则无物可比较,无差异性则无以分差等。探讨校训的共通性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着重思考不同的校训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是人们评价校训和比较校训的关键。笔者认为,校训背后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反映程度和校训背后的人才培养质量等三个方面,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其一,校训背后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有差异。校训是大学精神内涵的外在体现和凝练表达,宣示和张扬着大学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各各不同的校训背后,首先意味着大学所持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这方面的差异有时候体现为风格之别,更多时候体现为高下之分。前者的显例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1938年西南联大的校训订为“刚毅坚卓”,而在南迁合并之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有独立的校训,彼时北大校训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刚毅坚卓”作为新校训与合并之前三校校训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集中反映了民族危亡关头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以及战时对人才品格和意志的特殊要求,这是风格上的差异。后者的例证就更多了,仅举一例,清华校训前半句“自强不息”一语,目前至少完整地出现在另外七家高校的校训之中,以“自强”二字入校训的就更多了,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与清华相比,显然是存在水平差异的。
其二,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反映程度有差异。校训是大学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从理想状态来说,它是“生成”的而不是“建构”的,是“发掘”出来的而不是“制订”出来的。在实践中,校训反映大学精神的内涵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因而,一些大学会在发展进程中调整修改自己的校训,直至找到最能贴切地反映学校精神特质的校训为止。例如,兰州大学2003年确定校训为“博学笃行、自强为新”,2009年百年校庆前重订校训为“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后者更能够准确贴切地反映兰大坚守西北、艰苦办学、顽强拼搏的精神气质。再如山东大学老校训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2002年修改为“气有浩然、学无止境”,体现了孟子所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和精神气度,2011年又微调为“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强化了“为学”的价值指向。校训反映大学精神的程度差异是校训自身发展演变的一大动力。
·教育管理·论中国大学校训的品位之维
其三,校训背后的人才培养质量有差异。校训是大学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立基于人才培养质量这一“硬实力”。校训之于大学的关系,有如灵魂之于躯体、品牌之于产品。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越高,相应的其校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就越大,也就是说,校训的品质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大学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借助于比较可以更为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浙江大学老校训为“求是”,三峡大学校训为“求索”,前者取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者取自大诗人屈原代表作《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是”与“求索”二者仅一字之差,均出自名作与名句,若作为一般用语或作为两所中学的校训,品位难分高下,后者的社会认知度甚至还要高一些,然而一旦分别落实为两所具体的大学的校训,“求索”就立刻显得相形见绌,这种差别,应当理解为校训背后的大学有较大的人才培养质量差异所致。
校训之间的上述三大差异是同时存在的,因之其品位就必然出现多个方向上的分化,而在公众审美视野中,会出现更加明显的高下分别。校训在品位这一向度上存在高下之分,是探寻校训品位的评判标准的基本前提。事实上,校训往往是大学与外界接触时首先愿意展示并推荐的文化符号,外界在评价一所大学时,往往首先就会涉及对其校训的直接评价——大学的校训可以说随时随地被置于不同评价标准的评判之下。
二、判识大学校训文化品位的五个维度
校训浓缩着一所学校对内对外最基本的价值主张和教育理论,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必定是一校最认真、最用心完成的“文化作品”,集中了大学一切利益相关者的智慧。剖析校训犹如提笔著文,看似文无定法,实则有章可循。分析一些有影响的校训“作品”,可以发现好校训的成功都有一定之规。教育界内外之人,往往能够对各类校训进行品鉴点评,分出高下,也就是因为有实际的评价标准存在于人们心中之故。好校训之所以“好”,并非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必定有其独特优长。具体而言,好校训无一不是在思想源头、道德关怀、知识创新、气度境界和学术特色等五个方面有卓越而独到的表现,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校训评判乃至审美的五个基本维度。
(一)思想源头之维:文化元典的精神滋养
校训承载着立德与劝学两大基本功用。为增强这两大功用的说服力和渗透力,必须将其立基于最广泛、最深厚、最持久的文化认同之上,因而须为其找到最早的思想文化源头。各民族的“文化元典”创生于该文明的成熟期,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1],往往经过了数千年的传承淬练,具有超越时空的学术和文化魅力,因而,民族文化元典是校训最普遍、最直接的思想源头。溯源文化元典,使校训底蕴深厚,历久弥新,昭示着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品格。
援文化元典入大学校训是我国高校最普遍的做法,这方面的成例不胜枚举。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移借化用于《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和《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香港中文大学校训“博文约礼”源自《论语》,山东大学校训“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取自《孟子》,河南大学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来自《大学》,黑龙江大学校训“参天尽物、博学慎思”源于《中庸》。不难发现,文化元典之中的《诗经》、《周易》和“四书”等,其最能体现民族“基本精神”的部分,多已成为校训的直接来源。文化元典之中,能够体现教育特色且适合选作校训的表述本身有限,被援用之后又具有一定的独占性,因之,校训的品位往往从其赖以立基的思想源头上,就已经显现出高下的分野了。
校训的思想源头除了最普遍的文化元典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较为独特的来源,即汲取大学所在区域的文化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益成份,使之直接成为校训的内容。例如湖南高校对区域文化精神的发掘和运用,代表性的如湖南大学校训“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中南大学校训“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被学校发掘利用,既吸收继承了本区域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又标识了大学鲜明的文化个性,蕴含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深远喻意。
(二)道德关怀之维:谋求道德主体的挺立
校训的本义偏正于“训”字之上。“训”为形声字,《说文解字》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本义为劝说、归顺,引申为“用言语贯通使人心思如河流般流淌顺畅”。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最早对校训含义进行了界定:“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该德目而实践之。”该词条两次出现的“德目”,意即德育的主要内容。从概念上说,“校训”二字的本义已蕴含了“应当如何”的基本要旨,明晰了训育主体和训育客体之别,体现了校训在道德关怀上目的性和功能性的统一。
大学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使命,作为教育机构必须回应本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命题。重视君子德性的养成是我国教育的一大传统。我国自古就主张“以德先人”、“进德修业”、“德才兼备”、“修己安人”,《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学问”,《资治通鉴》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强调了道德对学问和才能的先导、引领、统率和调节作用。“这种道德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数千年,作为文明传承的机构与载体,中国大学必然蕴涵着这样一种独特的办学理念:大学除探索知识之外,还应当探索并完善道德;除为社会服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中倡导并践行道德。”[2]可以说,中国大学的文化基因中先天的蕴含了“德”的要素,校训本身为教育而设,因而无德不成训。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学生在校时间总是短暂而有限的,大学能够给予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终究会被新的知识和技能所替代,而大学为学生输入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其影响则是持久甚至终身不变的,因而校训从道德关怀方面立意,谋求道德主体的挺立,蕴含了清晰的价值指向和明确的道德要求。“德”的教化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者交感于耳目,无形者神交于内心,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方面的显例是:台湾大学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武汉大学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些校训总体不脱离为人为学之德这一基本主题,整合了全校师生的价值观,对其学生、教师和校友都具有持久的鞭策、约束或激励的作用。
(三)知识创新之维:张扬求知方法和求知态度
科学是对真理和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大学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停息的知识生产。任何时代,创新是社会对大学、大学对师生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求,促进创新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必有之义,因而,创新应为一个总体性、普遍性要求。作为校训,需要回应创新这一基本价值指向,同时找到具体的切入点,从巧妙的角度对师生提出知识创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校训最普遍的问题是同质化程度十分严重,雷同不光体现在表述方式上大量使用“四言八字”或“二言八字”句式,更主要地体现在遣词用语上,尤其是“创新”二字。“创新”作为词语大量进入校训内容,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该词的加入本意是体现时代要求,但经大量使用,现已成为最大的俗套,甚至呈泛滥之势。有研究者对112所“211工程”高校的校训进行了研究,发现“新”字及其同类表述出现频率达43次之多,重复频率达37.1%。[3]
检诸我国一批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学的校训,其实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不径言创新,却直指创新”这一问题。总体来看,这类校训分为“求知方法”和“求知态度”两大基本理路。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等,自求知的方法和途径切入,对学生提出了知识创新的要求;天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则共用校训“实事求是”、集美大学校训“诚毅”等,则从求知态度立意,自然而然蕴含知识创新要求,两种理路各有千秋,殊途同归。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兼具方法视角和态度视角,把二者恰当地统一起来,有两全齐美的效果。
从校训的实践性角度来说,激励师生养成良好的求知方法和求知态度,比之提出宽泛笼统的“创新”要求更为切要。因而,好校训的隐含标准之一即是:不见“创新”之形,而能尽“创新”之意。大学所教所学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社科知识,往往为无用之用,若直奔“创新”而去,则可能欲速而不达。当前校训中“创新”的过度使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的审美疲劳,这与校训的独特性要求完全不符,制订者不可不察,不可不为之戒。
(四)气度境界之维:注入文化张力和精神能量
大学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这二者是大学校训区别于中小学校训及“家训”、“厂训”最主要的特征。不同的大学所授知识本身相差较小,而知识接受者的学术眼界、精神境界和成就边界相异甚大。校训首先要体现“学”这一基本要求。好校训还要体现“大”的内涵,要有高远的立意和宏大的理想,给予师生以高度的自信和充盈的气度,体现超越的精神境界。越是著名的大学,越注重精神境界的注入,其校训的立意越高远隽永,气度越非凡,而越是一般高校,在精神气度上越难以有所作为。气度境界方面的表现,可以较直观地反映出校训的品位。
大学精神贵在高远,贵在气势恢宏,贵在能引导学子的精神追求。作为大学精神的点睛之笔,校训宜从精神至高点上注入大学所主张的气度和境界。这方面有一批好的校训“作品”:兰州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很好地体现了该校不畏艰辛扎根边疆、奋发图强的精神气慨,隐喻其在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当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西南大学校训“含弘光大、继往开来”,极尽“包含弘厚、光著盛大、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之意,大气典雅,厚重深远。苏州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融时空要素与道德要求于一体,方正凝重,超拔完美。中国农业大学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气势磅礴,胸怀远大。这些校训极富文化张力,充满精神能量,为学人注入了一种令人向往的豪迈气度和精神境界,有利于学生高贵精神气质的养成。对学校来说,气势恢宏的校训,为学生注入一种强烈的“文化中心感”和“精神优越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在地理上不处于文化中心或在类型上不属于综合性大学序列的缺憾。
讲到大学校训的气度境界之维,不得不提北大校训“尚未挂匾”现象。众所周知,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之一的北京大学至今未能确立正式校训,北大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四种提法的“校训”,但目前均未被正式认可。[4]北大校训厘定之难,笔者认为,原因恐怕并非所谓“政学张力”和“众口难调”之说,而是在于一时难以找到一则既能在气度境界上统领中国大学,又能与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相颉颃的校训,无奈只能暂付阙如,以无形代有形。
(五)学术特色之维:强化大学精神和教育理念的独特性
对大学来讲,特色即是招牌,特色即是优势。把学校的学术特色融入校训之中,使之与其教育理念融为一体,亦是一种巧妙的构思,既强化表达了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彰显学术特色定位,又使得校训更具辨识度、联想性和传播力。一些特色型的高校把握了这一点,推出了独具特色和个性的校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中央民族大学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华中农业大学的校训“勤读力耕、立己达人”,华侨大学校训“会通中外、并育德才”,中央美术学院校训“尽精微、致广大”,这些校训共同的优长即是很好地开掘了学校既有的学术特色资源,反映了学科的特质,强化了其在人才培养理念方面的独特性,校训与学校浑然一体,使人仅凭校训就可以推断学校类型乃至学校名称。
校训的修辞和叙述方式讲求微言大义、和谐隽永。将学术特色嵌入校训之中,应当恰当地升华提炼,使之更加隽永和含蓄,以符合校训审美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民大的“美美与共”四字抓住了各文明、各民族在交往中互尊互爱、互鉴互赏的精神主旨,中央美院的“尽精微、致广大”融合了造型艺术的要求和东方艺术品格,二者都有一种唯美的气韵,属于此类校训的上乘之作。由于未作提炼和升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中央舞蹈学院的校训“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和成都理工大学的校训“穷究于理、成就于工”,虽也较好地反映了学术特色,然而略显生硬,比之上述两家就稍逊一筹。同时也应当注意,校训体现的学术特色,应当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公认的而非自封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学术特色,否则难以达到相得益彰、浑然一体的效果。
校训家家有,成就各不同。综览以上数十条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各具特色的大学校训,总体不脱离“立德立人”与“励学劝学”两大方面,每一条都别具匠心和巧思,言近旨远,辞约义丰,似有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尽管具体校训的强调重点有所不同,或单项突进、一骑绝尘,或两全齐美、相得益彰,或博采众长、融为一炉,总而言之,好校训之所以“好”,好在其至少在某一方面符合上述标准,或者说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三、结语:好校训的文化价值属于全社会
校训是大学在精神上的“顶层设计”,是现代大学的“标准配置”。声誉的积累只是大学在体格上的“长大”,大学真正的历史,乃是其非人格化的精神建构的历史。[5]对于一所怀有理想的大学来说,以校训为中心的大学精神的建构是一项必备的、关乎宏远的基础工程。
校训的品位直接反映着大学的文化品位和学术水准。任何成功的校训,必定高度凝练地叙述着大学自身文化主张和教育理念。这些校训反映着特定时空下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水平,凝聚着全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校训是一条无形的文化纽带,一端联结着大学师生员工,另一端联结着它的校友及其更广阔的社会,居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引领、精神维系和价值调节功能,其影响远不仅仅限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而是远远超越了大学的物理边界,影响围墙之外的社会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校训远不仅仅是所谓大学“三宝”(校训、校园、校友)之一,更是属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共有的宝贵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冯天瑜.元典之树何以常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83-89.
[2]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兼论道德论大学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05(6):1-6.
[3]庞晓东.从“211”大学校训看中国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J].教育学术月刊,2012(6):27-28.
[4]丁艳红,陈怡,郑惠坚.大学校训的文化蕴涵及其功能[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7-86.
[5]韩亮.论大学精神建构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及其限度[J].江苏高教,2011(3):22-24.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