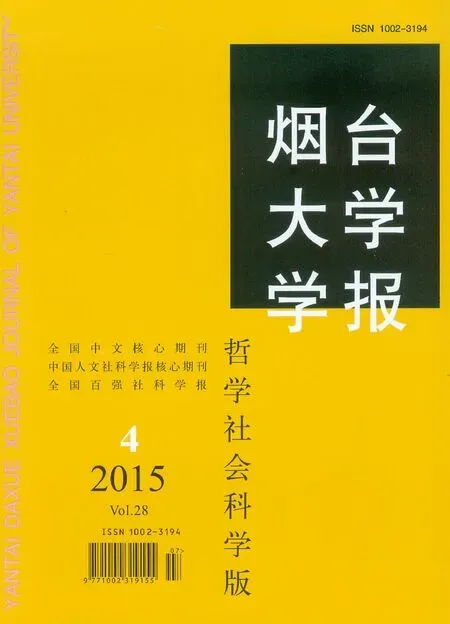《甲寅杂志》与民初言论界的“文学”浮现
邓 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甲寅杂志》与民初言论界的“文学”浮现
邓 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民初政论刊物《甲寅杂志》偶有文学创作,其大体因袭传统方式,基本不涉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学”的“现代”浮现的线索,表现于《甲寅杂志》的观念方面,在其众多的政治言论之中显得复杂、隐蔽,而所开拓的领域十分深广。《甲寅杂志》诸公以“人生”观照与评论小说,使得文学观念内化,同时也芜杂化,在其中不难发现新质。民初“文学”观念与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变化密不可分,在其内部逐步酝酿否定性因素,从而超越晚清的改良文学思潮。黄远庸就标出“新文学”一词,试图寻找根本的救济方法,认为“新文学”应与现代思潮接触,以启蒙的手段促人觉醒,改良人生。
《甲寅杂志》;文学;现代;人生;新文学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4.009
一
在五四之前的民初社会,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它们造成了巨大的共和危机,使得不断求索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大有用武之地,表现之一即为使用文言的报刊政论文字的空前繁盛。较之晚清刊物,一致之处在于现实政治的需求或直接或间接地带来某种对于“文学”的理念要求,整合出某些新的空间;不一致的是,在民初的这一时期,偶有的文学创作大体因袭传统文学,基本不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文学”的“现代”浮现的线索多表现于思想与观念方面的形塑,在众多的政治言论之中偶有“浮现”,显得更为复杂、隐蔽,所开拓的领域可能更为深广。在此,我们试图分析与重组一些不断重复出现的碎片,思考它们如何逐渐成为历史语境之中的构成性力量,乃至驱动性力量。
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在民初言论界有广泛影响的刊物——《甲寅杂志》,它以月刊的形式发行,创刊于1914年5月的日本东京,后转至上海,于1915年10月出版到第10期时停刊。在《甲寅杂志》之中,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民初现代知识分子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关注时政,并有针对性地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宪政——特别是英国的议会、政党、政府等知识,试图为新生的共和国移植与建立西方式的政治规则。在这些政论文章的语言使用方面,一改晚清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依托政府大规模兴起的自上而下“利俗”白话文的实践,而转向使用文言文,加之表达内容的需求,行文缜密而条理,向来有“逻辑文”、“欧化的文言文”之称——这可能也是中国文言文数千年发展的最后声音。在思想文化层面,《甲寅杂志》直接取径西方的眼光与做法,也为日后的《新青年》所继承。以致一位《新青年》的读者,将《甲寅杂志》与《新青年》视为延接与替代的关系:
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系纯党人之喉舌,皆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入政法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收益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分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愚以为今后大志,当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①《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无独有偶,另有一位《新青年》的读者也写到:
《甲寅》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时独一无偶。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甲寅》续出,《甲寅》之真直固在。独昔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尤望时时移译名人学说,如白芝浩诸篇然。②《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因此,我们会立即想到《甲寅杂志》与《新青年》的承接关系,或言《甲寅杂志》对《新青年》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两个刊物之中还有不少重要的共同撰稿人。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想沿袭使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线性思维方式,或如以往文学史那样,以五四为基点,再去返观与塑造包括《甲寅杂志》在内的“前五四”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做法。我们认为,民初《甲寅杂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视野与关怀,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的构成,而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在大量政论言论之中的浮现,很值得重视,从中透露出若干重要的时代信息。
二
让我们关注章士钊、苏曼殊与陈独秀这三位朋友在《甲寅杂志》一段文字因缘,以期说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文学”。具体说,即在《甲寅杂志》之中,章士钊著有文言小说《双枰记》,苏曼殊著有文言小说《绛纱记》,在小说内容本身之中偶有对小说文体的观点,如陈独秀所言,“烂柯山人(章士钊)前造《双枰记》,余与昙鸾(苏曼殊)叙之。今昙鸾造《绛纱记》,亦令烂柯山人及余作叙”③独秀(陈独秀):《绛纱记·序》,《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在这些往来议论留下的史料之中,较为集中表现出《甲寅杂志》诸公对“小说”以及文学的一些基本观点。
在《双枰记》里,章士钊谈及自己的小说追求:“然小说者,人生之镜也。使其镜忠于写照,则即留人间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价,吾书所记,直吾国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为忠实之镜与否,一任读者评之。”④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章士钊在给苏曼殊《绛纱记》所作的《序》之中,开篇就慨叹:“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彼自谓知之,仍不知二。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何也?知者行也。一知人生真处,必且起而即之。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生者也。”①烂柯山人(章士钊):《绛纱记·序》,《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词语“人生”出现了,并且这种对与小说的“人生”看法,已经与晚清新小说较为直接服务于维新政治的做法有了一定的距离,而试图以小说忠实表现人生的历程,与“人生”直接联系的多是“世道”,更多包含的是道德伦理方面的人生况味的思考与喟叹。
陈独秀后还在《新青年》之中,认为《双枰记》的主旨在于:
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人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烂柯山人之作此书,非标榜此义者也,而于此义有关系存焉。②独秀山民(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陈独秀评论用语与《甲寅杂志》中章士钊许多政论文字的术语相仿,“政治”、“国家”、“人民”、“自由”、“权利”、“社会”、“团体”、“个人”……这些词汇聚集而下,正好符合言论界的“文学”观念浮现的特点:在具体的批评之中,建构了一个团体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并将个人置于团体之前——这其实也为章士钊政论文字所一再表达。我们想说的是,思想观念的嬗变是否意味着晚清以来一个既有文学格局的即将突破?
陈独秀在分析《绛纱记》时,评述这篇小说的内容:
昙鸾存而五姑殁,梦珠殁而秋云存,一殁一存,而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五姑临终,且有他生之约;梦珠方了彻生死大事,宜脱然无所顾恋矣,然半角绛纱,犹见于灰烬。死也爱也,果孰为究竟也耶?③独秀(陈独秀):《绛纱记·序》,《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
这样的见解可以联系陈独秀对于章士钊、苏曼殊作品的一个总体看法:
乃以吾三人文字之缘,受书及序而读之,不禁泫然而言曰:“嗟乎,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死,曰爱。”生与死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说十二因缘,约其义曰:老死缘生,生缘爱,爱缘无明。④独秀(陈独秀):《绛纱记·序》,《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
这又回到对小说评论的“人生”看法与解读,我们继续读到的是无法解脱的生死爱欲,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以至于使用上佛教的教义,归于飘渺的缘生缘起、缘起缘灭。
可以说,民初《甲寅杂志》诸公以“人生”视阈观照与评论小说,使得文学观念不断内化,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芜杂化。在其中,既包含了他们复杂的人生经历及其在奋斗之中某种疲惫与迷茫,也有某种道德伦理的价值——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更为重要的是,不难发现新质的存在,如同前文章士钊与陈独秀的评论使用的若干关键词,“人生”也好,“个体”也好,“自由”也好,可以说对于“文学”的观念和知识情况与此时整体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变化密不可分,并在其内部酝酿与产生否定性因素,从而在文学见解上逐步超越了晚清时期的改良文学思潮。
三
这里需要把眼光扩展开来,在“文学”浮现的视野之下,以《甲寅杂志》为中心来梳理民初思想史发展的一些脉络。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刊发于《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颇为当时所关注。此文以一种强大的理性精神,反对晚清以来的“爱国心”: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①独秀(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感受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它实际上告别了晚清以来的那种“爱国心”,即那种直接为民族国家话语笼罩而无任何个人空间,或言个人仅是国家工具的“爱国心”,乃至于被当权者不断利用的“爱国心”。陈独秀正面标榜,认为需要建立的是个人理性的“自觉心”:“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②独秀(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对于“国家”这一虚幻的绝对存在,陈独秀直言批判:“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辱,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③独秀(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这样超越时代的议论,自然会引起极大的争论与反响。章士钊为之辩护:“往者同社独秀君作《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揭于吾志。侈言国不足爱之理”,“特独秀君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④孤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其实,章士钊面对民初的一片乱象,言语更为沉痛:“今言爱国,比于昔言忠君,畴昔疾首蹙额于君之所为,而不敢言无君,今有人尸国家之名,行暴乱之政,人之疾首蹙额于其所为,乃敢倡言有国不如无国。”⑤孤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在此情形之下,“团体”不足为恃,“个体”必然被赋予重大意义。很快,我们看到在民初的言论界,“我”被隆重推出,“我”成为解决民初乱局的重要手段,乃至于是“最后一根稻草”。
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发表的《国家与我》一文中认为:“曰道在尽其在我也已矣,人人尽其在我,斯其的达矣。此其理至易明,大凡暴者之为暴于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为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纾或径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为?”⑥孤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在今天我们看来这样的观点简直有点一厢情愿了,“我”不是一个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自足体,所构筑出的“我”本身就是绝对完美的,无视于社会具体环境,也无需作前提追问的。“我”的最大功能直接是针对当时黑暗政府,章士钊还写到:“故今之人辄怨政府之暴詈,哀吾民之无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价,非能如明珠之无因而至前也。今其所还之价,通国无一独立之人,到处无一敢言之报,人人皆失其我,人人皆不须此物,则此物胡来?”⑦孤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最终,在晚清以降政治不如人意,社会的危机不断出现之中,“我”被定格:“愚为彷徨求得解决之道,曰尽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请今之昌言不足爱而国亡不足惧者先尸之矣。”⑧孤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另可作旁证的是,章士钊在《东方杂志》还有一篇名为《我》的文章,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更为明晰:“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求我。上天下地,为我独尊。世间无我,既无世界。凡事我之所不能焉,未有他人能代而为之者也。他人所不能代而为之,未有孤特蕲向,存乎理想之物,独能代而为之者也。夫苟天下事,皆不能思议其为可为也,则亦已矣。一有可为,为之者断乎在我。是故我者真万事万物之本也。”①民质(章士钊):《我》,《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年1月10日。
有论者认为,诸如《甲寅杂志》以及这一时期有关的类似言论,正好说明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思想基点从集体到个体的嬗变。我们先且不说五四时期的“个体”,是否就是那么的纯粹与自足,这种似是而非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力图在历史中找寻线性而进化的文学线索,目的论倾向太过明显与僵化,实际上哪里会有那么单纯的“集体”与“个体”?《甲寅杂志》某些思想史意义线索的变化,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在现实的困境与危机之中,一些社会边缘的民间知识分子试图强行的历史突围,尚无力由此构筑新的文学范式与文学语言。陈独秀、章士钊等人有关“我”的话语,有着深广与焦灼的“集体”前提与内容,甚至我们还怀疑其中包含在宪政理想追求之中的某种挫败感。或者,还可以极端一点说,所谓的“个体”只不过是一种新的“集体”的表述,充满了精英式的担当与悲壮的情怀,颇能显示民初乃至五四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四
黄远庸与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的通信,由黄远庸首倡“新文学”,颇为引人注目。黄远庸用相当篇幅谈到民初中国社会一片黑暗而无路可走的情形,完全瞩目于“新文学”的拯救功能:
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谓存其在我者,即得为末等人,亦胜于今之所谓一等脚色矣。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②黄远庸:《通讯·释言》,《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黄远庸在这里表明了一个有力的观点:在现实面前,对章士钊式的“论政”实践已完全令人失望了,而试图另辟新路来寻找根本的救济中国的方法,这就是新文学。这种寻求“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不在于诸如章士钊等论政文章所涉及的国家、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机构,而在于更为抽象而内在的价值文化层面。具体说,“新文学”的功能应是使人与现代思潮接触,以启蒙的手段促使人的觉醒,改良人生,即是说形成一种以文学介入与创造新的政治的一种文化政治的思路——这也是日后五四文学革命一代的思路。固然,“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的说法,不无梁启超以小说为维新之本的功利思路,但它们所指向的方向已大为不同了,所表达的内涵也有了相当的差距。“文艺复兴”在文中的提及,也让人想起五四一代“文艺复兴”的情结,在这里有了提前的奏响。
章士钊给黄远庸的复信谈到:
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古初大地云扰,枭雄窃发,蹂躏簧舍,僇辱儒冠,幸其时政兴教离,教能独立,而文人艺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变为学圃,欧洲古文学之不亡,盖食宗教之赐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与民间事业相容,即莎士比、嚣俄复生,亦将莫奏其技矣。③章士钊:《答黄远庸》,《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章士钊之所以只能定位为民初《甲寅杂志》的人物,在于他坚持认为具体的政治,即政事的优先,国体、政党、议会等的优先,只有等这些先做好了,才能谈社会问题。文艺只能是社会问题之中一部分而已,更没有什么优先权和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政事的规范与清明,作为西方文豪的莎士比、嚣俄也没有意义。章士钊并没有为“文学”赋予一种宏大的“现代”意义,对于章士钊来说,政治与文学绝不能混淆起来,更不能以文学去解决政治、社会等一切问题,那样并不现实,反而会使得“文学”普遍地弥散开来,担当自身无法胜任的重任。我们认为,一方面章士钊的确是不能理解黄远庸的,就如同他日后不能理解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那样,他的文学观念与其政论一般,颇具英国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立场。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章士钊的看法其实并不乏理性与合理性,甚至可以以此反思黄远庸乃至五四文学革命一代人的某种“现代”立场,他们对文学的期待是基于一种信念的理想主义,并促使文学与民族国家层面的“深刻”意义结合,新文学在实践方面也造成了空前的浪漫情怀与需要总结的成败得失。章士钊的复信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如果历史按照章士钊的观点来发展,我们必然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了。
再联系到黄远庸在《庸言》杂志上的一段话语:
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而人群之激发实造端于感情。今有义务最足激厉感情、发抒自然之美者,莫如文学。窃谓今日中国,乃在文艺复兴时期。拓大汉之天声,振人群之和气,表著民德,鼓舞国魂者,莫不在此。吾国号称文字之国,而文学为物其义云何,或多未喻。自今往后,将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翼以筚路蓝缕,开此先路,此在吾曹实为创举。虽自知其驽钝,而不敢丧其驱驰之志也。①远生(黄远庸):《本报之新生命》,《庸言》第2卷第1、2号合刊,1914年2月15日。
这里面包含了较为复杂的信息:一方面,“民德”、“国魂”这些晚清民初流行语作为目的出现,是“文学”在功用上要达到的,所以“文学”是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根据事实、激砺感情、发抒自然之美——总体来说,思路大抵不能脱离晚清“文学改良”的路子;在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欧化”发展的思路,认为“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为创举,实为五四文学取径西方之先鞭,并且直接将这一文学发展的选择指向了价值层面的“思想文化”。
可以粗线条地说,是黄远庸而不是章士钊的思路更为接近五四文学——他们实际上已属于不同的文化政治理念。胡适谈到:“《甲寅》最后一期里有黄远庸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个政论大家的最后忏悔”,“他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他若在时,他一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同志,正如他同时的许多政论家之中的几个已做新文学运动的同志了。”②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3-134页。所以,胡适引黄远庸为同志,有极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民初政论界言论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某种正面联系。1915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远避袁世凯称帝的黄远庸被刺杀身亡,日后他的朋友还深情回忆:“我闲时常想着,若使远庸没有死,今日必变为浪漫派的文学。他本是个极富于情感思想的人,又是观察力最强不过的人,自然会与现代最新文艺的潮流相接近了。”③林志钧:《黄远生遗著·序》,黄远生:《黄远生遗著》,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9-10页。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我们也会发现黄远庸与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撰写《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陈独秀在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给人的印象不同于章士钊、胡适的英美式冷静与经验主义的理性,而是带有着某种法国大革命传统的理想主义与迅猛气息。
由《甲寅杂志》杂志,我们看到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王纲解纽”的一片混乱状态的中国社会之中,以边缘、精英的姿态出现,重新在知识阶层之中,而不再是以启蒙下层民众为旨归,全面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再以文言在观念上探索与赋予“文学”的时代意义。当1915年9月《青年杂志》于上海创刊时,民初政论家在此之后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由当日《甲寅杂志》中人的陈独秀的引领,中国思想与文学激情澎湃地翻开新的一页,“新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呼之欲出,召唤出一个新的历史行动主体。
The Tiger and Emergence of“Literature”from Critic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ENG 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s a magazine on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Tiger carries literary compositions occasionally,which generally has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way and hardly even touch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clue of literature modernity is complicated and concealed among political speeches,which is revealed in concepts of The Tiger,and it opened up profound realms.The writers of The Tiger appreciate and comment on novels from a viewpoint of life,which internalized and complicated the literature concepts.It’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new feature among their comments.The literature concept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re closely linked to changes of thought of the social elite,within which negative factors are brewing gradually and the reformed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surpassed.Huang Yuan-yong proposed the word“new literature”and tried to find means of relief.He considered“new literature”should contact with modern thought.By means of enlightenment people should be waken up and their life should be improved.
The Tiger;literature;modern;life;new literature
I 206.09
A
1002-3194(2015)04-0078-07
[责任编辑:诚 钧]
2015-02-16
邓伟(1975-),男,汉族,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研究(1898—1924)”(10CZW04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09YJC75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