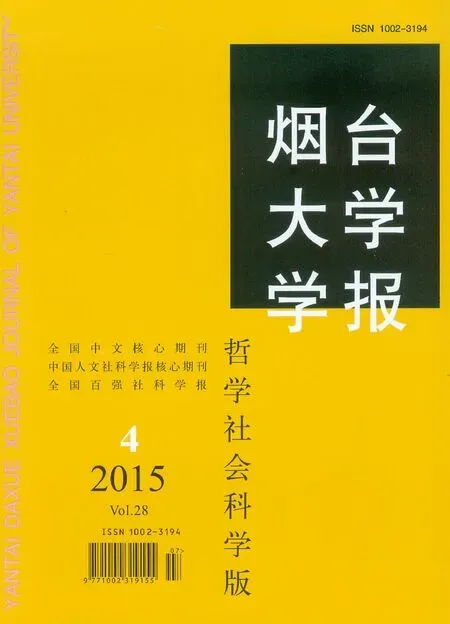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
——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安 宇,东·华尔丹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
——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安 宇,东·华尔丹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藏传佛教;自然环境;藏区;宗教信仰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4.013
青藏高原奇特的自然环境和博大神秘的宗教文化吸引了全世界研究者的目光,藏学因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①尕藏加:《藏学:一门21世纪的显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3月2日,第3版。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整体上对藏区的宗教、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进行多学科交叉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幸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员的《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于2010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近30万字,共八章,分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大部分,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地对藏传佛教与藏区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综合性地分析介绍。通观全书,有些重要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一、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的互相渗透
第一,作者通过分析藏族的神话歌谣,认为藏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中不断与大自然交往,形成了最初的宇宙观念。这种宇宙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基础之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这种古老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消蚀,但是依然潜藏在人们的行为观念中。“藏族先民就是在自己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提高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并逐步建立起具有深刻意义的宇宙观。由于这种宇宙观是藏族先民在同大自然交际中形成的,可以有无穷的变化,也可以不断修正。所以,藏族先民的宇宙观是不确定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变化,并趋于成熟。”①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第二,作者认为佛教对藏族人的宇宙结构论有重要的影响。“佛教在藏族地区立足并形成藏传佛教之后,完全替代了苯波教在藏族文化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从而改变了藏族人的古老宇宙观,他们开始用佛教的理论去重新认识大自然。”②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2页。这种影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宇宙观受佛教经典《俱舍论》的影响,认为宇宙空间无限且存在一个理想的与现实相对照的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将自然神圣化。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藏族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作者认为,“由于深受宗教宇宙观特别是藏传佛教宇宙结构论的影响,藏族人始终没能在科学意义上完全地掌握大自然的本质。”③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5页。由此导致藏族人对自然始终怀有神秘感和敬畏感,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
第三,藏传佛教继承佛教的思想将宇宙时间划分为六道,即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而人道具有其他五道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人类的修行和觉悟又有赖于“殊胜”的自然环境,其中青藏高原更是佛经中的圣地,藏传佛教就是通过这样的思想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
第四,藏传佛教密宗“即身成佛”的思想将修行者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僧侣投身自然修行秘法以求脱离凡俗,而“青藏高原这块神秘之地,恰好为这些修行者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④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23页。
第五,菩提心既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藏传佛教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使藏族人对所有“生灵”心怀怜悯,因此在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时能更融洽和谐,从而形成积极的生态伦理观念。
第六,藏族人对神山圣湖的崇拜,在客观上对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起着积极作用。这种客观作用,已经有学者通过数据比较作过有力的研究论证。⑤向红梅、张劲峰、许慧敏、郭华:《香格里拉县藏族神山与非神山植被比较研究》,《西北林业科学》2008第2期。
第七,藏族人长期生活在万物有灵思想的熏陶之下,自觉产生了保护自然的意识,对保护森林树木有积极贡献。如果说之前的分析都是从纯粹理论的角度阐释的,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是从具体形式上分析宗教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作者认为天葬的习俗使藏族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当世界各地尤其在广大农村,连年建造坟墓,致使耕地面积锐减,面临土地危机之时,藏族地区由于推行天葬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压力或矛盾。”⑥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45页。其次,藏文石经作为宗教思想的承载形式,体现了藏族佛教信众的“宗教同自然永存”的信念。最后,帐篷寺院是藏族人以全新的文化手段或宗教信仰方式与大自然理顺关系、和睦相处的一种大胆尝试。
总之,一方面藏传佛教思想中蕴含的宇宙观、轮回思想、“即身成佛”论、普度众生的思想,以及苯教中的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思想对于藏区信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藏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又影响到宗教思想的承载形式,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藏区特殊的丧葬形式、石刻佛经和帐篷寺院。并且在第二部分的个案研究中,作者以迪庆藏区的生态环境为例,具体分析了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神山圣湖崇拜,以及藏传佛教的教义、寺院和僧人在保护藏区生态环境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文化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鲜活丰富的材料。
二、藏传佛教对藏区经济的双重影响
尕藏加认为藏传佛教在藏区经济中以两种方式产生影响:一是文化意识形态,二是寺院经济实体,两种方式形成积极的和负面的双重作用。该书第一章就是在论述藏传佛教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第二章则是阐述其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对藏族社会的作用。这种影响是一个由内在观念到外在行为的过程。藏传佛教对藏区民众内在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们的物质观念、精神观念、经济观念的塑造,对藏区民众外在行为的影响则体现在藏区寺院的生存方式、信众与寺院的经济关系、藏区居民的消费模式、藏区寺院的经济功能等方面。
在物质观念上,由于藏传佛教“强调精神修养,而藐视物质的价值”,藏族信众受此影响,因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建设精神修炼的外部条件,使青藏高原逐渐改造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大佛教圣地”。①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58页。甚至,“随着宗教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在藏族社会中曾兴起一种风尚,凡一家人若有三子,常以一子或二子出家为僧”。②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5页。
在精神观念上,“藏族信众通过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把日常生活置于一种永恒的实体中,并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他们虽身在此岸世界,但心灵却在彼岸世界。因此,藏族信众不为现实的荣华富贵而竭尽全力,也不为高官厚禄而四处奔忙,更不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绞尽脑汁,只须追求精神的升华,为来世的投身铺路搭桥,从而获得彼岸世界的永恒幸福。”③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60页。
在经济观念上,经济价值是服从和服务于宗教信仰的,因为“宗教的信仰主义培育了冥思、禁欲的生活态度,而经济的理性主义则造就了追求利润、充满竞争的价值取向”,因此宗教信仰和经济的理性主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藏族民众在精神上十分富足而在经济上则相对贫乏。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的寺院一直垄断着藏区的经济文化,寺院的资产积累主要来自信众的宗教捐资,寺院建立之后为了自身发展也会“广收布施、施行摊派,以及开展化缘等推行宗教性的经济活动”。④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69页。作者将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消费活动归纳为四种:宗教活动性的经济消费、寺院建设性的经济消费、寺院僧人的物质生活性经济消费、寺院日常活动性的经济消费。⑤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71-73页。宗教性的经济消费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用于各种朝拜、朝圣和布施,由此寺院和信众形成一种互惠关系,作者将藏族信众热衷于布施的行为称作“无偿投资”,宗教精神追求和宗教“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藏族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藏族信众向寺院不断布施,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使寺院香火兴旺;反之,寺院也对广大信众赐予精神上的各种慰藉,满足他们的宗教心理需求”。⑥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75页。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在过去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尚不发达、集市贸易极为稀少的情况下,充当了青藏高原的集市贸易中心”。⑦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76页。一方面,藏传佛教在精神层面上维持其神圣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又依赖于世俗的寺院经济,寺院发挥着高原集市贸易中心的功能。个案研究中,作者通过列举拉孜曲德寺、亚东噶举寺、江孜白居寺、工布措宗寺、拉日色布寺、东嘎寺、噶陀尼寺、拉萨色拉寺等寺院,具体分析了藏区寺院的不同管理体制、寺院文化、经营模式,试图对藏区寺院进行类型归纳,并寻找有利于寺院适应社会发展的模式,与上文中的理论分析相结合、相对照。
三、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1949年以前,藏区的教育体制主要表现为寺院教育,这种体制造成知识掌握在少数僧侣手中而广大藏族居民则文化程度很低的现象。藏区僧侣的崇高社会地位造成藏族社会劳动力缺乏,藏传佛教注重精神世界的价值影响了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针对藏区传统上所沿袭下来的种种弊端,作者提出宗教的世俗化、理性的宗教信仰和发展藏区文化教育等建议,重点是利用藏传佛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
藏传佛教在教育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寺院教育上。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在于培养精通佛法的大德高僧,是以佛教的经藏、典籍为主的教育体系,相比现代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局限性。作者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局限性归纳为三点:第一,从教育的对象看,寺院教育只局限在僧侣队伍;第二,从教学内容看,其宗旨在于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授课内容是“五部大论”和因果报应的佛教教义;第三,从社会功能看,知识被少数僧侣阶层垄断,不利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藏传佛教的教义影响藏区的社会劳动力。由于藏区僧侣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大量信众入寺为僧,整个藏族地区重寺轻家,导致整个藏族社会劳动力不足,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经济发展滞后。此外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对藏区民众经商精神形成阻碍和抑制,使得藏区难以孕育具有商业意识的民众和文化社会环境。
通过分析藏传佛教的这些社会作用,作者提出宗教世俗化和宗教的理性信仰两种解决方法,以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者认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过程,而宗教世俗化的实质就是宗教的嬗变,也就是说,世俗化的宗教不像传统那样规范、严谨、神圣,最终还要失去昔日的宗教灵光,成为社会诸多文化现象中的一种普通文化。”①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06页。这种革新有两个方面:一是藏族传统文化从藏传佛教中脱离,独立门户,缩小藏传佛教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二是藏传佛教中的个别信仰形式融入信众日常生活,成为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比如藏传佛教的居士和嘛呢康。此外作者在后文案例中又以具体村落为例,从寺院、圣地、高僧、村落、村民、个体、群体、性别及年龄等不同角度说明了正统信仰、世俗性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现状和变迁。②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07-109页。藏传佛教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成分,为提倡理性的宗教信仰,作者提出:“必须利用当前科学文化不断冲击而理性居于权威文化地位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导广大藏族信教群众面对社会状况,接受经济理性主义,并将理性贯穿于整个社会思想观念之中,尤其是让藏族信众树立一种理性的宗教信仰。”③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12页。
四、藏区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融现象
作者以四川阿坝藏区的尕沟村、龙康村、树正村和松潘县为例,分析了藏区多元文化的不同类型,说明藏区存在的藏传佛教文化、汉族文化、苯教文化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并通过追溯巴塘县基督教、盐井天主教、昌都清真寺、拉萨清真寺在藏区的历史和现状,说明藏区存在的多宗教共存现象。在诸多案例中,作者既从村民和个人的不同层次分析藏区民间信仰状况,也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观察青年和老年的信仰程度;既看到同一民族的多种信仰,也看到不同民族的同一信仰;既看到信仰上的同一,也看到其不同和分裂。这就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藏区宗教信仰的具体状况,也为研究藏区区域宗教信仰状况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研究取向。
综上可见,《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重视藏区宗教文化生态在发展过程中的变迁,全面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藏区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把它们放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进行透视;对很少有人研究的藏传佛教藏文石经和帐篷寺院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从具体表现形式上充实了藏传佛教与藏区自然环境间的复杂关系;把寺院的宗教形态与经济形态并重,既认识到它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它的不利影响,并通过大量案例试图归纳藏区寺院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和文化模式;把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和僧侣与寺院的关系进行历时性的分析,说明其变迁过程;对藏区多民族多宗教交融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要梳理,为当下民族宗教和谐发展提供借鉴。
此外,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多样而丰富的案例充实了理论分析,能给研究者提供具有生动启发性的素材。该书较全面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了研究并试图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并有一定探索性。
但是,《藏区宗教文化生态》还存在继续深入探究的空间。首先,作者本人是藏族人,一方面具有很多其他研究者不具有的调查优势,同时却容易产生“走进去”易而“走出来”难的问题,分析很容易陷入藏传佛教思想束缚中,而作者似乎又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观点去纠正这一思想。因此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在两者间的摇摆,他很难通过主位与客位视角的变换来获得新颖的启示性的观点和分析路径。其次,作者对藏区的宗教文化生态进行全面地分析并探索其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全面性有余而系统性、深入性不足,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理论,强有力地分析和证明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三者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虽然通过藏传佛教作为核心,易陷入宗教思想分析的窠臼。其中,第一章整个篇幅都在分析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体现在宗教思想通过对藏族民众思想行为的塑造从而作用到自然环境的,而对于自然环境对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却分析得很少。该章后半部分,作者似乎是想通过丧葬、藏文石经和帐篷寺院这些宗教思想的载体来体现自然环境对藏传佛教的反作用,但是分析的过程又陷入到历史文化的泥淖,自然环境的作用体现的不明显,只是零星地分布在某些字里行间。如果只是分析宗教思想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而缺乏自然环境的反作用,那么这个分析就不充分、不全面,这也说明作者系统性分析上的不足。最后,书中一些用词方面显示出作者总是试图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看待藏族文化,而不是站在多元主义的角度。比如作者在分析藏族歌谣时说“当然,现在看来,这种世界或宇宙形成的认识,显得十分幼稚,可它揭示了藏族先民很早就有自己的宇宙观的事实。”①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0页。还有,作者在阐述藏传佛教对藏族宇宙观的影响时说:“总之,由于深受宗教宇宙特别是藏传佛教宇宙结构论的影响,藏族人始终没能在科学意义上完全地掌握大自然的本质”。②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第15页。在这里,作者已经预设了科学的绝对正确性,只有科学而非宗教才能认识自然的本质。当然,这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作者作为藏族人,渴望藏区快速融入现代社会而摆脱经济文化滞后局面的急切心理和探寻藏传佛教文化与科学精神互补关系的尝试。
虽然该书有一些不足,但是仍然不失为一本对当下藏族文化、藏区生态文明、藏区寺院经济研究者,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很有启发性的著作。作者多年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多年来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如《西藏宗教》《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雪域的宗教》《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等,发表的论文对藏族石刻佛经①尕藏加:《果洛石经的创建过程》,《西藏研究》1996年第3期;尕藏加:《果洛石经的分布及其规模》,《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尕藏加:《果洛石经产生的历史背景》,《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尕藏加:《果洛石经文化》,《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3期,等等。和藏族僧侣②尕藏加:《当代藏区僧侣与宗教职业生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藏族寺院教育③尕藏加:《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质》,《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体制④尕藏加:《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管理体制的演进》,《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等都进行过专门性的研究,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性的著述和进一步思考的结晶。
The Interaction Among Religion,Culture and Ecology: an Illustr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by KalSangGyal
AN Yu,DONG Hua’erd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Yinchuan 750021,China)
KalSangGyal systematically does a research about Tibetan’s religion,culture and ecology in his latest work Religion,Culture and Ecology in Tibetan Area attempting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above three correlative factors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cases.H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Buddhism on Tibetan culture and ecology from macroscopically and microcosmic levels.KalSang-Gyal emphasizes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ibetan Buddhism through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 excepting to guid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and get Tibetan rid of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lag
Tibetan Buddhism;ecology;Tibetan area;religious belief
C 95
A
1002-3194(2015)04-0108-06
[责任编辑:曹鲁超]
2014-10-21
安宇(1988-),男,山西阳泉市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东·华尔丹(1967-),男,藏族,甘肃天祝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甘青牧区藏族生态移民产业变革与文化适应研究”(NCET-12 -0664);北方民族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甘南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舟曲多元宗教的分析与比较”(YCX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