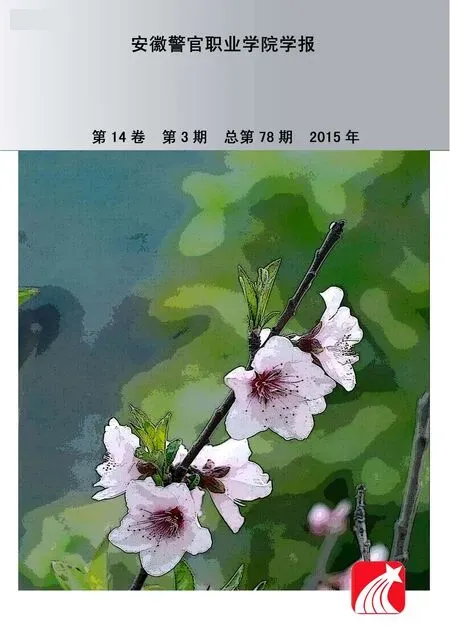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关系的失真与还原
柳一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关系的失真与还原
柳一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法律的自治性、司法与民主的纠葛以及精英主义思想,造就了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的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于思维焦点、思维背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但当前学界夸大了两者的区别,使得其失真。这些差异并不当然意味着两者的不可共存。事实上,在法治社会里,它们在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融通的。就中国当下情形而言,须还原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本相,并在尊重两者区别的基础上,以法律程序来沟通彼此的联系。
法律思维;法治;司法独立;民意
一、引言:法律思维研究的乱象环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大立法”时代,立法的要求使得法律人热衷于构建法律的自治体,藉此,法律能区别于其他规范体系而独立地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近些年来的调解压力也使得法律思维越来越受学界重视,法律人希望通过对法律思维的研究能一定程度上维护法律的独立和权威。且通过对法律人思维的研究,能对法律权利、法律信仰、法律价值、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方位、法律职业、司法改革等诸多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某种统摄和推理以及理论上的深化。[1]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对法律人思维概念和特征的简单介绍;其二,法律人思维与法学方法、法学教育;其三,法律人思维与法治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突出对法律人思维特性的归纳。这些研究似乎隐含了或假定了,不管真假:①法律人思维与其他思维不同,也应该不同;②这不同正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要求,倘若相同则严重妨碍法治建设。故基于法律思维的研究意义及对目前研究现状的思考,本文列出一问题清单,包括但不仅限于此: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有何不同;造成两者相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当前学界如何看待这一区别;两者又是否存在联系,若有,则存在什么联系;如何看待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等等。本文试就此发表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二、失真:放大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区别
当前学界一般认为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区别主要在于思维焦点、思维背景以及思维方式三方面。在思维焦点上,法律思维大多考虑法律正点,而大众思维则更多关注案件事实情节;思维背景方面,法律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而大众思维则为日常生活思维;思维方式上,法律思维多采以三段论为主的演绎推理,而大众思维则为类比。然学界对这些主要差别有放大之嫌,放大的背后更多地寄托了他们“美好的愿景”。
(一)思维焦点:法律争点与事实情节
法律案件能进入公众舆论往往因案件的某一方面能吸引大众眼球,而对法律人来说则是法律案件中存在的争点。涉诉舆论反映的是大众思维,它与法律人思维发生偏离,特别专注于案件事实情节——最为典型的是有着强烈对立性的当事人身份信息。以杭州飙车案为例,大众思维关于身份信息对立性的关注点主要有:其一、富二代与穷二代,双方贫富差异悬殊;其二、坏学生与好学生,富家子弟不学无术而穷苦人家子弟刻苦学习考取名校;其三、肇事方飙车撞人,受害方即将结婚。[2]同样舆论还较关注“玩的什么车?还是高级跑车”、“恋爱八年并且今年准备结婚,居然被撞死了”以及“看看被害人那张遗照,多可爱多可惜”等案件事实情节。而在这起案件中,法律人则较多关注案件的法律争点——是否为犯罪、犯什么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进而为作出判断而考虑犯罪构成要件,例如:犯罪的侵害客体(驾车撞人侵害的是不是特定的对象)、犯罪客观方面(超速程度、肇事车辆被部分改装)、犯罪主体(肇事者法定年龄与精神病排除)以及一些违法阻却事由。[3]这些例举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众将太多眼光放在案件当事人强烈对立的身份信息等案件事实情节上,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案件争议本身,而是其外围因素。而与之相对应,法律思维某种程度上能克服情绪的影响,根据专业知识来发掘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争点——在大众关注比较多的刑事案件中则主要表现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关注。
(二)思维背景:法律职业与日常经验
法律是一门技艺性规范,它要求法律职业具有高度专业性,因而想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历练。法律思维作为法律职业化的标志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职业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严密的逻辑体系构成。[4]法官判案的过程即为对这些规范进行演绎的过程,它具有程序性和独立性,要求法律人在遵守相应的程序基础上独立地作出判断。还是以杭州飙车案为例,法律人判断肇事者的罪与非否就需要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判断罪与非否就需要将案件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对应”,从而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在法律规范涵摄范围内,这一过程同时需要大量证据的支持。而对证据的运用则需要遵循证据规则,这一规则具有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它起码包括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四个阶段,而每一阶段又相应的有着繁琐的程序要求。以质证来说,质证就应包括证据的出示与说明、发问、质疑和答辩,而发问又涉及到发问的主体、对象、内容以及方式等。
与之相反,大众思维一般包括日常经验、传统习惯和常识三方面,它依据日常生活的、伦理的、道德的等方式来进行,易受他人暗示而影响判断,往往只是追求情感的宣泄与满足。还是以杭州飙车案为例,大众会首先对该案中的当事人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判断:肇事者为恶(富二代、坏学生);受害者则善(穷二代、好学生)。继而在这种情感偏好之下对裁判结果持这样的倾向性:肇事者恶,所以说的都是狡辩,不存在正当诉求;受害者善,所以诉求应支持。这一思维实际上是将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不加区分,把“上帝的事和凯撒的事”都交给法律去管。这种舆论的倾向性往往反映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大众将愤懑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了网络舆论中,从而,网络舆论的力量恰好与现实身份的力量构成了倒置的关系,现实世界中的强势者在网络舆论中往往沦为弱者,其正当的诉求也容易遭到公众的否定。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导致的后果即司法成了大众发泄各种不满(对道德现实、对官员作风、对富人行为等各种问题)的宣泄口。
(三)思维方式:演绎推理与类比推理
法律思维采用演绎推理,最为典型的是三段论的运用;大众思维则采用类比推理,将性质相似的案例作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最典型的演绎推理为三段论。以杭州飙车案为例,法律人思维在对肇事者的行为进行判断时会先找到一个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然后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从而形成一个判决,在判决中会判断飙车者罪与非罪,有责无责,量刑几何。当然,依具体的个案事实,所需要找寻的大前提可能不只一个,而是包括多个推理过程。此外,为保障大前提和小前提中的“中词”保持同一律,还需要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客观世界存在着普遍的联系,相似性是事物之间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类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中占有重要位置。大众思维采类比推理,类比需要寻找一个相似点,这一相似点需在性质上存在极高的类同性即“事物的本然之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一种形象的类比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思维,这使得大众思维对事物之间相似点的找寻异常简单甚至粗暴:所有的案件当事人只有善与恶,善需扬恶需惩。于是大众思维多要求同案同判,不仅是罪名一样,量刑也必须一样,至于案件事实不同点对量刑的影响大众思维并不太在乎。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除上文所归纳的三种主要区别外,还有这些区别:法律思维主要是依规则的思维,以权利为分析的出发点,尊重法律程序;而大众思维的主体(一般公民)则可能依朴素的法情感和正义观来思考问题,且极易受情绪影响。
(四)差别放大的背后:对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渴望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作为两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这一差异性受学者们所青睐,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学者们对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渴望,且欲借此研究向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导向,即倡导法治理念下的诸原则——法律至上、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等。其一,是对法律自治体的构建,借此与其他规范相区别。“为了使法律具有逻辑自治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高度发展的各个法律制度都力图创建一个有关法律概念、法律技术与法律规范的自主体。”[5]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使得法律与其他规范体系相区别,它要求司法与大众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大众思维往往有结果主义或实质主义的倾向——相较于法律人对程序的钟情,大众思维更加注重案件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效果。其二,是对司法独立的追求。法官只直面法律与证据,不能直面公众情绪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因为各种情绪所反应出来的问题只能更多地通过立法来予以解决,对属于立法的问题司法必须保持必要的克制。司法过程中应保持最起码的独立,排除大众思维的干扰,而以超脱的中立态度对权力、权利和义务作出判断明晰。其三,对精英主导的法治进程的偏好。法治在精英主义看来只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制度规范的过程,他们理应发挥主导作用,主导法治的发展路向并控制法治的实际运作,而民众只是法治的客体,被动地接受法律的统治。这一主导作用被认为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它是技术理性,而不是自然理性,对它的获得需要专业系统的教育或培训。此外,还因法律事务越来越繁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这使得处理法律事务机制的日益专业化。而专业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技术和知识的垄断,由法律人创造出来的法律概念、法律方法以及法律教育等都是在为这一垄断源源不断提供养料,阻断外行人轻易进入法律职业。
三、还原:联系是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关系的本相
在我国法治建设刚起步的阶段,立法迎来了大发展,这一大立法时期法律人特别渴望能构建起法律的自治体,因而法律人思维受到学者重视也属理所当然。但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已如期完成”后,我们是否还应夸大法律人思维和大众思维的差距?答案是值得怀疑的。
(一)对本相问题的基本考量
法律本身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法律思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源自于大众思维,现却因法律自治性、民主与司法的龃龉以及法治的精英化呈现分裂趋势。而法律思维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它就必须与大众思维有互译的可能。[6]且“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7]再者,法治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法律人在面对法治这一问题时应保持起码的独立。如果你问某人2+2等于多少,你会得到一样的答案,无论他是法律人还是非法律人。倘若法律问题都与此类似,很容易以精确追问的方法给出答案,那么无论实施法律的“人”何等不同都没关系,那就确实是“法律”在统治。[8]要是我们承认法治为法律的统治而非法律人的统治,那是否应该怀着谦卑的心态去重新认真审视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关系?
在法治的要求下,两者更多地应是寻求彼此的联系。那联系要实现哪种状态呢?简单一点讲就是实现两者的融通,它不是解构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而建构一个新的思维体系,而是在对法治的共同追求下,尊重双方差异性,努力挖掘自身对法治的有益因素,以法律思维为主导,并积极推动大众思维参与进法律思维。一方面需要建立能充分体现公民利益的法律自治体;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更多的途径让各种民意得到表达,从而实现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的良性互动。以法律人思维为主导是因为它是根据法律的思维,它的逻辑前提是法律,这符合基本的法治原则——法律至上。此外,法律思维基于证据和程序而存在,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能克服情绪化的影响。而更需推动大众思维积极参与到法律思维中来,是因为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法治的逻辑起点、运行基础和归宿在于社会大众和现实世界;第二,大众思维的背后指向是大众希望诉求能得到表达,能真正参与到法治建设的建设;第三,大众思维能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司法的监督,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从具体法律制度看两者的联系
我们抛开理论不谈,以具体制度而观之,亦可看出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从不是单纯地存在,而更多地是联系着,无论在我国,抑或他国。
1.思维焦点方面——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得以交流最好的产物,它体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能对司法决策过程注入更多的社会公正感、对社会弱势个体的保护、对强权在握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制衡、对腐败的或者专横的法官的对抗。而最为重要的,它为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在交流的过程中,大众潜移默化地受到法律人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这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管道。“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9]具体而言之,托克维尔甚至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中获得的,陪审员在这里可以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方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法律。[10]而作为公众的代表团参与审判,则能够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说法”的引入和“法官意见的融通”有效地融通了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差异。
此外,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须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陪审团制度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精英化所带来的缺陷。这一点在英国的治安官制度和德国的混合法庭制度中也可以受到一定的启发。
2.思维背景方面——法官制度
我国《法官法》第9条规定了法官任职条件,其中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这一规定大致借鉴了大陆法律一些国家的经验——在思维背景上法学教育以理论教育和专业实践相结合。在法国,担任法官需要在国立法官学院实施为期27个月的实务教育,除最初的8个月上课外,其余的12个月学员需以法官的职责参加审判,此后,便进入各种实习阶段。但彻底的原理性思维仍是法官的关键。[11]而在德国,想成为法官需要两次考试,在大学修完10个学期以上的法律课程后才可以接受第一次国家考试,此次考试合格后就可以成为研修生,之后在法院、行政机关、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进行为期两年的研修;第二次考试合格后可以成为“有资格的法律家”(候补官)。[12]法官的培养上大抵都需要完善的法律理论知识学习,同时也注重专业实践。之所以除理论学习外还特别注重专业实践,是因为理论学习有这样的一些劣势:(1)书面上反复出现的事实被假定为完整且切合实际的,但真正的法律问题还不到事实问题的千分之一。[13](2)法学院研究案例可以为法律人提供一种替代的生活经验,更提供了在其生涯中最可能遇到的特别的生活断片(诸如犯罪、违反合同和种族歧视),但大量的案例材料并不是深入这些材料描述的社会现象之中的可靠指南。[14]相较于理论学习,专业实践可以让学生走出校园而接触到更为真实的案例,在真实的案例中去更多的熟悉案件当事人的思维活动,对社会现象也能跳出法学的局限而多方面的考虑。因而,职业专业实践的加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理论学习的不足,专业实践的过程也正是吸收大众思维的过程。
3.思维方式方面——指导性案例制度
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制定成文法典方便大众思维对“三段论”中大前提的查找。法律规范的制定是各方利益综合的结果,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预先充分吸收了大众思维,这也使得法律具有正当性。从而当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后,法官则只是“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判决的作出也只是“制定法的精确复写”,此时的大众和法官更多的只是一个称呼上的不同罢了。“法律的滞后、漏洞、真空等诸多不完善就是这种现实在立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制定法从未存在并且也根本不可能出现。”[15]我国当前逐步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如同英美法系中的判例法,就是对司法现实很好的回应。“在判例法制度中,类比是作出判决的普遍的和最有效的方法。”[16]类推在考夫曼看来不只是水平横向的两个案件间的比较,而是指垂直纵向的法律构成要件与具体发生的案件相结合的问题。也即,我们不仅仅找寻两案之间的“事物本然之理”,同时也是在看这一“事物本然之理”是否能被法律规范所包摄。这一过程实则为法官价值选择的过程,“事物本然之中,法官也经常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论证判决的合理性。[17]因此我们可以在判决中看到法官往往会依托某一条法律原则将民意反映到判决理由中去,从而把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冲突转化为事实与规范的问题。这些过程都很好地融通了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因为在对法律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上法律和大众思维的期待是一致的——实现法治。而大众也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中清晰地看到对待民意的态度,以及民意问题如何转化为法律问题。这反过来又使得大众思维对法律人思维产生了某种理解和认同,如同审判团制度般法律人的思维进入了所有公民的头脑。
四、余论:法律程序是沟通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桥梁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存在差别不容置疑,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司法独立,特别是在当前不容乐观的司法环境下。季卫东教授将此形容为“舆论审判的陷阱”:“权力裹胁司法导致舆论容易沸腾,权力绑架舆论导致司法难以独立;在社会正义与司法正义的激烈碰撞中,司法不断丧失权威,舆论逐步成为规范,而舆论又是最容易被猜疑、偏执、欺瞒、恐惧以及仇恨所支配,非但不能促成和谐,反倒可能加剧冲突,增强社会的不确定性。”[18]但舆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监督方式,还可以为法律提供正当性证成。倘若有一种中介能在法律思维和大众思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则可能起到这样一种效果:首先,能为法治前提——良法——的产生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大众思维的参与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提供了正当性;其次,良法的存在使得大众守法从被迫到主动为之,为普遍守法提供了心理和社会基础,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再次,大众思维的参与能监督权力的运作,迫使权力置于法律之下。而法律程序就是这座重要的桥梁,关于法律程序的功能,我们大抵可以从权利保障、控制权力、法治和效率等角度来阐释,但于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而言则主要在乎其反思性整合功能。程序在本质上应是过程性和交涉性的,它是特定人互动的行为,在这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内心需求想对方,同时向社会展示,使人的主观意愿客观化。尤为重要的是交涉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这对于弥合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隔阂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3(2):9.
[2]周安平.涉诉舆论的面相和本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J].中国法学,2013(1):162.
[3]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J].中外法学,2013(6):1117.
[4]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7.
[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6.
[6]陈金钊等.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J].求是学刊,2006(4):84.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55.
[8][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9.
[9][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11:347,348.
[11][12][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4-275,279-280.
[13][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88.
[14][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6.
[15]王杏飞.指导性案例的法理透视[J].政治与法律,2008(2):35.
[16]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0.
[17]孙笑侠等.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5):51-55.
[18]季卫东.“舆论审判”的陷阱[J].浙江人大,2011(12):41.
The Distortion and Red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Thinking and Popular Thinking
Liu yizhou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00)
The autonomy of law,the disputes of the justice and democracy and the elitism ideology created the difference of legal thinking and popular thinking.The differences mainly focus on thinking,thinking background and the way of thinking,etc.But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exagge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even make its distortion.These differences do not,of course,mean that the two cannot coexist.In fact,it is interaction and contact in various aspects in the society of the rule of law.This point can be seen a little in the concrete legal system(the jury system,lawyer system and the case guidance system).In terms of China's present situation, legal thinking and thinking must restore its nature,a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the difference to communicate each other connection by legal procedures.
legal thinking;the rule of law;judicial independence;public opinion
DF0-054
A
1671-5101(2015)03-0105-05
(责任编辑:唐世业)
2015-04-10
柳一舟(1990-),男,湖北监利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13级法学基础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