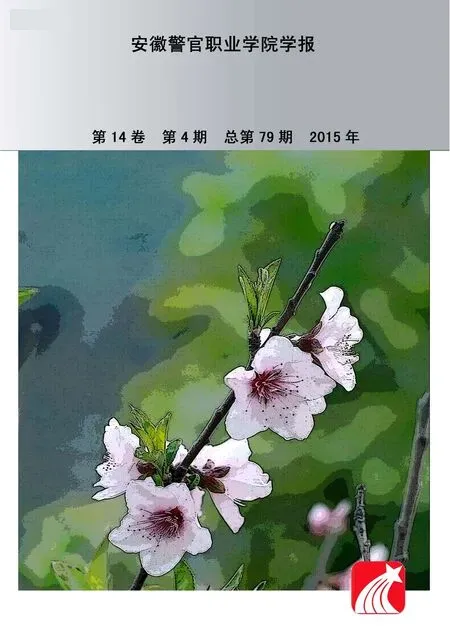论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与前景
梁婧雯(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论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与前景
梁婧雯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无疑是近十年来我国立法在专业服务机构组织形式上的一大创举。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优势在于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小众化的主要原因是设立条件较高、关于法律责任承担存在错误认识等。解决之道是:建立“直索责任”规则;改良律师事务所年检制度;完善法规,政策支持。如此,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中国律师事务所则必有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债权人保护
一、引言
“特殊的普通合伙”一词,最早出现在2007年6 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中,此后在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中得到细化,略略算来,它在中国已存在了近7个年头。7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经济势头强劲,法律服务业高速发展,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已然出现了一批合伙人众多的“航母级”律所。对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制而言,发展的黄金期已经到来。然则,现实却有些出人意料:
从2008年6月至11月,北京的大成律师事务所、新中银律师事务所和江苏的维世德律师事务所递交了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申请,这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位申请者。其中,2009年11月10日,在《律师法》(2008年修订版)正式实施后1年半,北京大成所才通过北京市司法局的审批,成为京城首家特殊普通合伙所。①关于京城首家特殊的普通合伙所,《中国最大规模律师事务所悄然转身“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献所给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无独有偶,在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直至2011年12月8日,方出现沪上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所——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而这已经是全国第14家。沪上第二家——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在一年之后才成功改制。
纵观全局,截止至2011年,我国已有约14万执业律师和13000多家律师事务所。但根据2012年7 月6日在包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研讨会”提供的数据,该种律师事务所在全国尚仅有40多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限责任合伙②此处即指特殊的普通合伙,二者内涵几乎一致,故在本文中将互换使用。在大洋彼岸倍受青睐的情况。2008年,美国名列前茅的50家律师事务所中,有43家采取有限责任合伙的形式。在合伙人少于100人的律师事务所中,采用有限责任合伙形式的远远少于200人或300人以上的大所。
这样的反差不得不引人深思。4年40多家,平均每年仅有10多家的增速,与该制度尚未诞生之时千呼万唤的舆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暂且不提北京市司法局1年半方通过一家律所改制申请的“惊人”
审批速度,素来有“改革先锋”之称的上海这一次竟然落在了最后①全国首批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共14家,上海首家该类型律所——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正是全国第14家。,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反观号称有“百万律师之众”的美国,有限责任合伙在顶级律所圈倍受青睐,有资料显示,近十年间有多家百年大所改制为有限责任合伙,像美国的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世达律师事务所等均榜上有名。[1]
面对这样的数据,笔者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是我们在移植这个制度的时候出现了偏差,还是它本身并不符合中国的水土?我们又应当如何打破目前的困境?下文,笔者将从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内涵、优势、问题以及展望这几个角度,为您揭开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神秘面纱,寻找被掩盖的真相。
二、关于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概念
《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律师法》第十五条对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做出如下解释: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律师事务所债务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律师事务所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律师事务所的一切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短短两句话一百来字,就是我国法律框架内对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最核心的规定。细细一想,其中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首先,如何界定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是否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再次,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份额以什么时期为认定标准?……此外,关于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和特殊的普通合伙之间的关系,就笔者所查阅的资料而言,竟也是众说纷纭。接下来,笔者将简要阐述有关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基本内涵的几个核心问题。
(一)重要概念的厘清
1.故意和重大过失
对于特殊的普通合伙而言,故意和重大过失无疑是一组最核心的概念。倘若无法界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区分也就无从谈起。二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故意和重大过失,在法理学上又可以统称为“过错”,界定的是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乃一种主观要素。法律以其客观性为基石,凡涉及人的内心活动,大多只进行宽泛的规定,允许审判人员按个案行使裁量权。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合伙企业法》还是《律师法》,都没有对此处的过错责任作出明确解释,这无疑给予了审判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鉴于律师事务所的特殊地位,笔者认为此处的过错责任应紧贴律师行业,高于对一般人的要求。
著名的“王保富诉三信律师事务所案”有效地佐证了笔者的观点。在该案中,原告之父聘请被告担任遗嘱见证人,但委托合同中仅约定一名律师到场见证,导致该遗嘱因缺乏一名见证人而无效,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判决中,法院认为:原告之所以聘请律师做见证人,是希望律师能够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识保障遗嘱合法有效。被告明知原告父亲的真意,就有义务告知其应该聘请两名见证人的事实。故法院最终认定被告败诉。[2]
由此可以得出,在执业过程中,律师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1)存在违法行为;②此处的“法”应作广义解释。(2)存在违约行为;(3)违反律师执业准则;(4)违反律师行业惯例。
除了以上四种之外,还应当考虑一种特殊情形:律师监督责任。《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九十五条规定:“律师对受其指派办理事务的辅助人员出现的错误,应当采取制止或者补救措施,并承担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充分履行监督义务的合伙人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此亦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监督责任应主要指团队合作情况,不包括合伙人对新律师的建议性业务指导和律师事务所管理者的日常性行政管理行为。
2.证明责任
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律师事务所侵权(或者违约)案件的证明责任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言下之意是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这毫无疑问是有失公平的。律师作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非专业人士很难证明律师是否存在过错。所以笔者认为,此处不妨效仿民法体系中关于特殊侵权的规定,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倘若律师事务所不能自证清白,就应当认定为存在过错。这固然对律师事务所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考虑到在医疗纠纷中对于医疗机构也有类似规定,笔者认为还是具有可行性的。
3.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份额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无过错合伙人承担的有限责任以其在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份额为限。但
是财产份额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数值,因为作为基数的律师事务所财产总额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问题接踵而至:究竟“律师事务所财产份额”是以过错行为发生时为准,还是以起诉时为准,还是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以起诉时为准较为合理,恶意转移财产的除外。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债权债务关系确立的时间,以过错行为发生时为准更符合法理,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这些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
(二)相近名称的辨正
1.特殊的普通合伙与有限责任合伙
笔者在检索信息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业内人士认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和“有限责任合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因是二者在风险承担上存有不同:“……(有限责任合伙)不能排除有人恶意利用出资额为赔偿上限的规定,使客户的风险加大。”[3]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我国的特殊普通合伙与美国法上的有限责任合伙别无二致,几乎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差别。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对特殊的普通合伙制进行追根溯源。
“特殊普通合伙”是一个从语法角度而言非常拗口甚至可能有些歧义的名称,但这个名词并非《律师法》首创,它首次出现于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不过正如同它那“非同一般”的名称一样,这个制度从调研、论证到最后的公告施行不可不谓是一波三折。早在2005年以前,立法者就已经确定要在我国引入有限责任合伙制,但碍于其他法律对合伙制度的单一规定,一时无法落实。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合伙企业法(修订草案)》时,第一次将合伙扩充为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三种形式。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司法部的建议,允许专业服务机构采用有限责任合伙形式。在《合伙企业法》的前两次审议稿中,立法者一直使用的都是“有限责任合伙”的字样。直到06年8月对该法的第三次审议之后,出于种种原因,才将名称修改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但就内涵而言,这两者并无根本差别。可以说,特殊的普通合伙就是有限责任合伙。由于《合伙企业法》珠玉在前,《律师法》也就不便改动,故而就这么沿用至今。
2.特殊的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以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有限合伙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合伙人分为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也不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且法律法规对于有限合伙人在行为能力和竞业禁止上的要求要低于普通合伙人。这与特殊的普通合伙在风险承担上有显著的不同: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下,合伙人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是不固定的,这与该合伙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有关。
三、特殊的普通合伙之优势所在
(一)专业化
律师事务所专业化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课题。所谓专业化,其实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得“小而精”,二是做得“大而全”。随着“个人所”与“特殊的普通合伙所”的合法化,这两条道路都有了实现的可能。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就是为了“航母级”律师事务所而量身定做的。
在传统的合伙所内,全体合伙人同呼吸共命运,每开拓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就意味着所有合伙人都要共担无限风险,哪怕那个领域你从无涉及。巨大的未知风险明显阻碍了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发展,而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则能有效减轻合伙人的后顾之忧。
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主任游闽键律师曾经这样评价协力所的改制之举:“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在法律服务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开拓出了很多新的业务领域。过去可能会有合伙人担心新领域的潜在风险,但现在的组织形式让大家底气更足了。”[4]
(二)规模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愈演愈烈,律师事务所的规模日益膨胀。从成百上千的合伙人到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律师事务所已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美国的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Baker&McKenzie)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77个办事处,1400名合伙人;[5]英国的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Overy)在3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6个办事处,525名合伙人;[6]我国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在境内外共有49家分所,律师总人数逾4000。[7]在这样律师总数动辄上千的大型事务所内,合伙人之间可能并不熟悉甚至互不认识,合伙组织所要求的高人合性标准已日益难以实现。但是在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模式下,合伙人从“无限责任”变为“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相当于给所有的合伙人买了一份“责任保险”。大家在执业过程中都会更加小心谨慎,因为一旦出现纰漏,很可能需要独立承担。这就有效地解决了异地分所独立承揽业务
却祸及总部合伙人的不合理问题,对于分所的管理大有裨益。
(三)国际化
正如前文所述,特殊的普通合伙(或者称之为有限责任合伙)已然成为国际高端大所的的第一选择,那么我国的这项立法革新就又有了更深更远的国际意义。一来,中国的顶尖大所可以以改制的方式顺利融入国际主流,使中国的法律服务业走向世界;二来也能够使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对外交往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可以比传统合伙时代更好地保护自己;最后,这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一大体现,为更多国际顶尖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我国设立办事处提供法律支持。
四、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我国小众化的原因
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有如此之多的好处,那为什么在我国依旧十分小众,以至于4年仅有40多家?这数量稀少的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阻碍?下文笔者将从设立门槛、政策、观念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为您深度剖析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在中国“遇冷”的原因。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制≧1千万资产+20名合伙人
这个标准相对于普通合伙所“30万以上资产+ 3名以上合伙人”的底线而言,要高出数十倍。很显然,这种高水准的硬件要求让很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在心动之初就自觉败下阵来。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在前文笔者提及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时,一直不忘强调这项制度是为实力强劲的超级大所量身定制的,这样的高基线本身也就希望起到吓退实力不足者的作用。
这样的考量并非全无道理。在美国,有限责任合伙主要集中于合伙人数在200至300以上的大所,而全美约84%的律师在个人所中执业,仅2%的律师任职于1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这样的数据告诉我们,虽然美国律所排行榜前50名有43家都是有限责任合伙,但除此之外,有限责任合伙的比例是并不高。有些人用美国法上关于有限责任合伙的宽松态度来攻击中国法律对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严苛标准,殊不知人家的宽容是建立在一个高度理性和发达的法律服务业之上的。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仅凭注册资本和合伙人人数去判断一家律所的大小,并不十分妥当,还应加入业务规模的大小为考量标准。他们认为先进制度绝不是单为大所准备的,即使是只有3个合伙人的律所也有适用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必要。[8]关于这种观点笔者持保留意见。确实,评价一个律所的大小并不能仅依靠资本和合伙人人数,但是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调和律师事务所规模扩张与传统合伙制高人合性要求之间的矛盾。那些业务规模大但是合伙人少的精品所与这里讨论的大小所并非适用同一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只有3名合伙人的律所哪怕资产再多,业务规模再庞大,都不适宜走特殊的普通合伙之路:仅有3名合伙人还不能够做到风险共担,那岂不是有违合伙制的根本要义?三人之间还要讲究有限责任,那与个人所或者公司又有什么区别呢?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年检时净资产不得少于1000万,否则就会暂停年检或者年检不合格。这实质上是在要求特殊的普通合伙所要常年保持高额的账面资本。这种额外要求无疑让合伙人们对改制一事更加谨慎。
本来大所就不多+高门槛+高年检要求……,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令中国的特殊普通合伙所诞生于一个残酷的客观环境中,自然量上也就稀罕起来。
(二)关于债务清偿上的错误认识
不知从何时起,拒绝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理由清单上多了这样一条:仅有过错者承担无限责任,其余人承担有限责任,会加大客户风险,造成案源流失。的确,在仔细研究之前,笔者也曾产生过这样的误解。但事实上,特殊的普通合伙与普通合伙仅是在内部责任分担上有明显差异,在对外债务清偿上几乎没有区别。
在论述债务清偿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特殊普通合伙所的对外债务进行分类。以《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七条为依据,可以将对外债务分为“执业活动中因过错产生的债务”和“其他债务”。对于后者而言,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与普通合伙别无二致,并非本文的讨论对象;而前者牵涉到无过错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问题,下文将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
图2中竖坐标表示子批量,纵坐标表示选择的工艺路线,横坐标表示工艺路线下的所有工序;式(25)中,数组O=[ot,r]4×r分别记录了工序加工所选择的机床、刀具、夹具、搬运设备,r表示工序个数;式(26)中,数组W=[we,r]w×r存储了调度过程中工序在机床上加工的顺序。
1.对外清偿顺序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为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这一规定属于一般性原则,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当然也不例外。
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在偿还外债的顺序上,律师事务所资产是排在第一位的,合伙人对外最多是承担补充责任而已。
2.对内分担规则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七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执业活动中因过错产生的债务,在对内责任承担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律师事务所资产足够清偿对外债务。当律所向债权人清偿完毕之后,有过错的合伙人以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足额补偿律师事务所支出的赔偿额。如果有过错的合伙人无力足额支付,那此时即须看该律所能否保持1000万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倘若不能,就要考虑其他合伙人是否愿意增加出资,以达到代为赔偿的目的。假设依旧是否定答案,那就应当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二条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等规定,解散该律所。
第二种,律师事务所资产不足以清偿对外债务。不足部分应当由有过错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之后有过错合伙人再足额补偿律师事物所。剩余步骤与第一种相同。
按照上述分析,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律师事务所,在偿还外债上都秉承律所资产优先的原则。所谓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之分,是债权人在律所资产不足时才需要考虑的情况。因而,就风险而言,律师事务所的财力才是债权人首要关注的对象,与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并无甚关联。坊间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增加客户风险”的传言,实则是对新制度的误解。
有观点指出,律所资产优先原则会导致有限责任的“滥用”:即通过合伙协议,尽可能压缩合伙企业的财产,导致债权人风险上升。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在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内,业务领域风险较小的合伙人一定希望律所资产越少越好,但风险较大的合伙人却可能因此流失案源。所以合伙协议首先是合伙人之间的一种博弈,在顶级律所内一定是趋向平衡。对于大客户们而言,律所的口碑比组织形式重要的多。
其实这样的忧虑立法者并非没有考虑到。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九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参加执业责任保险。这是我国建立替代性赔偿资源制度的一种体现。但遗憾的是,以上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具备细化实施的可能,尚有待完善。
(三)道德风险
在普通合伙制下,各合伙人之间利益攸关,相互有敏感的监督意识,以避免自己为他人的错误买单。因为经济的诱因,客观上造就了普通合伙所团结一心、齐心协力、荣辱与共的团队合作精神。
但是在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下,无过错合伙人可能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这就几乎将风险固定在自己的执业活动范围内。律师事务所内原先互相监督与合作的经济动因就此消散。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合伙人们会更加倾向于明哲保身,而不是主动履行监督职责。这无疑会导致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机制名存实亡,加剧事务所内部合伙人的独立化倾向,对于年轻律师的培养大为不利。
(四)法规有待细化,政策引导不力,各方认识有限
作为立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在法规篇幅上是极为“低调”的。在《合伙企业法》中,它仅占用了5个法律条文,共计458字,与有限合伙企业所占据的“半壁江山”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在《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条例》中也有些许相关规定,但大多是对《合伙企业法》的重申,细化、深入者少之又少。现有的法律规定仅能够让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步入运营轨道,一旦发生纠纷,就不足以力挽狂澜。举例而言,执业风险基金和执业责任保险本应是重要的替代性赔偿资源,但法律规定非常宽泛,不具备操作性。
作为一种新兴制度,又兼具高门槛、高要求的特质,在诞生之初,不被看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关部门制定一些奖励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支持、接纳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但是很遗憾,笔者并未检索到相关政策,甚至在实践中,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也鲜有报道。理论界在前些年还有些很热闹的讨论声,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但这些年也渐渐趋于平淡。在一个漠不关心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人敢做“吃螃蟹的人”呢?
前文提到,北京市司法局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
通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变更申请。可见不仅是律师界,就连行政机关也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漫长而严苛的审批程序令一些有所心动但不敢行动的业内人士直接打消了念头。由于双方对“新生事物”的认识程度都还有限,程序等各个方面尚不完备,许多大所还处在观望中,律所数量自然上不来了。
五、特殊的普通合伙之未来展望
(一)建立“直索责任”规则①直索责任是大陆法系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称呼,该制度在国内多采用英美法系名称——“揭开公司面纱”。鉴于“揭开特殊的普通合伙面纱制度”太过冗长,本文以直索责任简而代之。
直索责任规则,源自公司制度,更常见的名称是“公司人格否认”,又叫“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公司法体制下,直索责任可以穿透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使某些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利益。在美国法上,这种制度不仅存在于公司法中,也移植进了合伙企业法,称作“揭开有限责任合伙面纱规则”。这种规则适用于合伙人欺诈、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时的某些情况,同样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遗憾的是,尽管中国的债权人一样不放心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合伙企业法》却没有像美国法那样引入直索责任,这不得不堪称立法上的一大疏漏。
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在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立法上引入直索责任,并且可以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律所资产不充足。上文在讨论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清偿债务问题时,笔者其实遗漏了一种情况:律所资产不足以清偿外债,有过错合伙人亦无力补足余额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其余合伙人恶意缩减律所资产,欺诈债权人的情形,就应当认定此类合伙人存在过错,根据直索责任规则,追究其无限责任。第二,有违程序性要求。无论是美国法还是我国的《合伙企业法》,都要求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名称中标明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履行一定的公告义务,以免有欺诈债权人之嫌。倘若该种律所没有履行此类程序性义务,令债权人产生普通合伙制的误解,造成重大损失,就应当根据直索责任规则认定该所为普通合伙所,追究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
当然,直索责任规则的利用需要慎之又慎,应当时刻不忘欺诈和用尽其他救济这两大基本前提。若随意利用之,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二)改良律师事务所年检制度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第十四条,特殊的普通合伙所在年检时应保持最基本的设立标准,即1000万以上资产和20名以上合伙人。这项制度其实移植自企业年检,参考了国家工商总局《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的有关规定。年检制度对于企业而言似乎无可厚非,但是用在律所身上就有生搬硬套之嫌。我国法律并未将律师事务所定位为企业,律师事务所的注册和年检也都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而非工商部门。资本无疑是企业的生命线,但律所的根本却是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律所运营需要资金,但恐也不需要1000万之多。
更何况,根据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国家工商总局决定自2014年3月1日起停止企业年检工作,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在年报制度中,注册资本将不再成为核查内容,甚至企业在注册时大多不再存在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也无需提供验资报告。
律师事务所自然是与企业不同的。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是否取消注册资本的限制,笔者不敢妄言。但是不妨学习一下企业年报制度,灵活处理律师事务所的年检工作。比如,是否有必要要求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每年都保证1000万以上资产,这个标准是否可以下调一些,当该所出现不良记录时再恢复1000万的年检标准?
就像刘俊海教授说的,“企业年检防君子不防小人”。律师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行业,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更是行业翘楚,行政机关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做幕后的“协助者”而非台前的“指挥者”。
(三)完善法规,政策支持
在中国,特殊的普通合伙依旧是一个较新的制度。由于移植自海外,在本土又缺乏充足的实验土壤,法律规定不完善、执行经验不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和认同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新制度出台时的万众瞩目,到现如今的过问者寥寥,再任其发展下去恐要以惨败收场。一方面,立法者要秉承严谨的态度,结合实际需要,打磨、细化现存的法规,借鉴其他部门法的改良经验,大胆创新与尝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和律师界有识之士应当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界宣传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配合适当的奖励政策,定可以让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成
为中国法律服务业进军国际的排头兵。
六、结语
几经波折,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终于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一员。这不可不谓是中国法律服务业跻身世界一流的一道曙光。日本著名律师,国际律师协会(IBA)现任会长川村明先生曾说过,在法律服务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应对英美律师事务所进入本国并非首要问题,本国律师如何进军国际,在世界发出怎样的声音才是关键。
对于正在积极发展的中国法律服务业而言,不仅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来自国家的制度支持。虽然我国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尚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这费尽千辛万苦迈出的第一步已足以令我们看到希望。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W·希尔曼.论律师的流动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33.
[2]最高人民法院.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
[3][8]焦红艳.中国最大规模律师事务所悄然转身“特殊普通合伙”[N].法制日报,2009-12-10(3).
[4]范献丰.上海首家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揭牌——合伙人投入一千万分担风险[N].新闻晚报,2011-04-11(14).
[5]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EB/OL].[2015-04-11]http://www.bakermckenzie.com/zh-CHS/aboutus/.
[6]ALLEN&OVERY[EB/OL].[2015-04-11]http://www.allenovery. com/about/Pages/default.aspx.
(责任编辑:陶政)
[7]大成律师事务所[EB/OL].[2015-04-11]http://www.dachengnet.com/cn/about.
On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Prospects on Law Firms of Special Ordinary Partnership in China
Liang Jingwen
(International Law Colleg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Law firms of special ordinary partnership is undoubtedly a great undertaking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form of legislation during these 10 years. The advantage partnership is specialization, enormous scal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law firms of special ordinary partnership are not quite popular because standards for setting up such a firm are too high and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concerning the legal liabilities of the firm. The solution is 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direct liability, improve the annual inspection system of a law firm, perfect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eek positive policies. By doing so, we can foresee a prosperous future of law firms of special ordinary partnership in China.
【Keywords】special ordinary partnership; law firm; Limited Liability; creditor protector
【作者简介】梁婧雯(1992-),女,安徽合肥人,华东政法大学2014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5-14
【文章编号】1671-5101(2015)04-0028-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F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