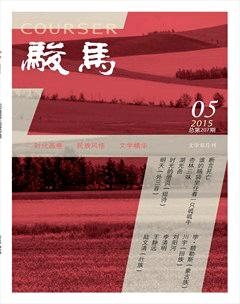谁的脑袋里住着一只呱呱牛
川宇
一
谁的脑袋里住着一只呱呱牛?是尤里福吗?不。是赛里目吗?不。是海哲吗?不。不。尤里福的白孝帽挡住了他大大的脑壳,呱呱牛怎么能跑进去?赛里目留着长长的头发,他浓密的头发一根挨着一根,每一根都阻挡了呱呱牛前进的脚步,呱呱牛怎么跑都跑不进去。海哲呢?海哲戴着她粉红色的头巾,刚从清真女寺出来,呱呱牛怎么能穿过那厚厚的头巾钻进她的脑袋?
你奶奶戴着白盖头坐在土炕上,一遍又一遍地掐着手中的泰斯比哈(念珠),念着《古兰经》里的一些句子。炕洞里她埋的煤聚在一块燃烧着,一些柴草也噼里啪啦地响着,炕面子很快被烧热了,紧接着暖炕的被子热了,你奶奶的脸也热了。你奶奶的脸一热,她就开始念经,“艾斯太俄非容拉亥力而咀买来贼”。她的声音不大,但足够你隔着窗户听到。哦,她在念讨白,讨白的汉译为“你祈求尊大的真主饶恕你的罪过”。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念经声中救赎着今生犯过的一些罪过。像她这样每天做五番乃玛孜(礼拜),虔诚念经的人,她的脑袋里绝对不可能住着呱呱牛。这是你可以肯定的事。但她偶尔会犯糊涂。她一犯糊涂,呱呱牛就会闪电一样地钻进她的脑袋。
你站在窗外透过玻璃看奶奶,你想确定那呱呱牛是否跑进了你奶奶的脑袋。你奶奶戴着白盖头,她白色的盖头厚实着呢,呱呱牛根本不可能穿过那盖头进入她的脑袋。更何况,她念经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句与句之间还拖着长长的尾音,听得人耳膜发颤。你听,那声音像一只跳跃的青蛙,顷刻间便从这头跳到了那头,从那头跳到了另一头。那声音让人无法捉摸。你根本听不清奶奶在念什么,但她就是念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地念,一行一行地念,大声地念,小声地念,在心里默念。她默念的时候,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土炕上,像北京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样,永远保持着不变的姿势和神态。你真的不敢想象有朝一日呱呱牛会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进入奶奶的脑袋,从而让她犯糊涂。但你不得不信,因为你发现了呱呱牛的秘密。呱呱牛,只是在奶奶犯糊涂的时候,才探出头透透气,把一切悲伤的,哀怨的,不着边际的事情统统以苦难的方式转移到了你奶奶身上。
其实,大多数时候奶奶都是明白人。只有在呱呱牛进入她脑袋的时候,她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不说话,甚至一整天也不说话。你记得特别清楚,这样的情形大约出现过三次。每一次,呱呱牛都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奶奶的脑袋里,然后顺着毛细血管东游西逛,或者像皮球一样在皮肤的表层弹来弹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让奶奶陷入短暂的休克。那样的结果是,大人们会围着奶奶,掐她的人中穴,用凉水一次又一次擦拭她的额头,直到从她的喉咙里传出一丝轻微的喘气声。你害怕听到那样的喘气声,它会让你惊颤,从而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与不安之中。
爷爷口唤的那一天,呱呱牛第一次进入了奶奶的脑袋。你清楚地记得,那天,奶奶傻傻地坐在南房的土炕上,木讷地看着一个又一个戴白孝帽的男人或者戴盖头的女人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左邻右舍问她话,她只是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她甚至忘了念经,忘了礼拜,她的整个脑子都被呱呱牛左右着。直到爷爷的埋体(遗体)被抬出家门的那一刻,她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她哇哇的哭声,哭碎了满院子的人,哭碎了你小小的心脏,哭碎了那只呱呱牛,让它无处遁形,最终不得不被一滴咸咸的泪水所掩埋。
漫山遍野的白孝帽,漫山遍野的白盖头,整个山台观都被送埋的人跪得满满的,白花花一片。你戴着白孝帽,那耀眼的白刺得你眼睛疼,像针尖一样扎在了你心上。你想起了小时候,爷爷疼你,疼在了心头上。土炕上,你骑着爷爷像骑着一匹老马,慢悠悠地从炕的这头走向炕的那头,再从炕的那头走向炕的这头。你咯咯地笑,用小小的手拍打爷爷的身子,还一个劲儿地说,口得驾,口得驾。人老了,会跑不动。马老了,也会跑不动。爷爷跑不动了,跑到了山台观上,跑到了那个长方形土坑里的偏堂(埋人的地方)里。你没有勇气走上山头,也没有勇气跪在那众多的白色之中,你只是一声不吭地陪着奶奶,抚摸着爷爷盖过的被子发呆,流两行清泪。
这该死的呱呱牛,它总是让人在悲伤与难过中度过。但你却无法找到它的踪迹。呱呱牛从爷爷口唤后,就销声匿迹了,再也找不到踪影。你奶奶花白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像盛开在五月的白梨花,让你想到裹着你爷爷的那几丈白色的穿布(尸衣)。
呱呱牛,你是不是追寻着爷爷的脚步去了?
二
你总是不停地追问尤里福,追问赛里目,呱呱牛到底住进了谁的脑袋?他们一问三不知。你问海哲,她更不知道,她去了遥远的省城读书,她怎么能知道村子里的那些事?问乃犹莎吧,她是奶奶的打心棰棰,她把奶奶照顾得无微不至。你问乃犹莎,她笑你吃饱饭撑的,没事找事。她说,你脑袋里有只呱呱牛。真的是这样吗?你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想把那呱呱牛从脑袋里敲打出来。
南房里,奶奶有事没事就拿着那本爷爷曾读过的经书,翻来覆去地读,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读得口干舌燥。如果乃犹莎在的话,她就会递上那把白色的小茶壶,让奶奶润润嗓子,然后乖巧地坐在一旁,听奶奶继续着她反三复四的诵读。乃犹莎真是奶奶的小甜心,换成你,你根本坐不住,也耐不下性子去听奶奶嘟嘟囔囔的诵读声。不仅如此,你还会绕着南房走,试图躲开奶奶嗡嗡的念经声。对,那声音就是蜜蜂展翅的声音。无论你躲多远,你总感觉有只蜜蜂在你耳边飞来飞去,嗡嗡个不停。是吗?是这样吗?你不敢确定。也许不是蜜蜂,也许是只呱呱牛,谁也说不上。
呱呱牛第二次进入你奶奶脑袋的时候,是你爷爷无常后的第三年。你本以为那呱呱牛已被奶奶的泪水淹死了,连渣滓也没有剩下。谁知你错了。错得离谱。那呱呱牛一直蛰伏在奶奶的脑袋里,它在伺机而动,一旦瞅准机会,它就会反扑,狠狠地咬向人最脆弱的地方,然后想尽办法去折磨人,最终让人不像人样。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一只小小的呱呱牛竟然可以支配人的意识,颠覆人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奶奶用手捂着头坐在炕角上,目光呆滞,神情涣散,任谁也问不喘她。乃犹莎问不喘,你也问不喘。呱呱牛在她脑袋里肆意妄为,导致了她眼中没有任何人的影子,她的耳朵也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怎么能这样呢?你担心地想,却又无能为力。你只能站在一边,看呱呱牛是怎样步步为营让奶奶走上苦难的开始。
事情的起因绝对不是一只呱呱牛所能想象的。奶奶的二儿子,素来麻,也就是你二大(叔叔),在你爷爷无常后的第三年也无常了。你二大无常的前几天,整个人骨瘦如柴,嘴唇像两片细长的小树皮碎片一样干裂,在慢慢的张合间才能吸进一些流食,从而维持他微弱的生命。那些流食,通过一条细长的塑料管子进入了你二大的胃。你看着那细长的塑料管子眼前发麻,不知所措。那管子多么像一条蠕动的毛毛虫,摇头晃脑地伸长着自己的身躯,一点一点滑进了你二大的嘴巴,滑进了喉咙,滑进了食道,滑进了大肠,最后滑进了他千疮百孔的胃。你看着那操持漏斗的白大褂,他将一些牛奶一点一点倒进连接管子的漏斗,忽然间觉得很恐慌。是的,恐慌。那呱呱牛定然钻进了你二大的胃里,要不然他怎么那般难受?你奶奶时不时会去上房看看你二大,然后一声不吭地返回南房,一个劲地礼拜,念经。院子里很少有人走动,除了你奶奶的念经声,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你二大无常的前些天,你奶奶念经的声音没有平时大,像一簇颤抖的火苗,一颤一颤地,颤得你心慌。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只是看着奶奶,听她将一句很短的句子断断续续念成一句很长很长的句子。哦,奶奶仍然在念讨白,“你斯太俄非柔克,力麻俩艾尔来木,引来克,按台……”句子的原意为“主啊,你求你饶恕你无意中犯下的过错……”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奶奶在念什么,那些句子的汉译是你后来从那本书中看到的。
你有种预感,蛰伏在奶奶脑袋里的那只呱呱牛很快会出现,它会让奶奶再度陷入一种无序的磨难之中。你的预感是准确的,你二大素来麻吸食了几天流食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无常了。你二大素来麻无常的那一刻,你奶奶掐的泰斯比哈从手里掉到地上,一颗颗四散开来,滚得满地都是。那一瞬间,你奶奶的心忽然咯噔一下,她好像知道儿子殁了,她无声地举起双手,结了一个都阿(祈祷)。然后对着上房跺脚,垂泪,吼叫。她骂素来麻二叔,不孝顺,让她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她骂爷爷没良心,丢下她一个人在这世上受罪。她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骂,骂着骂着她便一下子跌倒在地,晕了过去。大人们再次围着奶奶,将她抬上炕做一些急救措施,或者大声地喊她的名字。
你知道呱呱牛出现了,它在作祟,它再次让奶奶陷入了失控的状态。这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奶奶在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将自己撕碎,揉烂。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了。送埋的那天下午,在呱呱牛的操控下,你奶奶破天荒地走上了三年来从未走上的山台观,走上了那块埋葬着爷爷的坟地。那块坟地也将埋葬你的素来麻二大,他的坟紧紧挨着你爷爷的坟。乃犹莎搀扶着你奶奶跪在你爷爷的坟前,她哽咽着,你奶奶也哽咽着,风也哽咽着。风像个调皮的孩子,在模仿完奶奶孙子的哽咽声后,一会儿吹开乃犹莎的头巾看看,一会儿揭起你奶奶的白盖头瞅瞅,它甚至还钻进了你奶奶的袖筒,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窜来窜去。你奶奶浑然不知风的淘气,她只是一个劲地清理着爷爷坟头上的杂草,就像年轻时她第一次为爷爷理发一样,一根一根地理,一根一根地拔去那坟头的杂草。
阿訇(清真寺的教长)往坟坑里下埋体时,你奶奶没有流泪,她只是茫然地跟着众人结都阿(祈祷),然后颤歪歪地扭过头,一声不响地在乃犹莎的搀扶下原路返回。上山,下山,你奶奶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流。但你知道你奶奶心里的那条泪河已然决堤。是的,绝对是那样。呱呱牛在那条泪河上漂荡着,你奶奶怎么能好受?它不折磨死你奶奶才怪!如果让你捉住它,你一定会揪着它的耳朵审问它昔日犯下的无数罪过,让它在自己的忏悔声中不安与难过。这,比什么惩罚都好。
哎,那该死的呱呱牛,怎么说出现就出现呢?
三
事情的变化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你原以为那呱呱牛在你素来麻二大无常后会很快消失,就像你爷爷无常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谁知你错了,错得离谱。呱呱牛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躲在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时不时冒出来进入你奶奶的脑袋,在里面安营扎寨,兴风作浪。
你二大素来麻无常后,你奶奶病倒了。整整三天三夜,你奶奶蜷缩着身子躺在炕上,不吃也不喝。你大(父亲)鲁格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茫然不知所措。你四大买买提,你五大二不度,他们都一脸忧伤地蹲在廊檐下,商量着念索尔(祭奠)的事。你三大嘎细儿一大早去牛集买也贴(宰牲)去了。你姑姑阿依舍戴着白孝帽整夜陪着奶奶,她的眼睛哭得红肿红肿的,像两颗涂着红漆的小核桃镶嵌在大块头的洋芋上,看起来让人怜惜。你四娘曼竭和乃犹莎在灶房里给你奶奶熬着小米粥。你看着奶奶难受的样子,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可恶的呱呱牛,怎么能在进入奶奶的脑袋后,还能同时侵蚀更多的人的脑袋?瞧,大人孩子们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蔫蔫的,不是耷拉着头,就是神情没落。好了,呱呱牛,你的罪行不是几个茄子能够说清的。
给你二大素来麻念头七的那天,你奶奶的病得到了缓解。你想,或许那呱呱牛又藏了起来。藏起来了好啊,藏起来了你奶奶就不用受它非人的折磨了。天麻麻亮时,你奶奶就睁开了眼睛。你奶奶一睁开眼睛,就吵着要礼邦布达(晨礼),吵着要下炕去洗小净,你四娘曼竭和乃犹莎挡都挡不住。挡不住,那就随了她吧。乃犹莎扶着你奶奶下炕洗了小净,随后又扶着她上了炕。一上炕,她就铺开了拜毡,将那串她经常掐着的泰斯比哈放在一旁,虔诚地念经,跪下,磕头,起来,跪下,起来……你奶奶的身子很虚弱,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嗓子里时不时冒出来,颤颤的,让你不由得想起很早很早以前在乡下看到的一架手拉的风匣,手拉一下,风匣就动一下,灶膛里的火苗也随之大一些。你奶奶的嗓子就像个风匣,她在吃力地拉着,每拉一下,嗓子就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不仅如此,你奶奶还不住地跪下,起来,不间断地重复做着一些简单而复杂的动作。不,不,你奶奶的身子还特别虚弱,你甚至不知道她跪下的时候会不会起不来,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忽然跌倒。她怎么能经得起那样的折腾?事实上,你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天,她不仅顺利地礼完了邦布达(晨礼),还礼了撇师尼(晌礼),迪格(哺礼),沙目(昏礼)和护伏坦(宵礼)。
头七过后,你奶奶的病好了起来,她照常每天礼拜(祷告),念经,拿一些钱财舍散给穷人。你奶奶一天天精神了起来,她又重新拿起了那本被她磨得发破的经书,天天读着,日子也一天天过去。紧接着,是四十,百日。每一个祭日,你奶奶都会大声地念讨白或者诵读一段《古兰经》,以此怀念她的丈夫和儿子。这期间,谁也不敢提素来麻这个敏感的名字,一提到这个名字,呱呱牛就会在你奶奶的脑袋里翻江倒海,让她痛苦难受。还好,谁也没有在你奶奶眼前提起素来麻这个名字。这让呱呱牛无从下手。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起你二大的名字,说起他曾经的过往,好像他未曾来过这个世界。也许若干年后,没有人能记得他的名字。谁能说得上。
百日过后,一切都趋于平静,回归了原来的模样。院子静了,呱呱牛静了,你奶奶的心也静了。
一切平静的背后总酝酿着一些不平静的因子。
你以为风平了,浪才会静下来。其实不然,风总在吹,变着法子的吹着。浪也总在翻转,变着法子的翻转着。一些细小的风,它会在你不经意时悄悄亲吻你的头巾,吹皱一些或近或远的记忆。一些小小的浪花,它在归于平静时,会以一个点为中心一圈圈荡漾开来。你二大素来麻无常后的两年内,日子恢复了平静,每个人照常做着自己要做的事。你奶奶照常念她的经,你四娘曼竭照常摆她的小摊,乃犹莎照常做她的护士,尤里福照常打他的零工,买买提照常到处转悠,二不度照常做他的白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你知道,一段平静的日子后面,往往跟着一段不平静的日子。两年后的某一天,呱呱牛再次爬上了你奶奶的心头,打碎了她一贯平静的日子。这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事情。
碎了,都碎了。你奶奶碎了,你碎了,鲁格麻碎了,嘎细儿碎了,阿依舍碎了,二不度也碎了。所有的人都碎了。所有的人都被呱呱牛操控着垂头丧气,心胆俱裂。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从遥远的省城兰州传来了你二娘崽来拜无常的消息。那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霹得人晕头转向。谁也无法相信那消息的可靠性,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两年前,你奶奶的二儿子素来麻无常了。两年后,你奶奶的二儿媳崽来拜也无常了。你奶奶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掐泰斯比哈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根摇摇欲坠的稻草,随时都有跌倒在地的可能。你四娘曼竭扶着你奶奶,哭得像个泪人。你奶奶没有哭,她只是一个劲地念“安拉乎,安拉乎”(真主)。不知为什么,你总觉得你奶奶在哭,她甚至要比任何人都哭得悲伤,哭得肝肠寸断。对,就是这样。你奶奶早已哭干了泪,她干瘪的眼睛再也挤不出一滴泪水了。她只能把泪往心里流,任凭那呱呱牛在泪水积成的河流里漂啊漂,直到漂成一滴燃烧的泪。
不安分的呱呱牛,它怎么又开始作祟了?
四
你爷爷无常时,呱呱牛出现了。你二大无常时,呱呱牛出现了。你二娘无常时,呱呱牛同样出现了。呱呱牛总是那样,反三复四地出现,反三复四地折磨着你奶奶。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是不是逃脱了呱呱牛的折磨,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苦难的煎熬?
错。谁也逃脱不了那苦难。鲁格麻逃脱不了,嘎细儿逃脱不了,阿依舍逃脱不了,二不度逃脱不了,你也逃脱不了。所有的人都逃脱不了呱呱牛的折磨,逃脱不了苦难的煎熬。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告诉你,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无数次苦难,无数次苦难里爬着无数只呱呱牛,无数只呱呱牛会以无数种方式进入无数个人的脑袋,然后压得那个人喘不过气来,或是操控着那个人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那时候你还小,你根本不知道一只呱呱牛身上还背着无数个苦难,你只知道骑着你爷爷在炕上来回转悠。你爷爷无常的那一天,你才明白那呱呱牛是多么沉重,多么折磨人。这一点,你体会到了,其他人也体会到了。
你二娘崽来拜无常后,她娘家哥尤路思做主把她埋在了兰州南山上的一片坟地里。借口是天气太热,难以运送。这是什么借口呀?你二娘埋在你二大旁边,才是最理想的归属。算了,老家的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由他们去吧!他们肯定也被呱呱牛缠身了,才会做出那样不明智的决定。那天夜里,你二大的几个兄弟全都连夜赶到兰州,第二天撇师尼(晌礼)后送了你二娘的埋体。送埋的前一天晚上,你奶奶坐在炕上,馁弱极了,像一片落叶一样苍白,无力。她嘴里嘟嘟囔囔的,埋怨你二娘的女儿和儿子,怎么不做主把你二娘的埋体拉回张家川,葬在山台观你二大的旁边?埋怨顶啥用?你二娘的女儿和儿子,从你二娘无常的那一刻起就成了耶梯目(孤儿),他们哭都哭不急,怎么会想到那些事情?他们的脑袋里绝对也住着一只呱呱牛。绝对是那样。
三两年内,你二大素来麻被埋在了山台观,你二娘崽来拜被埋在了兰州,女儿撒曼在黑龙江安家落户,儿子必俩里蜗居在西安。好好的一家人,说散就散了。天各一方,谁能想得到?那以后,你奶奶越发显得沉默。她整天除了念经,礼拜,就是望着山台观发呆,或是长长地叹气。每逢主麻日(星期五),你奶奶还会请清真寺的满拉(念经的学生),给你爷爷和你二大上坟。可是,谁又能给你二娘上坟,在她的坟前念讨白呢?要是她埋在你二大旁边多好啊。你奶奶为此常常苦恼。她一苦恼,呱呱牛就会出现。她一苦恼,穿白大褂的医生就会出现。然后,你会看到一根细长的针头深深地扎入你奶奶的皮肤,缓缓地,向你奶奶的身体输送一些液体。再然后,你奶奶会沉沉睡去。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你害怕你奶奶一旦沉睡,再也不会醒来。
你时常想,你奶奶的脑袋里如果没有呱呱牛,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事实上,呱呱牛不仅仅住在你奶奶的脑袋里,它还住在每个人的脑袋里。它在脑袋里呈螺旋状不住地爬行着,旋转着,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人的脑神经里,转着转着就让人失去了原来的意识,转着转着就让人打碎了自己。看看吧,你姑姑阿依舍的脑袋里就住着一只呱呱牛,只不过它隐藏得比较深,让人不易发现而已。你之所以发现你姑姑阿依舍脑袋里的呱呱牛,是源于她的无意识状态。你奶奶告诉你,你二娘无常后的那些天,你姑姑整夜整夜顺着南河坝奔跑,没完没了地奔跑。不仅如此,她还经常看到人打嗝,没完没了地打嗝。你姑姑所有的行为证明,她的脑袋里住着一只呱呱牛。那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好多人脑袋里的呱呱牛都不容易让人发现。呱呱牛怎么会让人发现呢?它会背着沉重的躯壳,藏在你的血液里,你的骨头里,甚至你怦怦作响的心脏里。摸摸吧,摸摸你的脑袋,摸摸你那颗还在怦怦作响的心脏,那里面是否居住着一只呱呱牛?哦,闭上眼睛,用心感受,细细探查,你会发现你脑袋最深最深的地方蛰伏着一只呱呱牛。它趴在大脑细胞上,正在酣睡。它的两个腮帮子鼓鼓的,小小的肚皮随着嘴巴呼出的气息,一上一下,起起伏伏。它还有鼾声,它的鼾声随着你心脏的搏动,有一下没一下地响着。对了,它曾经苏醒过,以非正常途径控制过你的大脑,让你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人整天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人们说她有神经病。多么可怕呀。呱呱牛确确实实在你的脑袋里。
那个夏天,在一间白色的房子里,你奶奶整天抱着你,轻轻拍打你的身体,轻轻唱摇篮曲,直到把那呱呱牛拍得昏昏欲睡,唱得蛰伏了过去。这些都是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譬如鲁格麻的驼背,乃犹莎的肥胖,木海买的半臂,度闪的瘸腿,还有穆萨的落魄,主麻的潦倒,二不度的失意等等。大街上,随便走一个戴白帽子的人或者戴盖头和头巾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那只呱呱牛的身影。那些狡猾的呱呱牛,它们潜藏得很深很深,好多人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影子。就是看清了又如何?每个人最终逃脱不了身心的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旦被呱呱牛缠上,走上那条螺旋般的路,一切便又会变得不一样了。
呱呱牛就是漫长的苦难,漫长的煎熬。你不能以一种表象来衡量它躯壳里的是非功过,更不能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来衡量它内在的一些东西。在你生活的这个地方,人们把蜗牛叫呱呱牛,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你喜欢这个名字。苦难像一只呱呱牛,总是背着沉重的躯壳,那躯壳总是以螺旋状回旋着,不断给人造成视觉上的困惑,行动上的迟缓。一段很短很短的路,它走在上面,会将那条路走成很长很长的路。但无论如何,它存在着,它在走着。就像你奶奶念经,她会把一句很短很短的句子念成一句很长很长的句子,直到把那句子念完。两者是何其相似啊。因为苦难,所以迟缓。因为苦难,所以倍受煎熬。
有一天,当你遇见一只爬行的呱呱牛,请正视它的行走。说不上,那爬行的呱呱牛,那背着沉重躯壳的呱呱牛是你苦难的开始。朵斯达尼(朋友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正视了呱呱牛的行走,你就正视了你的苦难,你的煎熬。纵然那呱呱牛会在你的脑袋里爬出爬进,纵然它会掀起一些风浪,它也拿你毫无办法。这一点你必须要认清楚。
好了,不说这么多了。该来的会来,该去的会去。来来去去的路上,就让那呱呱牛给你带路吧。背上它沉重的躯壳,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回旋着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