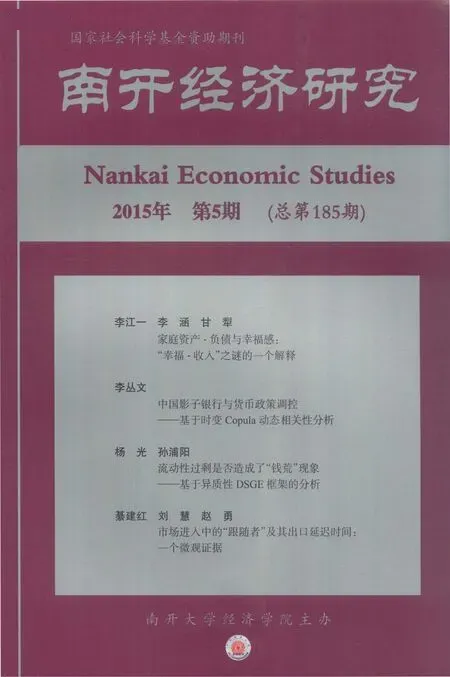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
李江一 李 涵 甘 犁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正因如此,各国都非常重视提高人民福祉。法国于2008 年开发了国民心理账户,开始关注民众的幸福感状况,并将其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和依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0 年正式宣布,展开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巴西2010 年通过19 号宪法修正案,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做得最为彻底的是不丹,该国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提出并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代替传统GDP,成为最早实施幸福工程的国度(鲁元平和王韬,2011)。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建国以来,历届政府无不把人民的幸福安康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
然而,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2013 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①资料来源于环球网的新闻报道,详见网址: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9/4343957.html。,在对156 个国家幸福指数的统计中,中国大陆仅位列第93 位,排名靠前的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同步提升,反而还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d Value Survey)2007 年数据,感到幸福的中国居民占比76.1%,,,,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显示,2011 年国民幸福比例为63.2%,,,,2013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56.7%,,,。著名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Eastcrlin 等(2012)对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最近20 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民众生活满意程度的相应提升。事实上,国民幸福感并未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在美国、英国、日本均出现过,这一现象最早由Easterlin(1974)发现,因此称为“Eastcrlin 悖论”,也称为“幸福-收入”之谜。
因此,探讨如何提高居民幸福感,特别是破解“幸福-收入”之谜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遗憾的是,家庭资产与负债作为影响家庭经济运行最重要的两大因素,鲜有研究将其纳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考察范围。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 年与2013 年的大型微观面板数据,将家庭资产、负债、收入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具体来讲,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以往研究遗漏资产、负债变量是否会对收入的估计造成偏差?第二,资产与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是否有显著影响?第三,各类资产或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第四,家庭资产和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如何?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无差别?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措施提高国民幸福感。
一、文献回顾
(一)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领域也横跨多个学科,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与经济学,随着效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呈指数增长(Kahneman 和Krueger,2006)。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在宏观层面,现有研究发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Di Tella et al.,2001)、收入不平等(Alesina et al.,2004;Oshio 和Kobayashi,2009;鲁元平和王韬,2011)、社会犯罪率(Alesina et al.,2004;Powdthavee,2005)、腐败(陈刚和李树,2013)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政府支出的增加,特别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显著提高国民幸福感(Wassmer et al.,2009;胡洪曙等,2012;蒋团标等,2013;谢舜,2012)。饱受困惑的是,国民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Easterlin,1974、1995),即“Eastcrlin 悖论”,也称为“幸福-收入”之谜。
近年来,得益于微观调查数据的日益丰富,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也是备受关注的是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考察。大部分与此相关的文献均证实,绝对收入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Diener et al.,1993;Ferrer-i-Carbonell,2005;Graham 和Pettinato,2002;Winkelmann 和Winkelmann,1998)。然而,微观层次的证据却与当前出现的“幸福-收入”之谜不一致,这就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寻找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新的微观证据。
相对收入论对“Eastcrlin 悖论”作出了很好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和他人比较,“攀比效应”使得自身幸福感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居民绝对收入不断提升的同时可能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样,绝对收入的上升可能不及社会平均收入上升得快。Clark和Oswald(1996)、Luttmer(2005)等文献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仅存在微弱的相关性,但与相对收入(他人收入平均水平)显著负相关,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绝对收入。然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收入”之谜的解释也受到挑战,这是由于相对收入也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当其他人收入上升时,居民会形成自身收入将上升的预期,幸福感反而会提高,Senik(2004)将此称为相对收入的“示范效应”。除了相对收入论外,“忽视变量(omitted variable)”理论也为“Eastcrlin 悖论”提供了一种解释。该理论认为,除了收入外,还有许多非收入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比如健康状况、生活态度、婚姻质量、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李后建,2014),忽视这些因素的影响,势必引致内生性问题,进而可能导致对收入的估计产生偏误。
当前,针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未取得一致结论。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在一个经济理论模型中同时考虑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主观幸福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其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当收入超过一定临界值后,非收入因素将起主要作用。在实证层面,Knight 等(2009)基于2002 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而绝对收入的影响要小得多。罗楚亮(2009)的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在控制相对收入的影响后仍较显著,但从影响大小来看,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影响远大于绝对收入。官皓(2011)利用200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采集的家庭数据分析了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他以问卷中直接询问的家庭收入在当地水平的高低作为相对收入的度量,发现在控制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利用CGSS2005 和CEIC2005的数据从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均两个维度对中国“Eastcrlin 悖论”进行了解释,研究结论认为保障中国社会机会均等程度,适当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以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可显著提高国民幸福感。陈钊等(2012)基于上海和深圳城镇社区入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社区平均收入和收入差距(与更高收入居民的比较)对居民本人的幸福感都有正向影响,可见,相对收入的“示范效应”在我国也显著存在。
除了收入外,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发现失业(Winkelmann 和Winkelmann,1998;罗楚亮,2006)、健康状况(Shields 和Wheatley Price,2005;Oswald 和Powdthavee,2008;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社会保障(李后建,2014)等因素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
不可否认,现有文献对国民幸福感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绝大部分文献集中于讨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与收入同等重要的家庭资产与负债在幸福经济学中的作用,少数研究从控制变量的角度关注了资产或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Knight et al.,2009;罗楚亮,2006;刘宏等,2013),本文将资产、负债、收入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拓宽了有关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视角。第二,对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讨论仍未获得一致结论,以往研究侧重从相对收入论的角度进行解释,从“忽视变量”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本文试图从“忽视变量”的角度解释“幸福-收入”之谜,并对仍存争议的相对收入论进行再检验。根据现有研究,忽视变量包括可测量但未被现有文献所采纳的变量,比如本文重点关注的资产、负债,可测量的忽视变量可直接加入计量模型予以克服。忽视变量还包括不可测量的变量,比如生活态度、婚姻质量、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李后建,2014),这些非物质因素通常与物质因素相关,忽视这些变量会对物质因素的分析造成偏误。举个例子,“吝啬鬼”可能更看重财富,而慷慨的人则不同,等量财富的增值更能提高“吝啬鬼”的幸福度,等量财富的减少会使“吝啬鬼”的幸福度下降得更多。我们认为,诸如性格一类的非物质因素通常是个体的内在特质,在短期内不随时间变化,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类问题。这样,通过对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估计结果便可证实不可测量的忽视变量是否影响幸福感。
(二)家庭资产、负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资产、负债如何影响幸福感的研究,我们通过总结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资产、负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揭示资产、负债影响幸福感的可能渠道。资产、负债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收入相似,资产、负债可从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层面影响幸福感。
从经济学的角度,资产、负债可通过影响微观经济行为来影响幸福感,比如消费。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是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认为理性消费者根据自己一生的财富来安排当前消费,其效用函数的基本形式是:U ( C ) = U ( α * Y + β* W)①经济学家通常用效用函数来度量幸福感,由此推导出的决定幸福感的方程称为幸福方程(happiness function),比如Clark 等(2008)。。其中,U(·)满足效用函数的通常假定,Y 是消费者一生的收入,W 是消费者一生的财富,W 等于资产减负债。由此可见,资产的消费品属性可通过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提高幸福感,同时,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还可产生财富效应②财富效应是指由于资产价格涨跌,导致持有人财富的增减,进而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的效应(Campbell 和Cocco,2007;李涛和陈斌开,2014)。而促进消费,进而提高幸福感,负债则会降低家庭总财富而挤出消费,从而降低幸福感。生命周期理论假设消费者可通过自由借贷平滑消费。在现实中,这一条件难以满足,消费者通常面临流动性约束,此时,资产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帮助消费者获得借款)而促进消费,进而提升幸福感(李涛等,2011)①李涛等(2011)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住房资产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而提高幸福感的机制,鉴于住房资产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引用该文的理论结论,具体推导过程不再赘述。。从心理学的角度,当自有财富增长速度低于他人财富增长速度时,“攀比效应”会降低幸福感,而“示范效应”则会提升幸福感。田国强与杨立岩(2006)将心理学的攀比理论引入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推导出了收入类商品(比如耐用品、汽车)和非收入类商品影响幸福感的更一般的方程,但他们的研究未考虑收入类商品的“示范效应”②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假设收入类商品的消费具有负的外部性,即他人收入类商品的消费将对本人的效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他人收入类商品消费的增长快于本人收入类商品消费的增长时,“攀比效应”会降低幸福感。事实上,若假设收入类商品的消费具有正的外部性,则可得出收入类商品具有正的“示范效应”,具体推导过程不再赘述。。
总结现有的理论研究,家庭资产可通过三种渠道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第一,家庭资产中的固定资产通常具有消费品的属性,比如房产、汽车、耐用品等,消费需求上的满足可提高效用,进而提高幸福感。第二,可抵押或具有投资品属性的资产可通过财富效应或缓解流动性约束而促进消费(Campbell 和Cocco,2007;李涛和陈斌开,2014),从而提升幸福感(李涛等,2011)。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攀比效应”会使相对资产规模较高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幸福感(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而“示范效应”会使自身幸福感随着他人资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李涛等(2011)、林江等(2012)、刘宏等(2013)均发现拥有住房或住房价值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Headey 和Wooden(2004)认为在影响居民幸福感方面,财富与收入同等重要。Knight 等(2009)基于中国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净财富每提高一个标准误,其幸福感指数将提高约0.07。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资产影响幸福感的差异,且资产的“攀比效应”与“示范效应”谁更占主导也是未解之谜。
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既有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首先,根据流动性约束论,当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时可通过借债平滑当前消费,从而提高当前经济生活的满足度,进而增加幸福感。黄兴海(2004)、韩立岩等(2012)的研究均发现短期负债促进消费的证据。其次,负债可通过影响心理和身体健康而降低幸福感。一方面,欠债较多的人因还款压力而可能影响心理健康(Brown et al.,2005);另一方面,沉重的还款压力还会挤出居民对“健康”的支出,比如欠款者会选择更便宜的药品或食用垃圾食品(Balmer et al.,2006),而健康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因此,负债对幸福感的短期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比如罗楚亮(2006)在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讨论中发现,负债与幸福感负相关,而刘宏等(2013)在分析住房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时却发现,住房负债与幸福感正相关。基于此,本文将对负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本文的创新在于:第一,本文以家庭资产与负债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这两项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填补了有关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空白,又丰富了家庭金融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将资产、负债引入幸福方程,从“忽视变量”论的角度解释了“幸福-收入”之谜,并对仍存争议的相对收入论进行了再检验;第三,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家庭异质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宗教信仰、生活态度、婚姻质量、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①我们假定这些因素在调查间隔的两年间均不会发生大幅变动。,从而可以得到更加一致可信的结论。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ina Household Finance and Survey,CHFS)2011 年与2013 年的两轮调查数据。CHFS 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现代抽样技术,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CAPI)记录问卷。2011 年,在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1 个区县,320 个村(居)委会收集了8,438 户家庭样本。2013 年,CHFS 对8,438 户家庭进行了追访,并将调查样本扩充至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8,143 户家庭,其中,追访成功的样本量为6846 个。调查信息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观态度、金融和非金融资产、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支出与收入、社会保障与保险等。其中,在主观态度问题中特别询问了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与身体健康状况。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追访成功的6846 户家庭样本进行分析。在实际分析中,因一些变量数据缺失,有效样本还会有所差异。
(二)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主观幸福感,我们以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代表其所在家庭的幸福感。CHFS 中的受访者是对家庭财务状况最了解的人,根据CHFS 的2013 年数据,家庭户主主要由受访者(70.13%)及受访者配偶(22.31%)构成,户主的幸福感可代表其所在家庭的整体幸福度,而受访者的幸福感与其配偶的幸福感高度相关,采用受访者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家庭的幸福感是合理的。对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来源于CHFS 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问题编号:A4011c),要求受访者在“非常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CHFS 对幸福感的度量采取的是有序离散变量,我们无法观测到家庭在做出主观幸福感判断时的效用临界值。严格来说,在计量回归分析中应采用有序离散选择模型(Wooldridge,2002),比如Ordered Probit 或Ordered Logit 模型,但是Ferrer-i-Carbonell和Frijters(2004)、罗楚亮(2006)的研究发现,在使用OLS 模型和使用Ordered Probit/Logit 模型所得到的回归结果中,系数或边际效应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因此,我们选择估计结果更易解释和估计程序更为简单的线性概率模型(LPM)。具体地,我们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哑变量,记为happiness,happiness=1 表示“非常幸福”或“幸福”,参照组为选择其它选项的家庭。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家庭资产与负债。其中,家庭资产包括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基金、债券、黄金、理财产品、借出款、保险账户余额①保险账户余额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与企业年金账户余额构成。、现金,非金融资产包括住房资产、工商业资产、土地、农业机械及农产品、汽车、耐用品②非金融资产的价值是受访者对自有资产的估值。耐用品不包括汽车(问题编号:C8001)。,我们将土地、农业机械、农产品统一归为农业资产。家庭负债包括住房负债、工商业负债、农业负债、汽车负债、教育负债与其它负债(主要由结婚、生病产生)。
除了家庭资产、负债外,我们在回归分析中还采纳了已有研究证实的有效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庭年总收入、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受访者社会保障状况、家庭总人数、失业人数与总人数比率、0~16 岁(含16 岁)少年占比、60 岁(含60 岁)以上老年人数比例和已婚成员比例。其中,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为哑变量③CHFS 询问了受访者及其配偶的身体健康状况,问题为“与同龄人相比,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选项包括:非常好、很好、好、一般、不好(问题编号:A2025b)。,若受访者身体健康为“好”、“很好”、“非常好”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受访者社会保障情况也为哑变量④CHFS 对社会保障状况的询问为“请问您退休/离休后领取的是下列哪种退休/离休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有11 个备选项(问题编号:F1001)。,若受访者退休后有离/退休金或社会养老保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将资产、负债、收入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以2010 年为基期),为减小极端值的干扰,我们对资产、负债、收入均作对数化处理,因存在取值为0 的情况,采取的方法是先加1 再取对数。
表1 描述了家庭资产、负债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对于资产升值(CPI 调整后的2013 年资产高于2011 年)的家庭,从不幸福转变为幸福的比例为15.6%,比资产贬值的家庭高0.9 个百分点。同时,资产升值的家庭中,从幸福转变为不幸福的比例为17.9%,比资产贬值的家庭低约4.4 个百分点。可见,人们对于资产损失更厌恶,这与行为经济学理论相一致。
从负债的角度,对于负债增加(CPI 调整后的2013 年负债高于2011 年)的家庭,从不幸福转变为幸福的比例为15.7%,与负债减少的家庭相当。但是,对于负债增加的家庭,25.4%的比例从幸福变为不幸福,比负债减少的家庭高出7.3 个百分点。可见,人们对突然增加的负债会感到更不幸福,但负债的减少对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有限。

表1 资产、负债与家庭幸福感变化
表2 报告了各变量在2011 年与2013 年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平衡面板样本中,感到幸福的比例从2011年的64%下降到60%。家庭资产规模有所上升,各资产类别中,又以房产、汽车、耐用品资产上升的幅度较大。家庭负债规模明显降低,负债对数值从2011 年的4.16 下降到2013 年的3.33,各子负债类别中,以住房负债的下降幅度最大,除其它负债(主要是结婚、医疗借贷)外,其余负债都有小幅降低。家庭收入、受访者社保状况均明显改善,家庭平均失业比例也从2011 年的0.04 下降到0.03。另外,家庭总人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体现出分家而导致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特点。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分析
(一)绝对资产、负债规模与主观幸福感
我们首先分析资产、负债的绝对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计量模型如下:

β1、β2是我们感兴趣的参数,表示资产与负债对幸福感的边际影响。i 是个体维度,t 是时间维度。Xit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家庭年总收入、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受访者社会保障状况、家庭总人数、失业人数与总人数比率、0~16 岁(含16 岁)少年占比、60 岁(含60 岁)以上老年人数比例和已婚成员比例。此外,我们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year2013(基期为2011 年)、个体固定效应ci。uit是误差项。
表3 汇报了式(1)的估计结果。为与以往的此类研究相比较,模型(1)、(2)未控制资产、负债,同时,为考察非观测异质性造成的估计偏误,模型(1)是未考虑非观测异质性的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估计,模型(2)是消除个体非观测异质性的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估计。可以发现,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收入均显著影响幸福感,但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收入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低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由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此可见,确实存在与收入相关的非收入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忽视这些因素可能高估收入对幸福的边际影响。
表3 模型(3)、(4)加入了本文关注的变量:资产与负债。同样地,我们考察了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差异。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模型(3))显示,资产、负债、收入均显著影响幸福感,但与模型(1)相比,收入的边际影响从0.022 下降为0.013,即遗漏资产、负债变量可能导致对收入的估计产生偏误。模型(4)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其它因素不变,家庭资产规模每提高1 倍,幸福的概率将增加0.018,家庭负债规模每增加1 倍,幸福的概率将下降0.005,二者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有意思的是,对比模型(2)与模型(4)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可发现,一旦控制家庭资产和负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对比模型(3)与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发现,即使同时控制资产、负债,若不排除个体非观测异质性的影响,收入仍将显著影响幸福感。对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的Hausman 检验t 值为61.7,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个体非观测异质性外生的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这就从“忽视变量”论的角度验证了“幸福-收入”之谜,即幸福并不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而随着家庭资产规模的增加或负债规模的减少而增加,忽视与收入高度相关的资产、负债变量及不可观测的非收入因素是导致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重要原因。既然资产与负债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那么不同类型的资产或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有何不同?表3 模型(5)将家庭资产划分成住房、汽车、耐用品、工商业、农业、金融资产六大类,分别考察了各类资产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仅仅只有房产、汽车、耐用品资产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比较诧异的是,工商业、农业、金融资产并不显著影响幸福感,可能的解释是:工商业资产的风险系数较高,这抵消了资产升值带来的幸福感;农业资产收益率低,无法产生提高幸福感的效应;金融资产中的无风险资产(比如存款、债券)具有可预期的收益,根据持久收入假说,预期内的收入并不影响个体经济行为,而风险资产以股票为主,近年来,股市的不景气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投资热情,股票资产自然也无法起到提升幸福感的作用。
表3 模型(6)考察了不同类型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①由于2011年调查问卷中并没单独询问农业生产借贷情况,所以我们无法考察农业生产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工商业、住房负债及其它负债(主要是婚姻、医疗借贷)对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汽车、教育负债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偿还汽车、教育负债的压力较小的缘故。表3 模型(7)对资产与负债各分类子项均进行了控制。可以看出,各资产、负债的估计结果大小与显著性均与模型(5)、(6)中相对应变量的估计结果相同。同时,控制变量在模型(1)~模型(7)中均较稳健,且与以往文献的发现基本一致。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表3 绝对资产、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

续表3
综上,资产与负债是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忽视这两大因素是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重要原因,尽管收入的增加是家庭财富累积的基础,但收入增加本身并不能增加居民幸福感,收入可能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来影响幸福感。从不同资产、负债的影响来看,房产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提升效应,但住房负债将会部分抵消房产增值带来的幸福感,政府应确保住房市场平稳发展,因为一旦房价大幅下跌,房产减值与还款压力将会对家庭幸福形成双重打击。工商业资产不仅不具有提升幸福感的作用,相反,由于经营工商业产生的负债还会显著降低幸福感。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汽车、耐用品资产可显著提高幸福感。因此,政府应长期保持拉动内需的激励措施。
(二)相对资产、负债规模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第二部分的文献总结中已阐述,在影响居民幸福感方面,资产、负债与收入具有相似性,已有研究发现,个体通常会将自身收入与他人比较,由此可能产生相对收入的“攀比效应”或“示范效应”。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相对资产、负债是否有如相对收入影响幸福感的“攀比效应”或“示范效应”?本部分将对此进行研究。与Senik(2004)、陈钊等(2012)衡量相对收入的方法相似,我们以社区/村层面平均资产、负债规模为基础来界定参照组。若以yct表示社区/村c 在第t 年的平均资产(负债、收入),那么,家庭i 在第t 年的相对资产(负债、收入)定义为该家庭的实际资产(负债、收入)yit与调查时所在社区/村平均资产(负债、收入)yct的对数差,即lnyit-lnyct,记为lnrela_yit,本文使用的相对指标有三个:相对收入,记为lnrela_inc;相对资产,记为lnrela_asset;相对负债,记为lnrela_debt。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考察相对资产(负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β3是我们感兴趣的参数,表示相对资产(负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其余解释变量均与式(1)相同。表4 报告了式(2)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首先,为与以往研究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对比,表4 模型(1)仅考察了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其它因素不变(包括绝对收入不变),相对收入每提高1 倍,幸福的概率将增加0.065,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时,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与官皓(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相对收入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原因,绝对收入并不影响幸福感,再次为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相对收入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发现与陈钊等(2012)的研究结论相反,我们没有发现相对收入具有“示范效应”的经验证据。其次,我们考察相对资产对幸福感的影响,表4 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其它因素不变,相对资产每提高1 倍,幸福的概率将下降0.049,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于我们同时控制了绝对资产规模,因此,模型(2)中相对资产变量系数的含义等同于,在家庭绝对资产规模不变的情形下,家庭所在社区/村的平均资产每提高1 倍,幸福的概率将增加0.049,即社区平均资产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正的外部性,这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完全相反。以往有研究发现社区平均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幸福感(Clark et al.,2009b;Kingdon 和Knight,2007;陈钊等,2012),与这些研究的发现不同,我们发现,相对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仍是“攀比效应”占主导,但存在相对资产的“示范效应”。究其原因,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第一,相比于收入的隐晦性,资产更易产生激励效应,比如,社区的创业者可能会分享创业经验,从而提高个体参与创业的信心;第二,社区资产价值的提高会使居民形成自身资产将上升的预期,比如,邻近小区房价的上升会使个体认为自有房产价值也将上升,但相对收入在这一影响机制上较弱:他人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自身收入也将随之增加。第三,我们考察相对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表4 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相对负债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家庭负债相对于资产和收入而言更加隐蔽,从而使得负债并不具备可比较的参照组。
表4 模型(4)是对相对资产、相对负债、相对收入都控制后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模型(1)、(2)、(3)相比,相对收入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对资产变量的估计变得更加显著,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对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其余各变量估计值的大小与显著性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估计结果较稳健。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1)~模型(4)中,即使我们控制相对效应的影响,绝对资产仍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这表明,资产除了从心理层面来影响幸福感外,还可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来提高幸福感,比如使用资产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用。

表4 相对资产、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资产、收入都是家庭的财富,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资产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与收入完全不同,相对资产对幸福感具有正的外部性,但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负的外部性。从这个角度讲,政府提高幸福感可从降低收入不均和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着手。研究还发现,相对收入形成的“攀比效应”是中国“幸福-收入”之谜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解释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相对收入论与“忽视变量”论均显著存在。
(三)负债影响幸福感的机制:负债影响健康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负债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但并不具有类似资产或收入通过相对效应影响幸福感的传导机制。那么,负债是如何影响幸福感的呢?基于已有的研究,负债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负向影响幸福感:一是偿债压力会影响心理健康(Brown et al.,2005),进而影响幸福感;二是偿债压力使得借款人不得不努力工作,甚至是通过生活的节俭以达到快速偿还借款的目的,由此可能导致借款人身体抵抗力恶化,得病概率上升(Balmer et al.,2006),进而影响幸福感。由于健康影响幸福已是学者们公认的结论(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所以本部分通过分析负债是否影响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而间接提供负债影响幸福感的证据①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分析负债是否影响居民心理健康。。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health_indicator 表示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们用两个变量来衡量:一是受访者及配偶中健康成员人数②CHFS 问卷仅询问了受访者及配偶的健康状况:“与同龄人相比,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选项包括:非常好、很好、好、一般、不好,问题编号:a2025b。我们将选择非常好、很好、好的家庭成员视为健康。,记为health_num;二是家庭月均医疗支出对数,包括医疗保险账户支付部分,记为lnhhmed。β1是我们感兴趣的参数,表示负债对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考虑到家庭可能因生病而举债,从而使得负债与身体健康状况互为因果关系,进而引致内生性问题。因此,与前文的分析有所不同,我们去除了家庭负债中的医疗负债。医疗负债包含于其它负债(othdebt)中,所以我们去除了负债中的其它负债③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控制变量中,有研究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对健康及医疗支出有重要影响(黄枫和甘犁,2010)。因此,控制变量X 除了包含前文分析中采纳的变量,我们还对家庭是否有医疗保障进行了控制,记为health_ins,health_ins=1 表示至少有一家庭成员拥有医疗保障,参照组为所有家庭成员均无医疗保障的家庭。此外,由于健康状况是决定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以家庭月均医疗支出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及配偶中的健康成员人数。
表5 报告了式(4)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其它因素不变,家庭债务每提高1 倍,受访者及配偶中健康成员数目将减少0.009 个,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简单的估算,我们可计算出负债通过损害家庭成员健康而影响幸福的概率:家庭负债规模每提高1 倍,将使家庭幸福的概率下降约0.09%(0.009*0.100(前文中健康影响幸福的估计值))。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不同类型负债对健康的影响不同,住房负债、教育负债显著降低了受访者及配偶中的健康人数,而工商业负债虽然对家庭成员健康具有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有意思的是,因购买交通工具而产生的负债与受访者及配偶的健康状况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购买交通工具提高了医疗可及性的缘故。模型(3)与模型(4)从医疗支出的角度考察了负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受访者及配偶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条件下,负债总额及各子项目负债均显著提高了家庭月均医疗支出。由此可见,负债通过影响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是负债影响幸福感的渠道之一。

表5 负债与健康
四、政策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它因素不变,社区平均资产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的“示范效应”,社区平均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则具有负的“攀比效应”,而负债则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成员身体健康而负向影响幸福感。那么,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促进资产的“示范效应”或降低收入的“攀比效应”或减弱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冲击?本部分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一)如何促进资产的“示范效应”或降低收入的“攀比效应”?
对于如何促进资产的“示范效应”或降低收入的“攀比效应”,我们主要从教育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教育既可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也能使人变得理性,从而可提高资产的“示范效应”或降低收入的“攀比效应”。我们进一步区分了有无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的差异,因为,接受过经济、金融教育的人可能更具经济头脑,从而“示范效应”更易发挥作用,同时,这类人通常也更理性,与人攀比的心理可能更弱。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lnrela_y 表示相对资产或相对收入。f_characters 表示家庭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我们考察两个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我们用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记为head_edu,该变量根据受访者报告的户主学历换算而来,如“大学本科”记为22 年;二是是否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该变量为哑变量,记为eco_class,eco_class=1 表示受访者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参照组为没有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的家庭。β2是我们感兴趣的参数,表示异质性家庭的资产“示范效应”与收入“攀比效应”的差异。
表6 报告了式(4)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考察了异质性家庭的资产“示范效应”,模型(3)~模型(4)考察了异质性家庭的收入“攀比效应”。对于资产的“示范效应”,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家庭,相对资产的“示范效应”越强,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地,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可显著提升社区平均资产的“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尽管受教育程度对于居民学习他人资产增长模式帮助不大,但经济、金融类知识可显著提高居民学习他人资产增长模式的能力。从收入的“攀比效应”来看,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收入的“攀比效应”越弱。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可显著降低家庭与人攀比收入的倾向,相对收入每提高1倍(社区平均收入下降1 倍),可使没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的家庭变得幸福的概率提升0.085,但会使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的家庭变得幸福的概率下降0.01,二者差异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受教程度的提高不仅可减弱家庭与人攀比收入的倾向,若同时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他人收入的提高还可能对自身幸福感产生正向激励。
(二)如何减弱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冲击?
对于如何减弱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冲击,我们主要从医疗保障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中发现,负债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成员身体健康而负向影响幸福感。因此,若医疗保障能为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提供保险,那么,医疗保障可减弱负债对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冲击,从而降低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我们在基本模型(式(1))中加入负债与是否有家庭成员拥有医疗保障(health_ins)哑变量的交叉项来验证上述猜想,我们进一步区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差异,其中,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包括公费医疗、单位报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主要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我们以city_healthins 表示是否有家庭成员拥有城镇医疗保障,以rural_healthins 表示是否有家庭成员拥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表6 模型(5)、(6)、(7)报告了在基本模型中加入负债与是否拥有医疗保障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拥有医疗保障并不能显著降低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特别地,拥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反而加剧了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尽管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身体健康状况更差的家庭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倾向更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因筹资水平较低导致了保障水平较低,很难起到保障居民身体健康的作用。然而,拥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可显著降低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这与刘晓婷(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仅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显著改善了居民健康状况,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未有效改善居民身体健康。

表6 政策分析
综上,通过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加强经济、金融类知识的教育,可显著提高个体学习他人资产增长模式的能力,同时降低与他人攀比收入的倾向,这将对提高居民幸福感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同时,政府应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为负债对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负向冲击提供保险,进而提升家庭幸福感。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 年与2013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家庭资产、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其它因素不变,家庭资产每提高1 倍,家庭从不幸福变得幸福的概率将增加0.018;家庭负债每增加1 倍,家庭变得幸福的概率将减少0.005。同时,不同资产与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家庭资产中,以房产、汽车、耐用品资产的正向影响为主,而工商业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影响不显著;在家庭负债中,以住房负债、工商业负债的负向影响为主,而汽车、教育负债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对资产、负债影响幸福感的渠道进行分析后发现,相对资产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正的“示范效应”:社区平均资产每提高1 倍,家庭幸福的概率将增加0.049,这一影响有别于相对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负的“攀比效应”:社区平均收入每提高1 倍,家庭幸福的概率将减少0.065。然而,负债不具有上述两种影响机制,负债更有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成员身体健康而影响幸福感。研究还发现,通过提高居民教育水平,特别是加强经济、金融类知识的培训,既可提高个体学习他人资产增长模式的能力,还能降低与他人攀比收入的倾向,这可对提高居民幸福感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是,针对负债通过影响家庭成员身体健康而负向影响幸福感的问题,当前医疗保障制度仅城镇居民医疗保障能够显著降低负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未能有效发挥其保险功能。
本文的研究同时对幸福不一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的“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解释。我们发现,一旦控制资产、负债及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非观测异质性(比如生活态度、婚姻质量、人际关系等),绝对收入不再显著影响幸福感,但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依然稳健显著,这就验证了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从攀比理论与忽视变量理论角度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经济理论模型。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不可否认,房产的升值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然而经历高速增长后的房地产市场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政府应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一旦房价大幅下跌,房产减值与偿债压力将对居民幸福感形成双重打击。其次,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工商业资产不仅不具有提升幸福感的作用,相反,由于经营工商业产生的负债还会显著降低幸福感。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再次,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加强经济、金融类知识的培训,以降低攀比心理造成的幸福损失,并提高居民学习他人资产增长模式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国民幸福度。最后,针对负债对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冲击,政府应在实现医疗保障全民覆盖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为负债通过降低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而负向影响幸福感提供保险。
[1] 陈 刚,李 树. 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13(4):37-58.
[2] 陈 钊,徐 彤,刘晓峰. 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12(4):79-101.
[3] 官 皓.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 南开经济研究,2011(5):56-70.
[4] 韩立岩,杜春越. 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J]. 经济研究,2011(1):30-42.
[5] 何立新,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 “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11-22.
[6] 胡洪曙,鲁元平.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2012(10):23-33.
[7] 胡洪曙,鲁元平. 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13(11):41-56.
[8] 黄 枫,甘 犁. 过度需求还是有效需求?——城镇老人健康与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10(6):105-119.
[9] 黄兴海. 我国银行卡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05(11):72-82.
[10] 蒋团标,朱玉鑫. 省际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影响的差异化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3):39-50.
[11] 李后建.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J]. 社会,2014(2):140-165.
[12] 李 涛,陈斌开. 家庭固定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4(3):62-75.
[13] 李 涛,史宇鹏,陈斌开.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J]. 经济研究,2011(9):69-82.
[14] 林 江,周少君,魏万青. 城市房价、住房产权与主观幸福感[J]. 财贸经济,2012(5):114-120.
[15] 刘 宏,明瀚翔,赵 阳. 财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3(4):95-110.
[16] 刘晓婷. 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 社会,2014(2):193-214.
[17] 鲁元平,王 韬.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1(4):1437-1458.
[18] 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 经济学(季刊),2006(3):817-840.
[19]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20] 田国强,杨立岩. 对“幸福—收入之谜” 的一个解答[J]. 经济研究,2006(11):4-15.
[21] 谢 舜,魏万青,周少君.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J]. 社会,2012(6):86-107.
[22] Alesina A.,Di Tella R.,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9):2009-42.
[23] Balmer N.,Pleasence P.,Buck A.,Walker H. C. Worried Sick:The Experience of Debt Proble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ealth,Illness and Disability [J].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2006,5(01):39-51.
[24] Brown S.,Taylor K.,and Wheatley Price S. Debt and Distress:Evalua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Credit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5,26(5):642-63.
[25] Campbell J. Y.,Cocco J. F. How Do House Prices Affect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7,54(3):591-621.
[26] Clark A. E.,Frijters P.,Shields M. A. Relative Income,Happiness,and Utility: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8,46(1):95-144.
[27] Clark A. E.,Oswald A. 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6,61(3):359-81.
[28] Clark A. E.,Westergård-Nielsen N.,Kristensen N. Economic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Rank in Small Neighbourhood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9,7(2-3):519-27.
[29] Di Tella R.,MacCulloch R. J.,Oswald A. J.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335-41.
[30] Diener E.,Sandvik E.,Seidlitz L.,Diener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lative or Absolut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3,28(3):195-223.
[31]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1974,89:89-125.
[32]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5,27(1):35-47.
[33] Easterlin R. A.,Morgan R.,Switek M.,Wang F.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25):9775-80.
[34] Ferrer-i-Carbonell A. 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997-1019.
[35] Ferrer-i-Carbonell A.,Frijters P.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4,114(497):641-59.
[36] Graham C.,Pettinato S. Frustrated Achievers:Winners,Lose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New Market Econom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2,38(4):100-40.
[37] Headey B.,Wooden M. The Effects of Wealth and Incom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J]. Economic Record,2004,80(s1):S24-S33.
[38] Kahneman D.,Krueger A. B.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1):3-24.
[39] Kingdon G. G.,Knight J. Community,Comparis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 Divided Socie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7,64(1):69-90.
[40] Knight J.,Song L.,Gunatilaka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4):635-49.
[41] Luttmer E. F. P. 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J]. Qua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963-1002.
[42] Oshio T.,Kobayashi M. Area-leve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 Happiness:Evidence from Japan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1,12(4):633-49.
[43] Oswald A J.,Powdthavee N. Does Happiness Adap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abil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sts and Judg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8,92(5):1061-77.
[44] Powdthavee N. Unhappiness and Crime: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J]. Economica,2005,72(287):531-47.
[45] Senik C. When Information Dominates Comparison:Learning from Russian Subjective Panel Dat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9):2099-123.
[46] Shields M.,Price S. W. Explo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England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2005,168(3):513-37.
[47] Wassmer R. W.,Lascher Jr. E. L.,Kroll S. 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Ideology Matter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10(5):563-82.
[48] Winkelmann L.,Winkelmann R. 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Economica,1998,65(257):1-15.
[49]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 The MIT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