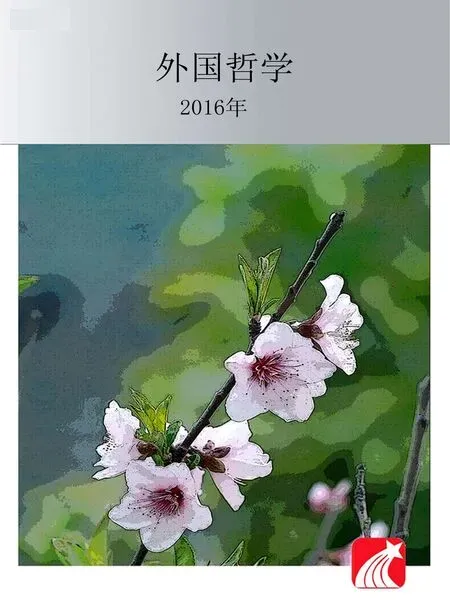回顾式必然性
——一种涉及进化逻辑的新模态观念
郑宇健
回顾式必然性
——一种涉及进化逻辑的新模态观念
郑宇健*
本文旨在引入一个我称之为“回顾式必然性”的观念。作为背景动机,我先举例讨论两类人为游戏,并由此转入人为游戏与自然游戏(即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历时彩票)之间的一种重要类比。而对此观念之特殊模态地位的合法性证明,则主要依赖于揭示它与一系列克里普克式后验必然性的标准表述之间的差异和类同。
回顾式必然性 后验必然性 历时彩票 不间断的选择链条 固定标示词
一、一种与游戏的常规结果相关的事后(视角)必然性
五子棋是很多国人熟悉的棋类游戏,用黑白两色棋子在围棋盘上进行。它学起来简单,要想精通其技却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一切对弈所含的开放性或不确定性的本质,植根于对手的下一步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预料的,这一点五子棋也不例外。本文无意在游戏的难易程度上作区分,之所以选五子棋作为例子,就是因为其游戏规则简单不过:除了棋手交替落子外,唯一确定胜负的标准就是谁先让己方颜色的五个棋子连成不间断的一条直线。
五子棋的常规结局自然是,在双方棋子覆盖整个棋盘之前,一方因其五个棋子连成一线而赢。与这种赢局相对应的似乎是一种伴随着赢家地位的概念必然性:赢家一方的棋子图案必定包含着一排五个连续的棋子。这一必然性之所以属于概念性范畴,是因为给定该游戏规则(或设计),上一命题之真是由该命题主词“赢家”的语义内容所保证的。进一步,我们不妨说,这一种必然性是规范性的,即如果我们不如此这般地规定并遵守这游戏规则,上述结局图案并不(一定)是原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本文之旨趣并不在讨论这平凡意义上的规范必然性,而在探讨如下这个易为人忽略的基本事实及其蕴义:任何胜负结局的背后都有一个历史链条(所谓对弈后的“复盘”就是回溯这个链条),这链条是由双方棋手每一次落子的实际顺序所构成。这链条的各个环节在双重意义上是偶然的,其一是谁都没有一个先定的通向那实际结局的路线图,其二是(除了开局第一步外)每一步落子均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对手所走的前一步──在对手有选择的范围内,这前一步是无法预测的。简言之,所谓历史链条无非是一系列偶然选择的轨迹或记录。这一基本事实值得发掘的蕴义恰在于历史选择的偶然性与游戏结局的必然性之间的相容与依赖关系。
继续以五子棋为例。无论谁是赢家,且无论其实际运作多么充满惊讶或意外,棋手(也包括旁观者)最终除了必然看到游戏规定的连成一线的同色五子之外,还必定在回顾时“看”到达致这特定结局的一条成功的历史路径,即一条因果环节上虽充满偶然、但却环环相扣从未中断的链条,而那构成着“胜利联机”的五子必定对应着该链条中(未必连续)的五个环节。
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我称之为“回顾必然性”的模态,其概念内容既未被我们上面提到的规范性的概念必然性所穷尽,也未被后者所明确地表达。让我稍作一点说明性的展开。
上述直接的概念必然性所欠缺的东西是与我们熟悉的偶然成功这一观念相关联的。任何游戏在结构上所要求的动态活动都意味着玩游戏时不可消除的偶然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令实际赢家一般只能在“事后”(即结局出现或已明朗化时)才被识别。与此“事后赢家识别”相对应的是,只有等到游戏结束才能确认实际走过的路径算是成功路径(相对涌现的赢家而言)还是失败路径(相对输家而言)。换言之,一旦结局出现,赢家此前的所有步骤所形成的链条就获得了成功链条这一身份或地位。盘面上可见的五子连通性象征着这底层历史中不间断的成功步骤之链。不管这连通的五子坐落于棋盘何处或嵌于双色棋子图案的哪一部位,那成功链条的事后回顾必然性无一例外地达成。
我想揭示的这种特殊必然性一方面区别于因果(规律)必然性,另一方面与事后眼光下的历史轨迹有着内在联系。事后眼光并不涉及任何关于游戏设计的新信息,而只涉及玩家作为赢家或输家的事实地位──不妨看作是一种后验地发现的地位。在我们转入对这种必然性之特点的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下关于玩家及其在游戏中所面临风险的一个较隐蔽的问题。
二、关于历时彩票的事后必然性案例
围棋盘上的棋子,不同于五子棋玩家或任何绿茵场上的足球员,充其量不过是这些玩家的替代品。一个游戏的人格参与者对其局部步骤或整体策略的实效会有认知性和情绪性反应,但其人造替代品却不会有。让我们考察一个简单的包含先定随机概率的真人游戏。
设想有一个多环节的筛选真人参与者的历时中彩游戏。每一环节都是一个小型彩票式关卡,即以某种事先设定的概率来淘汰一批已成功经历了之前所有环节的幸存者。通过每一关卡是获准进入下一关卡的必要条件,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剩下最后一位参与者即成为整个中彩游戏的赢家。假定游戏的设计保证永远有且只有一位赢家。
现在,从赢家的视角看,此前通过的每一环节都必然是成功的,而且其间的链接从未间断,尽管这连环中彩的动态过程于每一步皆充满随机性。这里所用“必然”这个词捕捉了我要讲的回顾式必然性的中心含义,即它是一种既相容于又依赖于正向偶然过程的逆向必然性。而且,只要给定彩票游戏设计,它就是一种实在的、非错觉的事后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性。
不妨用标准的可能世界术语来表述此中心含义:在任何可能世界W中,无论谁是此类彩票的赢家,他都将在回顾时发现一种同样的属性—一条“在W中是现实的”链条的不间断性,此链条存在于他相应的因果史背景中,一直通向处于彩票游戏终点的他自身的存在。他除了赢家地位外唯一的相关身份就是一个有着知性后见之明的幸存者/中彩者,可能世界语义学对于他的适用性证明了他在回顾中的认知对象的模态地位(即属于一种必然性)。
这种回顾式必然性的最有意义、最值得探索之处就是那内在于彩票游戏的参与者视角。设想某参与者正处于游戏当中的某一关卡前,从他的当下视角着眼,已历的和将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到此刻为止的暂时安全性或幸存性(对应着一条尚未间断的被选择链条),都是可认知的事实。而且,与这未间断链条相联的回顾式必然性之实现,依赖着该参与者已然经历的现实因果过程。但是,需要特别解释的东西正是从这种因果偶然性到回顾式必然性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可能的。这一解释上的需要不管对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中彩游戏来说都是同样存在的。
我们现实世界的自然进化过程可与上面描绘的人为历时彩票作一类比:假如我们将理性意向性视为自然进化游戏的终极奖品的话,那么人类这个物种就是这场包含着近乎无数环节的自然选择彩票的赢家。这些环环相接的源于基因突变的适应性变化构成着一条漫长但却从未间断的选择链条,链条的这一端就是上述标志着理性地位的终极大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超级历时自然彩票游戏的直接参与者或玩家们,严格地说并不是我们在日常宏观层面较熟悉的生物个体,而是在可遗传的随机性发生的层面上得以个别化的基因型。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自然选择机制才真有资格被叫作历时彩票。问题是,这一层面上并没有意向性,具有意向性的动物个体充其量不过是携带和保存这些基因型的相对稳定的同一性的载体,尽管自然选择必须通过生物个体行为层面的(环境)适应性发挥先导作用。①关于进化的基因视角的代表性观点,可参见R. Dawkins, The Sel fi 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而关于自然选择机制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的较全面讨论,可参见S. Okasha,Evolution and the Levels of Sel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即使我们忽略个体与基因型在作为彩票参与候选者资格上的层面差异,在自然进化尺度的大部分时段中,绝大多数有机个体也都谈不上是具备理性意向性的──因此也就无所谓从事像回顾历史这样的知性活动。
但是,就我引入回顾式必然性观念这一有限目标而言,上述局限并无大碍。假如我要进一步将此观念应用于某种关于理性意向性如何追溯其进化先驱的完备理论的话,上述局限就应设法克服。但现在我只需要一种较弱意义上的“回顾”,它并不要求所讨论的历时游戏的参与者具备意向性;具体点说,它并不要求它们能够对其历史先驱(如祖先类型)或“昨日的自我”作任何有意识的认知。②如果我们采用丹尼特(Dennett)在讨论所谓有机体的逆向工程时引入的“意向性姿态”的话,将那些非意向的自然游戏参与者(比如基因)视作好像具有前瞻及后顾的意向性,往往被证明在方法论上是很有用的。参见D. C. Dennett, The Intentionai St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相应地,一种更强或标准意义上的“回顾”则会有如上要求。
我们不妨考察一个特定的物种专有属性,比如说长颈鹿的长颈,以它作为事后识别的特征。所有现存的(正常)长颈鹿必定共享着一种上游因果史,即由自然选择形成的不间断的进化链条③假设其长颈属性对长颈鹿或其祖先的适应性具有相关的贡献,且因此其基因型才得以保存至今。,尽管它们作为个体无法认知这一历史事实或为之感到幸运。这一共享的由连续适应性变化构成的上游路径可以客观地归于作为一个物种的现存长颈鹿。这就是我所说的弱意义上的回顾式必然性。另一方面,自然主义框架内的科学假设是,人类认知官能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物种专有属性,而且它有能力在一种更强的即自觉的意义上体现回顾式必然性。这种包含主观性的强意义不仅不与弱意义相矛盾,而且恰在进化逻辑上依赖于客观的弱意义。
虽然我不准备在此论证如下题旨,但不妨指出它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的命题:自然选择游戏是一种从弱意义上的回顾式必然性之客观归属性向着其强意义上的主观(反身)归属性转化的历史进程。与之相关的另一命题是:在抵达这后一阶段之前,回顾式必然性的逻辑地位尚无法完全确立,或者说尚不能展现其区别于其他模态(如因果必然性或知识论必然性①关于其他学者对这些必然性种类的讨论的概要性介绍,参见B. Kment ,“Varieties of Modality”,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by E. N. Zalta. URL=http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 2012/entries/modality-varieties/, 2012。)的最鲜明特征。在余下的篇幅中,我将论证,上述弱意义上的回顾式必然性已然足够独特和重要,以致任何关心必然性来源问题的理论家都不应忽视它。
三、后验必然性之域:分殊与关联
先来比较一下这两个陈述句:
(1)晨星就是暮星。
(2)晨星有可能不是暮星。
句子(2)是明显的模态陈述,它仅在如下条件为真:句中二专有名词“晨星”和“暮星”的语义是由某种知性或描述主义的解读来确定的②参见 S. Schwartz,“Kinds, General Terms,and Rigidity: A Reply to Laport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9,2002, p.270。,而且该解读之所指在某(些)可能世界中存在。比如,在可能世界Wi中“晨星”所指称者是由描述语“早晨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确定的,在我们现实世界Wo中该描述所挑出的是金星。
与此相较,句子(1)并不直接包含任何模态词,而且显然不是一个分析或先验的真理,这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经验方式来确定句中二专名之所指及句子之真值。但是根据克里普克(1980)影响巨大的著作,句子(1)作为一个同一性陈述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晨星”、“暮星”皆为固定标示词。一个固定标示词在一切(其所指存在的)可能世界中唯一地确定同一个物体,所以任何关于两个固定标示词的同一性陈述在一切可能世界中要么全真,要么全假,只要它在其中任何一个世界中为真或为假。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对于这种名词标示功能的固定性之巨大热情背后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它可对所谓后验必然性予以背书。
然而,关于(1)类句子的一个疑问是,其所禀具的后验必然性是否捕捉了一个理论意义上很独特的观念?比如说,相对于因果必然性或因果史意义上的决定论观念,它有何独特性?虽然克里普克在讨论固定标示词之原初所指与该词的当下使用之间的关系时,用到了语义传递的因果史链条这个概念,但句子(1)所例示的这种必然性之终极来源,无非是任何物体或实体平凡地、永远地具备的自身同一性。这一事实不会因为有限理性者在发现这些同一性的实证过程中所遭遇的经验困难程度而受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克里普克式的后验必然性(至少就其各种同一性陈述而言)并非直接关涉因果史本身,亦即其模态方面并非植根于历史。
再考虑另一个陈述:
(3)西塞罗是那个由精子s和卵子e受孕而成的有机体。
这里的三个专名“西塞罗”、“精子s”和“卵子e”皆为固定标示词,句子本身也是一个有关同一性的陈述。这两点均与(1)相似,也许有人因此觉得(3)也属于后验必然命题。但是作为谓词的描述语“那个由精子s和卵子e受孕而成的有机体”却不一定是固定标示词①例如,我们可以论证说,任何受孕过程都会受到某些(体内)环境或时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显然是外在于精子、卵子等组成因素的。因此不难想象,在可能世界Wi(设想为实际世界,或描述谓词据以确定其所指的世界)中最终由s和e受孕而成的有机体不一定是数值上等同(numerical identity)于另一个世界Wi中的也来自s和e的对应者,哪怕两者在性质上或本质上非常相似。当然,人们永远可以选择将句子(3)中的描述语相对于现实世界Wo予以固定化,从而人为地令(3)变成必然命题。比如,用索姆斯(Soames)的术语来说就是,有些谓词只是“部分的描述性名称”。参见S. Soames, Beyond Rigid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五章。如需了解与此话题相关的本质主义式的固定化解读,可参见J. LaPorte,“Rigid designators”, in The Stanford Encycolpedia of Philosophy, ed., by E. N. Ialta. URL=http://plato.stanford edu/archives/sum 2011/entries/rigid-designators/, 2011。,任何非固定标示性的解读都将令(3)成为一个偶然为真的命题。比如,可视(3)为关于世界Wi或Wo内的一个与现实的西塞罗在相关属性上相似的个体的一种特定因果史构成的陈述;虽然这种陈述也许揭示了该个体的某种本质属性,但仍不足以改变其偶然真理的模态地位。①作为一个生物学术语,同卵双(多)胞胎虽然有着相同的遗传本质,但却属于可纳入描述语“那个由精子s和卵子e受孕而成的有机体”的独立而分离的个体。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3)中的西塞罗,在对其描述谓词作非固定标示性的解读下,乃是某跨世界的同卵双(多)胞胎之一。
接着让我们继续将(3)与以下句子作比较:
(3’)如果西塞罗存在,那么他来自精子s和卵子e。
(3’)的条件句形式有助于避免那类将(3)解读为偶然性命题的情况,从而令(3’)成为必然性命题。(3’)的后验必然性在于它抓住了西塞罗的生物遗传上的同一性与西塞罗于其中存在的可能/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结关系。比起句子(1)来,(3’)包含更多信息量──它陈述了超出自身同一性以外的因果构成性。但(3’)的局限在于它只陈述了一次性的因果构成。
最后我要引入以资比较的条件句是:
(4)如果任何赢家状态(或新地位)达成,那么就存在着一条不间断的历时链条,该链条的起点是某种非赢家状态(或无地位),终点则是该状态(或地位)。
我准备把条件句(4)当作我的弱意义上的回顾式必然性的标准表述。简言之,这种必然性可以客观地赋予或归属于任何符合一定结构要求的游戏中的任何赢家(或因玩此游戏而获得的地位)。篇幅所限,我姑且绕过可能涉及人为游戏与自然游戏在其各自设计上的异同的问题。②自然选择所对应的自然游戏虽谈不上有设计者,但却不代表不能从所谓“设计姿态”入手进行研究。设计姿态是相对于意向性姿态而言的另一种方法论姿态,人们可采取它来解释与功能种类相关的现象。密立根(Millikan)对这两种方法论姿态之间的逻辑关系(优先顺序)的观点与丹尼特有相当的出入。参见 R. Millikan,“Reading Mother Nature’s Mind”, in Dennett’s Philosophy, eds., by D.Ross, A. Brook and D. Thomps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就本文的中心脉络而言,此处最相关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句子(4)的模态或其他特征与(1)或(3)/(3’)的相应特征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作为对此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我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首先,在某种宽泛的历史(包括因果规律决定的部分和含随机偶然性的形成过程)意义上,一条特定的历史路径对于可归属于句子(3’)和(4)的回顾式必然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其中所涉过程是一次性的还是重复性的和累积性的。事实上,值得指出的是,(3’)和(3)所共含的来自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偶然受孕过程不过是一个更加漫长的生命过程的一小部分,在这更长过程的稍后阶段西塞罗(或其可能世界中的“孪生兄弟”)能在回顾时发现这条通向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不间断的形成链条。由此不难看出,与(3’)/(3)中受精卵形成过程相关的内在历史偶然性,在一种宏观自然史的尺度上,完全是同作为自然进化基础的机制过程一脉相承的──正是后者产生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物种。与此相反,句子(1)所包含的后验性却与这样一种本质创生的形成过程没有直接关系;它充其量可说是对这些早已存在的本质同一性的经验发现所需的知性过程。换言之,回顾式必然性不仅与像(3)这样的偶然本质性真理或像(3’)这样的后验必然性兼容,而且在其更有趣的自然游戏版本中还深深地植根于上述动态偶然性的累积效应。
其次,回顾式必然性观念,概括地说,要比仅仅基于自身同一性的必然性观念更能揭示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与进化论逻辑相关的某种根本性事实。它可以说在如下双重意义上具备理论意义:一方面,一个世界中的任何实在层面上的任何动态过程,相对于任何由其中可能涌现的稳定属性(比如对应于新物种的本质属性)而言,均包含着或适用于这种反向归属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反向关系,它其实可随附于(supervene on)不同的正向实现关系。它对所有自然物种的普遍适用性(甚至涵盖前生物的自然演化种类),以及对形形色色人为游戏中赢家地位的普适性,不但不减损反而更印证了它的特殊意义。进一步说,它也无法还原为任何自然规律中显现的因果必然性。理由之一:其向后回顾样式或向后归属性本身无法还原为相对应的正向展开关系之相反样式;理由之二:即使没有我们现实世界Wo中发现的(一部分)物理规律,回顾式必然性照样会成立。只要有最宽泛意义上的时间或历时连续性,以及涌现新事物的机会,哪怕在那些具备一整套不同的物理规律的可能世界Wi中回顾式必然性也仍然适用。
第三,相较于句子(1)所例示的后验必然性,回顾式必然性还具有以下三种重要特征,我这里仅粗略勾勒之。其一,上述特定历史路径能被个别化的参照点是已出现的实体或属性/地位,该实体或相应地位之实现本质上禀具着一种组合性结构,其组成部分可以是共时的或历时的;①例如,一个人为的多环节彩票游戏的赢家就有着一连串历时组成部分,它们就是该赢家以好运成功通过的每一步淘汰关卡。每一组成部分本身的(被)选择或形成构成着上述路径链条的一个必要环节。其二,任何对该实体或地位的物理实现均只能是一个历时过程,该过程能在机制上解释该实体/地位如何循序渐进地产生。历时步骤的复数性和累积性对任何赢家话语来说都是关键的,而任何可能世界Wi中新涌现的具有组合结构的实体/地位,逻辑上蕴含着这种步骤的复数性和累积性。所谓回顾式必然性之普遍性不妨看作是对这一广义进化逻辑之普遍性的表达②关于超出具体选择机制或层面的最抽象意义上的自然选择的讨论,参见S. D Kasha, Evolution and the Levels of Selection, pp.10-39。—一种(知性上别无选择的)以结果为出发点的表达。其三,如果所谈论的实体/地位是一个功能性种类的话,其组成部分会进一步包含某些特定类型的历史因素,比如祖先—后代相似性或遗传性。这些因素对试图解释功能种类起源的某些较成熟理论(比如,成因论[etiology])来说是必须被预设的。③关于成因论的代表性表述,可参见L. Wright,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An Etiological Analysis of Goals and Func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81;K.Neander,“Functions as Selected Effects”, Philosoply of Science 58, 1991, p.174。可见,回顾式必然性不仅预设着某种最低度的、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之实在性,而且倾向于包含着某种更强有力的或进化意义上的历史之重要性。
最后,给定回顾式必然性与后验必然性之间的异和同,究竟如何将两者分类,是一个隶属于另一个,还是两者同属某种更广的模态,似乎暂不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对本文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将回顾式必然性作为讨论历时实体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这一点,是否具备足够的理论动机和适宜的合法性证明。本文给出的明确回答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 Dawkins, R., The Sel fi 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Dennett, D. C.,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3. Kment, B., “Varieties of Modality”,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 by E. N. Zalta,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2/entries/modality-varieties/, 2012.
4. 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5. LaPorte, J., “Rigid Designator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 by E. N. Zalta,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1/entries/rigid-designators/, 2011.
6. Millikan, R., “Reading Mother Nature’s Mind”, in Dennett's Philosophy, eds.,by D. Ross, A. Brook and D. Thomps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7. Neander, K., “Functions as Selected Effec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58:168 - 184, 1991.
8. Okasha, S., Evolution and the Levels of Sel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Schwartz, S., “Kinds, General Terms, and Rigidity: A Reply to LaPorte”,Philosophical Studies 109: 265 - 277, 2002.
10. Soames, S., Beyond Rigid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 Wright, L.,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 An Etiological Analysis of Goals and Func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规范性、动态理性、行动哲学、意向性或内容的自然化等问题之间的交叉领域。在中英哲学期刊和文集发表过三十多篇论文,亦曾任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书评编辑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