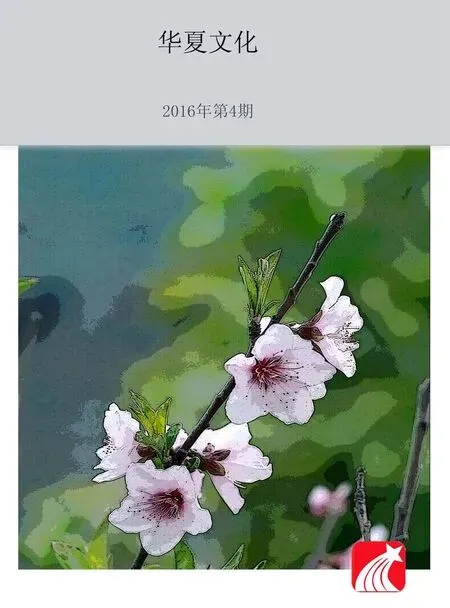谥法起源于殷考
□ 贺汪泽
·语言文化·
谥法起源于殷考
□ 贺汪泽
《说文》另有“谥” 字,“笑貌。从言,益声。”甲骨文有“益” 字:,象器皿里装满了水,往外溢之形,为“溢” 之本字。徐铉据《唐韻》注有两个读音:一为伊昔切,一为呼狄切。呼狄切正是“”的读音。现在“”也可以写作“谥”。 这是否是“谥” 之字义一分为二而造出的新字呢?如是,则“”为“谥”之讹变,读“兮” 也是将错就错了。而字义还是从“谥”引申出来的,即给逝去的君王加一个溢美的称号,作为庙号书写于木主,刊嵌在祖庙的神龛上,以后人们记得的就是这个庙号,而本名反而渐渐被遗忘了。
由于后人认为“桀”、“ 纣”也是谥号,有贬义,如蔡邕《独断》释桀为“残人多垒”, 纣为“残人损善”,遂认为“谥”不一定都是“溢美”,也有“溢恶”的。最显著的例子,一是楚共王,本名审,执政长达三十一年,临终时反省自己一生行事,认为晋楚鄢陵之战败给晋国,是自己最大的过失,害怕死后被追责,自请“为‘灵’(乱而不损)若‘厉’(戮杀不辜)”,这都是很负面的谥号,实际上是把丑话说在前头,堵住群臣的嘴巴,哀求不要加以恶谥。最终,议定其谥为“共”,同“恭”,即“既过能改”之义。知错改错,褒中有贬,当然算不得溢美之词。
另一个例子是秦桧,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奸相,死时仍权倾朝野,赠申王,谥忠献,荣耀非凡。数年之后,桧党失势,追夺其封号王爵,改谥为谬丑,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恶谥了。还有武则天,先称“则天大圣皇帝”, 旋改“大圣则天皇后”, 终定“则天顺圣皇后”。 前后三改,谥的美誉度就一落千丈了。
历史上,不只君王有谥,王后也有谥,大臣也有谥。即使不做官,挤进了社会名流,门生故旧也会给其拟一个谥,这样的私谥也不绝如缕。不过,无论谥出现过怎样的变化,君王之谥还是主流,是最富政治考量的,是标志一代风气的风向标。
谥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蔡邕说,黃、尧、舜都是谥号,“靖民则法曰‘黃’,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且不说这些字本身并不具备以上界定的字义,检甲骨文,有夔为,夏为,却不见殷人传说中的始祖契的踪影,更別说三皇五帝了。这说明黃帝、尧、舜、四岳、四凶都是殷代以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历史,尽管有的传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但从新史学观点看,他们都是传说中的氏族部落长老,误会成了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这些名号即使带有溢美的性质,也是悬隔数千年之后拟定的,与盖棺论定的“谥”不发生关系。
郑樵在《通志·谥略》中提出另一见解:“以讳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有讳则有谥,无讳则谥不立。”文、武、成、康,代代相续,这是帝王之谥。古籍记载与青铜铭文可互相印证,当然是可信的。《礼记·曲礼》也说:“死谥,周道也。”不过,周立国之初,文明程度远逊于殷,文武之谥法传承于殷,是不待言说的事实。现在,我们完全有可能揭示殷代谥法演变的过程。
祖先崇拜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就存在了。在殷人传说中,商汤立国前有十四公,前七公是自然神,举行郊野祭;从上甲微开始,报乙、报丙、报丁四公开始立庙祭祀,上甲()居中置顶, 报乙()报丙()报丁()退居第二层, 占的地位小, 所以用半框()标示,由于后代不知如此排列的用意, 遂将次序都搞错了, 甲骨文出土,得以纠正。主壬()主癸()距报丁中间缺四位,现在已无法推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象灯中火主,这也是后人的误识,实为“示”, 表示供奉牌位()上书“壬”、“ 癸” 两位先祖的名号。这六位先公名号都是以天干命名的,实际上就是排列次序,转换成某公名号,即庙号。这种庙号无褒贬含义,不具备谥的特征。
汤是商代开国之君,庙号为大乙,或称天乙。甲骨文称其为“唐”, 也有称“商” 的。 因上有唐尧,中有商契,史家遂改其为“汤”, 或称“成汤”。“ 天”、“ 成” 之称虽有褒义,不见于卜辞,也不能视为谥号。
殷代立庙似有两式:一式是大乙上承六公,一式是大乙只上承上甲,甲乙连称,一为始祖,一为开国之君,所以称大乙。此后三十王,一律都有天干名号,有的兄终弟及,有的父子相继。以弟继位,兄弟间有排名;以子继位,又有嫡庶之分,出生先后之别,死后都要入庙,其配偶牌位也要随侍在侧,都以天干名号。査《史记·殷本纪》,各位殷王都有一个固定名号,而在卜辞中,称祖某、兄某、小某、大某,实际上所指并不是那么固定,要确定某名指某王,还要考虑上下王的辈份关系综合考定。这种复杂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所有庙号都以天干排名的缘故。周代以后没有这个问题,每一王都有谥号,同一朝代谥号是不会重复的。不过,也有麻烦,能谥之字并不是很多,不同朝代中有重复,冠上朝代名才能够区分;像春秋战国,诸国林立,各国之君谥号多有重复,《左传》又是以纪事本末体成文,各国历史交错叙述,有时只有按图索骥才能弄清楚。
殷代哪些王公有谥号呢?先公中王亥(振)被称为“高祖”、“ 高祖亥”, 因为亥在自然神中扮演生育神的角色,他是人类的祖先,和山神、河神一同祭祀。此“高”,虽不是谥,但已启动了谥的意识。上甲也有称高祖的,其义与王亥同。“天乙”之名不见于甲骨文,证明谥还不及开国之君。甲骨文多次提到“中宗” 的名号,如:
彝在中丁宗。(《甲骨文合集》十二册38223片)
自中宗、祖乙,王受有祐?(同上,九册26991片)
《史记·殷本纪》认为中宗指太戊,太戊任用伊陟为相,伊陟又推荐巫咸治事,“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甲骨文为,象旗帜插于稳定物之中,上下飘扬之形,《说文》:“上下通。”中,乃中兴;或曰中和。如“彝在中丁宗”,只表示盛满祭品陈列于中丁牌位之前,还不算溢美之辞,另两处“中宗”已是确切的名号了,有谥的意义自不待言。“中宗”为谁?如为太戊,前著一“自”字,表示从太戊开始,至祖丁(中丁)、祖甲(河亶甲)、祖乙各位先祖,言之成理,则可以判定太戊已有谥号。《史记》记载与此一致。
太戊之后,殷代王室为立子立弟之事长期震荡,至盘庚迁殷,殷道复兴。中经小辛、小乙,至武丁得傅说、祖己辅佐,“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本纪》), 成就了殷代的鼎盛期。为表彰他的勋绩,甲骨文有大量的记载,称其为“文武丁”(《 甲骨文合集》十二册36534片)、“文武帝”( 同上,36168片),史书也在庙号前贯以“武” 字,称武丁,称高宗,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谥了。
附带提一笔,妣己被称为妇鼠,即鼠神,也许当时表达的是如鼠繁殖旺盛,并非恶谥。特别是妣己既为小乙妇,又为武丁妇,幸于父子二人,一定生育过很多子女,而成为求子的对象,自然是美谥;后世因鼠食谷享祭祀而遭挞伐,属恶谥之列,则是时移世易,社会观念变化造成的。陽甲之“陽”, 为“逷”之误读,陽甲即狄甲,史书记载为阳甲,实为有意为之,也可视为后人改谥之先河吧。
行文至此,加以总结:谥号发轫于对殷代强盛做出特殊贡献的太戊的表彰,确立于鼎盛时期的武丁。廪辛、康丁之谥反映殷代对粮食问题的关注,谷物增多了,死后就能得到溢美之辞。恶谥如纣、如鼠,此时也已开其端。
末了,再涉及另一种意见,有学者指出:“古时候并无谥法,凡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都是生号而非死谥。”“谥法大抵是在战国中叶才规定的,此事初由王国维揭发,继由我(郭沫若自指——引者注)加以补充,业已成为定论。”(《青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生前文王名昌、武王名发、成王名诵、康王名钊、昭王名瑕、穆王名满、恭王名繄扈、懿王名囏,皆姬姓,其登上王位之后,不再呼其名,仅以“王”称之,死后成了先祖,要在祖庙中立牌位,由此学习殷代后期的做法,议定一个溢美旳名号,这就是谥。至于赏赐臣下的彝器上也能见到这些名号,诗书中也偶尔一见,但存在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如《献侯鼎》铭文:“唯成王大求,在宗周,王赏献侯嚣貝,用作丁侯宗彝。”其意为:向成王祈求,在宗周神庙里,由王赏赐献侯嚣钱币,用作为丁侯铸器的开支。此卜如为吉,就是先祖成王批准了,献侯铸成器,将此卜文刊刻上去,以之炫耀,作永久纪念。因周代侯是世袭的,丁侯应是献侯之父,因其有功于王室,故能赐币铸器表彰,而手续是请示先王批准,故涉及成王,非成王亲授,意思是明白的。
又如《诗经·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是说后王在举行藉田仪式时,吁请成王,并非成王亲自主持大典。吴闿生《诗义会通》已说得很淸楚:“当是祭成王庙而告戒助祭诸侯,勉以农事之词。”郭沫若继承的是宋代欧阳修、朱熹的观点,将成王当成这场藉田典礼的事主,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牵涉到整首诗的解读,还有很多的话要说,超出讨论谥的起源的范围,有机会再作商讨吧。
(作者:江西省南昌市靑山湖区南京东路丰源天域五栋二单元302信箱,邮编330000)